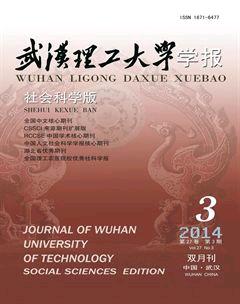传媒全球化语境下的媒介话语批判
张 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外国问题研究所,北京100101)
福柯说:“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1]在全球媒介化的语境下,媒介话语的巨大影响力正在印证着福柯的这个观点。在媒介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一个毋庸置疑且不可无视的重大事实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媒介话语紧紧包围,一切均在媒介话语中。无可否认,在很大程度上,媒介话语提供的形象和事实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受众对外界的信息源几乎为媒介所垄断,“我们主要通过新闻媒体来了解和理解外在的客观世界,从而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一个关于这个外在世界的想象图景”[2]。现代人类习惯于依靠媒介话语的传播来了解世界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并根据我们从媒介传播那里得到的情况进行行动和反应。
由于现实世界是散乱、无序与片面的,面对世界这样宏大复杂、瞬息万变的客体对象,人们不可能做到完全把握和不偏不倚地认知,也没有条件和可能去应对如此复杂并变化的各种综合体,因此人们需要一个简单的模式来重构环境,需要给事物制造秩序,以便掌握它。媒介话语用有序的方式梳理和解释世界、展现世界并赋予它们恰当的意义,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有秩序的意义世界中,满足了人们认知纷乱无序的外部世界的心理需要,从而媒介话语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表意体系。在现代社会中,媒介话语是语言与科技的紧密结合,当语言乘上媒介科技的翅膀,便具有了语言未曾有过的特性,也将语言的巨大影响力和塑造力充分地展现出来。
一、媒介话语的“去本真”倾向
语言是传播的本质,媒介话语是媒介传播的语言表意形式。所谓语言的“本真性”,通俗地讲,就是语言表意本身所具有的真实性和自然性。希腊语“logos”的本真含义是“言谈”、“言辞”,认为事物正是通过“言谈”、“言辞”得以自然现身,并且能够通过语言这个媒介传播和扩散,最终使我们的表达在他人那里得到完成和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的媒介性并没有破坏语言的本真性。当媒介话语突出了语言传播的工具性,语言的本真性便受到了损坏,因为语言的本真性存在于语言的工具性之外。也就是说,本真的语言是原初的语言、天然的语言,是一种神性的、自然的语言的自我创造与自我表达,从中可以见证出世界经验的本真性与鲜活性。
媒介话语的言说作为对世界的既有理解与目的性解释,从一开始就具有“去本真”的特点,它是一种依据目的和需要建构的话语,是一种在有限理解的视界中提供的一种主观阐释。媒介话语的“言说”不是一种事物的本真在语言层面上的自然呈现和自我表达,而是突出语言的实用性与工具性去有所目的地对事物进行表述,以达到传播与告知的目的。媒介话语以功能性作用为目的的特性决定了它的表述受到了各种规约。媒介话语作为语言的表意,它必然要符合语言文法的规律,同时它也有自身的一套话语规则,媒介话语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由一定的具有逻辑性的语言单位组成,每一层语言单位内部又都由意向连贯的意义单位构成,最终通过具体的词语、句子、语段的组织与表述使得意义得以实现,形成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意义整体。由于媒介话语最终是以传播为目的,有鲜明的效果目的性,因此在媒介话语内容的生产组织上,它将在综合考量传播意图、意义构建和受众的反应等方面之后,在特定的语境下,根据自己要表达的特定意思或要实现的特定意图,选择与其相适应的语词、短语、句式、段落组织、结构方式,或者图像、视频等科技手段,有层次地构建出来一个意义整体,从而形成为一个事物或者事件赋予一个确定意义的话语文本。媒介话语的这种构建方式,具有选择性和意向性,在话语构建的方法和技巧以及语段的衔接连贯手段等细节上,也辅助话语文本形成其预期意义的传播,具有鲜明的“去本真”属性,与事物本真的言说在自然中呈现的本质恰恰相反,媒介话语将语言揉捏组合成适应主观想象与构建需要的各种表意形式,失却了本真性,更多地沦为了一种言说者的工具。因此,从媒介话语“去本真”这一属性来讲,媒介话语对所谓真实的揭示总是可以有很多种可能,这是由它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此外,媒介话语在形成表述的过程中被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和塑造。尤其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下,媒介话语的市场价值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意义含量”与“意义偏向”,必须以市场的导向与受众的趣味进行生产,才能实现广泛传播并获得市场利益。对于媒介话语生产者而言,他们负有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升值的责任,因此对于市场需要的揣摩高于对话语“本真性”的追求,这就导致了媒介话语体系被市场商业的功利意识侵蚀,从而使得“本真性”在媒介话语体系中难以成立。
二、媒介技术对媒介话语的深度介入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揭示了媒介是当今世界的基础性技术,从技术性的角度概括了媒介技术与媒介话语之间的密切难分的关系——媒介话语的传播首先决定于传播媒介的性质,而不是传播的内容。波兹曼认为,每种技术都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技术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3]这一论断,揭示出媒介技术性是媒介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麦克卢汉的观点认为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感知模式,不仅是传递的形式,也是传递的内容。不同形式的媒介对相同的内容进行表达,会发生很大的效果差异,同时,传播媒介也决定媒介话语内容的组织结构形式。一定程度上讲,当今世界是通过传播媒介呈现在我们眼前,而我们是透过传播媒介来认知世界的。媒介技术本身也是一种意义的意义。
媒介话语是依托发达的媒介传播技术得以传播的话语体系,话语作为一种意识中的现实被生产出来,媒介技术模拟现实甚至创造现实,无论是在速度、广度还是深度上,它的传播与渗透都悄然参与了世界与社会关系的形塑。媒介技术不仅划定了传播对象的内容、范围和性质,而且它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隐蔽地渗透进受众的意识中。媒介传播的各种技术形式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日常经验的生活内容,影响着人们的感知方式,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重新确定媒介话语的象征效果。
爱德华·霍尔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一切技术性行为都既包含了显形意识的成分,又包含了隐形意识的成分,其特征是完全有意识的行为。一切技术性行为明白显豁,能被记录下来并实现远距离传授,这又使之与其他两种类型的整合判然有别。一切技术性行为的本质是,它处在最高的意识层次上。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处在最高的技术意识层次上。”[4]技术并非是中性的,它负载着价值,尤其当媒介技术成为人类文明文化传播的载体,它具有着政治、文化、伦理、人性等多重丰富的含义,它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技术上的判断、一种社会价值观。媒介话语不是一个纯粹中性的、客观的、全面的呈现,它有所倾向,经由选择、传播、接受,与价值观、世界观乃至可得利益紧密结合,最终体现在媒介技术的呈现与传播上,并经由技术手段扩大影响。面对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浩淼纷繁的信息与内容,如果不假以媒介技术的传播,相对来讲,这些信息内容便是“不存在”的。而意义和观念只有能通过媒介技术的广泛传播才能最终被纳入世界意义文化体系,因为没有媒介传播,人们对其便无法得知、无从了解,从而不可能将它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关于技术对媒介话语的重要性,尼尔·波兹曼强调新闻为“纯属技术性的想像之物”,是一种“媒体行为”,媒介技术对话语的组合与象征方式规范着和决定着话语的内容意义。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技术为社会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环境,媒介话语具有的技术属性使得它从传播形式到传播内容都会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
按照信息沟理论的观点,新传播技术带来的利益并不是对所有社会成员均等的,能够获得更多信息的人,是那些原本信息水准较高或信息能力较强的人。在社会上占有优势地位的人如富裕阶层等,因为可以更早更多地接近和采用传播新科技,因此他们拥有更多现实中的信息优势和话语表达优势。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传播科技发达的国家在媒介话语生产知识的过程中,通过先进的信息数字化技术可以迅速占领尽可能广的全球市场。
强调媒介话语的技术属性是因为之前没有哪一个历史时期如当今信息时代这样,可以依托高科技媒介技术,迅速传递信息和意义,使得媒介话语在瞬间遍布每一个角落。媒介话语的这种技术上的强势“攻占”,使得受众反馈和反应的余地愈加逼仄,甚至某些时候导致单向度的“魔弹”效应。当人们几近成为媒介话语的被动接收端之时,认识到媒介话语的技术性特征,是对媒介话语本身保持有清醒反思的前提。
三、媒介话语生产对传播速度的追求
速度意味着对时间与空间的征服,是人类的本能追求之一。对于媒介话语传播来说,传播的速度决定了占领与左右人们思维的地位,在消费语境下还意味着对市场的占有。
媒介话语的快速生产,为人们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闻快讯、时评报道、影视文化等各种形式的文化内容。通过媒介话语的传播,人们能够更广泛地更迅速地感知事物,但并不一定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事物。浩如烟海的巨量信息使得人们进入文化快餐时代,人们的接受与反应只能辅佐以技术而不是深刻的思考,这个过程中缺少了思想和交流。媒介话语强调即时性,提供了片断式的、不连续的叙述方式,因此不能够阐释潜在的、隐含的渐进发展过程,而往往这个缓慢的过程以及其中的细节才是理解事件的关键。传媒大亨默多克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围绕新闻组织的媒体系统可能有丰富的信息,无数的发生的事件提供成批的数据,但在认识和理解上却相对贫乏。它不提供背景材料和阐释性框架来让人们产生联想、看到‘广阔的画卷’,理解什么力量形成了现在的情势或能如何改变它们”[5]。布尔迪厄在研究电视时就指出,电视不利于思考与思想,因为时效性要求它的思维要紧急而快速,因此更适合于电视传播的是“固有的思想”,这种“固有的思想”是指“所有人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约定的和共同的思想,但同时也指一些在你接受时实际上早已被认可的思想,所以并没有一个接受的问题”[6],因此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流,交流只是一瞬间的,或者说交流也只是表现在表面上。媒介话语传播者之间的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抢夺时效性的速度竞争,因此采用先进的媒介技术形式也成为传播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速度被神化了的时代——人们已经发展到更多的是用速度而不是来龙去脉去描述事物的地步。”[7]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似乎不是为了寻找世界的真相,而是为了展示世界变化如此迅速。对于受众而言,他们甚至可以理解因为追求时效性而缺乏深度甚至真实性的新闻。
媒介话语生产传播过程中对速度的追求,使得思想、意义、内涵这些不适合技术速度特性的内容遭到一定程度的剥离和抛弃,其生产传播速度与意义思想深度之间一直存在如何平衡的问题,如果过分强调速度,就会欠缺深度,事实上,“速度,尤其是知识和信息沟通的速度已经制造了一个令人迷乱的、肤浅的图像世界”[8]193,维利里奥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技术短暂性的系统里,在这种系统里,作为评判标准的持久性和物质支持已经被个体的瞬间视觉和听觉所取代。”[8]194当追求速度变形为痴迷于技术速度时,媒介话语中因为“紧急性”、“快速性”的思维而带来的大量“固有思想”持续地冲击和占有人们的大脑,人们在应接不暇的接受过程中丧失了反思的机会与空间,进而导致了现代人类“理解性的危机”。媒介话语传播的初衷,是为人们更好地认知和理解外面的世界,而媒介话语的生产传播对速度的过分追求难免对此有所背离。
四、媒介话语天生的权威特质
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情况下,人们对媒介话语传播的内容倾向于无意识地接受,并信以为实。自从人类传播伊始,人们对负载着意义与信息的媒介符号便有着崇拜的情结。先民们将文字的出现归功于神的创造而加以顶礼膜拜,世界文化记载中都有类似的经验,诸如:古埃及将其归功于智慧女神,古希腊将其归功于神的使者赫尔墨斯,古中国则将其归功于四目神人仓颉,等等。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每一次新媒介的问世也都给世人带来了震惊,而最初印刷术的应用也很多是与宗教的传播相关,例如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佛教典籍《金刚传》,西方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约翰·古登堡印刷的第一部书是宣传基督教的《圣经》等[9]。从语言文字的媒介传播发展史来看,由于语言文字的媒介传播有巨大的影响力,人们一直对语言文字的媒介传播有一种崇拜心理,被认为是圣创神助的结果。这种对符号媒介的信奉与崇拜情结,深深地沉积在人类的意识深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媒介话语表征世界的这个时代,人们最直接的真实反映和固定思维习惯往往是如果众所公认的权威媒体已经报道过的,它的真实性就不用怀疑,经过媒介话语的传播,事件的意义似乎就得到了固定的定义。在人们没有足够的视野和能力理性地认识和审视自身和世界时,人们往往依恋某种外在的东西作为精神资源或“最高指示”,在这种追随信奉中,人们的主体性逐渐被腐蚀或者被削弱甚至是消失,比如古时的人常常将帝王看作真理和法律的化身,将他们的话视为金科玉律。虽然在当今世界由于科技知识教育的推广,传播媒介的神秘性已然消失,由于不可控性与不可知性所带来的距离感与超常感已经不见,尤其是如今已经发展到“自媒体”时代,媒介已被“祛魅”,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颇为熟悉的传播交流的技术手段,但是媒介话语容易受到“崇拜”的特质,并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究其原因,是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媒介话语依赖于新技术环境下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起了其表意的权威性地位,消息源的稀少性和有限敞开性使得拥有话语资源的媒介机构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优势地位,从而使得人们依赖它、迷信它甚而崇拜它。
我们还要注意到,媒介话语陈述具有的权威性,对于人们而言,拥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可靠性和认证性,媒介话语“经常表示出一种修辞的力量、神赐的魅力、说服力的逻辑、爱与恨的萌发、催眠术的幻觉效应等等”[10],冲撞着人们的心灵,鼓动着群体的力量,引导着人们的激情并使之爆发出能量。因此,媒介话语的生产传播不只是完成传播信息和反映现实,有时候它还有强大的支配力去影响事件或者改变事件,这种支配力产生于受众的主体性被媒介话语传播压抑甚而退隐,最终为媒介话语所引领与主导。在这个过程中,媒介话语对世界的优势定义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从各方面继续形塑我们栖居的世界,并使得人们对媒介话语形成强烈的依赖和信奉心理。
如果按照实用主义真理观去理解真理:一是把真理理解为与客观实在相符合,另一种是把真理理解为人们对于对象的信念,即“把真理定义为命题与事实的符合改为信念与事实的符合”[11],只要假设有人相信,这个信念就为真,那么,我们可以说人们把媒介话语看作了权威阐释,并将此当作一个信念,从而去相信媒介话语所提供的“真理”。而事实上,这些“真理”有些是与客观实在相符合,有些则与客观实在不相符合。因此,面对媒介话语传播,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判断力和审慎的态度,而不只是成为媒介话语的被动接收者。
五、结 语
“每一种语言形式都产生各自的环境,每一种语言形式都产生一幅地图。”[12]现代世界的显著特征便是媒介话语环境性,人们的实践与认知与媒介话语有着密切关系,媒介话语本身便是认知的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媒介话语传播讯息、解释世界,使得人们对现实世界有了更为广阔更为多面的了解,但是另一方面,媒介话语被生产出来之后便获得了独立性,它在表征和解释世界时,切断了人和世界的直接接触,它以语言的表意取代世界本身,迫使人们通过它来认知和了解世界。并且,媒介话语凭借强大的媒介技术力量得以迅速深广地传播,它不再只是传递信息,而且对现实有着强大的建构力和表述力,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促进了社会和文明的进程,甚至深刻地塑造着世界秩序与世界结构。
因此,我们必须警醒地认识到,在一定意义上讲,客观世界和意义世界都只是这个媒介话语结构系统的再现,现代人类认为自己所认知和把握的客观世界或意义世界,某种程度上是由媒介话语构成的那个世界的对应物,所谓的“事实”和“意义”因为媒介话语所具有的语言性质和语言结构自身逻辑的作用,变成了不稳定的能指符号的滑动而构建出来的媒介话语表述的“事实”和“意义”。在这里,观点与事实的解说一直为“社会管理者”所操纵,媒介话语对外界的简化、有序化的选择和组合,必然遮蔽了某些现实、虚化了某些现实,但是却在人们心中获得了与客观现实等同的地位,人们通过它来感知和认识外面更大的世界和环境,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体系。媒介话语在态度、认知、理解、价值观和行为等各个层面对人们有着重大的影响,成为一种实践力而介入现实生活。正如德国传播学者舒尔茨指出的,社会真实的“正身”无法验明,人们感知到的所谓真实是一种“片面的”真实,是通过媒介话语建构的结果,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无从断然区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察媒介话语遵循哪些规则建构“真实”与“意义”便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保持独立的判断力与清醒的思考力,在媒介话语密集丛生的时代传递理智的声音。
[1]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2]Walter Lippmann.Public Opinion[M].New York:Macmillan,1922:29.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 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4.
[4]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8.
[5]格雷厄姆·默多克.以媒体为中介的现代性:传媒与当代生活[J].庞 璃,译.学术月刊,2006(3):32-33.
[6]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 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8-30.
[7]R.舍普.技术帝国[M].刘 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4.
[8]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9]樊 葵.媒介崇拜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1.
[10]陈卫星.关于传播的断面思维[M]∥王岳川.媒介哲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25.
[11]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239.
[12]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