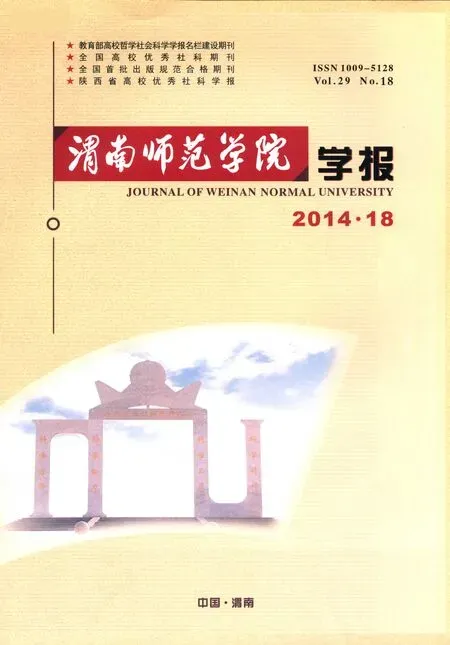再说《白鹿原》
——与陕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西北大学文学博士刘睿对话
陈忠实,刘 睿
(1.陕西省作家协会,西安 710001;2.西北大学人文学院,西安 710127)
【秦地文化研究】
再说《白鹿原》
——与陕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西北大学文学博士刘睿对话
陈忠实1,刘 睿2
(1.陕西省作家协会,西安 710001;2.西北大学人文学院,西安 710127)
刘睿(以下简称刘):任何一部作品的诞生离不开文学的传统,这部小说数十万字,波澜壮阔,在创作中,对前人著作,借鉴最多的是哪些?
陈忠实(以下简称陈):这在我是很难作出判断的事。我喜欢文学的诱因,是在初中二年级语文课上学到的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这应该是我平生读到的第一篇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不仅喜欢,而且惊讶,这样的乡村人和事都能写进小说,还选入中学生文学课本,我耳闻目睹的乡村人和事也不少,于是就在自选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这个时期我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赵树理的作品都借来读了,赵树理无疑是我崇拜的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也很自然地模仿他给小说人物取绰号的做法。
我随之又崇拜起柳青来,这是在读初三最后一学期时适逢《创业史》在《延河》上连载,一读便入迷为之倾倒。之后十余年间,先后购买过九部《创业史》,甚至在文革中《创业史》书遭禁的不堪时月,我给《创业史》包装上《毛泽东选集》的红色塑料封皮,偷偷阅读。我最初发表的几篇小说,被很多读者误认为是柳青另附笔名的作品,主要是说作品有柳青味儿。
新时期伊始,我集中阅读了契诃夫和莫泊桑两位短篇小说顶级大家的小说,不仅要尽快排剔极左文艺的影响,更要学习他们短篇小说的创作艺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读了多位苏联作家的小说,诸如杰出的短篇小说家舒克申和长篇小说家柯切托夫等翻译成中文的所有作品。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创人和杰出的代表作家卡彭铁尔和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王国》《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都读过……这些中外作家的作品都对我学习文艺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不同年龄段对不同作家的作品的阅读,对那个时代的创作探索都发生过启迪,要说一个“最”的人,一时尚不好排出。
刘:从创作的角度谈,创作《白鹿原》时最原始的动机是什么?是《蓝袍先生》创作时的一点触动,还是有自觉的意识去写“一个民族的秘史”,还是有一个别样的创作出发点?有没有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反思促使您进行创作,有没有在八九十年代社会文化思潮的碰撞中,在复杂内心的矛盾中,促使您反观传统文化的因素在?
陈:你的所有问句,我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唯一稍作调整的一句话是,《白鹿原》的创作是由《蓝袍先生》写作过程中触发的,随之就发展为你所说的“自觉的意识去写‘一个民族的历史’”。
刘:陕西小说界有个认识,就是创作水平的高低取决你有没有成功的长篇小说,您如何评价这种认识?这是不是您《白鹿原》创作的一个动力?
陈:这种以长篇小说评判作家创作水平的看法,大约不单在陕西文学界存在,而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观念。这种看法显然是偏颇的。前述的契诃夫和莫泊桑、苏联时代的安东诺夫和舒克申,都是享誉世界文坛的经久不没的文学大家,他们一生专注于短篇小说。再如鲁迅先生,他的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学的经典。在我来说,无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致命的问题在于作品本身。
我可以坦白地说,《白鹿原》的创作动力不在于此。1985年夏天,陕西作协在陕北召开“长篇小说促进会”时,我表态尚无长篇小说创作的打算,这是实情。不料就在当年初冬,因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创作而触发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欲望,几经筹备,直到动手写作,也没有想到“创作水平高低”的事,而是为自己做一个“死时垫棺材枕”的东西,告慰自己一生的文学梦。这种“枕头”之说,完全是面向自我的。
刘:《白鹿原》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史诗般的构建;醇厚的关中乡土气息;人物形象的生动;魔幻手法;隐含的社会政治反思。这些是否是创作时有意识要传达给读者的,还是水到渠成?另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想传达给读者?
陈:谢谢你对《白鹿原》书的评说。关于“史诗”,尽管有多位评论家说过,我仍然心虚,常识告诉我,时间是无情却又公正的考官,未来的读者是否还会对《白鹿原》发生阅读兴趣,自不敢断言。《白鹿原》书里所包含的思想,自然是我的生活体验,书写出来得以出版,就会实现和读者的交流。至于“魔幻手法”,当属错觉,“魔幻”的最为表象的特点是人的多变,诸如人变成动物等。《白鹿原》书里写了几场鬼事,鬼是中国民间最常见常遇的事,还有风脉,建屋修墓都要请风水先生把握好风脉,这些都算不得“魔幻”。
刘:探求“地域文化心理结构”,您认为关中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什么?等级观念、封建保守?
陈:在我有幸接触“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之后,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一个地域与另一个地域的人群的普遍性差异,表象是风俗习惯、服饰以及语言,而本质本色的差异在于不同文化影响铸成的心理结构。我曾阐述过自己对关中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看法,是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结构形态,这是由关中这方地域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关中人至今自豪自己生活的地域是帝王之都,有多少大的小的封建王朝都在此立都。无论哪个王朝,尤其如汉和唐这样的大王朝,都要在自己宫墙外围造就知书达礼更兼和顺的乡民,儒家文化被学人衍化成乡规民约,教化百姓,便建构了这一方地域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传统文化的优质,也有封建糟粕。
刘:文学的创作,提倡“为情造文”,不太主张“为文造情”,小说当然有生活现实的沉淀,但虚构的成分似乎也多得很,要达到传神的境界,难度极高。您在创作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陈:我在学习创作的不同时段有不同的难题,深化生活体验是一个相对而言一直存在且也一直追求解决的困难,由生活事象出发而产生的创作欲念,如何使其具有鲜活而尤其是独特的内蕴,是一直追求且也一直感觉不能完全满意的事。
刘:您的小说《白鹿原》通过渭北平原农村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变迁折射了中国近现代悲壮的农村变迁史,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渗透着您对农民生命际遇的深切关怀,您能不能谈谈朱先生这个人物给予着您什么样的文化理想?
陈:朱先生是我意念里的学人。他承载的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风骨等。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悲剧。我没有回避他的思想意识中的封建糟粕。然而,我更主要的是想让他彰显出传统文化的美。
刘:在十三朝帝都文化的影响下,是不是有男权中心思想在?方志中的贞妇烈女,唤起了您要通过田小娥这个形象发出一声呐喊,体现出您的女性观,您是否赞同?同时,性描写,似乎又有一种对女性把玩的态度在其中,似乎体现了您在女性观上的矛盾性,您如何评价?
陈:“男权中心思想”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下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有着十三个大小王朝立都的关中地区尤甚。田小娥这个形象,诚如你所说的是为被奴化被伤害的女性的“呐喊”。《白鹿原》书中设计的性描写,在我是一个再三斟酌的重要命题,尤其是田小娥这个形象所涉及的婚姻、家庭和性。我最终为自己确定一个框子或者说戒律,即揭示人物精神心理必不可缺的性,一定写透,不涉及此的性文字,争取一句也不要写。为此我曾归结了十个字的写性三原则,即“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且用小纸条写下来贴在案头。你所说的“对女性把玩”的阅读印象,可能是我在具体写作时仍然把握不准,多写了几句,造成读者有此阅读感觉。如实说来,我倒没有“女性观上的矛盾性”。
刘:《白鹿原》开头,是不是受《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响,一定要有一个吸引人的好开头。于是对“白嘉轩一生最引以为豪壮的是娶了七房女人”一句,有人评价,是为了博人眼球,有噱头的意味,您如何认为?
陈:《白鹿原》的开头是我的开头,蓄谋甚久确定的一个开头。
这个开头写了白嘉轩娶了七房女人的事,意在为白秉德临终前的那句话作铺垫,即:过了四房娶五房……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致命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白嘉轩的母亲说得比白秉德更直白更露骨: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这里不仅见出那个时代“无后为大”的孝的观念根深蒂固,也见出你前一个问题中所涉及的“男权中心”,不仅白秉德这个男人把死去一个儿媳续娶一个视为“再卖一匹骡子”,其母亲则更视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母亲)的心里的价值可见低贱到怎样不堪的程度。“博眼球说”和“噱头说”,大约只注意了白嘉轩娶妻丧妻的情节,而忽略了白秉德夫妇对此事的态度……不宜再说,再说就有违我不阐释人物和情节的自我约律了。
刘:文革中,您在西安见到柳青游街,对《白鹿原》中百灵被活埋,黑娃被枪毙,白孝文投机革命,以及朱先生的“翻鏊子”说,有没有影响?是不是有政治的反思在其中?这些人物的结局,似乎有了一种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跃进,您如何认为?
陈:这是一个在我很难判断的问题。反思是肯定的,上世纪80年代全民族都在反思,拨乱反正,我也有自己的反思,包括对社会命题之外的文学。我崇尚作家的生命体验,然而是否获得并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尚不敢吹。
刘:在阅读过程中,《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相比,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环境的描摹较少,您是怎么考虑的?
陈:这是出于对《白鹿原》的篇幅的考虑。初始构思时,考虑到所写的内容比较多,拟写成上下部,字数多少就不成为一个问题,肯定会为景物描写留有较大空间。最后构思基本完成时,已确定限定单本一部,字数控制在40多万字,风景描写的文字就成为首当节减的“多余”了。再,最后确定放弃描写语言,选用叙述语言,一种人物角度的语言叙述,主要是比描写语言省了字数,一句形象化叙述语句,可以包容几句乃至十余句白描语言的内容。风景描写只能在叙述中点到。
刘:卡彭铁尔开创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在小说的前半部表现较多,后半部表现很少,是不是发现一旦脱离白鹿原的独特文化环境,这种手法就失去了它的根基,还是有其他的考虑?
陈:前边涉及魔幻现实主义话题时我已说过,《白鹿原》书中无魔幻。在我的意念里,魔幻大约只是拉美地区乡民创造的神奇事象。中国民间只有鬼和神的诸多传说,我在《白鹿原》里写了一些鬼和神的神神秘秘的传闻,没有魔幻事象。
刘:《白鹿原》20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在您心目中,《白鹿原》在什么状态下就可以成为经典了?
陈:这是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尽管《白鹿原》出版20多年来获得超出我意料的好评,也一直处于不错的常销状态,然而我不想经典这个虚妄之事。常识告诉我,经典无论在学界,抑或在普通受众的群体中,都具有长说长读的不衰不弃的恒久魅力。《白鹿原》书出版仅仅20年,很难设想再过20年,还有多少人会对它感兴趣。话说到此,可见不是客气,是实话。
刘: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无法独立于特定的社会历史以及社会形态之外,伊格尔顿指出,即使是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作家,也不过是文学或文化机构的一种任命。在《白鹿原》经典化的过程中,是否感受到了这种“任命”?您如何评价?
陈:我既然如前述看待经典,就不会有关于经典“任命”的感受,也就不作“评价”了。
刘:《白鹿原》出版已经20多年,现今回过头再看自己的作品,您认为还有什么不足之处?
陈:《白鹿原》基本表述了当年的思考和艺术理想,企望更完美,却局限于当年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体验,仅能如此。今天回头看,有一些情节和细节仍有增强或消减的余地。
刘: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快速发展,面对城市文学有了新的面貌,您觉得陕西作家应该调整创作姿态,还是继续保持乡土文学的创作势头?进一步,在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学应该有怎样的时代使命?
陈:依我粗略的印象,仅就小说创作(无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的数量而言,写城市各种人群生活的小说,早已超过了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我有多种赠阅的文学刊物,单看小说类,写农村题材的作品占不到10%,这是全国文学创作的态势,陕西文学创作也莫能例外。何以如此,有待考究。在这样的创作态势里,我觉得不存在或者说不必强求“作家应该调整创作姿态”,抑或是“继续保持乡土文学的创作势头”的命题,道理很简单,作家是依赖生活体验及至生命体验实现创作的。无论城市,无论乡村,无论现实生活,抑或历史生活,作家发生了独特独有的体验,就产生创作欲望,随着体验的深化,就会完成构思,再完成创作。生活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作家,熟悉城市,对城市生活的变迁,对城市各个阶层的男女的心态裂变发生感应,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新的创作由此发端。再有一种现象,出生乡村且素以乡村为书写对象的所谓农村题材作家,后来进入城市且生活日久,随之写出城市题材的甚为优秀的作品,也当属一种扩展了的体验的展示。我意不必人为“调整”,依各个作家自己的创作兴趣而作出选择。
你说到的“乡土文学应该有怎样的时代使命”,这是一个太大的命题,颇觉惶然,且姑妄谈一点个人偏见。在书写乡村各种人物各种风情的小说里,不可或缺那种深刻揭示并展现乡村生活运动发展具有时代鲜活而真实印痕的作品,尤其是当代,共和国成立60余年的中国乡村的演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有幸和不幸,当有史诗产生。
2014年7月5日于二府庄
【责任编辑马 俊】
陈忠实(1942—),男,陕西西安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长篇小说《白鹿原》1998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