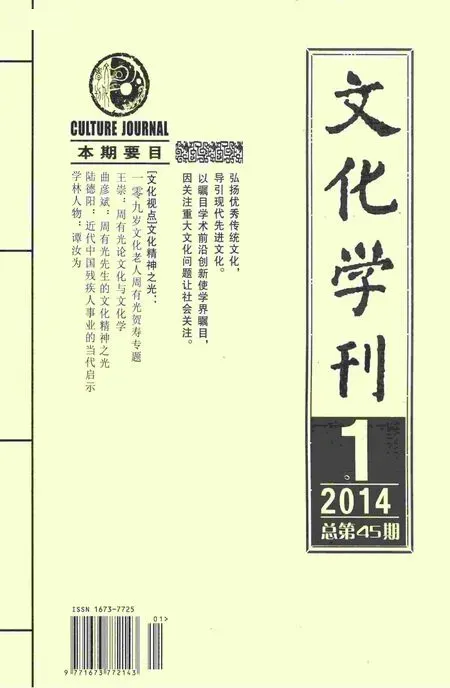两股道上跑的车
王充闾
一席话
叙写张学良的亲朋故旧、社会交往,我觉得有一个人需要缀上一笔,那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因为从他对于溥仪的关注,特别是为这位前朝废帝所设计的人生道路中,可以洞见其人格、品性和卓越的识见。
溥仪,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一个典型的能走动、会呼吸的时代玩偶,就其道路抉择、政治取向来看,诚然是可耻、可鄙的,然而,如果从人性的角度观察,那么,他的人生处境、惨酷遭遇,又确是可悲、可悯的。登基、退位之类的话题,与本章主题无关,且不去管它,这里只讲他被逐出紫禁城而日夜筹谋着还宫复辟之事。他的社交圈子很广,亲族之外,面对的主要是三种人:一是前清的遗老,帝师、老臣、忠仆、南书房行走;二是走马灯般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政客;三是阴险狡诈、虎视眈眈、居心叵测的东邻野心家。角色不同,心性各异,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千方百计要利用这个政治玩偶,达到其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就中,只有一个人例外,他没有政治野心,根本没想在溥仪身上打什么主意,只是出于友朋之间的真诚愿望,甚至是年轻人热心、好胜的习性,善意地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他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与溥仪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中叶,那时他不过二十五六岁,溥仪也刚过二十岁。他们相会于天津日本租界地宫岛街的张园,那里是溥仪的所谓“行在”办事处;他们在其他场合也见过面,可以说,交往较多。有人统计,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及张学良,多达二十处。
1990年夏,张学良在同日本广播协会 (NHK)电台记者交谈中,说到了早年他与溥仪会面时的一席话:
我在天津的一个饭馆吃早饭,溥仪突然进来看见我。我劝他把袍子脱掉,把身边那些老臣辞掉,你这些老臣围着你就是在揩你的油,你能天天出来走走,我倒很佩服你。我劝他,你肯不肯到南开大学去读书,好好读书,你作一个平民,把你过去的东西都丢掉,你真正做个平民。如果南开你不愿意去,我劝你到外国去读书,到英国或到哪儿去读书。我说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你虽然是平民,你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个平民,将来选中国大总统中有你的份。你如果今天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
从叙谈情景看,他们并非初识,而是相处已久、相知较深了。张学良言词峻烈,但态度是真诚的,设身处地,置腹推心,完全出自对溥仪的关爱。正如溥仪研究专家王庆祥所说的:“张学良跟溥仪交往,从来没想过利用‘宣统皇帝’这块招牌,恰恰相反,而是劝溥仪脱袍子,辞老臣,‘真正做个平民’,然而,他们政见不同,交往中潜藏着对立和斗争。张学良承继着老一辈的交往,同时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原则。”
王君的解读,片言居要,恰中肯綮。这里有三个关键词:(1)“没想过利用”他;(2)劝他“真正做个平民”;(3)二人“政见不同”“潜藏着对立和斗争”。
与少帅恰成对照的,是他的父亲老帅。从王庆祥《溥仪与张作霖》一文中得知,老帅曾经巴结过这位退位皇帝,叩过头,送过两棵高价的东北人参。当年拜见袁世凯大总统时,他也只是送上一棵,价值六千金;那么,两棵呢?前此,溥仪选立“皇后”时,老帅曾主动要把女儿献上,只是由于“满汉不能通婚”的清宫祖制所限,才算作罢。俗话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这一代枭雄精明绝顶,外壳是“忠君”,而内核却是利已——深知问鼎中原,还需利用“宣统”这块招牌。特别是老帅早就把满蒙地区看做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要提高在这一广袤地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清朝帝室与蒙古王公的特殊历史背景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当然,以复辟为职志的末代皇帝,也看中了这个“东北王”的政治地位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互为利用,这原本是他们之间的本质特征。
少帅奉劝溥仪脱去皇袍,辞掉老臣,真正做个平民,却是完全出于至诚,而且是绝对的高明。对于溥仪,少帅可说是仁至义尽。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已经弄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之际,他还不忘拉扯已经泥足深陷的溥仪。据王庆祥文中披露,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夜访溥仪,并甜言蜜语地说,日军在满洲的行动,仅为反对张学良,而对满洲毫无领土野心,并愿意帮助宣统皇帝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溥仪倾向于接受。张学良闻讯,于6日晚,往其驻地静园送了一筐水果,其中潜藏两枚炸弹,意在警告溥仪,让他清醒。翌年7月,溥仪任伪满执政四个月后,张学良又通过他的胞弟溥杰再一次进行规劝。溥杰后来有回忆文章,说:“暑假我从日本回国了一次,张少帅大概也得知了我回国的消息,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他的信,记得信的大意是:日本人歹毒异常,残暴无比,我们父子同他们打交道的时间长,领教够了。他们对中国人视同奴仆,随意宰割。你要警惕他们,并要劝诫你哥哥,让他同日本人脱掉干系,悬崖勒马。可惜,我当时为了同溥仪一道恢复满清王朝,对张少帅这些忠言根本听不进去,真是一桩终生憾事。”
时光不会倒流,历史不容假设。如果当日溥仪能够听进去这番话,笃信躬行,付诸实践,那么,他就不会背上“汉奸”“战犯”的恶名,远离那根历史的耻辱柱,余生将会现出崭新的霞彩。
至于说到少帅与废帝两人“政见不同”“潜藏着对立与斗争”,这是准确无误的。他们确实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岂止不同而已!这在对待日本军阀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次郎的态度上,暴露得至为充分。
三条路
张学良的忠告,对溥仪来说,有如秋风之过马耳;或者说,逆耳之言,根本听不进,这里有主观与客观双重因素。从主观方面说,溥仪复辟意志的顽强与坚定,应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
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他逐出紫禁城,当带兵进宫的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问他“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时,他曾爽快地回答:“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对他来说,无疑这是最光明的前途,最理想的选择。张学良的劝说,正与此恰合榫铆。
后来的实践表明,他的这种表态,纯属言不由衷,根本不是真心话。他的真实打算,却是:“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失掉的宝座上。”其间,北府二十四天,日本大使馆三个月,天津七年,以至后来潜往东北,可以说,无分昼夜,醒里梦里,时时刻刻,都在思谋着、策划着怎样还宫复辟。对此,少帅并非没有察觉,只是出于真正的关心,作为朋友,还是披肝沥胆地掬出至诚,为他做出具体的擘划:到南开大学进修,或者去英国留学;最后,当头棒喝,如果舍此不由,继续走那条幻想复辟的老路,那就等着掉脑袋吧!
除了少帅,可以说,溥仪身边的一切亲朋故旧,再没有人这样地劝过他,包括他的父亲载沣在内,那些遗老旧臣、皇亲国戚,还有军阀政客,用他后来的话说,身旁正有“一群蝇子”,整天嗡嗡营营地,吵得一塌糊涂。有些人,比如他的父亲载沣,头脑昏愦,未谙覆车之鉴,也就是见不及此,而更多的人,是从个人私利出发,把这个末代皇帝居为“奇货”,当做实现种种目的的政治工具。
溥仪后来回忆说:
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有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的说法则是“借外力谋恢复”。
我站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受着各种人的包围,听尽了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都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又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细计划。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给我出主意,抢着给我带路。
表面上,这些人期待复辟的目标是共同的、一致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各怀心腹事”,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以罗振玉为首的“出洋派”,主张“立刻出洋”,日本也好,欧洲也好,他们想望拉着这个末代皇帝,投靠到洋主子的卵翼之下,通过垄断居奇,收获各自的好处。以帝师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那些王公、旧臣、帝师、翰林们,则是惦记着这些名头,这些高位,使已经丧失了的重新回到手中。这一点,溥仪后来也看清楚了,他说:
我认为,那些主张恢复原状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好保住他们的名衔。他们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优待条件。有了优待条件,绍英就丢不了“总管内务府印钥”,荣源就维持住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的岁费。
就溥仪个人来说,复辟复位,是所至望,但他并不愿意重新回到紫禁城去,以免在那里遭限制、受约束,他的目标是“依他列强,复我皇位”。这样,他从北府出来,一头就扎进了日本使馆,实际上,从此也就投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怀抱,开始踏进罪恶与死亡的深渊,他却醉生梦死,酣然不觉,竟说:
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正是“好客”的地方。我在这里遇到的热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使馆主人看我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住不开,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我使用。于是,我那一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等又各得其所。在日本公使馆里,“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复了。……这些表示骨气的,请安的,送进奉的,密陈各种“中兴大计”的,敢于气势汹汹质问执政府的遗老遗少们,出进日本使馆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旧历的元旦,我的小客厅里陡然间满眼都是辫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接受了朝贺。……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下,日夜滋长着。
这种仇恨到了1928年7月2日,国民政府陆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发生,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末代皇帝发誓与国民政府不共戴天,可是,事实上,他根本不具备报仇雪耻的实力。怎么办?除了投靠列强、借助外力,就是发展自己的武装势力。他从蒋介石与张氏父子的发迹史中得到一个重大启发,“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正统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军队,自然要比一个红胡子或者流氓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与此同时,溥仪正在一步步地向日本军阀靠近。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子承父业、执政东北、特别是宣布“易帜”、服膺中国统一大业的张学良看作是他们分裂中国、吞并满蒙、建立“满蒙帝国”的最大障碍,由过去的百般拉拢,而变为切齿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了。受其影响,溥仪对于张学良的态度也随之而改变。他既不愿意张学良当“东北王”,更对南北统一持强烈反对态度,因为这不利于他实现复辟大计。
两条路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道路可供抉择:一条道路,是继续坚持奉系军阀的路线,沿着他父亲所闯开的老路亦步亦趋,战伐不停,穷兵黩武,使国内仍旧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如果这样做,则势必仰承日本人的鼻息,寻求列强的支持,实行所谓“保境安民”“满蒙独立”;另一条道路,是改弦更张,同老帅所惨淡经营的什么“东北王” “满蒙王”——也就是现代“李世民”的路线划清界线,坚决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他毅然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中的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的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现代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就张学良个人来说,实现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将领的政治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连番发出警告;后来见威胁恫吓不成,便又甜言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要全力支持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张学良却不紧不慢地说:“你想得挺周到啊,只是忘掉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几句话,噎得日本人目瞪口呆,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们原以为这个二十八岁的“愣小伙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兴风怒吼、咆哮山林的猛虎啊!
对于坚持走统一之路的果敢作为,少帅终生引以自豪。那一年,在台南参谒延平郡王祠,他曾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的爱国情怀:
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据《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记载:在同美籍华人、著名史学家唐德刚交谈时,张学良对此专门作过阐释:
学生从题干出发,多从运输距离和运输重量来分析运费成本进行分析,而图中没有具体运输重量,难以计算。最终根据运输距离推断,O点到原料M1、M2产地和市场距离距离相等,这说明M1、M2这两种原料对工厂的影响相等,即原料指数相等。当M1、M2和产品的重量都为1个单位时,将工厂建在这三者的中间,使之到三地的距离相等,这时的运输费用会最低,据此可推断选项D正确。这样讲解学生对原料和产品重量没有直观的认识,理解存在一定困难。
“你看出我这首诗有什么意思没有?我是在讲自己呢。是讲东北!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东北不是就没有了吗?我与日本一合作,我就是东北的皇帝啊!日本人真请过我当皇帝,真请过我呀!而且向我申明了,当皇帝!”
“哦,这事是谁干的?”唐教授惊讶地问。
“就是土肥原干的,他搞王道论。”
“他真叫你做满洲的皇帝?”唐教授重复问道。
“是啊,是做皇帝,做满洲皇帝。”少帅接着说了一大篇:
已经把话说明了!为这个,我同土肥原谈崩了,所以我就知道东北不能了 (当地口语,意为安定、平静)啦!那时,他一直不让我同中央合作。他说,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我日本帮你。那个时候,日本在东北奉天负责任的是秦真次,那时他们叫特务长官。我把秦真次找来,我要他换顾问,把土肥原换掉。土肥原本来不是我的顾问,他是北京政府的顾问,跟着我父亲回到奉天,接着就当上了东北的顾问。
我为此事跟他火了。本来,日本“二十一条”上订的,奉天的军人要有两个顾问,一个上校,一个上尉,一定要请日本人。我就跟秦真次说,我要换人。他说,你没有这个权。要不要顾问,这是日本政府的权啊。这可把我气死了。我这个人啊,我这个怪人,事情都是这么引出来的。我说,好,我没权,可他是我的顾问,我没权换,那好,但我有权不跟他见面,这个权我总该有吧?我就告诉我的副官,我说,土肥原顾问随便哪个时候来,我都不见。我说,我可以不见他,我不见土肥原的面!你是顾问,但我不跟你谈话。……没过多久,秦真次调回日本去了,土肥原又回来当上了特务长官。哎呀,这事情可糟了,我晓得这问题大了,他回来当特务长官,那就是升官了,这东北的特务都在他手里头。我就知道要来事了。
下面,我们再听听溥仪的陈述:
他 (土肥原)那年是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得住的。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 (指“九·一八”事变),只对付张学良一人,“因为他把满洲三千万人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再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眼光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 “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我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就去!”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
溥仪就这样登上了土肥原的贼船,从而一步步坠入了罪恶的深渊。
战后,土肥原被定为日本甲级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佐,一九四一年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十八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
同是面对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特务头子,少帅与溥仪,一个是以清醒的头脑、犀利的目光、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从民族命运、全局利益出发,义正辞严地断然加以排拒;一个却是纯然出于复辟称帝的一已私利,奴颜婢膝,毫无气节与廉耻地“为虎作伥”,充当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工具。他们由于所选择的道路天差地别,最后的结局也判若云泥:一个成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受世人景仰;一个沦为罪恶的汉奸、卖国贼,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以《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