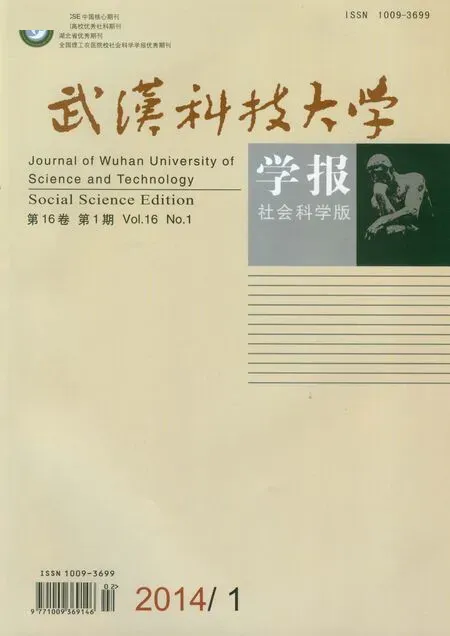1931年汉口水灾述论
——基于民国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朱 志 先
(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汉口位居长江中游,处于沟通上下游的枢纽位置,每逢夏季雨水连绵之时,汉口便面临江水侵入的危险。晚明以降,在汉官员已然明了江水对汉口形成的危害,接连修筑防护堤以抵御江水泛滥,如崇祯年间袁焻所修“袁公堤”、晚清张之洞所修“张公堤”等。但是,肆虐暴涨的江水常常会突破这些防线,给汉口带来巨大灾难。近代以来,尤其是1931年的长江大水,使全国多个省份受灾严重,而汉口尤以水灾持续时间久、受灾损失大而声震国内外。当时许多报刊纷纷撰文报道和评论汉口水灾,可谓是记载这场灾难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学界对此加以系统研究者尚不多①谢蒨茂《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记》(江汉印书馆,1931年版)是作者作为《新民报》记者亲身经历汉口大水灾况的翔实纪录,其相关报道对于研究当年汉口水灾颇具史料价值;袁继成《人祸加剧天灾:小记1931年武汉水灾》(《楚天主人》,1998年第1期),王玉德、范存俊、唐惠珊《1931年武汉水灾纪略》(《湖北文史资料》,1998年第4期),涂文学主编《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上册)》(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2页)均以编年体形式翔实记录了1931年汉口水灾;吴国柄《我与汉口中山公园及市政建设》(《武汉文史资料》,1988年第1辑),济民《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第2期),汪正本《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6辑《社会民俗卷》,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451页)均以亲历者身份讲述了武汉水灾的相关情况;章博《武汉一九三一年水灾救济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2年)、《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及余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北的水灾及水利建设》(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主要考察了汉口水灾中的相关救济工作;方秋梅《堤防弊制、市政偏失与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灾》(《人文论丛》2008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494页)认为汉口水灾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堤防弊制及市政建设中“马路优先”原则之偏失。上述文章对于研究1931年汉口水灾颇有贡献,但对民国报刊中有关汉口水灾的资料关注较少,本文着力予以梳理探究。。笔者拟通过对民国报刊有关汉口水灾报道与评论的梳理,勾勒其灾情,分析其原因,探究其影响,考察其赈济,以冀有裨于世人②诚如谢蒨茂《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记·自序》所言:“这次汉口的水患,据说是空前的大灾。正惟是空前的大灾,所以被灾的人没有应付的经验,不得不现出手忙脚乱的情形。然则把这次灾变加以纪录,使以后读到的人略略得到一些警戒,似乎是有益的。”。
一、1931年汉口水灾之灾情
1931年8月,长江发生特大洪水。由于7月份长江流域降雨量超过常年同期一倍以上,致使江湖河水盈满。8月,金沙口、岷口、嘉陵江均发生大洪水。当川江洪水东下时,又与中下游洪水相遇,造成全江型洪水。沿江堤防多处溃决,洪灾遍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省,淹死14.5万人[1]。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当属中国的第二大都会——武汉。把整个汉口、半个武昌、部分汉阳浸在水中数尺至丈余,长达一个月到两个月”[2]1-2。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一致认为,汉口水灾“较各处为甚,惟有以大批款项,作大规模之救济”(《申报》1931年9月10日)方可。当时众多报刊纷纷对汉口水灾灾情进行报道。
(一)有关汉口水灾的整体性报道
1931年8月,《新民报》记者谢蒨茂在《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记·自序》中称:“这次汉口的水患,据说是空前的大灾。”《国闻周刊》1931年第32期《军队与救灾》言:“汉口之大洪水,尤为空前未闻之大浩劫。”《银行周报》1931年第32号《水灾后之危机》指出:“武汉全镇,竟至覆灭。”《银行周报》1931年第33号《水灾严重中之救济情形》又言:“鄂渚之三镇,昔日繁华,顿成泽国。”
《国闻周刊》1931年第37期《水祸吁天录》一文对汉口水灾情况予以分析和总结:
统计汉口水灾,可分为三期。七月二十八九水入市区为第一期,被水者仅限于江滨及特二三区法界一带,水深处仅三尺许。八月二日丹水池决口为第二期,除特一区地势高亢,日租界防堵得力外,全市无一片干浄土。十四日至十七日为第三期,川水与襄水奔腾而至,江面逐日增长五寸至一尺不等。日租界亦被波臣征服,江水自八月二日灌汉口,至十八日达最高度,直至九月六七日开始退却,亘一月余日。
国松《汉局水灾之呼吁》(《电友》,1931年第9期)亦载:
此次汉市水灾,汪洋数十里,浸淫几两个月,灾情奇重,痛苦万分!虽云我国今年水灾,遍达十六省,不独汉市一隅;然调查各地灾情,水势之来,未有汉市之猛且大,受灾之时,未有如汉市之长且久者!据外国专家报告,认为汉市水灾,与日本地震相比拟,故全国水灾赈务委员会,以至全世界慈善家之目光,无不以汉市为中国水灾之中心点。
(二)有关汉口水灾的具体记载
《国闻周刊》1931年第31期《水灾惨重与救济》一文专门有“汉口惨重”一目,指出:“长江一带水灾以汉口最为惨重。七月三十一日汉口谌家矶江岸沿江铁道溃数口,长七八十丈,迄未堵住。江水高五尺内灌,后湖已成泽国。”8月2日早晨,居仁门间单洞冲破时,“当街居民溺毙甚众。老啼幼哭,惨不忍睹。模范区及中山路陆地行舟。卯刻溃决,全汉口市迄午,半在三四尺水中生活,迁徙者惨不忍睹”。《国闻周刊》1931年第32期《全国水灾惨重》载:“本年水灾遍于全国,迄现时止,全国遭水灾者已十六七省,灾民达七八千万,茫茫神州其真陆沉乎?而情形最惨重者首推汉口。”随之从“汉口洪水横流”“重要街道水量”“难民情形一斑”及“未来时疫可畏”四个方面记述汉口水灾灾况。8月3日,“被灾区域益广,市政府及济生马路之房屋,水已登楼,中山、民权、交通各路均已盈尺”。8月4日,“后湖一带一片汪洋,偶见树梢屋顶,及高耸之烟囱露出水面”[3]。8月8日,“汉口浩劫灾民十五万人待赈”;8月11日,“汉口江涛怒涨狂风毁堤,刘家庙风吹屋倒,毙人无算”;8月13日,“武汉江水又涨,情事万分严重”①见《国内一周大事日记》(《国闻周刊》,1931年第32期)。按:1931年8月8日《大公报》亦载:“一片汪洋万家号啕,汉口之空前大水灾;居民皇皇栖止无所饥肠待哺,洪流滔滔全市街巷均可行舟。”《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记》中称“汉口市全部陆沉”。8月13日,汉口各街市积水最浅者也有三四尺,汉口唯一的游乐场所中山公园亦浸在水下丈余,民生路等地最深处约三丈余,出现“流尸飘荡,收不胜收”的惨象。当时有打油诗云:“街上行船不见浪,冲到百姓房屋上。只说汉口有水灾,不知何日得安康。”。8月14日,“汉口江水达五十一尺八寸”[4]。8月16日,“江水已达五十二英尺九英寸。汉市殆全毁灭。江水仍然续涨”[5]。陆征宪《水灾祸国记》载:1931年8月初,武汉市全部淹没,当时长江水是五十尺一寸,若果江岸水标是四十六尺六寸,则江水与江岸相齐,8月19日江水已达五十三尺六寸,比以往最高的同治九年时的水位还超过三尺[6]。8月22日,“汉口各处水深十英尺十二英尺十五英尺不等。江水记录五十三英尺四寸,仍有增涨之势”[7]。白郎都《民国二十年之长江水灾》言:“自七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三日,止是两月间汉口各地均遭淹没。”[8]
(三)有关汉口水灾的灾情记载
《教育周刊》1931年第88期《全国大水灾情纪要》称:“八月中旬,汉口全市几已陆沉……无家可归者总计当不下二十二万之数,待赈者约十五万人。”
《圣教杂志》1931年第9期《时事摘要·各省水灾》载:
本年水灾遍于全国……沿长江一带集无一地幸免,而尤以汉口及两湖灾情最重。汉市居民几尽处水中,汉口区之灾民在二十万以上,虽经各官署慈善团体组织救护队,而被收容者,仅达五分之一,此诚令人酸鼻。
《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1年第6期《民国二十年水灾记》载:
鄂省水灾之惨重,从时间言,为八十三年所未有。从空间言,则全省六十八县,半遭巨浸。至汉口为鄂省精华所在,又为大江商业中心。经此大水之后,将来影响之大,概可知矣。查该市自上月二十六日水浸入特三区后,二十九日法租界大智门东站附近皆成泽国,至本月一日丹水池渍破,铁路外水,渐与路基齐。四日,水势泛滥,市内已在水中央矣。其时惟偶见树梢屋顶及高耸之烟囱露出水面而已。水之深处达三丈,浅处已数尺。据闻长江水量,在汉过去水标最高为五十英尺半,此次达五十三尺半,而江面前仅一英里有奇,今则数里以上,若江堤不溃,其高尚不止此数也。
《纺织周刊》1931年第19期《武汉水灾》载:
今年遍地均告水灾,而武汉为祸最烈,长江水量日日加涨,汉口一片汪洋,全部陆沉,虽最高之黄陂街,防患有力之日租界,均已不免,铁道路线,亦没水底,人民荡析离居,几无逃生之所,武昌全城亦水中,古称洪水猛兽,不图祸烈至此也。
综上所述,可见1931年汉口水灾之特点:水势凶猛,旷日持久,危害极大。
二、1931年汉口水灾之原因
1931年汉口水灾灾情严重,涉及范围广,当时各阶层人士撰文直陈其原因。有认为系迷信传说耽误防水;有认为是地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原因;有认为是防患不当,筹措不力;有认为此次水灾系天灾,非人力所能抵御①《国闻周刊》1931年第34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称:“现汉水量较六十一年前高三尺,实出意料之外。管理堤坝容有不注意处,然以本年之大水,纵十分注意,亦难防止云。由此观之,汉口水灾,实非人力所能御防也。”;甚至有认为系西方殖民政策所致[9]。
(一)迷信传说
有认为是汉口人把龙王庙毁了,所以龙王显灵用大水来淹没汉口;有认为汉口人心太坏,大水成为不可抗拒的惩罚。许多人甚至一些知识分子也信以为然,动议水退后重修龙王庙,此类人只有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2]6。“汉市公安局曾拟呈请恢复龙王庙,以安市民之心”②见《水祸吁天录》(《国闻周刊》,1931年第37期)。据汪正本《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载:面对急剧上涨的江水,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没有指挥官兵积极抢险,而是陈设香案祈祷龙王爷(参见《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6辑《社会民俗卷》,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涂文学主编《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上册)》(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亦有此说。。
(二)地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原因
谢蒨茂认为造成此次水灾是由于地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原因,从地理学上而言,汉口地势较低,成为青海、四川以及陕南、豫西、豫南等地水道的汇聚点,然后再东行入海,而汉口则为长江流域中心的一个大盆地,市区西南临襄河,东南滨长江,北枕后湖,形成一个三面环水的三角洲,这种三面环水的三角洲地带,在地理学上是常受水灾之地。从气象学上而言,每年春夏之交受北半球季风影响,雨量增多,而汉口以西的长江流域各省雨量势必增加,故夏秋之间长江水量比高,由于宜昌以上多山地、荆州以上多丘陵,故江水不至泛滥,而汉口则为盆地,故江水在夏秋之季几乎一定泛滥。1931年,因南洋方面的暖湿空气侵入中国南部,与来自中国北部的冷空气相接触而形成雨水,故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的水量皆比往年增加,依往年的惯例,每年夏秋之交,中国东南沿海必有飓风将湿暖空气吹散,降雨就会停止,但1931年东南沿海却没有出现飓风,因此该年份的降雨持续时间久且水量极大,水灾便难以避免[2]7-11。
有认为是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反应。1931年第10期《圣教杂志》载:近四十年汉口有三次水灾,分别是1887、1909和1931年,“据各地老者言咸谓此次水灾之严重,人民损失之巨大,有甚于前两次者多矣”。这三次水灾均相距22年,是太阳黑子运行周期11年之倍数,“好似长江流域大水灾之周期也”③见《长江流域第三次水灾》(《圣教杂志》,1931年第10期)。按:竺可桢、刘治华《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其影响》指出:“此说是否成立,当有待二十二年后之事实证明也。”(《时事月报》,1931年第7-12期)。。
(三)防范不当,筹措不力[10]
虽然汉口在地理位置上属于水灾易发地段,倘若政府及民众的防患意识强、措施得力、行动积极,尚不致于汉口全市陆沉。民国报刊对政府及民众有关防灾、救灾的不当记之甚多。
有认为市民缺乏防患意识。如江水最初侵入市内,主要是外交部汉口特三区市政管理局放弃职守,导致江水由该区江岸直入市内;单洞门一带,由于监工未能及时给予工人宵夜费,导致工人消极怠工,以至于溃堤,使济生一二三四五马路,全部淹没于深水之中[2]40。郑璜《南湖蚕桑场水灾后迁移厂址之商榷》(《农业季刊》,1932年第2期)亦指出:“今年水灾奇重,为从来所未有,固是堤防未修之过,究其根本,在人民强占水的位置,以兴农桑,而水来力争,有必然者。”
有认为政府筹措不力,未能积极兴修水利。《国闻周刊》1931年第32期《全国水灾惨重》一文专门以汉口为例进行介绍。1931年7月26日,“江水盛涨。特三区(即旧日英租界——引者注),低洼之地,有水侵入,市府及特三区管理局,漠然不以为意,而日侨奔走骇汗,赶购沙包……华人且嗤之以鼻,指为无事自扰”。7月29日,“法租界大智门车站附近,至伟英里止,皆成泽国。各处始手忙脚乱,为亡羊补牢计,用汽车装运沙包堵水,而工作拙陋,殊不足以阻水神之大驾。……铁路单洞门久失修葺,蚀剥不能胜任,倍受水之压力,势益不支。(八月)一日上午,已成涓涓不绝之势。市府、水利局、路局接得警报,曾派员实地勘察,彼等仍采取安详之步骤,未闻有何布置。二日黎明,
单洞门遂宣告解除责任,轰然一声,水势倾注,骤若奔马,居民从梦中惊醒,哭声震野。三日被灾区域益广,……武汉总部行营,亦化为一座水晶宫矣。”①黎少岑称防堵单洞门时,防汛部门所拿出的防汛物资仅是一千条麻袋,可谓筹备无力。参见黎少岑:《武汉今昔谈》(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2页)。
沈怡《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东方杂志》,1931年第22号)载:“此次武汉之大水,则更属骇人听闻,考其原因,不外近年水利不修,干支日就淤浅,诸湖受水之区,其洲渚复被私人纷纷侵占,以致水无所容,横决为灾。加以本年七八月间,各地雨量之多,面积之广,异乎寻常。上游又无森林及相当工事,水势直流急下奔腾泛滥,莫可抵御。武汉三镇适当江汉之冲,支干同时并涨,纵堤防如何坚固,恐在此种情形之下,大水仍可漫堤而过,况其本身原甚薄弱者耶?”李英浒认为汉口造成水灾的原因在于河道淤塞,容纳不及而泛滥成灾[11]。据称,1932年汉口的江面还没有1930年汉口的江面宽阔。
《国闻周刊》1931年第33期《大水后之防疫问题》载:
沿江涨水,汉口全市直有灭亡之虞。……此次水灾损害所以如此重大,事前与临时之防范不周,为一重大原因。但观汉口日租界迄今尚未浸水,而其他区域,早一片汪洋,则中国官吏之溺职,人民之疏忽,可以因比较而证明。
譬如,“汉口日租界所处之地势实极不利,因日租界地面较低于他处,然终以堵防得力,抗拒有力,而受害反在最后”②见记者《全国空前罕有之大水灾》(《时事月报》,1931年第7-12期)。《军队与救灾》一文亦指出:“抑闻汉口日租界地势最低下,此次独免被水;盖当水初涨时,日侨全体即拼命作堵水工程,故得免祸。”(《国闻周刊》,1931年第32期)《国闻周刊》1931年第37期《水祸吁天录》载:当7月31日“特三区已全浸水中。而日侨则以全付精神组织水灾防御会,在江岸配备沙包,并以泥土夹板为二道防线,河伯初亦取避实就虚之主义望望然去之。”。同样,美国密西西比河常有大水,但防患得当,人民受患极小。荷兰被海水淹没的可能性更大,但有好的堤工,故荷兰人可以高枕无忧,安然度日[12]。
有认为系政府官员玩忽职守、中饱私囊所致。
1931年8月21日《大公报》《谁造成汉口水灾》一文指出:当汉口出现江水泛涌时,“该区管理局毫未留意,省市当局亦不加闻问。待江水溢岸,沿江江汉关前渐成泽国,该局始以木板泥砖,略筑矮坝于各面江路口”,不到两天,随着江水上涨,“简薄之矮坝,正似螳臂挡车,顿被冲决,于是第三特区马路全被淹没”,而新任汉口市市长何葆华却玩忽职守,“不筹一预防之策”。
《国闻周刊》1931年第37期《水祸吁天录》载:
湖北省政府中人,有用政府名义以数百万修堤款经费,存在贩卖鸦片之川江龙公司,博取重利,结果该公司借故倒闭,堤款全失,以致沿江堤工,未能修理。
《抗争》1933年第8期《人造的水灾》指出:
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灾的教训,沿江土地人士为保障其田园庐墓之故,曾短衣缩食搜集巨款,当时并拨各埠赈款的一部分预为筑堤之用。在人民方面,已尽未雨绸缪之责,乃目前江水暴涨,险象丛生之时,突然发现堤款久假不归的事实。
据有关资料显示,堤款赈款成为官吏们挥霍滥用的资源③1930年蒋阎战争时,宋子文大肆挪用汉口修堤积存金,湖北水务部门亦不重视张公堤等分堤的修缮工作,导致洪水到来时出现溃决。参见钱俊瑞:《钱俊瑞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汪正本《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指出:在修张公堤时,官员中饱私囊,以致于“修复张公堤所用的面粉,可以堆一座面粉张公堤”[13]449-450。
民众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缺乏国家观念,在遇到灾难时,只有自保,难及国家。政府防灾意识淡薄,遇灾时未能充分积极应对,相互推诿,唯利是图,更加剧了此次水灾的危害性。
三、1931年汉口水灾之影响
1931年大水使繁华的汉口成为一片狼藉的泽国,其破坏程度之大,震惊国内外。1931年9月1日《中央日报》刊文指出:
汉口方面,商人之经济损失从各方面估计,自水患之日起,截至现在止,总在一万万元以外,政府方面,种种建设之损失,亦在三四千万之数,似此情形,再加以各县人民屋宇、禾苗、畜牲种种之淹没与毁坏,总计其数,自亦应以万万为单位。
(一)生命财产损失无数
武昌收容灾民七万多人,汉口灾民有二十余万,在汉两万余商店中有一半以上歇业[2]91。《国闻周刊》1931年第33期《将毁灭之汉口》载:汉口“水浸日久,屋基动摇,每小时内有数百房屋倒塌。数千人绝食,渐将饿毙,许多难民救援全断,死亡数目不可胜计。”《国闻周刊》1931年第34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载:汉口仅8月21至27日,一周间,溺死于洪水者就达1 700人。
陆征宪《水灾祸国记》披露汉口大水灾况:
自丹水池及单洞门溃决后,汉口全市除大(枣)街、黄陂街的最高地略有干土外,其余各地都被淹没,最深的地方水达二丈,浅处也有几尺的水,淹死的人畜,已经不可算计。无家可归的灾民总计在二十二万以上,待赈的约十五万人。财产的损失,除政府种种建设的损失还没估计外,只按各项商人和私人的经济损失来论,已在一万万元以上了[6]。
湖北农业技术研究会《民国二十年水灾后整理农桑畜棉稻五场计划书》指出:
此次大水为灾,乃非常之事变,武汉各场均蒙莫大之灾害。地面作物,悉被淹没,甚且场屋灭顶,全部坍塌。举凡近数年来各场锐意试验之种种成绩,尽付东流[14]。
(二)对汉口商业、金融业的影响
引起物价飞涨。诸如米商囤积居奇,哄抬米价;大椒豆由两百钱一斤涨至四百钱一斤,冬瓜南瓜由每斤八十文涨至一百六十文,等等,价格上涨可谓“有一日千里之势”,而新上市白菜的价格,更是“尤为不可思议”[2]16。
对中外贸易的影响。《中行月刊》1931年第3期《汉口水灾与对日贸易》一文载:
汉口每年输出米量不下二三十万吨,本年因洪水为灾,陷于不能生产状态。此外,如桐油、大豆、芝麻、菜种、高粱等汉口重要农产物完全杜绝输出。日本对汉口贸易将全然中止。汉口各项商品总输出额,一九二九年为一亿九千六百八十七万海关两,一九三○年为一亿五千七百万海关两,其中输出日本者占多数,由此可以推知此次水灾影响日本对华贸易之巨大矣。
1928年汉口出口值达到17 829万海关两,次年开始下降,1931年剧降至9 393万海关两。自1922至1930年汉口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出超,1931年因洪水泛滥,变成入超2 053万海关两[15]。
导致商业萧条。肇民《市民应全体动员防御水灾》(《汉口商业月刊》,1935年第7期)载:
(民国)二十年洪水,汉口沉浸于水者,达二月余。一切公私损失,迄今虽尚无正确统计,然就商业一部分言:据汉口营业税局发表数字:大水前纳税商号约一万五千余户;大水后,则减至一万三千余户。大水前税收标准,每月营业金额达二千八百万元;大水后则减至二千一百余万元。其创痛巨深可知。然二十年大水犹承十八九年极度繁荣之余,公私财力,尚可图谋善后,故虽遭受巨变,犹堪勉为应付;但各业已自兹陷于苦境矣。
《纺织周刊》1931年第19期《武汉水灾》称:
汉口为我国棉花最大集散之市,陕豫湘鄂之棉多聚于此,而川省纱布仰给于沪汉者,又必取道于此,以是商业之盛,仅亚于沪粤。今兹被灾,人民救生之惶,宁复有业,即此有形无形之损失,实不可以道里计。
1931年《教育周刊》编者评述汉口水灾的影响时指出:
汉口大水,为百年来所未有,各轮栈公司房之第一层完全没去,低浅之货栈,淹水达十余尺,货件漂流。各轮船公司虽有特造天桥木塔以供货物起卸,然来货完全断绝,中国中部之唯一商埠,商务已一蹶不振矣[16]。
商业萧条引发金融业衰退。《银行周报》1931年第32号《汉水灾影响沪金融》记载:
沪金融界向来与汉埠金融界及各商业往来款项,进出甚巨,夙仰商货流通,银根赖以周转,此次汉埠全埠水灾,商业中辍,大好商埠已成泽国,对于银款势无往来之可能。据调查所得,放与汉埠往来定期及不定期之款项,不下五六百万之巨。现居年关虽然尚远,而光阴荏苒,转瞬即届,不知可能清偿否?依照沪埠金融中人之希望,如能有半数归赵,已觉非常庆幸,就此可见汉埠营业困难之一斑焉。
《中央银行旬报》1931年第23期《汉口金融大势》载:1931年7月下旬,因水患阻断交通,导致“各路货物来源中断,商业停顿,市况清淡已极,一旬中拆息竟有数日无市,月底比期,银钱收交并不踊畅。”《中行月刊》1932年第6期《汉口日货贸易商完全破产倒闭》载:“汉口自遭水灾后,百五十家钱铺中,倒闭者已有三分之一。”鲍幼申编《湖北省经济概况》(《汉口商业月刊》,1934年第12期)云:“汉市各银行之业务,在放款方面,多以货物押款为大宗,民国二十年大水灾之发生,汉市各银行,多半损失不赀,尤以一般自设有货物堆栈者,受患更巨。”在这次水灾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因货栈所放货物被水淹没损失在一千万元以上,重庆聚兴诚银行汉口分行损失在一百万元以上[17]780。
(三)导致灾疫出现
1931年大水时,汉口顿成泽国,一潭死水在烈日高温下曝晒浸泡数十天,卫生状况之差可想而知。《国闻周刊》1931年第32期《全国水灾惨重》言汉口的“公共卫生,今日已无讲求之余地。其在江岸附近之被水区域,水势流动,尚无腥秽之气。若在市府及模范区一带,水由铁路外侵入,龌龊污臭,令人作呕。况附近菜圃农场,均为水神税驾之所,乡人无需乎肥料,遂演成空前绝后之粪涨问题。水区多属楼居,每当薄暮,各就窗口倾洩秽物,此情此景,殆浮于鲍鱼之肆。至露宿之灾民,就地粪溺,蚊蚋攒聚。”《国闻周刊》1931年第37期《水祸吁天录》亦称:
市民对于公共卫生之观念,甚单薄,公然倾洩,略不顾虑。警士在水区中之工作,笨拙如牛,不能一一绳之以法。在水势较深之际,其流动力尚强,迨水浅而流缓,臭恶之气,烈于鲍肆。十里洋场,纳污藏垢,数十万居民,皆棲息于羶腥中。无怪虎列拉、赤痢、伤寒、恶疾,蔓延各地。
水灾过后,必有疫灾。况且在此种极度恶劣环境中,更加助长了各种传染病的滋生。
国松《汉局水灾之呼吁》(《电友》,1931年第9期)称:汉口“白昼阳光张焰,积水便溺狼藉,恶气袭人,不胜掩鼻,夜间蚱蜢蚁蚋,会集室中,争食人肉!遂至疾痢流行,病者什九……”。《教育周刊》1931年第88期《全国大水灾情纪要》载:“武汉灾民近日患肠胃痢疾者甚多,有则发生急性传染病,不可救治。”《中华医学杂志》1932年第1-6期《湖北卫生防疫之工作报告》称:汉口“疾病统计,以痢疾为最多,霍乱次之,疟疾及急性肠胃炎又次之。”1931年8月23日《大公报》载:
武汉两市华界情形,成为困苦死亡之窟宅,两市自变成泽国以来,死亡者至少达1万人。赤手无家可归者,达40万人,每日死于痢疾与伤寒者甚多。医药界预料,洪水退后,必将有恶疫盛行。
当时《国闻周刊》对汉口疫灾情状报道甚多。《国闻周刊》1931年第33期《将毁灭之汉口》载:
汉口无地无水,最高之地,水深四尺,一种疹状伤寒疫症,已开始蔓延,当局无法防止。……霍乱及伤寒蔓延于水深八尺之华界,毫无医药救济。虽有金钱,购买生活必需品亦颇困难。水塔崩溃,饮水供给,亦生恐慌。数万病人因暴露在外,及缺乏食品不能救济,惟有待毙。嗟嗟,汉市人民何辜,罹此未有之浩劫?
《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8月18日“汉口灾民发生急性传染病”。《论评选辑》专门谈及汉口“大水后之防疫问题”[18]。《国闻周刊》1931年第34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指出:武汉附近积水中“充满腐败食物,漂浮人畜之尸体及污秽等物,无法排除,恶气蒸发逼人,亦无法逃避,更有染病之危险。刻因时疫死者达数千人”。汉口“每日死于痢疾与伤寒者甚多”;“洪水退后,必将有恶疾盛行。各处情形纷扰,灾苦情形,殊难描述……最可怕者霍乱、伤寒、窒扶斯等传染病,以非常速度蔓延于武汉区域。当局仅忙于设法供给数百万难民之食物,无暇防御”。《国内一周大事日记》载:8月21日“时疫蔓延”;8月22日“汉口因饥饿时疫死亡日多”[19]。
对于日益扩散的疫灾,汉市公安局、卫生管理处、省市立医院共同组设防疫事务所,积极进行防疫消毒,但由于仓促使然,效果并不理想。汪正本《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中载其亲眼所见汉口水灾后痢疫流行,“疫症发生后又少急救医药,医院病床少,医疗技术落后,对迅速传染如火燎原的疫症痢疾,束手无策。致死亡枕藉,哭声满城!”[13]
1931年大水灾导致汉口生命财产损失无算,商业、金融业因之萧条,以及各种传染性疾病流行,使这座素有“东方芝加哥”之誉的繁华之城,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人间地狱。
四、1931年汉口水灾之应对
面对汉口此次百年不遇之重灾,无论政府层面,抑或民间团体、个人,乃至国外人士,纷纷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救助。
(一)政府救济
成立湖北水灾急赈会救济股。7月31日,派出五个救济组,携带救济水及馒头向张公堤附近灾区进行救济,散发馒头一万五千余件,救济水五百余瓶;8月1日又散发馒头一万三千余件。到8月1日止,慈善会内收容所共收留灾民800余人,后来各个收容所均满负荷运转。随后又成立水灾急赈委员会(集中各界力量办理本省水灾急赈事务),常务会员由在汉军政商界及慈善界负责人担任。由于水灾严重且波及面广,在汉慈善团体虽尽力施救,但无奈杯水车薪,出现“灾民之呼号虽切,而实惠之施,仍尚无所见”[2]26-28。1931年8月28日,蒋介石乘永绥舰到汉视察水灾,29日夜,“视汉口各溃口”,随后指示财政部饬令汉口中央银行划拨三十万救灾款,让湘赣两省开放米禁[2]121。
(二)民间救助
8月20日,汉口商会通电全国呼吁赈济[2]119-120。时任湖北省水灾急赈会常委兼救济股主任蔡辅卿不顾年迈之躯,派遣多个救护队救助灾民,并在武昌、汉口两地设置救助站,收容灾民数万人。由于灾后疫情蔓延,蔡辅卿又组织医疗队奔赴各处救治[20]。
武汉大学由校长王世杰倡议,全校教职员工尽力捐助月薪作为医药费及赈款,并约集仁济同仁医院商量防疫办法[2]60。水电公司经理刘少岩雇用数十艘船只运载自来水发往各收容所,避免灾民饮用积水发生疫病[2]59。
各个同乡会积极运送灾民回乡。湖南在后湖及武泰闸务农者较多,湖南旅汉长郡同乡会会长石和湘等发起临时水灾急救会,雇用船只运送一千二百余名乡民返湘。旅汉黄陂同乡会亦组织小轮船运送乡民回家,以减少乡邻的损失[2]62。上海宁波同乡会、绍兴七县同乡会及上海四明公所等亦积极组织船只免费来汉护送同乡返乡。旅沪甬人张寿镛得知汉口灾情危急、在汉宁波老乡欲返乡却无船可乘,便个人筹资从宁绍三北轮船二公司调三艘轮船来汉转运同乡[2]125-126。
1931年9月,虞洽卿在上海组织武汉水灾急救会,积极救助汉口灾民。“虞洽卿一面募集捐款,组成医疗救护队,携带救援慰问物品,由三北公司派出专轮新宁兴号开赴汉口救济;一面汇款千元给三北汉口分公司经理殷惠永,殷接到汇款后购备馒头等食品,连同上海运来的救济物品立即派出扬安、宜安两拖轮携之驶往难民汇集的张公堤等处分发,并通知难胞如欲回乡可免费搭乘新宁兴轮返乡,船上免费供膳,有病者也可得到治疗。同时虞洽卿又电告宁波分公司同当地观宗、延庆和七塔三大寺院联络,准备收容到甬难胞临时住宿,并嘱预订大批油包、馒头等食品备用”[21]286,千方百计帮助宁波同乡摆脱这场灾难。
娱乐界也为汉口水灾伸出援助之手。1931年9月1日《申报》在电影《东方夜谈》宣传广告中提出:“每场加映《汉口水灾》二大本,洪伟烈实地拍摄”、“多买一票,多救一命”、“第一次的公映等于第一天的收入,牺牲助赈”。
(三)国外援助
为救助汉口水灾,美国红十字会捐助赈款十万美金,合银四十五万元;罗马汉口主教电请罗马教皇为汉口赈灾捐华银六十四万元[22]。
日本汉口同仁会医院于水灾开始,便“从事于救疗,又将院内医员总动员,别组第一诊疗班及第二诊疗班分驰各处,日夜诊疗,得以救者日有数千人。然以范围太广,恐有杯水车薪之患,乃由本部电命同仁会青岛医院分组第三诊疗班于九月五日发青岛,星夜驰往救援,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汉,翌日即开始诊疗”。东京的日本同仁会本部则连日数次召开理事会,协议救疗进行事宜,除电命在华各医院互相联络协力之外,更向留日之中华医士诸位劝驾,组织第四诊疗班,诊疗班“一行所携之医疗药品甚多,且医员之经验手腕,皆可以一当千,其能十分活动发挥仁术济世者,自不待言”[23]。
五、1931年水灾在当时学界之反响
1931年汉口水灾被称为百年未遇之灾害,给国人留下了莫大的创痛。水灾之后,政府方面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24]103-105。
当时许多学者撰文对汉口水灾予以反思。有指出防水的根本在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如凤年《中国的水灾问题》(《文化界》,1931年第1期)、《防救水灾勿忘治本》、《水灾恐怖中之水利问题》(《尚志周刊》,1933年第24期)等。罗承侨《造林与水灾》一文,通过理论分析及实践考查,认为植树造林有益于治水[25]。汉口水灾之后,张均鉴《预防水灾之根本办法》(《农业季刊》,1931年第1期)指出应该振兴林业、盛修水利。黄沛霖《水灾后应有之认识》(《农业季刊》,1931年第1期)亦指出应造水源林。
吕维谦《造林与防灾救民》亦言造林有助于防灾[26]。犖群《救灾更宜防疫》称:对于灾后防疫,“如汉口……等人口甚多,被水甚重之都会,尤必需严厉执行”[27]。
有建议武汉每年实行“防水节”,当天全城人民停业,“每人负土一囊,工作半小时(或纳捐规定数目,代替负土做工)”[28]。白郎都《民国二十年之长江水灾》详细分析了形成汉口水灾的原因,并建议修复水位预测及水位报告之设置[8]。
因为有1931年汉口大水的教训,“对于防水似乎较以前要更注意,武汉筑了一条工程浩大的长堤,长江一带都有堤工局的设立”[29]。但亦有学者指出:“前年汉口的水灾,受祸达数千万人,当时朝野上下都很注意,治本治标大计,政府都积极计划。”但是灾后,却因他故又放任自流,导致水患不断[30]。
[1] 佚名.1931年8月4日 长江暴发特大洪水淹死十四万余人[EB/OL].(2008-08-04)[2013-06-12].http:∥www.people.com.cn.
[2] 谢蒨茂. 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记[M].武汉:江汉印书馆,1931.
[3] 记者.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全国水灾惨重[J].国闻周刊,1931(32).
[4] 记者.国内一周大事日记[J].国闻周刊,1931(33).
[5] 记者.将毁灭之汉口[J].国闻周刊,1931(33).
[6] 陆征宪.水灾祸国记[J].平等杂志,1931(7).
[7] 记者.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J].国闻周刊,1931(34).
[8] 白郎都.民国二十年之长江水灾[J].扬子江水道季刊,1933(1).
[9] 史克士.我国空前水灾与帝国主义者之关系[J].市政月刊,1931(8).
[10] 王玉德,范存俊,唐惠珊.1931年武汉水灾纪略[J].湖北文史资料,1998(4).
[11] 李英浒.廿年来我国之水灾[J].大夏,1934(4).
[12] 缘.水灾[J].自由言论,1933(14).
[13] 汪正本.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琐记[M]∥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6辑(社会民俗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
[14] 湖北农业技术研究会.民国二十年水灾后整理农桑畜棉稻五场计划书[J].农业季刊,1932(2).
[15] 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J].近代史研究,1990(1).
[16] 编者.全国大水灾情纪要[J].教育周刊,1931(88).
[17] 何瑞宝.1931年汉口大水期间的金融业[M]∥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18] 佚名.论评选辑·大水后之防疫问题[J].国闻周刊,1931(33).
[19] 记者.国内一周大事日记[J].国闻周刊,1931(34).
[20] 严小士.武汉商界巨擘——蔡辅卿[J].武汉文史资料,1988(1).
[21] 汪仁泽,姚伟琴.海派实业第一人——虞洽卿商旅传奇[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22] 记者.中外努力救灾[J].国闻周刊,1931(33).
[23] 同仁会.日本对于中国水灾之义举续报[J].同仁医学,1931(10).
[24] 章博.武汉一九三一年水灾救济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2.
[25] 罗承侨.造林与水灾[J].江苏农矿,1931(19).
[26] 吕维谦.造林与防灾救民[J].农业季刊,1932(2).
[27] 犖群.救灾更宜防疫[J].妇女共鸣,1931(54).
[28] 肇民.水灾如何善后[J].汉口商业月刊,1935(8).
[29] 柏.大水灾的预防[J].时代公论,1933(12).
[30] 汉平.水灾[J].大学杂志,19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