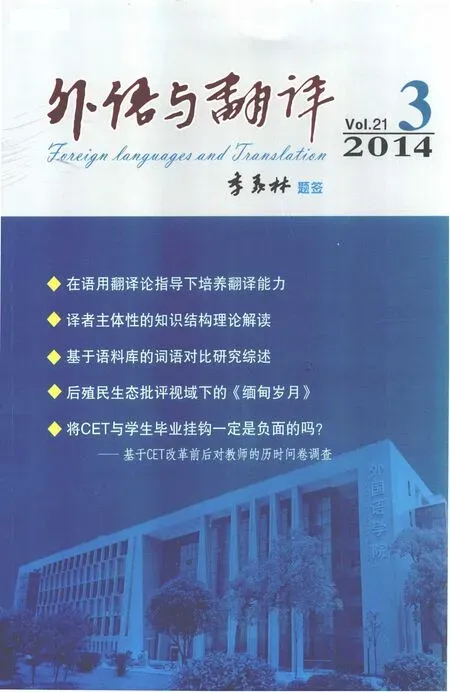装饰的变革浅析
(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服装系,安徽芜湖,241000)
主流学术界将装饰分为三种:纯粹性装饰、结构性装饰和实用性装饰。几千年来装饰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从表面装饰(纯粹性装饰)向结构性装饰(与结构结合在一起的装饰)发展的过程。现代工业设计的装饰之美,是通过结构化的整体去体现,而非依赖于物体表面的纹饰。利用产品本身的结构来成就外观之美,就是结构性装饰;利用表面纯粹性的装饰图案、部件来成就外观之美,称为纯粹性装饰;而有实用性,实际功能的装饰,被纳为实用性装饰。从造物文化产生至今,就形式而言,装饰包括器物造型和器物表面装饰两大类,整个发展历程分为两个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工业革命前,是手工业时代,这一时期是表面装饰的繁荣期[1]。工业革命后,在卢斯“装饰就是罪恶”这样激进的口号指引下,装饰一度被彻底摒弃,产品设计以功能为主,装饰和结构相结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后现代主义兴起,随着人们对现代主义机械冰冷的设计实践的厌倦,装饰的价值被重新肯定,重新进入到工业设计的领域,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手工业时代
装饰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手工业时代,在手工业时代,“装饰”这个词汇的产生要远远早于“设计”,设计基本上可以被等同于装饰。这一阶段装饰虽然大多能体现出与器形的结合,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仍然只是一种表面的“纹章”而已。这些表面的“纹章”仅仅是对器形进行修饰,与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就是占据几千年的装饰历史中绝大多数时间段的纯粹性装饰。这个时期的装饰无论风格还是题材都已经极其丰富,设计水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也已经非常成熟,但是无论艺术形式多么发达,本质上装饰仍然仅仅只是对器形的依附。到了手工业时代晚期,中国的清代,以及西方巴洛克洛可可时期,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了过度装饰的特征,表现形式就是建筑物以及生活用品表面堆砌着奢华繁琐的装饰纹样,尽情地展示工匠的高超技巧。用贡布里希的话说,这就是工匠们“压抑不住的填补空白的冲动”。这种形式奢侈浪费,最重要的是——未见得有多美。
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由此社会对待装饰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非常熟悉的转折点,就发生在卢斯身上,他的“装饰就是罪恶”的口号,犀利而明确地反映出当时社会人们对待装饰的态度,在设计界影响深远。其实,虽然卢斯对他所理解的装饰不遗余力地攻击,但他的论据,几乎完全立足于物质生产的效率,是从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角度提出的论点。卢斯认为,人们要是花时间在装饰上,就会“越过越穷”。装饰所谓的犯罪,在卢斯的本意来说,其实更多的是在经济和效率上,而非艺术上。在卢斯的定义中,装饰是指没有任何功能性作用的,没有实用性的东西。而什么是装饰?什么是无用?判断标准是什么?不同阶层、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一定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从某种角度说,今天的我们对装饰的感受与定义,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也许我们今天物质生活不再困难,但装饰仍然是普通人支付不起的奢侈品,那些去装饰化的,规规矩矩的机械而冷漠的现代主义方盒子建筑,就是这个时代为我们安排的巢穴。已经习惯了现代主义设计的我们[2],在对所谓有用的理解上是最低层最物质层面的,对功能这个词汇的定义,仅限于物质功能和使用功能。简单的说,对于一个 19世纪的中产阶级来说,裁纸刀就是有用的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今天我们则直接用手撕开信封。相应的,在对装饰的感受上,经过现代主义长期熏陶的当代设计师非常敏感。稍微高出最低层面一点的东西,都会被认为是奢侈,以至于当时卢斯本人所认为的很多不属于装饰的“自然材料”,在现代设计师眼中都是装饰。
二、工业革命时代
装饰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工业革命时代,分为早期和晚期。在早期,装饰风格新旧交织,变革与混乱交织,这是装饰革命的过渡时期,最突出的矛盾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样式和风格与新材料新技术之间的矛盾。因为传统的样式和风格在人们心中已经形成定式,所以,即使新时代的设计师们用新材料技术制造新产品,其旧有的传统形式和风格仍然在这些新产品中显得清晰可见。如从马车到汽车的发展史,就是这种历史惯性很好的说明。在汽车发明前,类似的交通工具是马车。所以早期的汽车设计,可以明显的看到从马车的造型渐渐转变的过程。刚开始的汽车就是在马车的造型基础上,做出少量修改。早期的汽车使用马车一样的巨大轮子,车身也和马车一样,都是木质的。直到福特 T型车的时代,才开始大量采用金属车身,逐渐的造型也渐渐变化,直到1927年,汽车的车轮才变成我们所熟悉的小轮子的造型。这种现象也是产品设计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流行是有规律可循的,最基本的规律就是持续性渐变性。在第二阶段早期这个过渡时期,(18,19世纪)设计主要表现为一种装饰的设计,这种装饰的设计又更多从传统根基起步,是一种从历史样式开始渐变的趋势。这成为20世纪设计生成与生长的开端。这个过渡时期,装饰仍然仅仅是被当做一种表面的纹章,实际生产中存在着大量装饰与产品外形不相符的情况。第二阶段晚期即是现代产品设计时期。这个时期的产品设计,多数摒弃了表面装饰,以功能决定形式,将装饰之美通过结构化而整体性地表现出来,力图使装饰结构化而非表面化。这个时期的装饰,被融合进结构之内,装饰本身就有功能作用,是结构的一部分,没有产生额外成本,是贡布里希所谓“顺便”的产物。而后现代主义运动以来,纯粹性装饰对于设计的意义被重新重视,我们在最新潮的工业设计中也常常能找到之前被深恶痛绝的纯粹性装饰的身影[3]。
总之,装饰的发展历程,与设计的发展息息相关。装饰艺术的历史构成了人类艺术史发展的主线。 整个装饰与设计的关系,可以简单归纳为:初期装饰较为重要,然后越来越重要,直至完全等同于设计。工业革命后装饰盛极而衰,设计界提出:装饰就是罪恶,直到现代主义运动兴起,设计与装饰彻底划清界限。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装饰随着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兴起,重新成为设计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当代设计理论认为,装饰艺术是整个现代艺术发展的动力,是艺术变革的主要力量,而装饰的尺度问题,始终都是设计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装饰始终不可或缺?Kent Brown所说的“自然憎恶直线”,自有其深刻的浪漫主义基础。人类总是在理性与反理性的两个极端中摇摆,而反理性一向都以自然为旗帜。从思想的直接表征——语言文字,到经过曲折外化的表征——艺术与生活方式,总归逃不脱物极必反,来回反复循环的宿命。像是一具老式钟摆,在这个单摆的扫荡里,今天的我们,面对着盛行的后现代主义,似乎又扫到了倾向于变化与装饰的那一半振域了。而处于这一半振域的人,当被问及一个没有多少实用性的形式价值意义何在时,应该怎样回答呢?也许是无法回答的,但人并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人们喜欢装饰,内心受到它的牵引,哪怕仅仅是因为被理性规范太久而产生的反推力,人们仍会坚持自己这样无可解释的价值观。人就是生来喜爱装饰的,而艺术不可能在生活中被干净彻底地与实用剥离,不得不说卢斯高估了现代文明对人类的改造[4]。
所以,设计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装饰,而在于怎样装饰,也就是装饰的尺度和地位。装饰是来自于人类心灵最深处的强烈需求,是不可排除的,犹如人们需要艺术一样。文化人类学者认为:“人类存在一种不能根除的强烈情感,即对于寂寥空间的恐惧和对于空白的一种由压抑而转化生成的填补冲动。”也即是说,装饰是源于人的本能。事实上,装饰对产品而言,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始终没有摆脱装饰对产品的影响,它是无所不在的,只要我们把产品的形式同美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装饰的因素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所谓“纯净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形态的装饰。况且这种形式的美学价值在今天看来也大大打了折扣。装饰既有结构上的功能,也有信息传递的功能和审美方面的功能。我们对历史上任何一种类型的风格进行解读,都不可能将装饰的因素排除在外,因为装饰总是和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存在没有功能的装饰,也不存在没有装饰的功能。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不再拒绝装饰,其主要出发点是对功能的定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物质功能和使用功能。
[1]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1.
[2]郭晶瑜.装饰的密码[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2(2):29.
[3]E.H.贡布里希.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3.
[4]威廉·荷加斯.美的分析[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