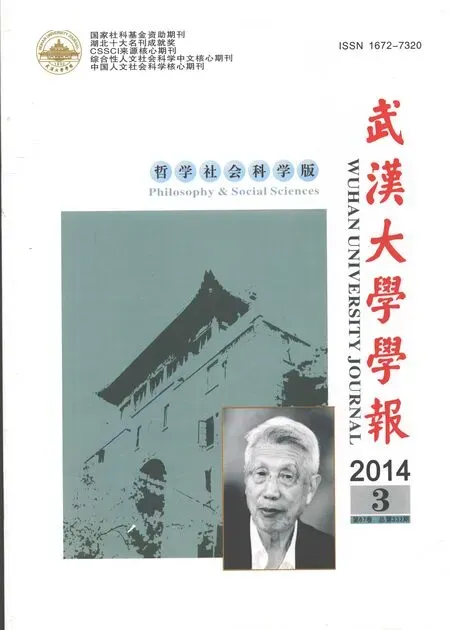《利维坦》中国家主权与个人自我保存权之间的张力
申 林
霍布斯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霍布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利维坦》中,这一著作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正如奥克肖特所言:“《利维坦》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哲学杰作。我们文明史上只有少数几部著作在视野和成就上可与之相比。”(奥克肖特,2003:172)在《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自觉而娴熟地运用科学的方法,从自然人的自然激情和自然理性出发,经过层层推理,推导出利维坦的建立、主权者的权利和职责以及臣民的义务和自由,整个过程具有严密的逻辑。然而,由于霍布斯的利维坦事业过于宏大,其中的因素又非常复杂,所以,百密难免一疏。因而,《利维坦》中也存在着一些逻辑上的悖论,其中国家主权和个人自我保存权这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张力是它的最大困境。
一、国家主权与个人自我保存权之间的张力
《利维坦》一书的政治逻辑很清晰。霍布斯根据对人性和自然权利特点的分析,指出了战争与恐惧是自然状态下人们的必然宿命。人们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追求和平,在自然理性的帮助下发现自然法,但由于缺乏外在力量的保障,自然法无法得到有效遵守,所以,人们仍然生活在战争状态中。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们再次在自然理性的帮助下,相互订立社会契约,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利转让出去,并授予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至高无上的权利,这样就建立了国家。被授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就是主权,拥有主权的人就是主权者,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民。主权者拥有至高无上和不受制约的主权权利,臣民必须服从;臣民拥有自我保存的权利,另外在主权者的法律未加规定的地方都拥有自由,保护臣民自我保存的权利是主权者的基本职责。
然而,《利维坦》整个政治逻辑的两个核心要素——个人自我保存权与国家主权却存在着张力。一方面,主权者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这些权利一旦转化为权力,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权力的专横,进而会侵犯个人的自我保存权。另一方面,臣民拥有近乎绝对的自我保存权,为了自我保存,可以逃避乃至反抗主权者的法律和命令,这势必损毁主权的基础。
这里首先考察利维坦中国家主权对个人自我保存权的损害。国家主权是否会侵害到个人自我保存权,关键在于它的性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专制的权力,还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权力?如果它是专制性的权力,它就会时常侵害到个人自我保存权;如果它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权力,那么它对自我保存权的侵犯就会小得多。
专制权力必然会侵犯到个人权利是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普遍共识。在他们看来,“天使统治人”是政治生活中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①麦迪逊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参见[美]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64页。,政治生活的常态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②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4页。,即使是“理想主义者”和“自由的最忠实维护者”亦不例外③米歇尔斯指出,理想主义者一旦掌权,不可避免地会退化成权力主义者,被裹胁进权力腐败的漩涡中(参见[意]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任君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1页);巴枯宁认为,即使是自由的最忠实的维护者在掌握权力后也会蜕变成暴君(转引自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第176页)。。而且权力由多数人集中行使也并不能避免一人集中行使时的弊端,“173个暴君肯定和一个暴君一样地富有压迫性”(杰斐逊,2011:239)。所以,不受限制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无论把它交到谁的手中都会导致暴政(托克维尔,1988:289)。但《利维坦》中的主权是否是一种专制性权力,学界却存在着较大争论。多数学者认为利维坦是一个专制国家。洛克批评利维坦是一种专制统治,认为它还不如自然状态好(洛克,1964:56-58);卢梭则批评霍布斯关于专制君主可以为其臣民确保国内和平的说法是错误的(卢梭,2003:11);施特劳斯、萨拜因和麦克里兰也都将利维坦主权视为一种专制性权力。施特劳斯指出,“霍布斯的主权学说给拥有主权的君主或人民赋予了不受限制的权利,而令他们随心所欲地置一切法律的或宪法的限制于不顾”(施特劳斯,2003:197);萨拜因指出,在霍布斯这里,“博丹关于限制主权者的宪法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萨拜因,1990:532);麦克利兰指出,“在《利维坦》里,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说为专制政府张目”(麦克利兰,2003:222)。现在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利维坦是专制国家,利维坦中的主权是一种专制性权力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黄裕生的一篇论文,他在此文中对利维坦的专制统治进行了严厉批判。参见黄裕生:《国家为什么不是缔约方?——论霍布斯的国家学说》,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利维坦中的主权者拥有的不是专制性权力。比如德国思想家施米特和英国思想家奥克肖特,他们都有霍布斯研究专著,在他们看来,把利维坦说成是专制国家是一种误解。施米特指出,几个世纪里霍布斯一直被视为是绝对王权的先驱,但霍布斯的国家和法学学说中特有的法制国家因素总是被低估了(施米特,2008:111-113);奥克肖特认为,主权者的统治“不是任意的而是法律的统治。……霍布斯不是一个专制主义论者”(奥克肖特,2003:229-230)。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利维坦视为专制国家⑤王利认为利维坦是绝对主义国家,但不是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参见王利:《国家与正义:利维坦释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汪栋认为,《利维坦》中包含着宪政的成分(参见汪栋:《霍布斯公民科学的宪法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孔新峰认为,霍布斯在主权者权力与臣民自由之间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主权者的权力是有限的(参见孔新峰:《从自然之人到公民:霍布斯政治思想新诠》,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持此种观点论文有:艾克文的《利维坦与现代民主制度》,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吴增定的《霍布斯主权学说初探》,载《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等等。。
本文认为,霍布斯本人并无建立专制制度或为专制政府张目的目的,他只不过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主权,对内消除内乱,对外抵御侵略,提供秩序与和平,确保人们的安全。这从以下几点可以得到证明。首先,专制制度的出发点多是为了维护特定群体的特权统治,但霍布斯建立利维坦并不是为了维护君主或寡头的特权统治,而是为了保护人们的安全,“他为君主制所作的辩护不过是表面文章”(萨拜因,1990:526),主权者的统治地位最终也取决于是否能够保护臣民的安全。其次,专制统治多是任意统治,但霍布斯反对主权者任意统治,主张主权者制定“为人民的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确的法律”,“对各个等级平等施法”,“正确地执行赏罚”。再次,专制统治下臣民缺乏自由,但霍布斯却赋予了利维坦的臣民较多的自由,只要是主权者沉默的地方,臣民就有相应的自由。最后,霍布斯本人也否认自己为专制政府张目。在《利维坦》结尾时,霍布斯说道:“这讨论不偏不倚、不忮不求,除开向人们阐明保护与服从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外别无其他用心。”(霍布斯,1985:261)在《论公民》一书中,霍布斯也提到,自己的著作“不是一个帮派分子的言论,而是一个渴望和平者的言论,他对自己国家眼前的灾难怀着不无道理的忧虑”(霍布斯,2003:致读者的前言第15页)。
然而,尽管霍布斯本人并无建立专制政府的目的,但利维坦本身确实是一个专制政府。《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关于专制政府的含义是:“拥有绝对权力、且不受法律限制和宪法控制、通常是君主制的政府。”(韦农·波格丹诺等,2011:1)利维坦恰好符合这个定义。专制政府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力不受制约,而利维坦的专制性恰恰就在于主权者权力的不受制约。由于“按力建立”的国家通常比“按约建立”的国家更容易实行专制,所以,我们只考察按约建立的国家中主权者的权利即可。
首先,主权者不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霍布斯提到,主权者不受民约法的制约,可以任意废除。虽然霍布斯也提到,主权者应当服从那种超越天地、永恒不变的自然法,但主权者在实际中是否服从自然法则取决于他的良知,而主权者的良知是无法保障的,因为《利维坦》中的主权者并非是《理想国》中的哲学王那样的人物。前面也说过,霍布斯也提到,主权者应当“制定良法”和“平等施法”,但它只是“应当”,仅仅是对主权者的建议,而不是有效限制主权者的制度安排,所以并不是制约主权者的根本办法。
其次,国家机关内部缺乏制约主权者的力量。“以权力约束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为特点的分权制衡是制约政治权力非常重要的途径。洛克和孟德斯鸠都认为,没有分权制衡就没有个人自由。但霍布斯强烈反对分权制衡,认为分权制衡会制造多个主权者,进而引发内乱,并将英国内战归结于此。实际上,分权制衡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内乱,近现代国家的宪政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能解决军队中立化问题,军队不介入不同国家机关的权力争斗,那么分权制衡就不会导致内战。正因为利维坦中缺乏权力制衡,所以就很难限制主权者的权力专横以及由权力专横导致权力滥用,进而就无法有效保障臣民的自我保存权。
再次,社会力量也难以制约主权者。虽然主权者是经过人们的同意而产生的,但正如罗素所言,“在霍布斯的体制中,主权者起初一选定,人民便最后退了场”(罗素,1996:74)。所以,尽管利维坦在建立之时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但利维坦一建立,人民的政治权利就被剥夺了,主权者的独裁取代了人民的民主。霍布斯的意图虽然是打掉那些妨碍主权权威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建立统一的秩序,垄断全部暴力的合法使用,但一旦超过正常的程度,主权秩序就可能演化为主权者的专制统治。
最后,臣民的权利也无法限定主权的边界。贡斯当指出,“主权只是一个有限和相对的存在,……它应当被约束在正义和个人权利所限定的范围之内”(贡斯当,1999:57、63)。但在霍布斯看来,臣民的权利并不能限制主权者,比如那些被洛克以降的自由主义者视为最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在霍布斯看来都是可以侵犯的。霍布斯说道:“臣民的土地私有权是排斥所有其他臣民使用他的土地的一种权利,但却不能排斥主权者。”(霍布斯,1985:193)所以,尽管霍布斯赋予了臣民比较广泛的自由,尽管他也建议主权者不要随意侵犯公民的财产,但这些权利和自由并不能限制主权者。
尽管霍布斯经常使用的是主权者权利(right)而非主权者权力(power)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布斯仅仅将主权者不受制约的政治行为限定在权利上而反对其在权力上的运用。实际上,权利提供的是一种正当性,主权者不受制约的权利(right)为主权者不受制约的权力(power)的运用赋予了正当性,使其在运作时面临更少的障碍。虽然霍布斯在有些地方也将主权者的权力限定在“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但一方面他没有将这一限定贯彻下来,后来将其扩展至“主权者所做的任何事情”;另一方面,即使将其仅限于公共和平与安全方面,但如果在这方面主权者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而为,也必将会制定错误有害的政治决策,这也势必侵害到臣民的个人自我保存权和其他自由。
综上所述,尽管霍布斯没有建立专制政府的目的,但他还是在不经意间使利维坦变成了专制政府。“主权不论是像君主国家那样操于一人之手,还要像平民或贵族国家那样操于一个议会之手,都是人们能想象得到使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霍布斯,1985:161)利维坦中主权者所拥有的不受制约的权利和权力,最终必然会侵犯个人的自我保存权,从而违背了建立国家的初衷。
接下来考察第二个方面。自我保存是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出发点。在利维坦诞生之前的自然状态中,个人的自我保存权是绝对的,自然人为了自我保存,可以“寻求并利用战争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助力”,也就是说可以不择手段地进行自保,包括任意攻击他人。按照常理,利维坦建立后,个人的自我保存权应该保留但同时要受到相应限制,但霍布斯在保留它的同时却没有对此加以应有的限制。自我保存权在利维坦中仍然具有一种近乎绝对的地位。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明确提到,自我保存权是不能交出的:“任何人在按约建立主权时,都不能认为放弃了保全自己人身的权利,一切主权的定约成立,就是为了人身安全。……不抵抗强力的允诺在任何信约中都不能转让任何权利,而且也没有约束力。”因此,“如果有人以武力攻击一个人,要夺去他的生命,他就不能放弃抵抗的权利,……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伤害、枷锁或监禁”(霍布斯,1985:100、106、227)。
霍布斯曾大力宣扬主权者对臣民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他还以《圣经》中大卫杀死乌利亚为例,说明主权者处死无辜臣民尽管违反了自然法的公道,但对臣民并没有构成伤害,只对自然法构成伤害。但这并不代表霍布斯认为主权者可以取消臣民的自我保存权,实际上,在他看来,谁也不能取消臣民的自我保存权,即使主权者也无此项权利。霍布斯说道:“每一个臣民对于权利不能根据信约予以转让的一切事物都具有自由。……如果主权者命令某人(其判决虽然是合乎正义的)把自己杀死、杀伤、弄成残废或对来攻击他的人不予抵抗,……这人就有自由不服从。”(霍布斯,1985:169)这样,霍布斯一方面说主权者可以对臣民任意生杀予夺,另一方面又说臣民拥有不服从乃至抵抗的权利。对于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霍布斯解释道:“允许他杀我,并不等于说在他命令我的时候我就有义务要杀死自己。‘你可以任意杀我或我的朋友’这句话所指的是一回事,‘我将杀死自己或我的朋友’所指的又是另一回事。”(霍布斯,1985:169)这样一来,霍布斯就赋予了臣民不服从乃至反抗主权者的权利。“当我们拒绝服从就会使建立主权的目的无法达到时,我们便没有自由拒绝,否则就有自由拒绝。”(霍布斯,1985:169)
在霍布斯的上述论述中,臣民的自我保存权并没有超出应有的范围。但霍布斯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以致使臣民的自我保存权越过了正当的限度,这主要体现在霍布斯赋予了臣民反抗法律乃至公正法律的权利。霍布斯说道:“如果有一大群人……犯了死罪、人人自知必将因此而丧生,那么这时他们是不是有自由联合起来互相协助、互相防卫呢?当然有,因为他们只是保卫自己的生命,这一点不论有罪没罪的人都同样可以做。”(霍布斯,1985:170)从霍布斯上述言论再加上前面所说的自我保存权“也适用于伤害、枷锁或监禁”这两句话中,我们可以推出下列情形:如果臣民犯了罪,即使主权者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也不管是不是死罪,当主权者派人来逮捕他们时,他们仍然具有联合起来武力抗拒乃至杀死逮捕者的权利;当主权者派人把他们囚禁起来时,他们有联合起来杀死狱卒越狱的权利。尽管霍布斯强调人们的联合不能以推翻政府为目标,也不能以维护其他公民的权益为目标,而只能以自保为目标,但如此作为,就是在引导那些犯了罪的人对抗法律,就是在践踏法律和破坏社会秩序,还会引发其他人的效仿,如此一来,它虽很难推翻利维坦,但却在不断侵蚀着利维坦的基础。
此外,在对外方面,霍布斯在一定程度上还赋予臣民可以不服兵役或战场逃跑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要受到某种限制。霍布斯说道:“一个人如果奉命当兵杀敌而予以拒绝时,主权者虽然有充分的权利把他处死,但在许多情形下他却可以拒绝而不为不义。……同样,两军交锋时,一方或双方都有逃亡的事情,如果逃亡不是出自叛逆而是出自恐惧,那就不能认为是不义的行为。”(霍布斯,1985:170)虽然霍布斯紧接着又做了补充,对逃避服兵役和逃避战斗做了主体和时机上的限制——应募入伍、领受粮饷的人不得逃避,国家防卫有要求时不得逃避,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教导人们,为了自我保存可以对保卫利维坦不尽义务。由于有了两重限制,它的危害不至于像对抗法律那么严重,但也不利于利维坦的防御。如果说前者是从积极作为的意义上损毁利维坦,后者就是从消极不作为的意义上损毁利维坦。
二、国家主权与个人自我保存权张力的症结所在及启迪意义
在《利维坦》明晰的整体逻辑中之所以会出现国家主权和个人自我保存权之间张力这样的逻辑问题,其症结在于:一方面,霍布斯没有区分主权和治权,将主权的至高无上等同于治权的不受限制;另一方面,霍布斯在个人自我保存权的问题上,没有区分好自然权利与法律权利。
主权和治权是不相同的,主权强调的是最高政治权力的归属,而治权强调的是最高政治权力的行使。霍布斯前后的不少思想家都对主权和治权进行了区分。博丹是主权理论的奠基者,他的主权理论中就包含着主权和治权的区分。博丹说道:“如果人民选择一个或几个公民,给他们绝对的权力来治理国家,自由统治,不必受到他人否决权的约束,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裁判再受到任何申诉,……然而,我认为他们并不拥有主权,因为他们只是被信任而在特定时期行使权力的受托人。”(博丹,2008:31)霍布斯之后的洛克和卢梭也都区分了主权和治权。洛克把主权交给人民,而把治权交给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卢梭把主权和治权中的立法权都交给人民,把治权中的行政权交给政府。由于主权和治权之间的区分,主权的至高无上就与治权的不受限制相脱离了,因而主权至高无上并不意味着治权不受制约。
霍布斯的失误就在没有区分主权和治权。霍布斯在论述人们订立社会契约向主权者进行授权时指出:“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承当这一人格的人就称为主权者,并被说成是具有主权,其余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臣民。”(霍布斯,1985:131-132)霍布斯的这段话包含两个主体,一是“这一人格”,二是“承担这一人格的人”。但霍布斯并没有将“这一人格”也就是抽象意义上的全体人民视为主权者,而是将“承担这一人格的人”也就是“某一个人或一个多人组成的集体”视为主权者,并将“主权”赋予他。霍布斯本应当将“这一人格”亦即抽象意义的全体人民视为主权者,将主权交付于它,并将权力的实际运用委托授权给“承担这一人格的人”,让他行使治权。这样一来,至高无上和不受制约的只是不会转化成实际运作权力的抽象意义上的全体人民的权利,而不是转化为实际权力运作的受委托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权力。这样,它就能严格限制在“权利”领域中,而不会转化成政治权力,从而就能避免权力的专横。
遗憾的是,霍布斯对此并没有做出应有区分。由于这些“承担这一人格的人”既是主权者,又是治权者,所以,他们手中的抽象的主权权利很容易转化为具体的治权权力,至高无上和不受制约的主权权利转变为治权之后,就成了一种绝对的、不受控制的专制权力。因而,霍布斯在不经意间使利维坦成了具有强烈专制色彩的国家。
如果霍布斯对主权和治权进行应有的区分,把抽象意义上的全体人民视为主权者,霍布斯关于主权权利的论述就是非常正确的了。首先,在一个国家中,抽象意义上的全体人民就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宪法和法律不过是他们的意志而已,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制定、修改、废止和恢复法律。抽象意义的全体人民的权利高于任何个人、团体和机构的权利。其次,在一个国家中,抽象意义的全体人民所掌握的主权也应当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全体人民的主权权利不能转让给其中的某些公民,这样就会导致少数人的专制,更不能将它转让给外国人,这可能会导致国家的不复存在。全体人民的主权权利也不能分割,不能将一部分权利交给部分人民,再将另一部分权利交给另一部分人民,或再分出一部分权利交给其他人民,这样,国家就无法统一。
霍布斯对主权和治权的未作区分还导致他对政治统治理解的失误。由于他只关注主权自身的效能而忽视治权的不同行使会产生的不同后果,所以在他看来,“一切政府形式中的权力,只要完整到足以保障臣民,便全都是一样的”(霍布斯,1985:141)。正如萨拜因所说,“对他来说,除了在绝对权力和完全无政府状态之间、在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和无社会之间加以选择之外,别无其他可供选择”(萨拜因,1990:529)。这种认识所导致的结果是,“它蕴含了对于区分好的和坏的制度的可能性的否定,以及对混合制度和法治的可能性的否定”(施特劳斯,2003:196)。难怪霍布斯认为自由城市路迦城并不比君主专制统治的君士坦丁堡有更多的个人自由。
霍布斯的另一个失误就是在个人自我保存权的问题上忽视了自然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区分。应当承认,在整体的意义上,霍布斯对于自然权利和法律权利还是做了明确的区分。霍布斯把自然状态下人们所拥有的对一切事物的权利称之为自然权利,而把国家状态中未有法律禁止的臣民行动空间称之为法律自由:“臣民的自由只有在主权者未对其行为加以规定的事物中才存在”(霍布斯,1985:165)。尽管法律权利和法律自由的概念并不相同,但霍布斯在同等的意义上使用它们,“权利就是自由,也就是民约法留给我们的自由”(霍布斯,1985:225)。但是,在个人自我保存的问题上,霍布斯却混淆了法律权利与自然权利的区别。在自然状态中,由于缺乏一个共同权力的呵护,所以,人们在面对他人的侵犯与伤害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进行自卫。在国家状态中,面对他人对自己的不法侵害,在国家权力未能及时对个人加以保护时,个人也有正当防卫对不法伤害者进行还击的权利。但在国家状态中,面对法律判决特别是公正的法律判决,如果罪犯加以抵抗拒不接受惩罚,那就不具有正当性,因而也不能成为一项权利。但是,霍布斯却把它视为一项权利。这实际上是把自然权利给直接移植过来,忽视了自然状态与国家状态的区别以及在这两种不同的状态下人们权利的区别。霍布斯本人也讲到,在自然状态中,缺乏共同权力,而“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没有国家存在的地方就没有不义的事情存在”(霍布斯,1985:96、109)。但在国家状态中,由于有了共同权力,所以也就有了正义与否、正当性与否的区分,也就有了权利和非权利的区分,只有正当性的行为才应当被法律规定为权利,非正当性的行为就不应当被法律规定为权利。抵抗乃至武力抗拒公正的法律判决乃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根本不应当成为法律权利,而霍布斯的失误就在于此。虽然霍布斯也极力教导臣民不要受古希腊和古罗马著作家说教的影响,要服从主权者,但由于把自我保存权推向绝对化,这就使得这种教导很难发挥作用。
霍布斯在主权理论和个人自我保存权理论上的得失对于理解政治生活颇有启迪意义:
首先,霍布斯主权理论的得失对于理解人民和宪法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人民与宪法的关系可以从制宪权和宪定权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从制宪权的角度看,人民高于宪法,因为宪法不过是作为主权者的全体人民意志的产物,人民有权制定、修改、废止和恢复;从宪定权的角度看,不再存在全体人民这一抽象主体,而是组成它的一个又一个的人,作为人民这个群体构成的一分子,每个公民以及被全体人民委托具体行使政治权力的人和机构都要遵守宪法,任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机构都没有超越宪法的特权,从这种意义上看,宪法又是至高无上的。总之,人民只有在作为主权者时高于宪法,而作为公民和治权者时则要服从于宪法。所以,不能笼统地讲到底是人民高于宪法还是宪法高于人民,关键看在什么层次上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次,霍布斯个人自我保存权理论的得失对于理解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边界颇有助益。在政治生活中,公民权利是第一位的,政治权力是第二位的,所以,政治权力首先应当受到限制,使其不至于危及到公民权利。宪政是限制政治权力的有效政制安排,是保障公民权利与个人自由的根本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尽管公民权利优先于政治权力,但它也不是绝对和无限的,也应当受到限制。其一,如果公民的某些权利不受限制,就可能侵犯其他方面的权利。政治生活中存在多重价值,因而就有了多种权利,这些权利之间要保持某种平衡。尽管某些权利是人们生存的最基本权利,在价值序列上优于其他权利,在政治生活中应当优先考虑,但其他权利亦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所必需,如果此项权利的边界过大,它就可能会侵犯其他方面的权利,并最终损害人们的根本利益。其二,如果某些公民权利不受限制,很可能会侵犯其他公民的同种权利及其他权利。权利实际上是一种行动空间,由于在社会中公民的行动空间是特定的,所以某些公民的行动空间过大,必然会挤压其他公民的行动空间,这样就会侵犯到其他公民的权利。其三,如果公民某些权利不受限制,就有可能削弱政治权力的效能。尽管政治权力只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手段,但如果手段发生故障,目的的实现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公民某些权利边界过大,很可能会影响到政治权力的正常行使,反而影响其维护公民权利的效能。
[1] 艾克文(2010).利维坦与现代民主制度.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2] [英]奥克肖特(2003).《利维坦》导读.应星译.现代政治与自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 [法]博丹(2008).主权论.李卫海、钱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 [英]韦农·波格丹诺等(2011).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 [法]贡斯当(1999).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6] [美]汉密尔顿、麦迪逊等(1980).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 [英]霍布斯(1985).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8] [英]霍布斯(2003).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9] 黄裕生(2012).国家为什么不是缔约方?——论霍布斯的国家学说.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10] [美]杰斐逊(2011).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1] 孔新峰(2011).从自然之人到公民:霍布斯政治思想新诠.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2] [英]罗素(1996).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3] [法]卢梭(2003).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4] [英]洛克(1964).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5] [美]麦克利兰(2003).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6] [法]孟德斯鸠(1959).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7] [意]米歇尔斯(2003).寡头统治铁律.任君锋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8] [法]托克维尔(1988).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 [美]萨拜因(1990).政治学说史(下).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 [德]施米特(2008).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美]施特劳斯(2003).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
[22] 吴增定(2007).霍布斯主权学说初探.天津社会科学,5.
[23] 王 利(2008).国家与正义:利维坦释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4] 汪 栋(2010).霍布斯公民科学的宪法原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