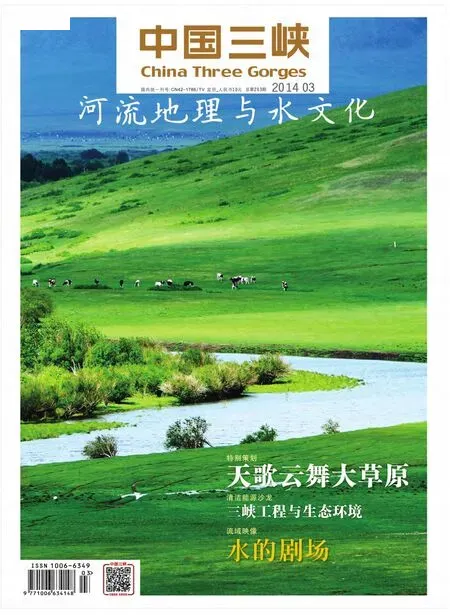看山看水到永嘉
——楠溪江纪略
看山看水到永嘉
——楠溪江纪略
文/邹汉明 编辑/柳向阳


楠溪江边的古村落屿北村。 摄影/邹汉明
到永嘉第三天,获赠《永嘉县志》一部,清光绪间永嘉知县张宝琳延聘黄棻、戴咸弼(此公嘉善人,算我的半个同乡)等纂修,中华书局二〇一〇年标点出版的一个新版本。煌煌三大册,提在手上沉甸甸的。装帧也不错,心里喜滋滋的。旧志,原刻本早已绝迹。影印本当然好,但不多见。其实我也不讲究版本,时间上只要民国以前纂修,都喜欢。
到一个山水清明、人文蔚盛的地方翻阅旧志,是近年我乐此不疲的一桩美事。
回瓯江边的梦江大酒店。找《永嘉县志·舆地纪志·叙水》一节。永嘉之水,支分派别,尽在其中了。赫赫有名的楠溪,当然也流在清季文人的笔端:
楠溪,在城北十五里。(《方舆纪要》、嘉靖《志》俱作十里)。源出天台、仙居诸山,有大源、小源从东南流入界,与本邑仙居乡之李、樟、蓬三溪,清通乡之小、藤、珍、欓四溪,贤宰乡之罗溪,共八溪合流,而南至潮漈,逶迤三百余里,入永宁江为楠溪港,盖合北境四乡诸水,源远流长,下通潮汐,俗称北港……
旧志里的楠溪即现在众口传诵的楠溪江。“江”字是旅游业勃兴后所添加。楠溪多出一个“江”字后缀,古楠溪一变而为今楠溪江,却也开始浩淼和雄阔起来,叫法上还特别地松口爽亮,很遂了现代人的一般心意。旅游业的策划和营销有时还真有灵感一现的笔力。今日楠溪江响当当的名声,怕真的与这个外加的“江”字有关呢。当然,楠溪乃江乡之源,它完全担当得起“楠溪江”这一新的称谓。楠溪本就不是小溪,晚清《永嘉县志》不惮其繁列出流入楠溪的八条溪水,可谓明证。兹胪列如次:
珍溪在城北二百里清通乡四十一都。
水出双坑,入楠溪。
欓溪在城北二百里清通乡四十二都。
水出杨坑,入楠溪。
滕溪在城北清通乡四十四都。水出大若岩,入楠溪。
小溪在清通乡四十六都。水出界坑,入楠溪。
樟溪在仙居乡五十二都。水出双坑,入楠溪。
蓬溪在仙居乡五十都。水出西坑,入楠溪。
李溪在城北三百里仙居乡。水出菰田,入楠溪。
罗溪在城北三十五都贤宰乡。入楠溪。
真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楠溪江逶迤三百里,沿途合八溪之水,终于成就它大一统的规制。可以说,是大自然千般万般的宠爱,托举了楠溪江的不凡;也是楠溪江开放的胸襟,让它在永嘉的山水中孤峰独绝,开辟出一道清流来。遥想在某个丰沛的雨季,八水合成一水,八个声响混成一个声响,八份汹涌搅成一份汹涌,楠溪江如一条神气活现的龙,腾蛇竞雾,浩浩汤汤,奔腾而来。其声势,动太阳而移星群。而每到枯水季节,溪水骤减,江中的汀州一一显露,圆滚滚的鹅卵石一粒一粒浮出水面。白色的河床呼应着蓝色天空,八水如兄弟般默默献出自身的细流,以大自然固有的谦逊来成就它。今日楠溪江,其声汩汩,其水流碧;无须万钧雷霆,也不必乾坤日夜浮了,一路但有虫声相送,星月牵伴,峰峦和古树照应,溪流将丝丝入扣地、散漫地、笃悠悠地流入中下游的田家村舍、匹夫匹妇的心以及从这个基数庞大的群体中提升出来的士大夫的灵魂——南渡以来永嘉人文,是与这条溪流慈母般的滋润、哺育有关的。

楠溪江边的苍坡古村,背景之山即笔架山。 摄影/邹汉明
合上旧志,深深吸纳一口油墨的清香,是该去楠溪江实地踏访的时候了。
此站,叫青龙湖。此岸,是山野人家。此时正是获月,新打的稻谷摊晒在水泥场地上,一片金黄。我暗想,这白净的米粒穿了衣服的时候,实在也有一股浩大的富贵气——即使生在如此僻静的山乡,竟也不减半分。太阳照射下的这一地金黄,我眼光一扫,顿生欢喜,似乎还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太阳味道。旁边是一只肥犬,懒洋洋地打着盹。它对于突然而来的我等城里人,不管不顾,头都懒得回。这毛色油亮的土狗,看得出,见过世面了。往下走几步,清风徐来,水声也一并送了过来——青龙湖的渡口已到。忽听得一阵捣衣声,不知怎地,心头油然而冒出两句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呀!这是真正的捣衣声,一记一记又一记,敲打在魂灵上头。但见村妇一人,先拿湿漉漉的衣服往洗衣板上搓洗,接着拿起一截木棍,尽力捣打。笨拙、厚重的捣衣声就是这样响起来的。可以说,大唐天宝年间李白在长安听到和看到的此声此景,悠悠千载,迄于今日,仍是这声音,仍是这朴实的姿势。文明的递进,有些东西其实不需要更改,比如楠溪江边这淳朴的人性,比如眼前这翡翠般湛蓝的楠溪江水,又比如山间尖新的太阳光和略带甜味的空气。还有,晒场上这黄灿灿的稻谷……一念及此,早几年熟稔于心的米沃什的一首诗突然有了新的领悟:
当月亮升起来,穿花衣的妇女漫步时
我被她们的眼睛、睫毛、和世界的整个安排打动了
依我看,从这样一种强烈的相互吸引里
终归会流出最后的真理
我相信真理是朴素的,就应该在这具有太古气息的原野上流出。
楠溪江在此转了一个弯。此弯如月牙。亿万斯年的楠溪水是尽力又尽职的搬运工。丰盈的激流在不远处冲积成一道滩涂。秋季,水落而石出。滚满一地的鹅卵石缝隙里,长出了细长的青草和芦苇,生机尽现。湖波上,还有白鹭贴着水面飞,间或立足于这一片新生的滩涂,像极了一个古遗民。
我们要到对岸去。摆了渡过去。对岸,是尚在整修中的青龙湖山庄。有妇人正以土法酿酒。米香与酒药味正好拌和了,略带一股酒酸味。料想不数日后,酒家将有一大缸混沌的土酿醇香扑鼻,不禁嘴馋。
山庄里出来,沿着溪边一稻田转去青龙湖中央的龙头岩。不看不知道,一看,满心欢喜。攀援而上,汩汩楠溪江尽收眼底。龙头岩如摆放在楠溪江中央一张巨大无比的凳子,坐在这样的一张石凳子上,幕天席地,还临水,还可以打坐,谈禅……还可以饮一口村妇自酿的土酒。另有山风、溪声,皎洁的明月相伴,那是何等的福气!回想刚才有人说山庄里可以开文学笔会的闲话,我忽发奇想:春暖花开的时节,或者八月中秋之夜,很可以在这里办一个文学讲座的。当然啦,讲座的人要有真本事,所传之道必得令湖中听讲的鱼虾跳出水面来点个头,那,讲座才算成功哩。否则,岂非怠慢了清风明月下这世间少有的湖光山色。
楠溪江漂流,在我这是第二次。江上漂流大概是搞了很久的一个项目了。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林斤澜老领着汪曾祺等一帮同好来永嘉大饱真山水的眼福,就有这漂流。而且那次,汪老的记录是漂了三个多小时,真正令人羡煞。记得我第一次来,漂到最后,终于耐不住碧青青溪水的诱惑,便扑通一声跳到了清澈无比的激流里。所以,那次漂流的最后一段水,我实际上是与水融为一体后游完的。
这次照例是坐竹筏,但我脱了鞋子,放出一双久在樊笼里的大脚,让细腻的水流和缓地流过脚板——这实在是太过于美妙的感觉。
竹筏高翘着一头,在船老大的把持下,顺水而下。有时遇到激流,噗噗有声,洁白的水滴珠玉般地从筏子的缝隙里跳将出来,挨到你身上。须知,单个的小水珠总归是调皮的,不像抱成巨大的一条怒江,肆意横行,令人恐惧。
这是一段绝美的水程,也是一段绝美的山路。流水山转。山是眉峰皱,水是眼波横,两者同为美人的脸部特写。两岸的山峰都不高,山体平缓舒展,如伸开邀约的一个长长的怀抱。楠溪江多滩涂,此处容我移用汪曾祺老的文字。汪老的感觉自非一般,他写楠溪江:“滩林很美,但很谦虚,但将一片绿,迎送往来人,甘心作为楠溪江的配村,绝不突出自己。似乎总在对人说:‘别看我,看江!’”
不仅看江,还要将身体的一小部分浸淫在江中,似乎那才对得起这条江的清澈和盛情。我一边与江水亲近,一边几乎要吟唱出声来:楠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

瓯江,对面即温州。 摄影/邹汉明
除了看江看山,当然也要看一看古村落。屿北、苍坡、芙蓉这些古村落,如今很像楠溪江伸开长长手臂摆放着的一只只青花小碗。精致,婉约,也很容易碎裂。那青花小碗上面的花纹,如同今人喟叹的永嘉文化。中国的瓷器,世界第一,实用而兼具审美,但也很容易碎。因此,它们需要格外地加以珍藏和保护。当它们逼人的美丽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时候,遵循小心轻放的原则,总是没有错的。珍贵楠溪江,应作如是观。
山水,是大自然的骨肉。它们是连为一体的。三百五十年前,我的乡先辈、有清一代文宗朱彝尊(竹垞)避难永嘉,寻山问水,写下“我欲看山到永嘉”的诗句。竹垞被称为谢灵运后最重要的永嘉山水知己。他的《永嘉杂诗二十首》,我一路读来,至为亲切。竹垞是领略了楠溪水美的大诗人。《永嘉县志》“楠溪”条目下,附有朱彝尊的《雨渡永嘉夜入楠溪》诗,可以一证。
竹垞说,我欲看山到永嘉;我说,看水还是要来永嘉的。看山而不见水,一定少了美目顾盼的灵性。何况我看到的这段水,好像仍旧是从谢太守的山水诗、金风亭长(朱彝尊号)的杂诗中剀切而细腻地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