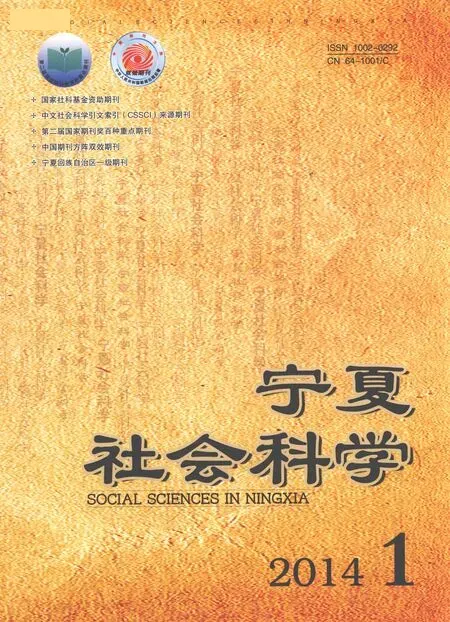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
朱丽娅,雍少宏
(1.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2.宁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一、引 言
在价值哲学理论中,价值结构是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价值结构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准则评判体系。在价值结构理论中,舍勒的“四等级价值样式说”是最有影响的理论。舍勒按照价值的持久性、共享性、独立性和体验性,将人类价值分为感觉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四类价值,并认为人类价值结构是秩序性排列关系的价值等级[1]。
社会实践活动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评价标准,因而,价值结构具有民族差异性,也即不同民族所依赖的资源和条件对其生存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差异,会导致调节社会关系的价值结构相殊,从而形成不同的价值文化。在人类早期实践活动中,中国内陆农耕生产活动和西欧海洋水业及贸易活动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结构。随着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领域的扩大,不同民族交往以及社会关系的同构,不同价值评判标准也会发生交流、碰撞,从而使各自的价值结构发生嬗变,最终形成具有相对普世的价值结构。
中国正处于快速社会转型期,也是新旧价值标准交替之际,在旧的价值标准被打破之后,新的价值标准尚未形成的过程中,会形成“价值缺位”从而造成“价值混乱”现象[2]41。要治理这种价值混乱现象,必须厘清原有价值结构以及我们希望达到的社会样式所具有的价值结构的特征。中国原有价值结构就是影响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儒家“义—利”价值结构,我们希望达到的社会样式就是参照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建立的具有中国特征的现代化社会价值结构。西方以“财富”为核心而形成的价值结构与中国儒家“义—利”价值结构是不完全相同的两种价值体系,对东西方价值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对构建新型的具有中国特征的现代化社会价值结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中国传统儒学的“义—利”价值结构
对中国人思想和心理影响最广泛、深入和持久的莫过于儒家文化或儒教,伦理道德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自孔子以“仁”和“礼”为元维度建构人的内在美德修养和外在规范维护的伦理道德结构后,中国历代儒学家不断对其进行深化、扩充。孟子首创性善论,将孔子的“仁”扩充为“仁义”,并以此为最高的道德规范;荀子则以性恶论发展了孔子“礼义”的思想,主张“法以定分”、“礼以定伦”,将“礼”进一步推及为等级制度;董仲舒更明确提出“三纲五常”、“重义轻利”的伦理学说,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构成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道德的完整体系;程(颐)朱(熹)学派则将纲常礼教推崇到“天理”的高度,提倡“存天理,去人欲”,高呼“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3]193-195。儒家文化既符合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又符合封建社会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因而被统治者们奉为官学而大力推广、普及,成为主流价值信仰。在这种主导价值理念下,经济政策实行重农抑商,排斥商品生产、交换和消费。历代统治者的经济政策一般均采用奖励垦荒、轻徭薄赋、限制土地恶性兼并、兴修水利等措施扶植农业,而对“末务者”则采取课以重税甚至种种人身侮辱的方式来抑制打击工商业的发展。
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观以农贵商贱为主流,在这种主流价值观中,又可分为重农轻商和重农抑商两种观点。重农轻商以商为农济为立论,以农为本商为末,将商业作为农业的补充和辅助,为农业生产提供有限的物资,为务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要去饰存朴,去巧存实。“百工者,所使备器也。器以便事为善,以胶固为上。商贾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为要,以坚固为资。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王符:《潜夫论》卷一《务本》)重农轻商虽有轻重之别,但也有并举之意,重农抑商则完全排斥、压制商业,视商业为游业,商人为浮食之人,不生产粮食,而以淫巧奇异逐利趋华,诱民好逸恶劳,导致伤民败俗、贫邦乱道。“游业末事,以收民利,此贫邦之原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王符,《潜夫论》卷一《务本》)“工商逐末者,重租税以困辱之。民见末业之无用,而又为纠罚困辱,不得不趋田亩,田亩辟则民无饥也。”(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三《风俗》)
影响中国长达几千年的“重农贱商”经济价值观的根源来自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伦理思想。在孔子“义”和“利”的价值格局中,“义”和“仁、礼、智、信”共同构成了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和人的道德修养结构。孟子将“义”确定为“羞恶之心”。韩非子则将“义”划分为四个维度:“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义,贱敬贵义,知交朋友之相助也义,亲者内外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韩非子·解老》)管子进一步将“义”扩充为七个维度。“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戮;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谐辑睦,以备寇戎。”(《管子·五辅》)由此可见,“义”即社会公义和做人的道义,也就是做人做事的社会准则和道理,是最高的社会价值。墨子讲“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就连主张法礼分伦的荀子也将义置于最高的社会精神位置,“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孟子更是鲜明提出“舍生取义”。君子是展现“义”的主体,何谓君子,“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可见君子就是“务治”之人,遵守礼义、治国安邦是君子的职责。君子在治理和管理万物的过程中,不但要统一法度、礼节,还要申明其中的“义”——道理、准则,并贯穿到各种活动之中,教化民众遵法守礼。君子在治理经济这一国计民生的事务中,道义自然是题中之意。
第一强国之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忧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所以,“君之所务者五: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益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管子·立政第四·五事》)。君子教化人民按自然规律的时令节气垦殖稼穑、勤劳守分,则会五谷丰登,仓廪充实,是国泰民安的基本路径和义理。粮食是国强之关键,务农是粮食之根本。治理国家的君子主要职责就是劝农、教农、励农。如“故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吕氏春秋·上农》);“善为国者,其教民者也,皆作壹而得官爵……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商君书·农战》);“使民无得善从,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夫民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帅先天下”(《宋书》卷一四《礼志一》);“是以先王敬授民时,劝课农桑,省游食之人,减徭役之费,则仓廪充实,颂声作矣。虽有戎马之兴,水旱之沴,国未尝有忧,民终为无害也”(刘勰:《刘子》卷二)。因此,“夫耕籍之义大矣哉!粢盛由之而兴,礼节因之以著,……孝悌力田赐爵一级。预耕之司,克日劳酒”(《梁书》卷三)。人们依附于土地也是实现“忠人和”的基本条件,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只有常年厮守、共同劳作才能亲亲、孝悌,才能实现完成儒家“纲常礼教”——这一人和的最高道德理想。经商者必常年游离于土地和家庭之外,不但难以尽忠尽孝,还可能为利益而去竞争,利令智昏,破坏社会的人伦道德秩序。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轻商、贱商、抑商也是“道义”的诉求。
第二安国之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民朴易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吕氏春秋·上农》)。那么,怎样才算民朴哪?“莅之以清心,镇之以无欲,勖之以弗倦,翼之以廉谨,舍日计之小成,期远致于莫岁,则浇薄自淳,心化有渐矣。”(《宋书》卷五二,列传十二)可见,民朴是影响国家安定的“大义”,只有固守土地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才具有“质朴”的品质。质朴的心理结构包括清心、无欲、勤绩、廉谨、期远。治理国家的君子就是要采取措施促使人民形成质朴的人格品质,“复朴素而禁巧伪”。“民富知礼”是儒家治国安邦的主要思想。首先,追求生活富足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天有时,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与天下共者,仁也。”(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二《册林·立制度》)其次,“富”要符合社会伦理价值,“富”按伦理体系划分为三个品级,“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民富的标志是“仓廪实、衣食足”。富民的实用标准就是农业产出成果。“故建国者必务田桑之实,弃美丽之华,以谷帛为珍宝,比珠玉于粪土。何也?珠玉止于虚玩,而谷帛有实用也。”(刘勰:《刘子》卷二)再次,富民是国家安定的基本条件。“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汉书》卷二四,贾谊:《论积储疏》)同时也是实现“礼治”的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因此,“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扈乡轻家,扈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
第三治国之道义在于蓄储俭用。中国历代学者的主导经济观将垦殖博收始终放在社会管理最重要的位置上,同时储备粮食也是最主要的政治,是治理国家的“大义”。“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汉书》卷二四,贾谊:《论积贮疏》)。“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故先王治国,有九年之储,可以备非常救灾厄也。尧汤之时,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载大旱,不闻饥馑相望,捐弃沟壑者,蓄积多故也。”(刘勰:《刘子》卷二)在广积蓄的基础上,还要人们特别是贵族阶层要以“义”为入,节俭省用。“道义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财货可保,因以兴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旧唐书》卷一三五)所以“王者不殖货利,不言有无。耗羡之财,不入于府库;析毫之计,不行于朝廷者,虑其利穴开而罪梯构。……节欲于中,人斯利矣,省用于外,人斯富矣。……是以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之产,不重非衣食之货,不用计数之吏,不畜聚敛之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三《策林·不夺人利》)。“若不节之以数,用之以伦。则地利屈于僭奢,人财消于嗜欲。而贫困冻馁,奸邪盗贼,尽生于此矣。……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三《策林·立制度》)
综上所述,“义”是儒家文化赋予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统领一切事务的指导思想,政治统治以“仁”为义,社会秩序以“礼”为义,人际交往以“信”为义,教育学习以“智”为义,经济活动以“农”为义等。儒家文化之所以被历代社会推拥为最高的思想工具,就在于其建构的以“义”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体系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和功能。“重农轻商”的经济价值观是其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环节。为了社会稳定而主张将人们的活动限制于固定的地方,依附于土地,清心寡欲,重礼轻利,以勤劳生产更多的农产品来体现欲望的满足,以获取“实财”(粟、帛、畜等)为荣,以攫取“浮财”(钱币、饰品等)为耻,从而实现国泰民安的社会“大义”。在义的价值结构中,“利”是“义”的对立面,逐利必然会去义,多利必然寡义,二者无法统一,商人就被冠以“奸商”、“小人”的污名,与“奸臣”、“佞吏”相提并论,同为社会所唾弃、羞辱的对象。由于工商业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被统治思想置于边缘地位,在现实制度中受到制约、压制,其活动就十分微弱,从而也就难以纳入理论家、思想家的研究视野,反过来也就难以形成指导工商业活动的理论思想和制度规范,在长达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虽然商业活动一直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从未停止过,但与政治文明、军事文明、道德文明等光辉灿烂的社会文化相比,中国并未形成完整而鲜明的商业文明。具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指导人们通过商业获取财富的价值观,缺乏指导工商业活动的制度规范,无论是习惯法还是成文法都很少见,更没有财富社会责任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华文明中的商业文化是一种羸弱状态。
三、西方新教伦理的“财富”价值结构
宗教基本上是一种交易的关系[4]35。人们通过对神的崇拜(祭祀、祷告等仪式)来交换神对人的保佑、庇护或灵魂的拯救。西方人普遍信奉的基督教教义,是由马丁·路德的“西方文明史上最灿烂的明灯之一”的新神学思想点燃,后经约翰·加尔文系统完善而成的《基督教原理》阐释的“因信称义”上帝“预定论”新观点,并以此为思想基础而制定建立的一个良好社会秩序的宗教纪律和规范。新教伦理既具有基督教控欲主义的教规,如严禁赌博、酗酒、生活奢侈、豪华宴会等,又将上帝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人们对上帝的笃诚信仰,不一定表现为远离现实进行修道院式的苦行修炼,也不一定表现为各种形式化的赎罪方式,而更多的应体现在个人日常生活和自己事业中的行为,用在职业劳动和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施展才干、奋发有为回报“真实的、公义的、仁慈的”上帝的恩典。因此,恩典、信仰和善功是西方人神往“上帝”、经营人生而难以分割的宗教心理核心元素[5]389-409。韦伯通过对不同宗教伦理的研究,发现新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吻合,新教伦理的价值观符合资本主义的职业观:上帝拣选的“预定论”让人获得财富,通过全心全意营运生财来富裕自己,以填补人所感到的不足,也是获得救赎的一种美好信号——“归荣光与上帝”;职业劳动是“由上帝安排的工作”,是教徒们必须承担的、不容懈怠地去圆满完成的义务,因而人们应毫不犹豫地去挣钱,以“增添上帝的荣耀”,同时也会使宗教兴旺发达。新教伦理为新教徒形成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心理上”的理论依据[6]485,再加上遍布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带来的人文和科学的繁荣所提供的社会条件,为进行资本主义经营所依托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建立大开方便之门。在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营运过程中,各种商业交换制度也就相应建立和完善,且日益精细化。韦伯在探讨西欧商业合伙史中,发现西欧最初的商业合伙形式——“索塞特”、“康曼达”等以单边合伙和连带责任制度为规则,后来逐步发展为多边合伙——普通合伙以有限责任制度为规则,并以法律条款加以规范,如《罗马法》等许多地中海沿岸商业活动繁荣的地区中世纪就已形成许多商业法[7]20。更为重要的是还形成了商业社会组织,如西欧起源于乡村作坊和专业户自愿联合形成的基尔特(行业公会)组织,在工商业拥有强有力的合法权力。为了保护同业利益,基尔特杜绝行业内自由行动,自相竞争,并对从业者严密监视,强加干涉,不允许侵害消费者利益,引发不平;力求货真价实,公平交易,不许偷工减料和过分得利。对违约欺诈采取严厉制裁。后来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详细的行业条规,并发展为周密的管理技术[8]212。这一较高社会化形式的商业组织形态,培养了人们的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韦伯认为,这是从形成“某种心理”到行为的过程,而行为又是随着资本主义经营的需要,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产生、发展才越来越成熟起来的[6]486。
资本主义是商业高度发展和繁荣的社会形态,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可称之为商本主义社会,交易或交换(包括商品交换和社会交换)是这一社会形态的主要文化特征和人们的行为特征。总结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文化的价值结构,可以得出以下推论:财富观、财富规则、财富责任是商业文化的三个主要元素。
1.财富观。怎样看待财富是财富观的核心问题。怎样看待财富从本质上讲就是怎样看待人的欲望,因为人们获取财富的原始动机就是满足人的欲望,而人的欲望是多样且无尽的,因而人们获取财富的动力也是不竭的。一种文化是否鼓励人们获取财富,往往决定着社会的繁荣程度和活力状况。爱尔维修把欲望看成像人体循环的血液一样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运转,“欲望会鼓动一个国家,唤起它的工业,激起它的商业,扩大它的财富和势力;而这种欲望的停滞,我敢说将会置若干国家于死命”[9]524。斯密在曼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论断的基础上,提出商业社会也即文明社会,人的欲望是整个社会的发动机。正是在欲望的推动下,人们从事经营,深化分工,改进工艺,最终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得到了增长。欲望而生自利,自利而求同情。同情表现了文明社会对公民的情感要求和道德要求,是文明社会的精神动力。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是禁欲主义文化,其对人的欲望的限制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人的行为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中,要求人们通过苦行修炼达到神的世界,是统治者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的需要,同时也导致社会发展进程缓慢。自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改革,特别是新教伦理的价值理念提出后,人们自发响应,人的欲望得以释放,人性自由得到解放,人们获取财富不但得到上帝的认可,而且是为上帝增添荣耀。正是基督教的财富合法性的确立,激发了人们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2.财富获取规则是社会秩序尤其是经济秩序有效运转的可靠保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一种法则,按照这种法则获取利益就会被社会所认可,也就获得了攫取和拥有财富的合法性。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社会秩序的形成有两种方式:生成的秩序和建构的秩序[10]12。生成的秩序是依据自身的信仰、价值理念而派生的行为;建构的秩序是依据社会政治体系而强加于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宗教信仰促使人们产生许多自发行为,为了获得上帝的“拣选”而一丝不苟地完成职业工作;通过开拓创新获得商业机会以赢得更多的财富为上帝增添“荣光”;承担社会责任扶弱济贫以体现上帝“仁慈、博爱”的恩典等。商业活动促使社会将零散的商业习惯法则逐步演化为较为完整的成文法,最终形成既有体系又有细则的商业法规。沃尔夫冈·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主要特征或先决条件划分为三类: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现代资本主义精神[7]35。韦伯则将“理性持久的企业,理性会计学,理性工艺学,理性法,理性精神,生活行为合理化以及理性主义经济伦理”看作是资本主义系列的“显著特征”[7]34。现代资本主义完备的企业制度和商业规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家户商业合伙中的无限连带责任的贸易组织方式,在这种组织方式中,人员组成以家庭成员及其家庭帮工(包括仆人和雇工)和货物代理人(行商)为主,合伙人或者以出资为股份或者以出力为资本,以自发的“信用”为纽带从事着海上和陆地商业活动,家户合伙者之间超越情感而以利益为核心建立起责任和信任关系。后来普通合伙以其更为理性、有效的组织方式得到社会认可和快速发展。普通合伙将家户与商事企业分离,建立商务活动共同基金以及资本清算账目和簿计,合伙人对商务活动承担有限责任,个人资产与合伙资产剥离,并形成了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如出资人一般分得合伙企业所得利润的四分之一等。这一早期的商业合伙形式,培育了人们持久发展企业的意识、计算精神、契约精神、责任明确的观念等规则心理,为“可计算的判决和法律执行”的资本主义组织架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7]73-95。
3.财富责任是人们利用财富满足需要时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模式。人本身具有自利性、物质性,同时还具有社会性和精神性,人是“生物自然物”和“社会同一物”的结合体。“利己”与“利他”是人心理及其行为选择的矛盾统一体。财富是用来满足无限膨胀的个人需要,还是分割出一部分用来满足公共需要,除取决于按社会契约通过缴纳税收建立公共组织建构公共服务体系以满足更广泛的公共需要,还取决于个人的“公益”动机,而文化是个人公益动机的主要来源之一。基督教自新教改革后,对个人欲望的态度由禁欲主义转变为控欲主义,摒弃了旧教伦理中严酷的禁食、禁性及自我体罚式的修道主义教条,鼓励人们合理地满足个人欲望,但禁止纵欲和浪费,“饮食足够维持健康,但极其简单和节约”,多余的财富用以帮助更需要的人。因为“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一点神的火花,因此所有的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都被一条人类理性能辨别的宇宙自然法则所束缚,这条自然法则就是公正的美德、对职责的忠诚、勇气、自我控制和普遍仁慈”[4]12。“一个富有的人看见自己的兄弟缺乏,却硬着心不理,怎能说他有爱上帝的心呢?孩子们!我们的爱不应该只是口头上的爱,必须是真实的爱,用行动证明出来!”(《约翰一书》3:17-18)基督徒利用上帝的恩宠得来的财富对弱者和无援的人施与救济,是天经地义的,是替上帝普撒博爱的雨露,无须得到被救济者的感恩戴德,被救济者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行为将爱施与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将爱进行传递扩散,以体现上帝那“仁慈`、博爱”的恩典。
四、两种价值结构对中国现代社会价值结构建构的影响
价值评判的本质是如何调节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或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价值结构就是调节关系的准则结构化安排。中西方传统文化中调节社会关系的价值评判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也即“义”是主导社会一切事物的最高准则,是社会价值系统的序参量,“利”是从属于“义”,为“义”服务的,如果“利”有利于“义”的体现、伸张,就加以倡导、保护,如果不利于“义”,就加以限制、约束,如果有害于“义”,就加以打击甚至消灭,这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价值结构则是“利体义用”,保护个人利益是最高行为准则,“义”是为“利”而生,“义”服务于“利”,无论是政治上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还是法律体系“保护私有财产”的一系列制度建构,或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契约关系构建等,都是为“利”而形成的制度性安排。“民主”在西方话语中的文化要旨是:个人的权利高于集体的权利,坚持个人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2]27。
中西方两种价值结构各有利弊。中国儒家文化以“义”为主导的价值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的期远、勤勉、质朴的品质修养;国家节俭省用,管理者唯欲是防、唯度是守等思想和理念,对现代社会仍然有普世的指导价值。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利”的贬低、压制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严重制约了人的进取、开拓和创新精神,同时也是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商业文化积贫积弱的根源,与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西方传统商业文化以“利”为主导的价值文化,将私有财产、个人权利(包括感受、生命、自由、选举)等放在首位,形成了一整套“利益制度”和“利益价值体系”。在这种价值哲学的指导下,弘扬了人“天然进取”的本性,激起人们开疆扩土、冒险创新、独立自主的精神,同时还发展了信仰观、秩序观和法治意识,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良好物质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但西方文化“利益算计”的理性精神,具有较强的攻击性,缺乏亲情与和谐的文化积淀[13]144-156。这和国际化中的文化多元化及各文明对话沟通和谐发展的格调不相融合。
中国现代社会快速发展需要建构新的价值结构。中国现代价值结构不同于传统的价值结构,在于要不断发展经济,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财富的积累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发展新型工商经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的实践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中国现代价值结构也不同于西方价值结构,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谐发展的根本原则,这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大“义”,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结构既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社会心理条件和基础,又为现代价值结构提供丰富的营养。
因此,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基本样式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与具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船共渡的发展模式,其价值结构是“义利共体”,“义”和“利”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序参量,二者同体,相融相济,不可偏废。“利”是“义”的基础,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民众认同性的前提;社会主义制度规制下的政治、法律、道德、风尚是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人们追求生活水平、质量提高等幸福指数的保障。“和谐”是“义利共体”价值结构的精神实质。“义利共体”的和谐精神主要表现为义利共生,“义”和“利”要和谐共生,不能因“义”而去“利”,也不能因“利”而废“义”;义义相宜,各种“义”相互接济,政治制度、法律规范、道德风尚等相互配合、相互适宜、长短互济,不能突出一端而不及其余;利利相容,各利益主体相互接纳、沟通、共情,各美其美,共同富裕,不能为自利而毁他利;体体沟通,在全球范围内各文明体、经济体、民族体通过政治协商、文明对话、经济交流等方式加强沟通交流,达到互谅互让、和平共处、相互促进、共同繁荣,不能以霸权代替对话。
总之,中国传统“义体利用”价值结构为中国现代“义利共体”价值结构提供了宝贵的人文精神基础,西方“利体义用”为中国现代价值结构建构提供了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1]张彦.当代西方价值排序理论的范式演进:从舍勒、哈特曼到杜威[J].学术月刊,2013(2).
[2]鲁品越.“价值”的层次与“相对普世价值”的生成[J].学术月刊,2012(6).
[3]姚鹏,方广锠,范桥,袁坚.中国思想宝库[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4]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第6版)[M].袁传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康天意.文明的狂飙疾进时代[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祖嘉合,梁雪影.工业文明[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7]马克斯·韦伯.中世纪商业合伙史[M].陶永新,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0.
[8]温德诚.精细化管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9]爱尔维修.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0]雍少宏,朱丽娅.益组织行为与损组织行为:中国特征的角色外行为模型及其经验实证[J].管理学报,2013(1).
[11]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Kjell Goldmann,Ulf Hannerz and CharlesWestin(eds.)[M].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Taylor& Francis Group.
[13]周建波.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J].管理学报,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