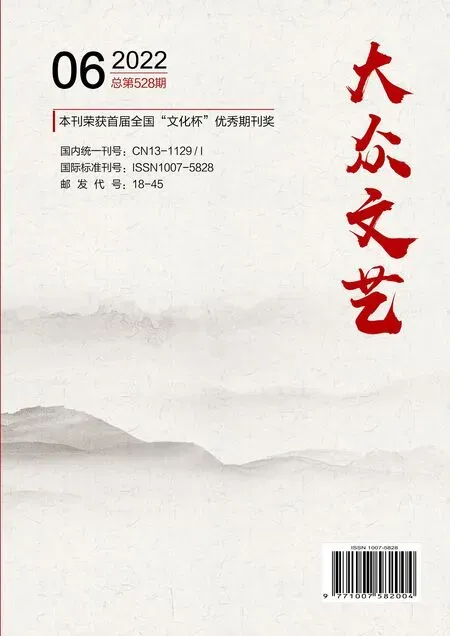两汉妇德标准之变
——从刘向《列女传》到武梁祠列女画像石
郭炳利 杨红超 (商丘师范学院 河南商丘 476000)
两汉妇德标准之变
——从刘向《列女传》到武梁祠列女画像石
郭炳利 杨红超 (商丘师范学院 河南商丘 476000)
刘向的《列女传》确立了西汉妇德标准,影响广泛。武梁祠以《列女传》为文本创作了表现女性道德主题的列女画像石。两者之间关系密切。然而,《列女传》文本的流传与图像的表现之间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从武梁祠列女画像石的选材标准和空间分布来看,两汉妇德的标准经历了从宽松多元到严苛单一的转变;从“才德”并重到一味强调“德”的演变;女性的独立人格和仁智才华完全让位给贞节道德。
列女传;武梁祠;列女画像石;妇德标准
刘向的《列女传》是研究汉代妇德标准的不二文选,影响广泛。汉代考古遗迹中也多有以表现妇德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汉晚期武梁祠的列女画像石。而这两者关系密切,即武梁祠列女画像是以刘向《列女传》为本文的创作,可谓插图本。但两者又不能简单对等。一方面武梁祠中的列女画像只占刘向《列女传》极少的篇幅,只能算作节选本。另外,从两者的创作时间来看,据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列女传》编撰于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而武梁死于公元151年,祠堂建造年代应在公元147年到151年之间。文本与图像之间相差近两百年,经历了从西汉后期到东汉晚期的历史演变。我们就从文本与图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着手,探究两汉妇德标准的演变。
一、刘向《列女传》及其反映的西汉妇德标准
(一) 成书背景及主要内容
刘向(约公元前79年–公元前8年),生于汉昭帝时,历经昭、宣、元、成四朝,为西汉宗室。西汉后期成帝、哀帝生活奢靡,沉溺享乐,宦官外戚交替专权。刘向《列女传》即编撰于汉成帝永始元年。刘向作此书的目的,班固在《汉书》中明确指出:“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实际上为刘向所编的是七篇,另一篇是后人续编。刘向编撰《列女传》,就是要借古讽今,劝诫汉成帝,反对后妃逾礼。全书以儒家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观念作指导,按妇女的封建行为道德准则和给国家带来的治、乱后果,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篇,每篇15个故事,共105位妇女的事迹。其中的《孽嬖》篇收录的是以女色误国的邪恶堕落的妇女传记。通过塑造正反两方面的女性典型,树立符合儒家理想的妇德规范,以劝诫天子,教化百姓,在社会上广泛推行妇女的道德教育,借以维护封建秩序。
(二)刘向《列女传》与西汉妇德标准
刘向《列女传》共分七篇,在篇首都有序言,说明每篇选择并归类的原因。从中反映出西汉时人对妇德标准的要求。
《列女传》七章内容,除去女祸篇《孽嬖》不谈,典范妇女的事迹大致可归为两类:一是贞顺节义类,主要集中在《贞顺》《节义》篇。如舍己救人的鲁义姑姊、鲁孝义保,从一而终的陈寡孝妇,守礼而死的楚昭贞姜、宋恭伯姬等,约占全篇30%;二是仁智才华类,《母仪》《贤明》《仁智》《辩通》篇皆属此类。如严厉教子的楚子发母、邹孟轲母;讽劝国君的周宣姜后、齐桓卫姬;劝夫爱民勤政的周南之妻、陶笞子妻;出口成章的柳下惠妻;见识高远的楚武邓曼、赵将括母等;富于辩才和政治头脑的齐钟离春等,约占全篇70%。
从刘向《列女传》的取材,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汉时代的妇德标准由“贞顺节义”和“仁智才华”两部分组成,而后者显然更为刘向所重视,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另外,“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这六者之中,女性只要具备其中的一两项,便是当时表彰的榜样。母仪、贤明、仁智和辩通,特别是后三项,主要是从才识、气质、能力、精神风貌等智力因素、人格因素来评价女性的,只有‘贞顺’和‘节义’才是纯粹从道德的角度来评价女性的。”[1]p69这说明作者的立传标准相对宽松,反映出作者宽泛的道德伦理观念,也说明西汉对妇女的评价是相对多元的、宽容的。在西汉,聪明才智、气质能力、精神风貌,甚至语言能力等都是评价女性的重要标准。
然而,“妇德”不是一个抽象的、超历史的概念,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变化。刘向编撰《列女传》,以文本的方式确立西汉妇德标准。时隔近两百年,武梁祠以《列女传》为文本,创作列女画像石。但文本与图像之间既有联系更有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武梁祠列女画像在对《列女传》的选材标准和范围方面有明确的倾向性。地方祠堂自觉地、有意识、有倾向地选取特定题材加以描绘,反映出东汉晚期社会流行的一般性妇德标准,而这种标准较之西汉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二、武梁祠列女画像石及其反映的东汉妇德标准
(一)列女画像石的选材
武梁祠位于山东济宁嘉祥县南十五公里处,是兴建于东汉晚期的一处祠堂。祠堂内部的画像石,以其艺术的完美和主题的丰富闻名于世。其中尤以历史故事题材的完整性和思想性独树一帜,为研究东汉时期的道德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依据。
列女画像石是武梁祠历史故事画像中重要的一个系列。武梁祠列女画像共八幅,全部以刘向的《列女传》为创作文本。面对刘向《列女传》105个故事,武梁祠只选取了其中八位妇女的事迹加以描绘。她们分别是:梁寡高行、鲁秋胡妻、鲁义姑姊、楚昭贞姜、梁节姑姊、齐义继母、京师节女以及无盐丑女钟离春。这八位列女分别选自《列女传》三个篇章,其中前七位选自第四、五篇(即《贞顺》《节义》),只有无盐丑女钟离春属于《辩通》篇。那么,作为有文本可依的列女画像,武梁祠的设计者何以在面对《列女传》数以百计的故事中独独钟情于这八位女性典范?这样的选择是随意和偶然,还是带有明确的倾向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究。
武梁祠的列女画像是典型的以图像阐述历史文本,而“在对历史进行阐述的尝试中,武梁祠画像的设计者比一个以文字叙述历史的史家所享有的自由要少得多。不同于一本书,画像的篇幅已经由祠堂的空间预先决定;设计者必须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经济有效地表现他的观念,其结果是细节部分必得大量省略,题材必须精心挑选以成为对重要历史主题的提示,或者作为较大历史类别的象征。”[2]p73那么,武梁祠在有限的空间表现中选取的八位列女画像是要表达怎样的历史主题呢?如上所述,八位列女中的七位都属于同一主题,即“贞顺节义”。显而易见,“贞顺节义”已经从刘向《列女传》宣扬的多元妇德标准中被推崇为东汉晚期的主流道德观。
(二)列女画像的空间分布
有学者研究发现,武梁祠中的“历史人物被特意挑选,列入同一装饰区域,是因为他们都联系着一个中心主题。”[3]p166或为忠,或为孝,或为其他的主题。我们来看这八幅列女画像的分布位置,她们分布在武梁祠后壁和左壁的上部和下部装饰区域。七位列女画像从右至左、首尾相连集中分布于后壁到左壁上层,显然属于同一主题。而选自《辩通》篇的丑女钟离春的故事则被单独绘制在武梁祠左壁下层最左端,与其他列女在空间分布上区别开来。这引起了学者的好奇:“令人迷惑的是,钟离春的故事也出自《列女传》,但她却被单独放在这里,与其他女性形象分开,这种安排是不是有意设计的呢?”[4]p165根据同一主题出自同一装饰区域来看,我们可以推论出,尽管钟离春同样出自《列女传》,但从她在画像石上的空间分布来看,她的出现是与其他的故事组合成另一个特定主题,而与上面七位列女故事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点已有学者做过令人信服的论证。因此,从画像分布来看,富于辩才和政治头脑的钟离春不属于武梁祠列女主题的表现对象。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武梁祠堂装饰中对历史故事的排列特别重视每一系列的第一幅画像。这种结构是从汉代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中派生出的。例如《诗经》各卷的第一首诗称作‘四始’,被认为含有解读整部经典的‘密码’。武梁祠中的列女画像以梁高行故事开篇。”[5]p301梁高行是一位美丽的女人,年轻守寡,许多贵族,包括国君本人都在打她的主意。为了避免再婚的危险,她割鼻毁容。在武梁祠描绘的列女画像系列中,这位寡妇端坐于帷帐中,右手持镜,左手握刀。画面以此表现了最紧张刺激的一刻:这位著名的美女正在割掉自己的鼻子以维护其忠贞。梁高行传中所记录她说的话,清楚地传达出祠堂刻画这一故事的基本教化意义:“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马填沟壑。妾守养其幼孤……妾闻妇人之义,一往而不改,以全贞信之节。”[6]p58梁高行的故事作为开篇出现在武梁祠列女画像中,其分布的位置和出现的次序是我们解读武梁祠列女画像主题的“密码”。
综合来看,武梁祠列女画像的空间分布也可以进一步证实,“贞顺节义”已成为东汉晚期最重要的妇德标准。钟离春尽管选自《列女传》,但她在武梁祠的分布位置说明她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物出现,与其他七位列女并未形成统一的主题。因而证实武梁祠列女画像集中表现的是“贞顺节义”的妇德主题。同时为了突出贞顺节义的主题,画家将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梁高行的故事放在画像开篇,为我们解读列女画像的主题提供了钥匙和密码。因而,从武梁祠列女画像的选材和分布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武梁祠作为当时社会普遍性的丧葬祠堂建筑,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东汉妇德标准主要倾向于“贞顺节义”。
三、结论
通过对刘向《列女传》以及武梁祠列女画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两汉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妇德的重要基础,妇德标准在这一时期定型并流传后世,极大地影响着后世中国妇女的命运。第二,西汉时期,妇德标准确立之初,贞顺节义和仁智才华并存,后者更为时人所重视。这一时期妇德标准相对宽松多元,妇女精神相对自由。第三,东汉时期,随着儒家伦理体制的完善和全面推广,“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道德伦理规范成为限制妇女人格独立的枷锁。贞顺节义的呼声上扬,仁智才华等人格和智力因素退居其次。这一点既表现在武梁祠画像上,也可以与东汉流行的另一部有关女性的著作相印证,即班昭的《女诫》。班昭在《女诫》中主张妇女应该柔弱顺从,贞节不二,却把才智视为可有可无。
总体而言,从刘向的《列女传》到武梁祠列女画像,从文本的流传到图像的表现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历史变迁。两汉妇德的标准经历了从宽松多元到严苛单一的转变;从“才德”并重到一味强调“德”的演变;女性的独立人格和仁智才华完全让位给贞节道德。女性开始逐渐退出精神独立的舞台,被推向道德伦理的狭路,这也直接导致后世妇德标准向畸形发展。
[1]刘巨才.选美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2]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M].北京:三联书店,2006.
[3]同上.
[4]同上.
[5]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刘向.列女传,《四部丛刊》(六十)[M].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本,1937.
郭炳利,女,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讲师,硕士,中国美术史研究方向。
杨红超,男,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美术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