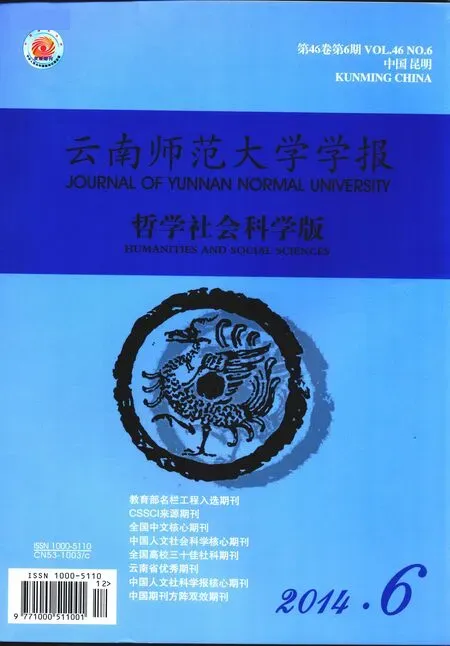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的学术研究*
丁文丽, 王文平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的学术研究*
丁文丽, 王文平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先生处在一个物质环境极度恶劣同时学术氛围又极度浓郁的联大校园之内。8年间,处理完公务与教书之余,陈先生发表了诸多文章,内容涉及金融、外汇、经济思潮、抗战对策等诸多领域。一方面从当局困境着眼,提出针砭时弊的对策,另一方面从抗战大局出发,为抗战胜利建言建策。这8年与抗战前后一起形成其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高潮期。
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学术研究
一、研究环境
西南联大时期,生活与研究的客观条件都非常恶劣,这一情况无论是在长沙、蒙自还是昆明,一直都没有改观。特别是在昆明,一方面空袭频繁,命悬一线。据战时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从1938年9月至1944年12月,“日机派往云南执行轰炸与侦察任务的各类飞机共3599架次,执行轰炸589次。”[1][p.102]频繁的空袭,使得生命安全没有丝毫的保障可言。与其他联大师生一样,陈岱孙先生也是生活在不停跑警报的惶恐之中,其在昆明先后有3个住所,两处皆毁于轰炸。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严重昆明物价几年之内翻了三四百倍,联大教授们大多无法解决基本生存所需。闻一多曾在北门街治印,梅贻琦夫人曾在冠生园卖定胜糕,即使如工资最高且在“中央研究院”兼职的陈寅恪先生同样感叹,“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陈岱孙先生当然也是饱受通货膨胀折磨,虽然无家室之累,但当时却拮据的连一根香烟都买不起。最后,图书资料匮乏。陈岱孙先生早年搜集的学术资料及《比较预算制度》手稿全毁于战火,联大时期由于战事紧张,交通运输及经费问题致使图书资料匮乏。当时联大师生就是在这样一无图书,二无设备的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其艰难可想而知。
无论物质环境如何恶劣,但始终挡不住联大人对学术赤诚而热烈的追求。据《吴宓日记》记载,当时对学术的追求即使是在跑警报时都不例外,“11∶00警报至,至旧地山上花坑中避之。食面饼,读《楞严经》,完。”“9∶00警报至,独行至旧地山上花坑中坐避。是日炸马街子、温泉等处。食面饼。作《梦觉》诗之(二)(三)(四)。”[2][p.356]正是由于这种无处不在的学术热情,为联大营造了一个非常浓郁的学术氛围。联大时期,这种学术氛围不仅存在于防空洞之中,同时还充斥在校园里每个角落,无论是师友之间还是师生之间,学术的交流与争论无处不在。从整体来说,联大恶劣的物质环境与优良的学术环境的巨大反差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陈岱孙先生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物质环境极度恶劣同时学术氛围又极度浓郁的联大校园之内。8年间,处理完公务与教书之余,陈先生发表了诸多文章,内容涉及金融、外汇、经济思潮、抗战对策等诸多领域。一方面从当局困境着眼,提出针砭时弊的对策,另一方面从抗战大局出发,为抗战胜利建言建策。这8年与抗战前后一起形成其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高潮期。
二、学术思想
陈岱孙先生弟子晏智杰教授认为,“从1934年到1947年,这是陈岱孙著述的第一个高潮期”。1934年到1937年陈岱孙先生在清华执教,1938年到1946年8年多的时间则在西南联大。据《陈岱孙文集》上卷所收录的文章来看,清华4年陈岱孙发表文章很多,但不属于本文讨论之列。而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创作主要集中于1938年至1941年的前5年,其间共发表文章20余篇。
从《陈岱孙文集》收录的20余篇文章来看,陈岱孙先生在此段时间主要关注抗战的经济对策、法币汇价、华北伪币、通货膨胀及经济的自由与统制思潮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客观上反映了他在抗战时期的经济学思想。
西南联大与抗战相始终,而1937年至1941年正是敌人气焰最嚣张的抗战初期。增强后方的经济力量,为前方提供坚实保障,成为这一时期陈岱孙所有文章的主题。这一主题又衍生出战时工业化思想、战时财政思想、战时金融思想等学术思想。
(一)战时工业化思想
工业化问题,在抗战前学术界已经展开过大规模的讨论。重工、重农、工农兼重在当时都有不小的支持势力,最后“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于1935年底制定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政策,并展开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活动。但由于重工业发展艰难繁复,不能一蹴而就,从1936年的短期繁荣来看,“民国”政府的重工业虽有所进步,但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轻工业倒有了长足的发展。风云突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事爆发,不久京津及东南沿海地区全部沦陷,刚刚起步的工业发展几乎全部丧失。面对这种情况,国内经济学界及当局政府中有很大一批人坚持认为,应该在后方大力发展工业及重工业以支持抗战。但陈岱孙先生认为此举绝对不可取,并坚信后方工业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暂时放弃艰难繁复之重工业
陈岱孙先生不仅不主张重新发展重工业,而且还认为应战期间应该暂时放弃艰难繁复之重工业。其原因如下:
(1)时间不允许。战事爆发之前,尚属备战阶段,一切皆从长远计,应该也必须注重发展工业及重工业,唯有如此中国才能逐渐从一个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这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一定也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但目前战事已经开始,我们已经由备战变成了应战,前方的一切需求都由以前的非急切变成了刻不容缓。一个是急不可待,另一个又不是一蹴而就。因此陈岱孙先生在《计划后方经济拟议》中写道,“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时间较长,不能短时间内为我们所利用”。[3][p.125]虽然“重工业是工业化的基础,而也是军队机械化现代化的基本。我们有种种的考虑,恐怕费力多,而成就少。我们现在是应战,而不是备战”。[3][p.367]
(2)财力不允许。中国自清末以来,国运衰微,军阀混战,列强瓜分。特别是1935年刚刚发生涉及全国的“白银风潮”,白银的大量外流导致通货紧缩,银根枯竭,人心浮动,资金外逃,全国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上海31家民族资本纱厂停工的有8家,丝厂停工的达28家,面粉厂开工的只有14家,不到原有厂数的一半,商店倒闭的多达521家。”[2][p.149]“钱业发生风潮,尤为惊人……计有大同行33家,当时倒闭者12家,计去三分之一以上,小同行27家,当时倒闭者17家,计去三分之二。”[3][p.98]一方面工厂大量倒闭,另一方面金融业也随之破产。全国经济体系处于崩溃边缘,“民国”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宣布改革币制,发行法币,才算躲过灭顶之灾。虽然随后1936年经济有所复苏,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战事随之而来,京津要地及东南富庶区域全部沦陷。在财力拮据的状况下,想要在后方发展重工业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事情。因此陈岱孙先生说,“我们是一个穷国,平时讲建设,尚有捉襟见肘的窘态,何况战时,穷则必须穷干,则财力亦有限了。”[3][p.342]“如果我们的力量有限,而此类工业的发展,必须吸收我们有限力量之一大部,使得当务之急反而没有做好,那就大有考虑的余地了”。[3][p.261]
(3)人才及地域不允许。虽然西学东渐从清末已经开始,但是真正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实在是少之又少,重工业的发展不是少数几个人就能完成的。而且,“我们贸然把这样重要艰难的事业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个人失败事小,而国力因而虚耗事大。”[1][p.137]发展重工业必须有合适区位,比如当地是否有煤、铁等原料,倘若区位不合适,同样无法发展。而“民国”政府现在控制的地域,哪里有煤,哪里有铁尚需进行勘探,同样非一日之功。因此在人力与地域区位方面也不具备条件。
陈岱孙先生认为无论从时间、财力上来看,还是从人才与地域区位上看,在战时的特殊情况下,都不适合发展重工业。因此“我们不但不主张办于维持生活绝对不可少以外的工业,并且以为繁费艰重之重工业亦应暂时放弃”。[3][p.75]
2.后方工业化必须进行统制
一方面战时情况特殊,关系民族存亡大计,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最终之胜利;另一方面战时财政困难,在本已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做有限资财之最有效利用。因此,必须在一个宏观的统筹安排之下进行最有效的生产,来满足最急切的需要,这就是战时最有效也必须采用的经济模式——统制经济。
为使全国上下所有力量能朝同一个方向努力,达到所有力量最有效的协调配合,战时一切都应在最高当局的协调统制之下,工业化当然也不例外。工业化要在后方有效的开展,而不至于虚耗国力,从建设到生产都需要完全在政府的统制之下。
(1)建设统制。后方工业化建设必须在统制之下,建设什么样类型的工业,建设多少,都需要政府从宏观角度出发,进行协调,才能不靡费国家资财。而在建设统制中,政府要分清轻重缓急,以自身财力为限,鼓励后方原来工业发展。因为这一部分工业没有受到损失,原有基础都在,无须耗费过大成本即可直接服务抗战。同时政府还要鼓励沦陷区的资金内移,并吸收外资共建后方工业。另外政府还要根据自身需要,独立投资建设一些必不可缺的工业。只有在三者同时着力之下,后方的工业化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建设起来。
(2)生产统制。工厂建设起来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必须在政府的统制之下。战时是非常时期,后方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前线取得抗战胜利。那么后方工业化建设的目标可以锁定为两点,即满足前线军事需要与满足后方基本衣食需要。目标既已确定,工业化生产的内容当然也就限制为与此密切相关之项目。即与战事密切相关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并且即使是前线的军需品和后方的生活用品也有严格限制,“军用品一项,只能集中于能力所及之制造,而暂时放弃其艰难繁费者……至于衣食一事,只认定维持生活不可缺少之粮食与衣着,绝对不得超过于此外。至于其他平常时期所用增加人民生活享受之工业,当在暂时放弃之列”。[3][p.149]
(3)成本的计与不计。陈岱孙先生还在工业化建设问题上提出一个成本问题。当时举国都认识到此次战争,关系民族存亡,因此无论政界还是学术界许多人都在呼喊着不惜一切牺牲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群情激昂,影响深远,后方工业化建设与生产上也存在着这种思想。陈岱孙先生认为,“一切新企业的举办都不考虑到成本的高低,其危险性是很大的”。[1][p.235]所谓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的做法只能局限于与前线军需密切相关的事业,因为“这一类事业的用品是供应前方作战需要,是维持前线作战能力的必需品。在任何状况之下我们都不能不力求补充供给……我们也只能忍受,而不能斤斤计较。”[2][p.248]同时陈岱孙先生还认为,虽然与前线密切相关但非我财力等因素可迅速生产出来的或与本次战争关系不大的,也不在不计成本之列。而“与军事没有直接或密切关系的经济建设,不顾成本只求建设的态度,实在是大有考虑余地。”[3][p.75]总之陈先生就是要指明“不论代价”的战时心理,如果广泛存在一切后方建设,将突然增加政府负担,而与战事无所裨益。
(二)战时财政思想
财政在国家生活中居于非常重要之地位,而战时财政则是在非常时期能否维持前方继续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其地位显得愈发重要。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即言战时财政具有3个重要特点,即“收入需迅速、收入需巨大、须有安全持久之税收。”[1][p.201]战争将造成巨大的消耗,国家财政因此面临巨大损耗,如何增加国库收入,既是一个关系前方战事能否继续维持的,又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陈岱孙先生认为筹措如此巨大的款项,无非有三途,即税收、公债、通货膨胀。但由于三者对物价的影响不尽相同,因此战时政策选择须有所慎重。
(1)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弥补财政巨大损耗的一个可靠途径。陈岱孙先生认为,税收“只是将人民原有购买力之一部分直接转移归政府,总购买力没有增加,不过人民与政府间分配的比例变更了。”[1][p.245]因此不会发生提高物价的影响。从抗战大局出发,政府可以采取增税率与税种的方法来解决部分财政紧张问题。但制定税种时要注意增税主要是增加富人及使用奢侈品者的负担,这样一来即可增加收入,又可不增加贫困人民负担,还可以减少奢侈品的使用,为国家节约资财。
(2)发行公债,是政府调节财政的另一项有效工具。抗战以来至1939年“民国”政府共发行7种公债计法币23亿元。陈岱孙先生认为,国债的发行,认购主体应该以人民为主,只有大部分被人民认购了,剩余的才能由银行接收。否则银行大量接收国债,将间接导致信用膨胀,引起金融与币制安全问题。而就当时国债发行民众认购过少的情况,陈岱孙显出了莫大的隐忧,其在《物价、财政与建设》中言,“如果公债发行不由人民承购,而由银行承受,或表面上,虽由人民承购,而人民可以之向银行抵押贷款,银行得以此项债券为放款之法定准备,则公债发行将间接的造成通货膨胀,而引起物价变动的结果。”[3][p.315]因此,“如果我们不谋补救,一旦危险发生,我们的生产力将大受打击。”[3][p.45]后方人民的承购能力虽然不足,但是整个西南西北地区幅员辽阔,陈岱孙先生认为,人民的承购能力并没有达到饱和点,仍然有待可发掘,否则不待人民承购,直接委以银行,终究会形成通货膨胀的恶果的。
(3)通货膨胀,陈岱孙先生始终认为通货膨胀战时虽不可免,但却是最不可取的一种方式。早在1936年法币刚刚发行,经济学界便有人担心会为通货膨胀埋下伏笔,当时陈岱孙先生便对通货膨胀的成因、性质、后果及其与岁计的关系做了系统研究,并完成了《通货膨胀与岁计》一篇宏文。其核心理念一直影响了他一生对通货膨胀的看法。战时则完成了《通货膨胀性质的一斑》一文,着重阐述了通货膨胀与公债之间的区别,澄清了一般人的误会,并再次重申了《通货膨胀与岁计》的核心理论,即通货膨胀是一种剥夺人民财富于无形的不公平的“坏税”。在政府用以增加财政收入的诸多手段中,陈先生认为,战时通货膨胀虽不能完全避免,但需用之谨慎。此举虽可蒙蔽人民于暂时而阻力最小,但不加控制,其危害性将非常之大。因此“一个比较稳重点的战时政府财政当然力求避免通货膨胀的方法”。[3][p.325]
(三)战时金融思想
陈岱孙先生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博士,主攻方向为财政金融学。其战时金融思想应该涉及金融业的各方各面,但由于《陈岱孙文集》收录文章有限,诸多领域无文献可征,无法窥其面目。现仅就文集收录来看,尚可以了解其关于外汇及华北伪币的一些观点与看法。
1.法币外汇思想
1935年民国政府改革币制,确定法币的无限法偿地位,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即虚金本位制。一方面使得法币与英镑挂钩,另一方面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维持法币汇价稳定。由于外汇准备充足,加上无限制买卖外汇的政策,自法币发行至卢沟桥事变之前,汇率一直稳定在14便士左右。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战事使得中外进出口商开始考虑规避风险或投机牟利,大量将手中法币兑换成外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将14便士左右的汇价一度维持至1938年3月,随后因外汇偏紧,汇价一路下跌。1938年伪华北傀儡政府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准券,妄图聚拢法币套汇。因此国民政府颁布《购买外汇请核办法》,开始外汇统制,由于当时战事发展迅速,东南地区沦陷,国内已经形成沦陷区与非沦陷区两个外汇市场。1939年年初法币汇价基本稳定在8.5便士, 2月下降至8.25便士,3月中英外汇平准基金成立,在香港、上海公开出售,由于投机及日伪套汇严重,6月7日,平准基金委员会放弃维持8.25便士的汇价,一时人心惶惶,汇价迅速跌至6.5便士。7月中旬后,继续下滑,至8月12日仅为3.5便士。
陈岱孙先生就是在这种外汇情况的大背景下,在6月25日及8月13日分别撰文《法币汇价问题》《法币汇价问题申论》对此前外汇市场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的方法。
对于当时的外汇形式,陈岱孙先生着重研究外汇平准基金之所以放弃维持8便士汇价的原因,对于日伪套汇的严重程度与日伪套汇的主要途径,并阐述了货币对外汇价与对内购买力之间的关系,同时针对当时外汇困境提出3个可行的方法。
陈岱孙先生认为,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之所以放弃维持8便士的汇价,最接近事实的原因有两点,即怕基金损耗殆尽与选择8便士维持并不是其初衷。
陈岱孙在阐述基金之所以会损耗殆尽时,主要采用了英国经济学家G.Goshen的国际借贷说。首先8便士不是一个市场出清时的汇价,8便士高于出清时的自然汇率。其次,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国际贸易中方始终处于入超地位,战事爆发导致沿海重要工业区丧失,可出口之物大量减少,而进口之需求不减,因此今后的国际贸易中将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贷方金额一再放大的条件下,自然就会导致汇率的下跌,而平准基金继续维持8便士的汇率,必须由中英外汇平准基金来支付的金额将越来越大,“如果汇率超过自然水准太高,有限的基金的运用总是有出无进,终有损耗净尽的一天。”[3][p.169]再次,基金委员会初衷并不是为维持8便士而维持8便士,当初之所以选择8便士的汇率是因为8便士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一度保持很长时间,比较接近市场出清时的价格。但目前8便士已经高于出清价格,因此放弃维持也在情理之内。“换言之,外汇基金当初所希望维持者也是一个近于自然的汇率”。[4][p.48]对于日伪发行伪联准券套汇一事,陈岱孙先生认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其套汇的主要途径应另有所在。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在北平扶植汉奸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伪华北临时政府”,1938年2月又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并于3月10日起发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并宣布在华北地区禁止法币流通,一切法币必须折换成伪联准券方可流通。日本妄图用这种方式,聚拢法币,然后再到上海套取外汇,破坏中国外汇市场。但由于华北发行伪联券并不成功,大批老百姓不愿将法币兑换成伪联准券,而且还将法币珍藏起来。因此陈先生认为华北伪联券的发行失败,注定他们在套汇方面不能起到主要作用,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只就以伪币套取法币以间接套取外汇言,过去的情形不至于十分严重”。[5][p.163]对于只有印刷成本的伪币来说,虽一有机会必定会套取外汇,但伪联准券发行之失败注定其不是主要套汇之途径。陈岱孙先生认为,日本套取我国外汇主要还是通过大量倾销日货,获取法币,然后再去换取大量外汇。“我们对日货贸易总是入超,过去数月我们全部进口贸易增加,而以日货之输入为最。此项输入日货之一部分自是以我输往日本的货物为抵偿。然其差额必须以外汇补足。我们对日贸易入超数目越大,我们外汇损失也越大……这个漏洞确是我们外汇基金的威胁,所以所谓敌人偷窃我们外汇的手段归根还是以国际贸易为主。”[6]许多人们都将汇价作为国家经济能力的晴雨表,汇价下跌很容易引起恐慌情绪,认为法币必然贬值,通胀将随之而来。面对当时风行的思潮,陈岱孙先生运用购买力平价说一方面解释汇价下跌与物价无必然之联系,另一方面又用汇兑心理说,对这种恐慌的情绪,加以重视。
瑞典经济学家G.Gassel的购买力平价说认为,货币的对内购买力决定其对外价值,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崩溃,物价高企,那么外汇一定会做出下跌反应;但是如果货币的对外价值决定不了对内的购买力,国家的信用会破产。因此陈岱孙先生说,“我们承认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崩溃,信用破产,当然会反映及于货币对外价值。然而翻过来,一个国家货币对外汇的跌落,不一定就是经济崩溃,信用破产的征象。简单地说,外汇率的涨落与国内经济的盛衰有可能的而没有必然的联系。”[3][p.65]陈岱孙先生还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影响外汇涨跌且与国内物价无关的其他因素,最后得出结论,汇率涨跌一方面与物价没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汇率下跌,本身是可以鼓励出口,遏制进口,平衡国际收支的一个工具。因此当汇率下跌时,希望以前迷信汇率的人,不要恐慌与焦虑。
汇率下跌便恐慌,这是当时迷信汇率者的普遍情绪。虽然这一恐慌并没有学术上的根据,而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联系。但是对于这种心理恐慌,陈岱孙先生以为并不能视而不见。“尽管这个心理作用是根本不正确的观念,而其影响还是可以很深刻的”。[2][p.121]汇兑心理说认为,集体的心理因素将会对汇率的走势产生巨大影响。陈岱孙先生正是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说,“汇率的剧变,造成一个怀疑法币的心理,而这个怀疑的心理可以牵动法币对内的信用与购买力,因此在应付现时的立场,我们法币汇率的相当稳定,有他的好处。”[7][p.145]沦陷区在敌人控制中,入超及套汇情况都较为严重,汇价跌幅较大。但为维持人们对法币的整体信心,经常不得不将非沦陷区的外汇为沦陷区买单。因此如何在不继续无限制供给沦陷区以外汇,又能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汇率的原则下,还不损害法币对内的购买力,是当时汇市一个亟待解决又非常棘手的问题。陈岱孙先生针对此种情况,提出三点可行之策。(1)沦陷区与非沦陷区的外汇应严格完全分离;(2)在沦陷区内,外汇基金主动操控一个接近市场出清水平的一个汇率,不断调节沦陷区国际收支,最终实现外汇自给;(3)非沦陷区内,政府通过统制进出口贸易来左右外汇需求。陈岱孙先生将沦陷区与非沦陷区的外汇市场完全隔绝起来,然后沦陷区由外汇基金主动调控汇率,达到调节国际收支目的。非沦陷区则通过政府统制进出口贸易,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赚取外汇购买军需。这一见解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来看都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因为日军正对国民政府的大后方进行封锁,要在往昔隔离两个汇市不大容易,但当时处于特殊时期,恰好可以做到。但由于不能直达当局首脑部门,影响力不足,这一意见最终只能被束之高阁罢了。
2.关于华北伪币的看法
为达到全面侵华的目的,1938年2月日本在北平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开始新一轮的对中国金融的攻势。1939年伪临时政府宣布法币一律按6折行使,3月11日后,一律禁止流通,持有法币者,于19日之前,到各银行兑换成伪联准券。但华北地区的人民,不但没有去大量兑换,反而将法币珍藏起来,法币不但没有因禁令折价,反而升值。针对这种现象,陈岱孙先生提前预言,只要抗日前途光明,法币不可能被伪币击溃。
陈岱孙先生之所以有这样大胆的预言,主要是基于华北人民对法币的信任及对伪币的不信任。
币制改革后,法币的地位十分稳固,华北地区没有更换通货的需求。而抗战爆发后,法币一直保持着对外信用,华北人民对法币有信心。作为全国通货的法币,只要全国其他地区的法币都正常使用,华北地区的法币就始终保持其通货的价值,绝对不会因为伪政府的一纸禁令而丧失价值。
华北伪币则不是全国性通货,它只是存在于日军控制的沦陷区的几个大城市内,连沦陷区的游击区域都未能覆盖。华北的外商银行不承认伪币的通货地位,更不与之进行外汇交易。最重要的一点,华北伪币由于没有准备金作保障,仅仅是只有印刷成本的废纸而已,不仅不能购买欧美外汇,就是连购买日元外汇都不能。因此华北人民对其没有任何信任可言,不久华北伪币果然维持不下去,大幅狂跌。为此陈岱孙先生还特意写了一篇《华北伪币狂跌》的时评,在时评中陈岱孙先生还大胆预言,“近来所谣传的他们在华中京沪一带还要再办一个银行推行在华北所试验而失败的金融政策。然而只要基本的情形一样,这些新花样不免要蹈此前的覆辙的”。[1][p.203]
三、结 语
20世纪上半叶,中华大地一直战火不断。特别是影响最大的8年抗战,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而“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华民族自强图存的探索激情,富国、强兵、救国思想空前活跃,政界及学术界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8][p.28]从宏观地域上来看,后人常把这一时期空前活跃且纷杂不一的经济学思想,划分为国统区战时经济学思想与红色根据地战时经济学思想。陈岱孙观点基本可以划归于国统区派的主流经济学思想,虽然这些经济学思想没有完全成为当时的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支撑,但是其真知灼见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1] 陈岱孙.陈岱孙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 陈岱孙.陈岱孙遗稿和文稿拾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陈岱孙.东方赤子·大家丛书·陈岱孙卷[C].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
[4] 唐斯复.陈岱孙纪念文集[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5] 晏智杰,唐斯复.陈岱孙学术精要与解读[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6] 丁文丽,王文平.略论西南联大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大贡献[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7] 吴宓.吴宓日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8] 陈岱孙.陈岱孙文集(下卷).经济学是致用之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Mr.Chen Daisun's academic research at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DlNG Wen-li&WANG Wen-ping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In the eight years at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Mr.Chen Daisun was in an extremely poor environment materially but enjoyed an especially good academic environment.In addition to handling official business and teaching,Mr.Chen published quite a few papers,covering finance,foreign currency,economic thoughts,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and others.On the one hand,he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he put forward work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Thus,this period became the first harvest time of his academic career.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Mr.Chen Daisun;academic research
F092
A
1000-5110(2014)06-0144-07
[责任编辑:乔小洺]
2014-09-09
丁文丽(1972—),女,江苏句容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和教育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