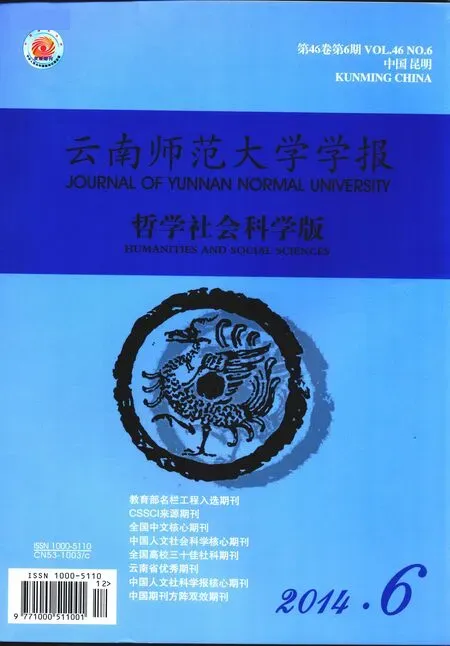神性与诗性:东巴艺术的生存空间与艺术表现*
陈龙海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神性与诗性:东巴艺术的生存空间与艺术表现*
陈龙海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东巴艺术是纳西民族创造的艺术奇珍和重要的世界文化记忆遗产,它源于纳西民族的宗教信仰——东巴教。作为一种带着原始意味的宗教,东巴教是以自然神为中心的多神教,其神灵鬼怪多达2400多个,这就决定了东巴艺术的宗教色彩和神性生存空间。由于没有现实的蓝本,也就决定了这些洋洋大观的神灵鬼怪形象的塑造带有非理性的性质,东巴们的艺术创造是一种典型的“诗性”创造。首先,他们以“万物有灵观”作为思维基础;其次,其创作以超乎寻常的想象、鲜明的情感倾向和略貌取神的大写意为特征。而东巴文,既是文字,又是东巴艺术的组成部分,它处于文字发展的童年期,其永远的象形意味弥漫着诗情画意,是一种“诗性”文字。本文还从地理优势、民族性格和宗教情怀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东巴艺术神性空间和诗性表现的文化原因。
东巴艺术;神性;诗性;生存空间;艺术表现
东巴艺术是盛开在云贵高原上的一朵艺术奇葩,是纳西民族在发祥、迁徙、融合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珍贵的美术遗产,她带着鲜明的民族记忆与民族特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盈的精神理想。东巴艺术包括面偶、泥偶、木雕、木牌画、布卷画、纸牌画、象形文字、音乐、舞蹈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仅以造型艺术为例展开探讨。
一
纳西人生活与艺术的不解之缘源于他们代代相传的宗教信仰——东巴教。东巴教是一种带着原始意味的宗教,纳西先民笃信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神灵鬼怪主宰着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一切,于是他们对此顶礼膜拜。由于地域的闭塞与交通的阻隔,东巴教便作为纳西人的民族记忆与集体无意识而代代承传。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到生产收获、造屋建房、凿井取水、求学经商、祛病求福等等,从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到日常生活的大小事务,都要举行或大或小、或繁或简的祭祀仪礼,智者东巴就成为他们人生和生活的全能导师。
东巴教是一种以自然神为崇拜中心的多神教,带着明显的原始巫术的特点,信仰“万物有灵”,因此,自然界的各种物象和自然现象都被赋予了神性和灵性并加以崇拜,并创造出一系列的神灵形象,如天神、地神、山神、水神、火神、谷神、土神、石神、风神、云神、雷神、太阳神、月亮神、星宿神等等,虎、牦牛、蛙、白鹤等动物也都在神灵之列。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神祇,最大之神叫萨依威德,其次为依古阿格、恒迪窝盘,还有美利卢、莫毕精如等。女神有沈神、盘孜莎美等。武神有九头格空神、四头卡冉神。护法神有东格、优麻等。[1][p.44]
上述诸多神祇来自于东巴教自身的创造,另有从外来宗教引进的来自天界、地界、地下界三个层次的神灵,即所谓“最新神系统”,于长江引述白庚胜先生的观点:“‘神灵’在天界,‘人’与‘署’在地界,地下界为‘鬼怪’的范围。所谓‘署’,是掌管自然空间的神灵,与‘人’是同父异母兄弟,‘署’主自然,人主社会,两者互相依存,又有冲突。‘署’大多为两种动物或人与动物的混合体,但基本上总是有蛇的形象。在这三个层次中,鬼怪常常闯入地界害人,天界神灵下凡拯救人类,在这种互动中,东巴担当一种十分重要的角色,代人祈神,代神镇鬼,也借神力调节人与署的关系。东巴沟通人神的作用,在这里集中体现出来。”[2]此外,纳西族的始祖、远祖以及主教东巴等,都被尊奉为神。
与神灵相对的是鬼怪系统,是一个与神、与人相对立的存在,习惯上将这个系统排列为:“此(鬼)、妞(怪)、毒鬼、争(仇)鬼、忍(飞)鬼、霉(飞怪)鬼、姆(饿)鬼、恩(水)鬼、呆(恶)鬼、拉(无头)鬼、娆(星)鬼、端(邪)鬼、尤(殉情)鬼、臭(秽)鬼、妥罗(不育)鬼,等等。”[1][p.44]
据有关专家的统计,在东巴教中的神灵、鬼怪共有2400多个,[3][p.18]真可谓洋洋大观矣!有人说,印度是一个善于造神的民族,但纳西民族与之相比,不仅毫不逊色,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纳西人生活在一个神灵鬼怪弥漫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人借助神灵的伟力驱逐鬼怪,以祈求福祉,禳除祸殃。在人神共舞、神鬼博弈的过程中,建构着纳西民族特有的生存秩序和精神世界。东巴艺术就这样存活于一个众神蹁跹、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神圣、神秘、陌生、怪诞、幽默等构筑了它的基本品格。张正明在谈到楚艺术时指出:“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出生的,楚人的精神生活仍然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又熟悉又陌生,又亲近又疏远。天与地之间、神与鬼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察,而又不可思议。在生存的斗争中,他们有近乎全知的导师,这就是巫。”[4][p.112]以此来评说东巴艺术也是十分贴切的。东巴艺术属于原始艺术的范畴,纳西人的祭祀仪礼带有巫术的性质。如果说,楚人的“全知导师”是巫,那么,纳西人的“全知导师”则是被称作“智者”的东巴。洋洋大观的神鬼谱系铸就了东巴艺术的基本品格,东巴艺术也就在这神鬼蹁跹的世界里生存和发展。
二
宗教与艺术的关系,向来纠结不清,或亲密无间如孪生兄弟,或老死不相往来形同陌路。后者如犹太人,宗教之于这个多难民族的重要性无须多言,但他们又反对偶像崇拜。犹太人认为至高无上的真神亚卫既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也就是无形无限的、抽象的,任何有形的、有限的、具象的形象都是对神的大不敬。不仅如此,这种观念还以神学律令的形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摩西十诫》第二诫中明确规定:“不可谓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所以,威尔·杜兰说:“有了这一诫,艺术即无法发展。因为不可雕刻偶像,这一来就把大部分的艺术扼杀了。加强一神观念,就好处来说,使犹太人早已脱离了‘迷信’及‘人神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的纠缠——尽管《旧约五书》中之耶和华具有不是人性——但却使众所共认知力优异的犹太人,除了宗教外,在艺术、科学乃至天文方面,全交的是白卷。”[5][p.394]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禁止偶像崇拜的律令对艺术,尤其是雕塑和绘画的影响不能不说是最直接的。据《旧约》中记载,当年摩西带领那些饱受埃及法老奴役的犹太人出走埃及回归故土的途中,因铸金牛而加以崇拜,上帝竟发怒要灭绝他们。犹太人只是个例外。世界上大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其宗教艺术都是繁荣昌盛的,如印度教、佛教、婆罗门教之于印度,以及佛教流播地的中国、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基督教之于西方世界等等。
纳西民族不会像犹太人那样,因尊神敬神而不给神造像,他们不仅造,而且大造特造。东巴艺术的创造者就是东巴,平常时节,东巴们与普通纳西人一样,要上山放牧,下地耕作,亦或兼做木匠、铜匠、泥瓦匠、医生等。只有在祭祀中,当他们披挂上阵时,他们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东巴。东巴艺术家的创作,无论从思维方式,还是创作过程与创作手段,都是“诗性的”。
最早提出“诗性”一词的,是意大利思想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维柯,在其《新科学》一书中,他把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叫作“诗性智慧”。在维柯看来,人类正是运用了这种诗性智慧,才创造出了“诗性的玄学”(哲学)、“诗性的伦理”、“诗性的政治”、“诗性的语言”等等。具体地说,“诗性的”是指早期的人类以自我为中心,通过“以己度物”的方式来想象、联想,来进行情感推理,并以这种方式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现象以把握世界,亦即主体通过心灵的想象、联想来创造或建构世界,以类比联系和象征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和阐释事理。需要指出的是,维柯所创立的“诗性智慧”的范畴,即是20世纪思维科学学者所说的“原始思维”。这一范畴是维柯在研究早期人类思维和社会意识的发生时提炼出来的,它只含有时间上和思维形态上的初始含义,与某些西方学者从种族歧视和文化价值论角度将“原始”一词等同于某些未开化民族那种“野蛮”、“落后”、“愚昧”的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
前文已经述及,东巴教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性质的以自然神为起点和主流的宗教,其思维基础属于原始思维,亦即“诗性智慧”,它继承和延续了原始思维的“万物有灵观”、“互渗律”和“生命一体化”等观念,用“以己度物”的方式来认知世界,认知外界自然事物。在此逻辑起点上,作为与鬼神交往、为宗教服务的东巴艺术,其创作过程和创作手段都是充满“诗性”的。韩非子云,画鬼魅易,画犬马难。意思是说,犬马为人们所常见和熟悉,画得不像,人们一望而知;鬼魅谁也没见过,怎么画人们也难指其暇。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则不然。犬马有现实为蓝本,而鬼魅则无实物参照,全然存在于想象中。因此,东巴艺术中的众多神鬼,东巴们必须超越现实之上去实现艺术的创造。
首先,超乎寻常的想象。所有的艺术都离不开想象,但东巴艺术家的想象力的丰富与高超是其他宗教艺术家无法相比的。因为东巴教中的神鬼数量极其庞大,并且没有实物的参照,随机性制作的神鬼形象完全凭借东巴们的想象,没有“眼中之竹”的蓝本,只有“胸中之竹”的图式,直接形成“手中之竹”。东巴们每次所捏塑、雕刻或绘画的神鬼形象都具有不可重复性,都是唯一的,这种随机性的创造过程实际上还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在汪洋恣肆的想象中,东巴们的创作所强调的是个体的体验,所重视的是经验和直觉感悟。笔者在丽江考察时,曾请教过一个资深东巴,问他依据什么来塑造神鬼形象,他笑着说,想象。以布卷画《神路图》为例:《神路图》为送葬之用,“乃直幅长卷画的世界之最,它的画面宽度约在20至40厘米之间,但高度约在15至20米。它是人类最高的绘画作品……它以连环画的形式,由下端开始作画,按情节的步步攀升,绘画亦扶摇直上。由千里之下的地狱黄泉,一直画到九霄云外的天堂福地。”[6][p.128]从该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死者灵魂先被投进阴森恐怖的地狱,受尽惨不忍睹的磨难;接着东巴施法,神灵显威,死者灵魂逃出地狱,在九座鬼山、九座鬼海里,与无数魔鬼进行一系列的殊死搏斗,终于来到欢乐人间;然后,经由东巴的超度,死者灵魂得以升入天国,最终到达三十三层青云之上的神天福地。如果说,对人间花香鸟语、动物云集等情景的描绘还有现实的依凭,那么,地狱和天堂中鬼怪与神灵形象、景象铺陈和由此展开的曲折的故事情节,就纯属出自东巴们非凡的想象力了。
其次,鲜明的情感倾向。东巴们的创作过程不仅需要情感参与,而且情感主导了整个创作。就祭祀来说,东巴的情绪宣泄与表达,他的喜怒哀乐直接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一场较大规模祭祀下来,东巴们往往累得精疲力竭,心力交瘁。东巴载歌载舞,念经做法,指挥各路神灵与层出不穷的鬼怪进行搏斗,时而吆喝、时而怒斥,悲喜交加,怨怒相杂,自始至终,情绪饱满,情感充沛。与我们常见的面无表情的和尚不紧不慢地念经、敲打木鱼,实在要费力得多,精彩得多,也更具有感情色彩和戏剧效果。最根本的原因,不正在于东巴们情感的投入与丰盈吗?再以捏塑面偶为例:东巴们在塑造神灵时,无不毕恭毕敬,小心翼翼,未见有丝毫的马虎之处,所以,神灵塑像一律庄重精致;而捏塑鬼怪时,则要随意得多,简单得多。即是在材质的选择上,也可看出东巴们的情感倾向。一般来说,神偶用大麦或青稞炒面作为原料,其质地细白,粘性适中,做成面偶后不易变形;而鬼偶则用苦荞炒面,虽然其造型功能较强,但其色黑、味苦,属于较劣的食物。在木牌画中凡属于神灵的造像不仅精致细腻,而且色彩绚丽;而属于鬼怪的造像则相对有些草率,色泽黯淡,有的干脆就使用白描,不施色彩。
第三,略貌取神的大写意手法。与佛教等宗教艺术的精雕细刻不同,东巴们的即兴创作往往采用大写意的手法,省略了细节的刻画,以大的体块和极其简洁的笔触摄取神灵鬼怪的动态和神情。如面偶、泥偶的制作,往往信手捏塑,一气呵成,简练明快。东巴们全凭一双巧手,几乎不借助其他的工具。一团面或一块软泥稍加揉搓,几经捏塑,顷刻间,神偶或鬼偶便呈现在眼前,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微微凹陷的两个洞就成眼睛,细细的一条缝线即是嘴巴,手足则更加精简。但从整体上看又无不神灵活现。神灵固然威严,但威严中透露出慈祥、恭温,平和,洋溢着丰盈的世俗情味,使人感到亲切和蔼,仿佛可以与之促膝谈心;鬼偶虽有狰狞的一面,但没有恐怖感,有的甚至像舞台上搞笑的小丑,在滑稽幽默中消除了疏离感,体现出原始美和稚拙美。木雕比面偶、泥偶稍微精细,但也是大刀阔斧,无意于对细部的刻划,与一些非洲部落制作的木雕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自然天成,质朴灵奇。木牌、布卷和纸上的绘画(最初应该是刻凿在岩壁上的),继承和延续了原始艺术的线条造型手法,以极其经济的笔墨勾勒出被表现对象的轮廓,删繁就简,逸笔草草,追魂摄魄,尽显自然之妙,似非人力之所成。在虚拟的神鬼空间中展现着丰厚的世俗情怀,未知的世界由此变得清晰和真实可感,优美动人。于是,纳西民族的灵魂、信仰和精神就有了实实在在的寄托之处、栖居之所和安顿之地。
谈及东巴艺术的诗性创造,就不能不说东巴文字。
东巴文字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被誉为“人类文字史中的活化石”。虽然它的创制年代至今还无法确定,从时间上看,它比3300年前的甲骨文要迟得多,然而从文字发展阶段上来看它比甲骨文却要早得多,东巴象形文字带有人类童年时代的印记,以“诗性”为根本特征,正如维柯所指出的:“由于学者们对语言和文字的起源绝对无知,他们就不懂得最初各民族都用诗性文字来思想,用寓言故事来说话,用象形文字来书写。”[7][p.213]这一说法是符合文字起源的历史的。东巴文最初是用来书写东巴经文的,可以说,东巴象形文字为纳西民族建构了一个多元神性、灵性的空间,它是根植于纳西民族神话与神性的土壤中,描述纳西民族远古记忆和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存在。同时,东巴文字也是东巴艺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除面偶外,木牌画、布卷画和纸上绘画等都离不开东巴文。至于东巴书法和东巴文印章,那是纯粹以东巴文为载体的艺术。
东巴文字就是一种“诗性文字”,“大体说来,其造字的用意可分为:依类象形,显著特征,变易本形,标识事态,附益他文,比类合意,一字数义,一义数字,形声相益,依声托事等十类。”[8][p.95]尽管其造字的用意种类繁多,但具有图画性质的象形符号是东巴文字最主要的构成因子,它经历了一个由图画到图画文字的演变过程。赵世红、何品正先生指出:“早期的东巴文字以图为主,辅以少量的符号,这可在木牌中找到。严格地说木牌并非一幅美术作品,这是纳西先民向神灵说着什么‘请神保佑,让我等渡过难关,我们一定厚谢您的大恩大德’等等。由于当时没有文字,先民们只好把它画出来,先画所求的大神,再画请神驱赶的鬼,最后画上敬神的物品,木牌下部的这些文字写的就是谢鬼以及酬神的言辞。图画记事的原始办法被木牌画的守旧规程保留了下来。在东巴经书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早期的动物类文字画,四肢齐,五官全,与真实的物体相比不少什么。随后,省去后半截,再后,只剩下一个特点突出的头部了。”[6][p.95]阅读东巴经文,仿佛游走在一个诗意的空间,扑面而来的诗情画意将我们带入久远的纳西神话语境中。当我们面对东巴经文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个图画所组成的灵异画面,那些灵动质朴的造型——神灵、鬼怪、等物、植物、人类活动等等,无不令人心往神驰而又不知所云,但总抵不住它的美的诱惑和由此引发的审美愉悦。下面略举几类东巴象形文字:
A.描写自然物象的:
B.描写动物形象的:
C.描写植物形象的:
D.表现人及其活动的:
其实,上述这些东巴文字,即使不标注出释文,我们也能一望而知其大意。比起埃及、玛雅的象形文字和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其图画性和象形意味更浓,但埃及、玛雅的象形文字和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早已成为一种历史存在,早已消失了文字的交往功能,只有东巴象形文字,仍然鲜活着,活在东巴经文中,活在东巴教的祭祀仪礼中,活在纳西人的人生大事和生活的细节中。
三
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一部《艺术哲学》无非用大量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史事实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即艺术的性质、面貌、特色等都是由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要素决定的。这一论断对我们探究东巴艺术的文化成因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东巴艺术的神性生存空间和诗性的艺术表现手法自然有其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笔者以为,最重要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地理优势。纳西族是古羌人的后裔,分为三个部落,即东部的禾氏部落、西部的梅氏部落和尤氏部落,他们居住在黄河西北部一带,生存条件十分恶劣,所以,大约于秦汉之际他们被迫开始了艰难的民族迁徙,东西禾梅二部落在迁徙中,因频仍的周边民族战争的摧残而分崩离析,被迫离开故地,逐渐融合到其他族群之中。尤氏部落则不然,他们在群山耸立,江流环抱,平坝开敞、草甸辽阔的环境中居住了下来。木丽春先生指出:“尤氏部落有三面环金沙江,一面抱海的负险地利,所以尤氏部落世代躲潜在丽江江湾盆地的口袋底。人称‘奉科’,意为潜鼠洞窟。尤氏部落避开南诏北犯,吐蕃南侵的两强作为跳板的过境地;境内又无令人垂涎的盐铁富利;故能躲开唐王朝、南诏、吐蕃三强之间拉锯式的战争旋涡。”[9][p.18]躲开了战争的侵扰,获得了相对和平、安宁的生存环境,使得纳西族的文化有了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物产资源,也使纳西民族实现了生产方式的转变。“正是由于这种较‘温和’的地理环境迥异于纳西先民古羌人所处的更为艰苦的西北高寒地带,从而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也就必然从粗放、漂泊的游牧方式转变为一种更为合适的可以自给自足的以农耕模式为主的小农经济作用下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由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10][p.760]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在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往往在形成该族群的文化特色和民族性格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这是我们认识纳西民族性格的逻辑起点。
第二,民族性格。纳西先民羌人的血液里流淌着剽悍、勇猛和刚强,那是环境使之然,他们时刻要为整个族群的生存而战,而丽江的江湾腹地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没有兵戎战事,无论秦汉魏晋,在诗意的栖居中,祖先的拼杀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并非纳西人甘愿逆来顺受,而是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下,首先要考虑这个族群的生存。所以,“尤氏部落的酋领,有一整套以欠债为宗旨的对部落内部人与人之间,和对部落外部的部落与部落之间和谐相处的方略:‘还了神的欠债,心上无疙瘩;还了鬼的欠债,晚上睡安稳,还了胜利者的欠债篱笆变牢固,还了仇者欠债,道路变宽阔,还了人的欠债,行路没有坎坷,还了友人的欠债,心里没有倾斜。’尤氏土酋利用这些处理内外亲疏的施政方略,当尤氏土酋为吐蕃所有时,他龟缩在老鼠洞里,都以为奴的弱势者的面孔出现;有时对主子献以牛羊,金银等供物,买得吐蕃王朝的喜悦。对吐蕃和南诏的争斗中,尽量跳出战争的漩涡,常持观望态度,若吐蕃王朝支派尤氏部落从征,尤氏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不作护主的紧跟的拼命征战,留一条宽松的退路。”[9][p.18-19]正是纳西先祖尤氏土酋的这种主动示弱和审时度势的策略,为部落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机会,并逐渐形成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发祥和成长的经历,对于培植民族性格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所以,纳西人性格中的隐忍、宽容等可以看作的一种民族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和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的形成,也使纳西民族性格具有典型的农耕文化的特点。农业生产不像游牧、商业那样,因内需不足而事外求,在不断迁徙流动和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培植起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农耕生产固守一地,靠天吃饭,自给自足,形成了静定、保守的性格。在丽江这块风水宝地上,纳西人不需要为生计付出太多,只要稍勤耕作,风调雨顺的田野就能给纳西人提供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因此,纳西人温和、文雅、保守、悠闲、自足、快乐,似乎所有的纳西人对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的满足,他们将这一切都归功于神灵和祖先的护佑,对他们的祭奠和膜拜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纳西男人通常是不下地劳作的,任凭健妇们春播秋收,他们有的是闲暇的时光,他们将这闲暇的时光消磨在法事、泥塑、绘画和音乐等艺术之中,慢节奏的生活和保守的性格使他们重复着千百年来代代承传的艺术法则,在神性的世界里,以诗性的表现手法使东巴艺术存在着,并继续增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房龙才说:“一国的艺术,是该国灵魂的可以见得到和摸得着的表现形式,这是千真万确的。”[11][p.54]对于纳西民族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第三,宗教情怀。建立在家族宗法制基础上的农耕生产方式的长期保留和循环往复,使得“古老的氏族传统遗风余俗、观念习惯长期保存、积累下来,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12][p.10]换言之,人类早期的社会结构、思维方法、伦理习俗、宗教信仰、审美趣味、艺术表现等,在很大程度上被东方各民族完整地保存下来,在哲学认识论和艺术表现特点等方面留下了远古时代的深刻的历史痕迹。
如果不走进纳西民族,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环节和精神世界之中,我们很难想象艺术对于这个古老民族的日常生活和人生信仰是何等的重要。毫不夸张地说,纳西人的艺术即是生活,生活即是艺术,他们活在艺术中。走进纳西村落和纳
西人家,我们会被扑面而来的宗教浓情和艺术氛围所感染,仿佛回到了一个久远的年代,唤醒着我们早已遗忘的人类童年的记忆。触目所见,在山坡上插着成片的绘有神灵或鬼怪的木牌,树上系着五色缤纷、图案怪诞的旌幡,墙壁上有东巴文抄写的经文,入夜时分,如果你幸运,你还能欣赏纳西的歌舞,当然是与某种祭祀有关的歌舞……纳西族“他们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实际上就是一项项宗教活动。……刚到村头,人们可以见到一个个似塔非塔的东西,腹中是空的,有些灰烬与燃烧的树枝。这是向天神祭拜的社塔,塔心烧火,火上盖以有浓香味的柏枝等,柏枝上放些面粉、酥油等食物。顿时,灶塔上部的出烟口升起一股白烟,这白烟称之为‘天香’,所敬献的面粉、酥油等祭品随烟升空,天神们便能享用到。灶塔称‘天香灶’。村外的天香灶按家族而建造,每逢节庆之日,家族成员都到该塔前向天神祭献天香。平常日子,各家在家中敬献天香……观完天香灶步入寨子,黄板屋已进入视线,屋顶中央插有小旗,松枝、竹枝等物,小旗随风摇摆挺抢眼的,这便是该家庭的胜利神……来到村里,但见不少人家的正房后墙或山墙侧面,竖有七八米高的只在顶部留有一些树枝的小松树,一棵、两棵或三棵不等,有的似还飘着写有文字的布条……它是超度死者的旗幡标志……绕过后墙来到大门前,门上不仅写有古文字的对联,奇特的是,挂有三块木牌,左右两侧绘有卢神(阳神)和沈神(阴神)。此二神虽非东巴教中的最大神祇,但他俩最贴近民众,类似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救百姓于水火……”[6][p.26-27]各家各户室内的神灵陈设,更是五花八门,或保护家庭不受鬼魔的侵害,或为去世的长辈延寿等等,不一而足。至于为年满12至13岁的孩子举行的成人礼、婚嫁、祛病、丧葬等等大事,那就必须操办规模较大的祭祀仪式,场面壮观,热闹非凡。东巴时而装神,时而扮鬼,指挥诸神与各路鬼怪较量搏斗;看客们能懂得东巴的一举一动,他们时而悲摧,时而欣喜,时而怨怒,时而紧张,时而释然,在嬉笑怒骂中进入宗教的迷狂中;时紧时慢的鼓点、引商刻羽的音乐、诡谲神秘的舞蹈伴随始终;还有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游走其间,模仿着东巴的言行举止……这与其说是一个个宗教仪礼,不如说是一场场艺术盛宴。人生、宗教、艺术就这样水乳交融,难分彼此。但纳西人的艺术是有着鲜明的功利目的的,他们从来不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点与原始民族有相似之处,正如格罗塞指出的那样:“原始民族的大半艺术作品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而是“想使它在实际的目的上有用的,而且后者往往还是主要的动机,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13][p.234]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纳西人的宗教情怀也会有所变化。如果说,纳西人早期的宗教信仰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和禳祸祈福意愿的表达,那么,当下围绕东巴教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则更多地带有娱乐的性质,在国泰民安的盛世,在民族团结、科学昌明的今天,纳西人的驱鬼敬神,或可看成是一种与鬼神同乐、自娱娱众的人生盛宴。
[1] 杨世光.丽江史话[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2] 于长江.神性与美 东巴文化及其对当代人的启示[J].艺术评论,2004,(6).
[3] 和志武.东巴教和东巴文化[J].郭大烈,杨世光.东巴文化论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4] 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5]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上) [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6] 赵世红,何品正.东巴艺术[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
[7] 维柯.新科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8] 方国瑜.“古”之本义为“苦”说——汉字甲骨文、金文、篆文与纳西象形文字比较研究一例[J].郭大烈,杨世光编.东巴文化论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9] 木丽春.东巴文化通史[M].北京: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
[10] 杨曦帆.丽江洞经音乐及其人文地理环境[J].白庚胜,和自兴.玉振金声探东巴——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1] 房龙.人类的艺术(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2] 李泽厚.试谈中国人的智慧[A].中西美学艺术比较[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13]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Deity and poetics:Living space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of Dongba art
CHEN Long-hai
(School of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Dongba art is an artistic treasure and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world created by the Naxi ethnic group,and has its origin in Dongba religion of the Naxis.Dongba religion has the elements of primitive religion and is a multi-deities religion with God of Nature at the center.This religion is related to more than 2,400 deities and spirits with their own features.Without actual models from the reality,the Dongba artists have created the images of these deities and spirits with some irrational feature,thus,a typical poetic creation.They believe in animism and have outstanding imagination and strong feelings as well as divine craftsmanship in their artistic creation.Dongba pictographs are both Dongba written characters at the initial stage and Dongba art with a poetic taste.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deity and poetics of Dongba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eographical vantage point,ethnic features and religion-loaded feelings.
Dongba art;deity;poetics;living space;artistic expression
J0
A
1000-5110(2014)06-0083-07
[责任编辑: 肖国荣]
2014-03-2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东巴艺术的多重文化属性与艺术创新(11YJA760006)。
陈龙海(1962—),男,湖南长沙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