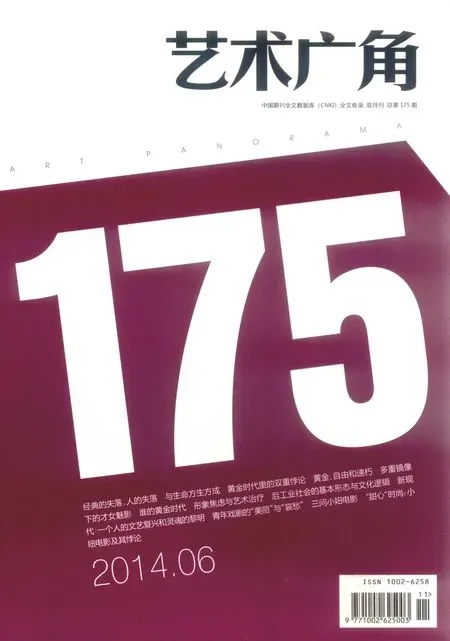青年戏剧的“美丽”与“哀愁”
纪鹏
青年戏剧的“美丽”与“哀愁”
纪鹏
谈及“青年戏剧”,我有很多话想说,一则是我作为观众喜欢看青年人编导的戏剧,二则因为我这几年多少张罗些校园戏剧的事情,接触的戏剧爱好者都是纯真无比的青年人。但青年戏剧的题目真是太大太深,我就谈一些感性认识吧。
2012年10月末,我在北京的木马剧场看了一场由青年导演王翀出品的话剧《乔布斯的美丽与哀愁》。这是一部独角戏,内容题材都很新颖,讲的是和乔布斯以及苹果公司相关的故事。编剧是美国人麦克·戴西,一个年轻的“苹果”发烧友。而这部作品的翻译和导演则是这两年在北京颇玩出了些名堂的王翀,他的《雷雨2.0》《中央公园西路》等作品我也看过,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青年戏剧人,做戏寻求创意与突破,不愿意恪守传统戏剧原则,容易将戏剧做向极端。作为北京青年戏剧的代表人物,王翀于2012年发起了“新浪潮戏剧运动”,而作为“新浪潮运动”的主力作品,这部《乔布斯的美丽与哀愁》实如其名,既让我看到了“美丽”,也让我深深为我们的青年戏剧感到莫名的“哀愁”。
《乔布斯的美丽与哀愁》应该算是时下比较流行、也比较典型的青年戏剧,其表达形式新颖,运用了大量的高科技元素和“苹果”元素。投影、视频、灯光等的配合,为表演者营造了足够的气氛,让观众丝毫不会因为一个人表演而感到枯燥。应该说,戏剧从立意和表现上确实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这也是目前青年戏剧最大的优点——有创新,有突破,有发展,有想法。但在作品展现这些“美丽”的同时,我也看到戏剧内容结构十分松散,整部戏舞台元素比较庞杂,缺乏一些必要的戏剧故事性和冲突性。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部戏内容与形式的呈现,不禁让我联想起很多我看过的青年戏剧。以我个人来看,目前国内青年戏剧的生存和发展现状真的和这部戏的名字一样,是一个“美丽”与“哀愁”共存的矛盾体。
青年戏剧的“美丽”
时下中国戏剧发展最好的两个城市是北京和上海,而这两座城市的戏剧市场的繁荣与火爆,离不开青年戏剧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以我常年观戏的体会而言,北京至少一半以上的戏剧作品是由青年人创作的,而上海的比例应该更高。这些青年戏剧作品虽然良莠不齐,但大多能体现年轻一代对戏剧、对人生、对社会的认知。而更为我所欣赏的是一些作品和一些年轻编导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这些都让我们青年戏剧表现出很多“新的东西”。
强烈的戏剧表达欲望和清晰的自我意识,是当代青年戏剧工作者一个很明显的特征。现在所说的青年戏剧人大多是75后,主体是80后,这个群体教育环境与文化背景与前代不同,他们似乎具有一种天然的表达与倾诉的愿望,愿意与周围人分享自己的心得,分享自己的心情。落在戏剧这种更为主观的表达工具上,他们的表达欲望就更为强烈了。因此,青年戏剧更愿意紧扣时代脉搏,更愿意主动触及一些现实问题(有些甚至是敏感问题)。就比如,乔布斯刚刚过世,王翀就马上奉献了关于他的作品,这种表达的欲望和速度,都是以往不能想象的。当然,若谈到表达的深度与广度,我更推崇的是另一位青年戏剧人——徐昂。作为相对“刻板”的北京人艺旗下的年轻导演,徐昂表达的勇气和态度都是令人钦佩的。2010年他的作品《小镇畸人》就以春秋笔法大胆地鞭笞了体制性和社会性的陋习,而2011年他推出的《喜剧的忧伤》,从更高级的层面上讨论了艺术创作的本质与误区。可以说,以徐昂等为代表的青年戏剧人所呈现的这种表达的锐利,恰是这个发展变革的时代所需要的,他们的作品比某些一成不变的传统戏剧作品,更能被当代观众认同,也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现在的青年戏剧人思想更为开放,创作理念更为自由,而且越来越多的青年戏剧是基于兴趣出发创作而成的。因此,青年戏剧作品的内容往往带有明确的自我意识,而创作的主题和题材则更加多样化。这种多样化表现为表达主题更加广泛,戏剧特色更加鲜明,表达更加自我,简而言之,一些前人未能涉猎的主题,未能展现的情感,现在青年戏剧人都乐于去尝试和探索。于是,可以看到关于艾滋病、同性恋、小三儿等敏感题材的戏剧作品,也可以看到深掘人性阴暗面的戏剧作品,当然也会看到细致入微描写人类普适情感的戏剧作品。这些作品至少都表现了这些青年戏剧人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而且相当一部分作品确实能够直击人心,让观众对一些社会和人生的问题进行反思。在这方面做得最突出的,应该首推“至乐汇-怪咖”剧团。这个完全由年轻人组成的戏剧团体,几年来一直坚持创编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戏剧作品,每一部作品主题都十分鲜明、表达都十分大胆。犀利、深刻的《驴得水》,以及《六里庄的艳俗生活》《老佛爷的爷》《破阵子》,以及《狐狸小晶》等出色的作品,无一不展现出他们不拘一格、自由开放的创作风格。在这种风格下所打造的作品,都个性突出、生动鲜活,让观众们叹服青年戏剧人的才华和勇气。
当前青年戏剧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是它的“新”“奇”“特”,而最能表现这种“新”“奇”“特”的,就是青年戏剧所呈现的丰富多彩的舞台表达。很多真诚致力于戏剧创编的年轻人视野较之前辈们更加广阔,因而不太愿意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往往能够充分发挥奇思妙想,充分利用舞台假定性,奇妙配合灯光舞美,大胆应用肢体表现方式……总之,他们在舞台表现上充分调动一切能调动的因素,来为观众呈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戏”的状态。比如北京赵淼以及他的“三拓旗”倡导的肢体剧,青年导演黄盈推崇的“一戏一格”,王翀的“新浪潮”等,都在尝试和探索着属于自己的舞台表现方法,为观众奉献别具一格的戏剧表演方式。更有甚者,像至乐汇仿照台湾作品推出的《三人行不行》,已经将三人互动的舞台表现做到极致,而台湾的另一位新锐导演李宗熹,更是在他的情感大作《Hi,米克》中让颇具实力的青年演员彭梓桁以人扮狗来表现戏剧主题。舞台装置也是青年导演作为舞台表现的重要利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北京传媒大学杨阳工作室制作的《最后只好停下来》,舞台由一个既可以固定,又可以前后左右摇摆的房间架子构成,演员根据表演需要在这个架子内翻转腾挪,而架子则可以配合演员进行不同状态的调节。观众常常会为这些青年戏剧富有趣味、充满智慧的动态表现而击节称赞。这些奇妙精彩的舞台表达,也正是青年戏剧具有强大吸引力和生命力的表现。
青年戏剧在表现语言和节奏上比较符合年轻人的欣赏品味,因此很多青年戏剧工作者都致力于打破传统戏剧的“第四堵墙”,积极与现场观众进行沟通与互动,从而将戏剧与现场秀相结合,让观众不但是观看者,更是感受者。早在2010年,黄盈便在自己的《马前马前》中完全打破了舞台和观众的概念,将观众席变成了可以随时搬动的移动座椅,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需要不断移动位置来配合演员表演,甚至在某些场景下观众自身也是表演者。这种设置让身处其中的观众真正地融入这个戏,跟随演员去体验戏剧的故事。而像黄盈这样探索戏剧与观众关系的表演实例还有很多,比如饶晓志的《你好,打劫》,其最早版本的舞台呈现就是开放的,四面都是观众。至乐汇的《驴得水》也在现实主义表演之中加入了与观众互动的情节。当然,在这方面尝试最多的应该是孟京辉了(他已经不算年轻,但仍然可以纳入青年导演的行列),他的戏几乎每部都有演员在观众席的表演,可谓“照顾”观众情绪的第一人。这种与观众互动的模式固然有利有弊,往好了做可以让观众对剧作更有感觉,更有兴趣,做得过分自然会让人有一种脱戏的感觉。但青年戏剧人这种打破固有戏剧模式,探索新鲜元素的勇气,还是很让人钦佩的。而作为青年戏剧,或者是先锋戏剧的一个符号,互动模式也承载了很多青年戏剧人对观众心态的理解与把控。
青年戏剧的“哀愁”
戏剧作为一种小众艺术形式,能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生存和壮大,青年戏剧的作用非同小可,其潜力更是不可限量。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青年戏剧在相对自由、无拘束的状态下发展,固然可以得到充足的营养,但却难免会在纯天然的环境中生长出一些庞杂的枝枝蔓蔓。所以中国青年戏剧也有令人担忧甚至“哀愁”的地方。
如前所述,青年戏剧的“新”“奇”“特”自然是可喜的,但这种突破并不等同于无原则的标新立异。可以看到,时下的很多青年戏剧作品,为了追求标新立异,从根本上忽视了对基本戏剧元素的继承和学习。笔者作为观众曾与一些青年戏剧人有所接触,也参加过一些演后谈的环节。给我的感觉是,时下的一些青年戏剧工作者对所谓的先锋戏剧极其推崇,而对以“人艺”为代表的相对传统的戏剧风格则嗤之以鼻。他们反感京剧的程式化表演,甚至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主义都很不“感冒”,他们推崇的是用方法来做戏剧,用新潮的观念来包装戏剧。于是,许多所谓的戏剧表演都沦为一些穿着奇装异服、口音怪里怪气的人进行一些不知所谓的表演。于是,越来越多所谓的诗剧、音乐剧、实验剧不断超越着观众正常的想象。客观地说,以“北京人艺”为代表的经典话剧模式,不是最完美的,也不应当是唯一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艺”的剧作每一部都是根基稳重的,每一部都是有灵魂、有主旨的。传统戏剧表演的铺平垫稳、起承转合、节奏控制,恰恰是时下很多叫嚣时尚、先锋的青年戏剧所缺失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些青年戏剧人毫无原则地轻视传统戏剧和传统文化,必然会造成戏剧基础的缺失,这也是他们的戏剧不接地气、缺乏灵魂的重要原因。
青年戏剧的“哀愁”还表现在很多青年戏剧工作者过分沉溺于表现手法的创新与实践,忽视了对戏剧本身的锻造与完善。在一个结构不完整、缺少足够戏剧冲突和故事内容的剧目中,一味地炫耀自己的舞台表现,实在是有些本末倒置了。我怀疑那些所谓“大师级”的类似行为艺术的戏剧演出能走多远,能被多少观众真正接受。我个人还是很古板地倾向于称为“戏剧”这个东西一定要完成一个具有足够合理矛盾冲突的故事。有不少青年戏剧人只愿意在戏剧中玩弄花活,而不愿意好好讲述一个完整故事。这里就不得不再次提及已经被媒体炒作得如神一样的孟京辉了。他应该算得上是目前国内使用舞台语言、彰显自我戏剧性格的翘楚。但在我个人看来,孟京辉最大的毛病恰恰是他的戏剧越来越不会好好讲故事了。他和妻子廖一梅共同完成的“悲观主义三部曲”,舞台技巧一部比一部高超,可故事性却一部比一部弱。《琥珀》故事尚可,《恋爱的犀牛》已经开始充斥如同梦呓的撕心裂肺的呼号,而到了《柔软》,就只剩下看似富于哲理、实则空洞乏味的独白了。他的其他作品,也是一以贯之的炫目与苍白共存,《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主角们变成了摇滚蹦迪的“嬉皮”;《蝴蝶变形记》将《老妇还乡》改得面目全非,而所有演员在最后集体脱得赤条条只剩下内衣……孟京辉的舞台始终气魄十足,灯光舞美始终诡秘深沉,但戏剧的冲突、故事的脉络却总是在这些花哨的技巧下沉沦消隐、不知所踪。这种戏初看觉得挺有劲儿,但它们如同爆竹一般,一阵绚烂过后除了几缕硝烟,什么也不会剩下。更令人有些“哀愁”的是,孟京辉作为北京青年戏剧节的发起人之一,多年来对这个国内最重要的青年戏剧活动进行艺术把关,尤其近三四年,他按照自己的口味在戏剧节上引进了一大批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的戏剧。这些将形式主义玩到极致、却同样缺乏戏剧故事性的戏剧,让很多国内青年戏剧人似乎大开眼界,于是一大批效尤者应运而生。这是中国青年戏剧的幸运还是不幸呢?笔者不敢妄加断言。但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我看到了很多观众对于这类戏剧的不满。如果说演戏的目的还是要给观众看的话,我想观众的态度应该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现在的青年戏剧工作者更加愿意借助戏剧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与观点,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它能够成为青年戏剧人创作戏剧的一种动力。但凡事过犹不及,如果只是一味地强烈地表达自己,倾诉自我,却不能好好地对戏剧的脉络和逻辑进行必要的梳理,戏剧就会沦为一种简单的无理性的表达工具,而非面向大众的文化载体。但现在恰恰有相当数量的青年戏剧作品缺少对自我表达欲望的梳理,对戏剧表达内容也只会做“加法”而不会做“减法”。因而,这些戏剧作品呈现给观众的往往是凌乱的、近似疯狂的表现,这样的戏剧常以先锋自居,但其骨子里却是对戏剧驾驭能力的缺失。比如孟京辉旗下的刘晓晔,其人表演能力突出,而且有一定的曲艺功底,这本是他安身立命的利器。但他与孟京辉合作的几部戏剧,如《两只狗的生活》《希特勒的肚子》和《混小子狂欢节》等,无一不在戏剧创作的思路上呈现出随意性和无节制。戏剧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了随性讨论社会话题兼展现自我才艺的工具,而半点看不出戏剧的条理性和艺术追求。他们的表现恰如《喜剧的忧伤》中所描述的“团长”李胜来,在每部戏里都要加上个耍手绢的环节。这种无克制的表现欲其实并不是戏剧应该有的。在北京、上海,相当多青年戏剧人在取得一定成绩后,乐于去这样无节制、无条理地玩这种表达戏剧。我个人以为,这种趋势万万不可成风,不疯魔不成戏,但太疯魔怕也难成好戏。
总的来说,青年戏剧虽谈不上多么成熟,但仍然充满着魅力与生机。近年来,青年戏剧也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像黄盈的《黄粱一梦》、赵淼的《水生》《署雷公》,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国际认同。这表明我们的青年戏剧大有可为。但年轻的戏剧人也确实应该在创作与创新的路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把真正属于戏剧本质的东西还给戏剧,让“美丽”表现得更加充分,而让“哀愁”少一些,再少一些,让舞台这方寸之地,真正绽放别样的光华。
纪 鹏: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东北大学话剧团指导教师,编导话剧、肢体剧作品有《明天继续》《我的卓别林爸爸》《You are not alon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