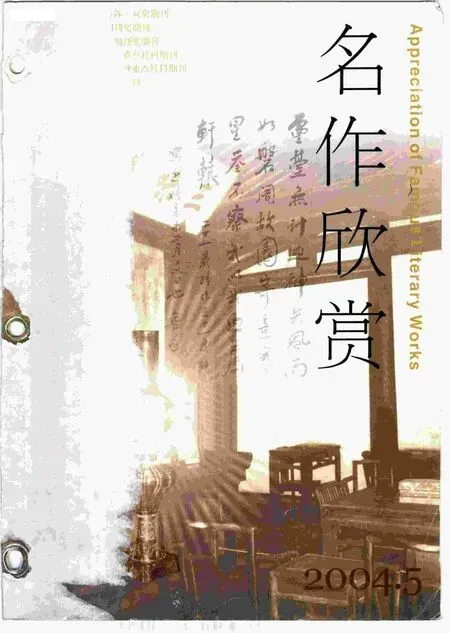先锋的“落地”:从《隐身衣》看新世纪格非的创作转型
⊙李 莹[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作 者:李莹,中国海洋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发表,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式。小说创作突破了一直以来着重于内容的范式,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的热衷。由此,先锋派文学步入了文学史。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一批作家进行了大胆的文本实验,试图将元小说的叙事方法发挥到极致。他们熟练地运用叙事圈套、叙事猜测和故事人物的符号化等手法,沉溺于叙事迷宫而乐此不疲。
格非,被称为中国的“博尔赫斯”,这大部分源于他在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创作。他作品中所呈现的叙事迷宫、叙事空缺等特点,成为先锋派文学的一道风景。格非的前期小说,如《青黄》《迷舟》《镶嵌》等,无不充满了扑朔迷离的艺术氛围。而到了90年代,格非逐渐放弃了先前的写作方式。那个热衷于形式实验,并善于营造文本迷宫的叙事者,开始沉淀自己,并逐步改变原本梦幻而富于荒诞感的先锋姿态。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中,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而是作为叙事的中心重新回到作品,使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现实维度得以建构。不难看出,格非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变化:他试图通过关注人物的命运,关注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处境,以及他们细腻的心理变化,揭示生存的意义,从而使得他的写作更具现实性。
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先锋派较少灵活性,对于细微差别较少宽容,它自然更为教条化——既在自以为是的意义上,也在相反的自我毁灭的意义上。”①仅仅在形式上充满先锋意味的创作,并不能成为源源活水,相反,也会桎梏了作家的创造力。“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绝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②2012年3月,《隐身衣》面世,这不能不让众多读者眼前一亮,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先锋文学正在逐渐褪去叙事迷宫的浮华色彩,而变得成熟和厚重。
“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一个谬误。”格非选择了尼采的这句话,印在《隐身衣》一书的扉页上。这句话似乎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这部中篇小说各章节的名称,无一不是乐曲、乐器等与音乐相关的名词:KT88、《彼尔·金特》、奶妈碟、萨蒂、《玄秘曲》……这是整篇小说的底色,它渲染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对文本结构和意义的生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融入了格非的切实生命体悟。古典音乐纯净而优雅,它建构着人类所向往的美与善的乌托邦世界。然而,在小说中,格非向我们展示了与它背道而驰的另一极——知识界所蕴含的隐忧;在世俗利益的冲击下,人间至情的淡漠与泯灭;个人在大社会中的无奈与迷茫。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提出,以及对由其引发的人性本质和价值取向的验证和拷问,表明格非的创作已经转向一种新的艺术面向。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了古典音乐发烧友崔师傅所经历、见闻的社会百态。“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是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以简驭繁,富有深意。随着叙述的深入,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不仅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令人措手不及,甚至难免心灰意冷。小说中“我”与玉芬恋爱到结婚,在各种诱惑下,爱情遭遇了变质。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亲情本应给予人温暖和力量,可是,就在“我”无家可归的时候,姐姐崔梨花竟不惜运用一切卑劣的谎言和伎俩,将亲弟弟赶出那间墙体漏风的破败屋子。一起长大的发小蒋颂平,就在“我”走投无路向他求援的时候,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恶言相向,尽显油滑奸佞本色,患难中难见真情。
在叙述结构上,格非摆脱了以往的跳跃式叙事,而以一定的时间为节点,展开线性叙述。其中,唐山大地震、“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经济时代是连结故事的重要背景。以崔师傅在褐石小区给客户制作音响机器开始,以在褐石小区给这个客户调试机器结束。小说整体寓于圆满的叙事结构中。更为关键的是小说中流露出的对现实的观照意识,叙述者将“我”定位于隐身人,“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由此,“我”可以冷眼看纷繁的世相,更加客观地向读者阐释社会现象。
小说最关注的,莫过于对知识分子群体价值取向、精神内质变化的探究。这一在世人眼中清高自重、博学多闻的读书人形象,在《隐身衣》中受到了极大的反讽:“知识分子间的谈话,你是很难听得懂的。你听不懂也没啥奇怪的,但他们说话时那种郑重其事的腔调和口吻,却不由得你不着迷。那是一种能够让任何荒唐的观点立刻变得入情入理的腔调。”从文化角度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如今娱乐至死的年代,在各种信息大爆炸的冲击下,人们的审美和价值取向受到了严峻的拷问和挑战,其中不乏在迷茫与困惑中随波逐流之辈。而知识分子,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言人和传播者,竟对此无动于衷,甚至在媚俗艺术和金钱利益的冲击下,忘却了本该承担的文化启蒙、净化灵魂的责任。不同于以往作品对战争背景和历史题材的选择,格非更加关注当下的现实人生和社会动态,集中了社会日益尖锐的热点问题加以暴露,关注人物的命运,重视故事情节的完整,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展开对人文精神的关注,从意义的消解转为对理性深度的追求。
丁采臣,在与这样的世界无法磨合而绝望时,选择了结束生命。他是小说中充满神秘色彩的刚性人物,既有感知艺术的敏锐灵性,也有无法与世俗融合的无助。在社会大背景下,小人物总是自我真实地活着,他们退到历史边缘状态,活得卑微、庸常、凄惨,但活得本真、自足。而文中的“我”,就是一个“喜欢让自己的感觉停留在事情表面的人”。这似乎也是作家格非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发出的无奈的慨叹。“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只要你捅破了这层脆弱的窗户纸,里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经不起推敲。”小说营造了一个“世外桃源”——在古典音乐熏陶下,有着良好信誉的发烧友的圈子。这也是作家格非向读者传达的精神寄托,即使世界纷繁杂芜,个人仍要找到能够让灵魂得以沉淀和净化的角落。但在具体的小说技法上,格非仍显得不够成熟,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与鲁迅等现代作家相比,格非对此类题材的把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在这篇写实主义小说中,我们仍能看到作为先锋作家的格非的影子。比如,崔师傅向蒋颂平借宿服装厂而遭拒绝的窘态描写:“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起身告辞。如果你在那一刻见到我,一定能觉察到我脸上的狼狈和羞惭。”在这里,第二人称“你”的运用,是先锋小说创作经常使用的技法,尤其体现在“元小说”技法的叙述中,意在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
当代文学史上,先锋小说“第一次将某种历史意义上的‘当代生活’变成了文学作品形式特征的社会对应物……旧秩序的风蚀剥落和新秩序雏形期的变动不居,不仅是一代人内心生活的外部风景,还在更为关键的意义上成为其语言构造的内在逻辑。随着一代人逐渐显露为一种历史的声音,这个过渡时代的全部混乱将在新的主体的自我叙述中成为一部精神史的自然依据”③。当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地向前迈进,在大时代话语瞬息万变的情势下,先锋小说作家们也在纷纷调整自己的创作策略,这在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妻妾成群》等作品中都有体现。
正如加布里埃尔当在《艺术的使命与艺术家的角色》(1845)中写道:“艺术是社会的表现,当它遨游于至高境界时,它传达出最先进的社会趋向;它是前驱者和启示者。因而要想知道艺术是否恰当地实现了其作为创始者的功能,艺术家是否确实属于先锋派,我们就必须知道人性去向何方,必须知道我们人类的命运如何。”格非的《隐身衣》,以及当代先锋小说作家的部分创作,在对现实生活的对抗性以及在话语运作上的某些实验性之外,开始对人的精神维度进行独立探索。重要的是,他们把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内质放置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显示出作家在体悟探寻人的种种存在秉性、拷问人性内在的品质上都跃入了一个新的层面,体现了浓郁的人文关怀。他们逼视着人在自我拯救的过程中的心灵际遇和方式方法,这种方法需用生命、心灵去注解,不能只用道义、良知、真理等概念来阐释。作为学者型作家,格非的亲力实践无疑是发出了象牙塔中一声强烈的呐喊。
①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4页。
② 丁增武:《先锋叙事∶漫游和回归——潘军中篇小说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③ 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第362页。
[1][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4).
[3]格非.隐身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