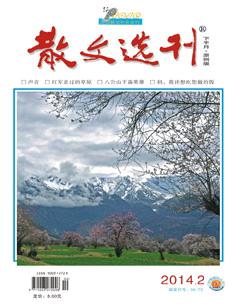苹果
杨立英

那年夏天,娘从外面带回家几个苹果。我冲进家门的时候,娘正把最后一个苹果放进吊在房梁的竹篮里。娘以为我没有看到,于是在我进门后,她若无其事地从竹篮边快速地走开了。
那是一个简单实用且功能强大的装置!绳子从房梁上垂下,另一端拴上钩子,竹篮挂在钩子上,里面放着干粮或其他吃食,竹篮的高度恰如其分地固定在娘能伸手触及而我无论如何也够不到的位置,当然,这样的装置除了防小孩子外,还可以防猫防老鼠。
我还无法抵挡住一个苹果的诱惑。娘出去后,我在屋里转了几圈,阳光从窗棂斑驳地透射进来,一个清晰的路径在我头脑里呈现,那是通往竹篮最快捷的路径。
晚饭过后,一家人在天井里纳凉,而我却毫无兴致,我的魂被竹篮里的苹果勾走了。
一人回屋睡觉不是我的习惯,为了让我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又必须设计一些理由,这是需要勇气的。我几次想跟娘说我困了,但一想开口,心跳就加速,犹豫了几次,最终我还是说了出来,然后装模作样地打了声长长的哈欠。娘说:“困了就回屋去睡!”
借着月色,我爬上炕钻进了蚊帐,躺下后,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竹篮,很长的时间。最终,我还是鼓起勇气悄悄地下炕,爬上椅子,再攀上墙边的桌子,踮起脚尖,伸长身子从竹篮里摸起一个苹果。那一刻,我感觉心脏怦怦乱跳,腿有些打颤发软,幸好一股苹果的清香弥散出来,抚慰了我的不安。我匆匆地回到炕上,把自己和苹果裹进了被单儿。我在不安和甜蜜杂糅的心情里沉沉睡去,梦里,我望见了我家的柳树上长满了苹果,我攀上柳树,抚摸着一个个又红又大的苹果,感觉一下变得特别富有!
“都给我起来!谁偷拿了篮子里的苹果?今晚不交出来,就先把她的手剁了!”娘的呵斥声把我震醒。娘不是个性情温和的女人,但这样大的火气却是第一次。我浑身开始颤抖,慌乱中,把滚到被单角的苹果又紧紧地攥在了手里。
这时,爷爷裂肺的咳嗽声穿墙而至,打破了黑沉沉的宁静。记不清从何时起,爷爷就这样整夜整夜的咳嗽。娘暂时放弃了对我们的“审问”,从竹篮里抓起两个苹果匆匆往外走。
从我们的屋子到爷爷的屋子只有几步的距离,娘走完这段距离的时间,是我逃脱罪责的唯一机会。
娘的前脚刚迈出门,我一骨碌爬出被窝,一手抓住苹果一手提着娘用旧粗布为我拼结的裤衩,下炕,爬椅子,再攀上桌子,一切行云流水般的麻利,可还是晚了,放苹果的手没等收回,娘已匆匆破门而入。
一切静止下来,只有煤油灯的火焰闪闪烁烁,我呆呆地站在桌子上,娘直直地盯着我。我两手紧紧地握着变松的裤衩边缘,越握越紧。或许因为用力,瘦弱的我灯笼架般的筋骨清晰可见,油灯的光把我投射到墙上,细脚伶仃的。
我的恐惧和委屈在娘慢慢靠近桌子时暴发了,我突然放声大哭,无所顾忌。我释然地迎接即将要来的狂风骤雨。让我猝不及防的是,娘一把把我拽进怀里,搂得紧紧的,突然一声也大哭起来。当娘红肿着眼帮我擦泪时,我瞬间感觉一世界的温暖把我淹没。那天晚上,我蜷缩在娘的怀里睡着了,睡梦中我又望到了我家的柳树上挂满了一树的红苹果……
对于娘从暴怒到温情的突然转变,我感到非常不解,直到后来的一天,我也做了母亲。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