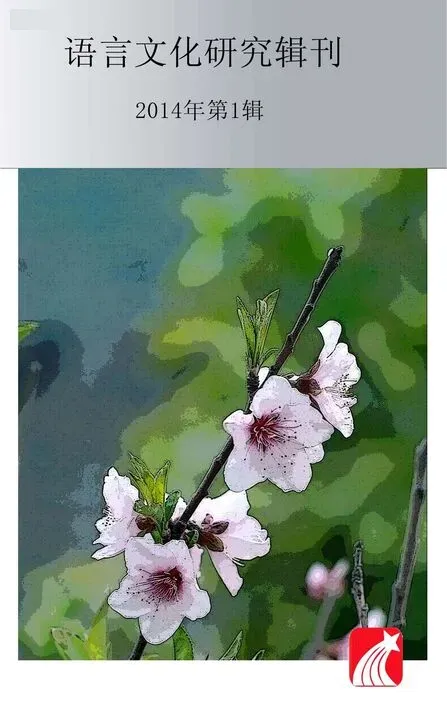从吟诵到凝注:sēma观照下的欧洲艺术分野
从吟诵到凝注:sēma观照下的欧洲艺术分野
陈中梅先生在分析荷马史诗对后世欧洲认知史的影响时,提出塞玛 (sēma)作为逻各斯 (logos)和秘索思 (mythos)两大元概念之间的链接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本文借鉴陈先生的学术视角,力求通过分析荷马史诗,展现在塞玛 (sēma)观照下欧洲诗歌艺术和视觉艺术两大形式的分流和对抗,提出其对构建东西方艺术总论的重大意义。
sēma logos mythos 诗歌艺术 视觉艺术
一 引言
陈中梅先生在解析欧洲文化基本结构时,提出荷马史诗中的塞玛 (sēma)可以作为秘索思 (mythos)和逻各斯 (logos)的链接点,从而将欧洲认知史推至荷马史诗。同样,我们也可以在对塞玛这一核心概念的梳理中,觅得欧洲艺术发展的一些线索或者先兆。
二 塞玛观照下的欧洲艺术分流
根据 《利德尔 &斯科特希英大辞典》①Henry George Liddell,Robert Scott,Roderick McKenzie&H.S.Jones,A Greek-English Lexicon(9th Revised edition),Clarendon Press,1996.,sēma有如下释义:②参见 《Liddell&Scott希英大词典》I-Pad版 “sema”词条 (Ancient Greek:Apps version)。(1)sign or omen(标
记或示兆);(2)sign by which a grave is known(筑坟之记号);(3)token by which any one's identity or commission was certified(身份或任命之信物)。格雷戈里·纳吉教授(Gregory Nagy,1942—)在 “24小时阅读古希腊英雄” (The Ancient Greek Hero in 24 Hours,2013)①Gregory Nagy,The Ancient Greek Hero in 24 Hours,The Belknap Press,2013.课程的 Hour 7中,援引大量文献和艺术品,探讨塞玛在荷马史诗中的含义及其功用,重点分析了 《伊利亚特》第23章中各位阿开亚人首领参加车赛的段落,指出塞玛是阿基琉斯和帕特罗克洛斯在人间的最终印记。在儿子安提洛科斯出赛之前,睿智的长者奈斯托耳叮嘱道:“然而,高明的驭手尽管策赶相对迟缓的驭马,却总把眼睛盯住前面的标杆,紧贴着它拐弯…… 我要告诉你一个醒目的记号,你不会错过。”②[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第23卷),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28页,第322—326行。对此,纳吉教授指出,“此地标充作车赛的拐点,而车赛正是帕特罗克洛斯葬礼竞技的高潮”③英文原文为:“As we will learn from the text,this landmark is meant to be used 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course of a chariot race that is being planned as the culminating athletic event of the Funeral Games for Patroklos”,Hour 7 of“The Ancient Greek Hero in 24 Hours”.参见 https://courses.edx.org/courses/HarvardX/CB22x/2013_Spring/htmlbook/0/,2013-05-12。,“正因战死的帕特罗克洛斯的事迹为今人所吟诵,那位远古的无名英雄方可显名”④英文原文为:“That is because the unnamed hero from the distant past becomes a named hero from the immediate present of the Iliad.That hero is Patroklos,and he died just now,as it were,in Iliad XVI”,Hour 7 of“The Ancient Greek Hero in 24 Hours”,参见:https://courses.edx.org/courses/HarvardX/CB22x/2013_Spring/htmlbook/0/,2013-05-12.。纳吉教授从部族英雄崇拜仪式的角度,运用人类学与语言学的方法,论证帕特罗克洛斯是 《伊利亚特》流布过程中阿基琉斯的镜像和代言人。阿基琉斯作为“在场”英雄,通过礼葬和祭奠挚友帕特罗克洛斯,将古老的史诗传统和鲜活的部族勋业合为一体,赋予其流传后世的品质。参加葬礼并角逐车赛的诸位英雄,以竞技的方式播散死去英雄的功业,在他们荣归故土后也在子孙面前重新演绎这一段悠远的悲歌。由此看来,阿基琉斯所持实为诗歌艺术理念,即古老的传唱艺术。往昔的事迹和人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没无闻,只有通过世代口耳相传和四方吟诵助其载入史册。荷马史诗文本的修订和传播,不也多亏数代先辈的辛勤劳作?
当然,阿基琉斯并非等到挚友离世后才突发吟诵往昔功业的念头。早在奥德修斯等人前往说服其重返战场之时,他就在独自吟诵。“他们行至慕耳弥冬人的海船,傍临营棚,发现阿基琉斯正拨弄竖琴,愉悦自己的心魂 ……其时,他以此琴愉悦心魂,唱诵当世的英雄,帕特罗克洛斯独自坐在对面,静默,等待埃阿科斯的孙子唱完他的段落。”⑤[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第9卷),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第185—191行。阿基琉斯骁勇善战,乃阿开亚人中第一战将,此时也在歌咏心目中的英雄,扬其声名使之不坠,而他的挚友帕特罗克洛斯静坐一旁聆听,准备接续唱诵下一个段落。此处的描写引人深思:英雄在吟诵之时,听众只有一位,而且是惺惺相惜的挚友,而这唯
一的听众也随时准备接替英雄而唱诵自己熟悉的段落。作为古老的诗歌艺术形式,传唱其实蕴含了现代文艺理论中的很多论题。传唱者和阅听者之间的角色互换,让我们想起杜尚装置作品中包含的艺术理念。德里达的 “播撒”(la dissémination)和 “分延”(la différance)看似玄妙,却可在史诗传唱的田野调查中觅得痕迹。对读者接受状况的考察,正是将书面文本和口头文本重新汇流的尝试?细细品味这一场景,结合上文车赛中提及的塞玛,我们大体上同意纳吉教授的论断。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借助塞玛蠡测西方诗歌艺术的源起和发展。“告诉我,缪斯,你们居家奥林波斯山峰,女神,你们总是在场,知晓每一件事由,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只能满足于道听途说的传闻。”①[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第2卷),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第484—486行。缪斯女神之所以能够传授诗歌,全仗她们 “总是在场”(pareste)。神可以长生不老,突破时空的局限,全知全能地调配一切可供吟诵的材料,并借此得到世人的尊崇和膜拜。“总是在场”的优势令人类自怨自艾,徒唤奈何。“雕刻师是一类工匠,诗人则是一类弹唱者,前者的活动纯属人类的活动,而后者的活动则是受到诸神的启发,甚至连在希腊哲学家中,非理性的与神秘的成分最少的亚里士多德也说:‘eutheon e poiesis’”②[波兰]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版,第87页。。神赋论长期流布,即便到了今天,仍然不时改装登台。当然,人类也非束手无策,塞玛作为解困之方应时而生。虽然个体的生命有限,但代代相传的吟唱方式,完全可以克服这一难题,将古往今来可歌可诵之事沉淀并加以发扬。若依靠世代传诵充实群体记忆的宝库,我们自然用不着将一切灵感寄托于神灵的护佑,神赋论终将让位于摹仿论。“宙斯给我俩注定可悲的命运,使我们的行为,在今后的岁月,成为后人诗唱的歌谣。”③[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第6卷),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第357—358行。作为当事人的海伦,清楚地知晓自己的行为可以超越时空,为后世所熟记和唱诵。功业和旧事,不但为史诗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还成了悲剧作家挖掘人类生存意义的保留地。“起初,诗人碰上什么故事就写什么戏,而现在,最好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几个家族的故事。”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8页。文学自主意识的苏醒,让古希腊悲剧作家将心中的哲学观和人生观灌注于作品之中,在观众耳熟能详的文学素材中提炼出全新的意义。同一题材由性情迥异的悲剧作家处理,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摹仿取向和层次。对传统极为看重的古希腊人,正是依靠这样的集体记忆一步步摆脱对神赋诗篇的笃信。
如果说 《伊利亚特》中的塞玛为我们勾勒了古希腊人依靠族群的力量接近艺术的尝试,《奥德赛》中的塞玛更多展示出作为个体的古希腊人对艺术的趋近和逼视。奥德
修斯造访泰瑞西阿斯的魂魄,探听自己的前途,后者告诉他:“你要带上造型美观的船桨,出游离家,直至抵达一个地方,那里的居民不知海洋,吃用的食物里不搁咸盐,不知头首涂成紫红的船舫,不识造型美观的桨片,那是海船的翅膀。我将告诉你一个醒目的标记,你不会错闪。”①[古希腊]荷马:《奥德赛》(第11卷),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第121—126行。比较此处的 sēma(标记)与帕特罗克洛斯葬礼上的车赛拐点着实有趣。尽管两者都暗指 “坟墓”,体现出部族英雄崇拜和人神关系这样的原始宗教意蕴,但在艺术指向上却有所不同。车赛拐点作为亘古不变的参照物,兼具祭祀和铭刻双重功能。奥德修斯要寻找的标记,则是标示身份的艺术特征。
古希腊人在探求艺术和哲学的过程中,除却世代吟诵的诗性方式外,还有凝注和观照的造型方式。“在希腊人心目中,建筑、雕刻与绘画三者彼此密切相关,但此三者与诗歌、音乐、舞蹈则全然无关。简单地说,前者是观赏的,后者是抒情的。”②[波兰]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洋古代美学》,刘文潭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年版,第36页。其实,即便在 《伊利亚特》中,奈斯托耳也叮嘱儿子 “总把眼睛盯住前面的标杆”。奥德修斯返乡途中,亲历各处风情,若真遵从泰瑞西阿斯的吩咐,带上船桨出游,找寻那一个醒目的标记,未尝不可视作对造型艺术的追寻。“头首涂成紫红的船舫”和 “造型美观的桨片”,不正是对典范造型的提炼吗?克服生命局限的方式,不单单是世代的唱诵,还有实时即刻典型形象的描摹和塑造。莱辛在 《拉奥孔》中对诗画关系的论述,正是这两种艺术探询方式的回响。“这种虚伪的批评对于把艺术专家们引入迷途,确实要负一部分责任。它在诗里导致追求描绘的狂热,在画里导致追求寓意的狂热。”③[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奥德修斯与妻子和父亲相认的段落,若是细细品味,不乏对这两种艺术探询方式的注脚。“如果你真是奥德修斯,我的儿子返归,那就请出示明证,让我信你是谁。”④[古希腊]荷马:《奥德赛》(第24卷),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92页,第328—329行。莱耳忒斯不轻易相信长相,要求儿子拿出明证,这正说明他在将眼前之人与心目中的儿子比较,看能否一一吻合。造型作品面世前,艺术家心中也会有一个模型,将其典型化和场景化,就是一件件成品。虽然此处涉及的是认知意识,其实蕴含了丰富的艺术论题。将秘索思和逻各斯两个元概念涉入其中,就能清晰地察觉造型艺术中包含的观察、比较、呈现等具有逻各斯质素的向度。“因为精制的床中,有一特殊的机关,由我自己,而非别人造出。庭院里有一棵遒劲、茁壮的橄榄树,叶片修长,繁茂 ……这些便是床的特点,我已对你描述,但我不知,夫人,我的睡床是否还在原处。”⑤[古希腊]荷马:《奥德赛》(第23卷),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52页,第188—203行。裴奈罗佩定要考验奥德修斯,直到后者将婚床的特点一一说出,才与之相认。我们知道,奥德修斯和阿基琉斯在
荷马史诗中虽说都是英雄,性格特征和个人气质却迥异。阿基琉斯刚烈骁勇,自己吟咏前世英雄的业绩,也将成为后人诗歌艺术的素材,而奥德修斯多样的身份和跌宕的经历却为我们打开另一扇大门,呈现出心智的力量。作为能工巧匠,奥德修斯在 《奥德赛》中出场,返乡前听闻且讲述自己的业绩,而一旦踏上故土,却要将其王者的身份隐去,靠探察和智谋完成对向自己妻子求婚的人的复仇,重登王位。令人玩味的是,最后奥德修斯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竟然是作为造型艺术成果的婚床,而婚床从未被挪动的事实是否也暗示了奥德修斯将凭造型艺术家的身份享受后世的尊荣。进一步讲,作为集宗教情怀和直观特质于一体的诗歌艺术,将为人类 “管中窥豹”以测天机的造型艺术让渡出大片空间。
结合柏拉图对床的著名隐喻,我们是否可以说:诗歌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分野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初现端倪?或者说,诗歌艺术和视觉艺术,在突破古希腊人神分界的努力中各自发挥其功用,沉稳有力地将摹仿论推上历史舞台,成就了经典的古希腊文艺观。“在审美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之间,他们未加区分。他们用 theoria这个字,同时表示审美的观赏和科学的探究,这个字的原意就是 ‘观看’。”①[波兰]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洋古代美学》,刘文潭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年版,第47页。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哲学的系统梳理和归置,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的是这两种艺术形式。如果说古希腊诗歌的传承和吟诵仍需依靠神赋的权威,那古希腊造型艺术的勃兴则为人类思辨和分析提供了范式和学理依据。观诸后世,这一分工至关重要,可为西方认知史上 mythos和 logos之争提供功用角度的诠释。
三 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由荷马史诗,我们探寻西方艺术和文学的源头,与神赋论和摹仿论并辔徐行。反观中国文化,作为视觉艺术的文字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给诗歌艺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文字本来只是用以抒情指事的符号。可是汉代人却越来越关注它本身 …… 同理,文字组合而成一篇文章,本来也只是用来抒情指事。但是,如果作者读者都期待在指涉、感染、抒情诸功能之外,更多地关注诗歌的功能,把文句写得更华丽,便形成了对文学美的追求。”②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上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44—45页。
古希腊的诗歌艺术作为最后的先验阵地,逐步隐入传统之中,视觉艺术经过自身的涤荡和沉浮,走向了两极分化的道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现
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些充满张力的一组组对举都可以完美地展现两者的消长。换一个角度考察,这些历史思潮的更迭自然也可以视作后者对前者的压制和前者对后者的反制。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将诗歌艺术和造型艺术完美地融入汉字之后,培育出诗、书、画一体的艺术审美情趣,熔铸了传统文化中的文艺基质。龚鹏程先生在 《中国文学史》中多次强调历史中的审美活动,其实就是想唤起国人对中国文学自身蘖生和荣华的重视。“文学艺术只是诸艺术之一,其他艺术并不利用文字或主要不依文字……可是在中国历史中它往往逐渐变成文学艺术。”①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下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456页。文、艺融合,固然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但我们是否因此而错失了将两种艺术方式并举和参发的机会?从更高的层面讲,中国文化没有走上西方文化的发展道路,这是否也是一个动因?
比较两种文化中不同艺术形式的歧变和融合,考察漫长历史进程中诗歌艺术和造型艺术在两种社会机体中的延伸向度,可以给我们构建东西方艺术总论提供极大助力,从而推动两种文化的深层次比较和融合。长期以来,将东西方对立的思维模式占据统治地位。细细想来,这是否也让我们走了很多弯路,步入很多误区?在认知和审美的原初阶段,东西方之间的共鸣会大大出乎我们意料!
尹 晟[1]任 西 娜[2]
([1]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2]北京城市学院基础学部,北京 100083)
From Recitation to Reflection:The Western Art in Light of“sēma”
Chen Zhongmei holds that with“sēma”functioning as the linking point between“mythos”and“logos”,the western cognitive history can thus be traced back to Homer.In light of the concept of“sēma”,the western aesthetic history can be reexamined by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epar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poetic art and visual art.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art form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art theory.
sēma;logos;mythos;poetic art;visual art
Yin Sheng[1]Ren Xina[2][1]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048;[2]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Beijing City University,Beijing,100083
尹晟 (1982—),男,汉族,四川成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读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教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古希腊文学研究、英语教学法等。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05号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 (100048)。Email:tomsword@126.com。
任西娜 (1980—),女,汉族,河南南阳人,英语教育硕士,北京城市学院基础学部英语教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法等。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69号北京城市学院基础学部 (100083)。Email:xina_ren@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