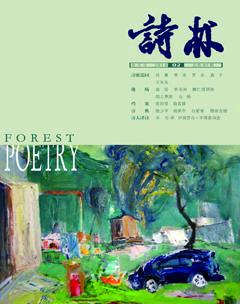在向心力下的诗歌写作
耿玉妍
我最早读到朱永良诗歌,是在那本主要由黑龙江诗人构成的《九人诗选》里。这本以地域为标的诗集,把朱永良建构成北方诗歌版图的一个构成部分,标举他与黑龙江诗歌写作的同质性以及整个黑龙江诗歌的族群性。从阅读来讲,这本书确乎提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路径。因为把中国北方诗歌看做整板一块的文学群落,某种程度上符合实际并可以凸显北方诗歌的“质”,高屋建瓴地划分中国诗歌版图。正如萧开愚所分析:“北方人的诗主体表达判断,语言所负担的认识内容优先于语言的自身内容,哈尔滨人的诗较多示人以思虑和犹疑,毕竟指向决断。”这种处理世界的方式我们在很多黑龙江诗人那里都可以感受到。然而这样的地域诗学一旦过于强调,势必会淡化诗人的独特声音,朱永良就是这样一个嵌在黑龙江诗人群里又有自身独特发声系统的诗人。要进入朱永良的诗歌世界,我们要暂且搁置《九人诗选》所指引的地域学方向,而从朱永良诗集《另一个比喻》的个体诗学入手。
我对这本诗集里诗歌主题的印象是,它们似乎遵循着类型学原则,呈现一种聚合的版图。总体可以分为这几个:对生活的回忆,如《雨后》《也有的形式》《雪地》;对语言的思考,如《我献出了一个下午》《音乐和死者》;对时间的沉思,如《一个人》《灰尘如时间》《时间的流逝……》;以及其他内涵不一的即兴诗。这些主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诗人写作的疆域,但并不全是,剩下的是对主题的展现方式。如果说潘维等诗人所代表的“江南诗歌”看重诗歌的表面意象,用喻体本身的绵绸质感支撑起一首诗的美学主体的话,那么北方诗人朱永良就是典型的“地心引力式”的写作。在他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主题和缤纷呈现最终总是迂回地回到他最核心的表达。他的诗里存在一股向心力,所有的元素都被这个向心力吸引着,并以此作为它们存在的意义。换句话说,朱永良对诗歌有一种哲学的控制欲,诗歌在他的手下最终要回到认知的归宿上去。依照他的主题,我们可以勾勒出朱永良处理世界的某些诗学路径。而这些路径,又都指向了向心力的存在与其巨大的引力。
一、被内化的风景
作为古往今来诗歌中的重要元素,风景承担着很大一部分的诗意构成,朱永良的诗歌就尤喜以风景作为一首诗的外衣。以观看的方式和对象的特质为标准,我们可以把这里的风景分为两类。一类存在于他的窗外,诗人只能看或者听,而不能亲历的风景,比如《四月的下午》中那些“盖房子的人们和发了芽的树”,或者《1986年11月5日上午》中的“收获完了的田野”;另一类是亲历的、故事性的风景,多见于他回忆生活的自传式诗篇,如《春天的夜晚》中的“春天的凉风”和“道路、车辆、闪耀的灯光”。阅读这些诗歌我们会发现,诗人将所有笔下的风景都内化成内心感受的投射,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意象的重新阐释、改变、扭曲。然而诗人对这两类风景的定性和处理方式并不一致。看第一类诗,还以《四月的下午》为例:整个的下午没有声音/远处是盖房子的人们和发了芽的树/一只苍蝇飞进屋子/使我感到节气的分量。
抒情主体坐在室内,而风景在室外。“盖房子的人们和发了芽的树”是远远的,只占据抒情主体眼角膜的一角,主体是麻木的、冷漠的,超脱于外界,此时的风景只是一个概念,它引发倦怠。但一只苍蝇“飞进屋子”,使主体“感到节气的分量”,它打破了“窗子”的隔阂,也打破了主体的倦怠,主体感兴趣于与风景的联结。接着往下看:它停下翅膀,交叉着前面的两只脚/碰巧找到了敞开的那扇窗子/然后,把声音带向了别处。
苍蝇还是飞走了,把声音带到了别处,于是风景又退回了窗外,与主体隔着窗子观望,依旧互相不关心,依旧引发倦怠。独坐于窗前的抒情主体又回到了诗歌开头的心境——整个世界退回远方的孤独和麻木。
在这首诗里,风景与其说是形象性的,其实更确切地说是概念性存在。“远处是盖房子的人们和发了芽的树”此句唯有“远处”有效,标志风景的性质,其余都是填充物;而“苍蝇”仅仅是作为打破隔阂的使者存在,这个意象本身的主要特质作者没有用到。由此可以看到,对于这一类风景的内化处理,朱永良用的是掏空其客观内涵而赋予诗歌需要的特质的方式,这种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缘性的,是一个事物的外围特征。
在另一类风景的处理方式上,朱永良采取了另外的做法,如《春天的夜晚》:春天的凉风刮过二月的夜晚,/我的眼中是道路、车辆、闪耀的灯光/还有黑暗。我坐在车里,/看着这一切出现、消失……//我又想到: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时我看看坐在身旁的女儿:/在她十四岁的眼神中/有着一种纯真的宁静。
在此,诗人绵密地描述了周边的风景,但之后又直接抽离了它,转而对心境的抒写。风景于是有了通向内心之路的功能,是一种前抒情,指向抒情的准备工作。在这里,风景被内化成内心书写的一个段落。这一类型的风景内化是通过抽离、转向和拼接实现的。
朱永良对风景的兴趣总不长久,最终总会回到对内心的抒写,内心像一种重力拉扯着他的目光,而风景被当做媒介使用,被内化了。
二、被空置的时间
相比于物理学的客观时间,文学文本里的时间更多类似一种拉伸术和填充游戏,伴随着主体对对象、情感的体验而展开,展露一种立体的风情——时间犹如实物,可长可短可高可低,可以说,文学时间即回忆。红楼梦里黛玉唱完长长的《葬花词》,那边宝玉才经历了短短的几分钟,这就触目惊心地展示出文学时间的虚构性和主体性。在写于2003年的诗作《一个人》中,朱永良展现了一个时间从“文学的”过渡到“物理的”的心理过程:一个人经历过的一个个日子,/就像河水般不断涌现的时间,/它们连续地出现,又急切地消失,/仅仅成为他曾经存在的痕迹。//一个人无法再重新比肩它们,/一次落日就是一次永远的逝去。/这就像他唯一的出生,同时/也带来了必定死亡的结局。//这也是所有事物遭遇的命运:/从无到有,再归于无。/那难以计算的白天和夜晚/演绎着世界没有结局的变幻。//或许虚无比存在更接近本质,/或许虚无最终是唯一的真实。
在第一小节里,作者的时间是“一个个日子”,是主体的时间、体验的时间,代表着与时间同步进行的生活,和新鲜饱满的生命体验,但后来,它们“仅仅成为他曾经存在的痕迹”,时间内部的生命体验已经变淡了。而后面的“也带来了必定死亡的结局”展现时间的空洞性——从终极而言,时间无法带来任何东西,除了虚无。最后两节作者将时间观从生命体发散到所有事物,指明世界的空无。在这首诗里,作者展示了生命时间的饱满和主体性,但紧接着反驳了它,呈现时间空洞的本质。而在另一首诗《时间的流逝……》中,朱永良指出了时间的冷漠性和类似数学的精确性:时间的流逝就犹如看过的一页页书籍/不同的是,唯有它严格地遵守着页码的排列顺序。
作为一首诗的开头,它引领着这首诗的基调,这种置身事外的时间感觉贯穿着整首诗的抒写,时间,被打回原形成为基础的物质,被标上标号,形成顺序……而另一首《关于“世纪”一词》,处理“世纪”这种宏大的时间,作者依然是将它空置:与清朝变成民国,/民国变成共和国,/文言文变成白话文,/方言演变成普通话,/等等等等无关,/“世纪”只是个量词,/它只是有时好,有时坏,/仅此而已。
诗人漠视“世纪”作为实体存在的事件,掏空它的内涵,而认为“世纪只是个量词,仅此而已”。在虚无主义基调之下,诗人将宏大的时间“世纪”也空置成了一个物理学概念。其路径是将其空置,从而使得时间变为可观看的、有规律的,将时间本身与时间经验的主体性割离开来。朱永良的笔下,与文学时间的惯习相比,他的时间是被空置的,并且有数学的精确。
三、被延宕的历史
在另一些相比于玄思题材的冷静,略显温情脉脉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生活的轨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叙事成为中国现代诗坛的惯用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与抒情是不兼容的。侧重叙事的诗人比如于坚,与侧重抒情的诗人比如海子,他们所构成的诗歌路子基本没有交叉。在朱永良这里,可以看到叙事冲动与抒情冲动的冲突、争斗。因此与哈姆雷特的复仇冲动与沉思冲动的冲突相类似的,朱永良的文本里面同样表现出这两种相反冲动交织留下的痕迹——延宕。延宕即延迟,就是一个环节超过它所应该有的时间轨迹而延迟到另外环节的时间轨迹上去。在这种叙事性比较强、并且有诗人自传特征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回忆被延宕了。比如这首《雪地》:我和女儿离开那片雪地,/没有人的雪地又重归平静,阳光安详。/如果我们今天没到过这里/它的平静或许会持续一个冬季。/现在我们把快乐留在雪地上/快乐上面又爬满阳光。
在这首记录雪地玩耍的诗歌中,诗人在叙述完“离开”之后,开始自己漫长的延宕:他停留在“离开”这个动作上,开始漫想——假设今天没到过雪地,雪地会怎么样;而今天我们来过了雪地,雪地又会怎么样。可以看出其中论道的冲动打断了叙事的正常节奏,无限延长了“离开”这个动作。而在其早年的一首《雨后》里,这种轨迹的交叉表现得更为明显:你我相见是久日雨后的初晴,/回忆的雷声,渴望的闪电,/思念的绵绵细雨/刚刚成为过去。/你我的目光化作虹,/上面驶过音符、方块字/和神的旨意。
在这首戛然而止的小诗里,诗人记录了与知己见面的回忆,首先叙事“你我相见是久日雨后的初晴”,但紧接着开始用比喻来抒情“回忆的雷声,渴望的闪电”两行之后又回到叙事“你我的目光化作虹”,之后开始对此句的拓展“上面驶过音符、方块字和神的旨意”,叙事在此诗里只是引出抒情的工具,它们构成了骨架而填充以抒情的血液。可以看到朱永良的抒情冲动使得他数次打断自己的叙事进程,穿插进抒情的诗行,而叙事在几行之后又开始浮现,又穿插抒情,这样往复,构成了他诗歌中自传书写的延宕。
四、被否定的语言
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已经超越了它基本的表意功能,而成为我们存在于世的方式。我们通过语言思考、表达,形成精神的自我。一位诗人与语言的亲缘关系本应更为密切,因为语言在诗人的手中是与精神最贴合的传达。但在朱永良的诗中,可以看到他对语言的复杂态度——对语言的天然吸引力的逃离,对语言价值的否定。如在这首小诗《我献出了一个下午》中:为了写出一行诗,我献出了一个下午。/但又说回来,那并非完全真实,/首先,下午不属于任何人;/其次,我献出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目光,双手,一些平凡的感情/以及纸和笔。如果说这个唯一的/下午,拥有了我和那行诗/那可能更接近发生的事实。
“下午”压倒了“诗歌”而成为更高的真实,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诗人对“诗行”价值的否定。这首诗里的价值逻辑是这样的:现实比诗行真实,诗行与我一样不真实,可以虚化。在这里,诗行所代表的语言成了生活之下的某种价值物,诗人对语言进行了价值虚化。
正是由于词语取代了真实,构成了今日生活的主要面貌,才同时异化为一种戕害性力量。而人在此是无法逃离的,只能默默去承受。这首诗里作者展示了语言与人的冲突,因此可以说,在朱永良这里,语言是被虚化的、否定的。他并非如尼采般接受语言巨大的塑形力量,而从语言的虚妄与异化出发批判它。
而不管是对风景的内化、时间的空置,或者延宕的手法和对语言的否定,根本上都离不开朱永良诗歌里巨大的向心力—— 一种内向的视角和对沉思的耽爱。朱永良在处理外在题材譬如风景或者历史时候的心不在焉和有意无意的内化都指向了这一点。诗中无处不在的玄思更勾勒出朱永良其人的北方特色。至于对时间和语言的处理,也从根本上暗示他对于世界表象的不信任,和对于更深层世界的热爱。他是一个游移的、内向的,在巨大向心力之下写作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