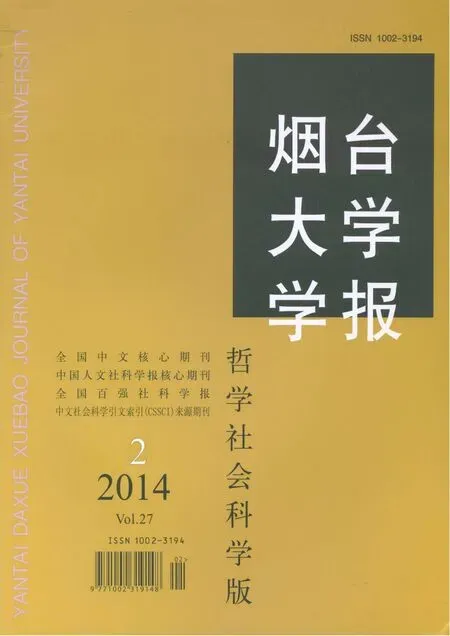命运反讽、荒诞梦幻与象征手法
——评内洛尔《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之艺术特色
庞好农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命运反讽、荒诞梦幻与象征手法
——评内洛尔《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之艺术特色
庞好农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命运反讽可以分为柳暗花明型命运反讽、一见钟情型命运反讽和好意误解型命运反讽。这些命运反讽都妙趣横生,具有逆期待性和隐含性。内洛尔笔下的梦幻充满荒诞,荒诞映衬着梦幻,并使梦幻与现实水乳交融。小说中使用了多转性象征、启示性象征和寄予性象征,讽刺社会阴暗面,赞颂人间真情,体现了作者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内洛尔在对命运反讽、荒诞梦幻和象征手法的创新和探索中导入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促进了美国黑人小说艺术特色的多元化。
格洛利娅·内洛尔;《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命运反讽;梦幻;象征手法
格洛利娅·内洛尔(Gloria Naylor,1950-)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著名的黑人小说家。迄今为止,内洛尔已经发表了六部小说,即《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1982)、《林登山》(Linden Hills,1985)、《妈妈日》(Mama Day,1988)、《贝利咖啡馆》(Bailey's Café,1992)、《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The Men of Brewster Place,1999)和《1996》(1996,2005)。此外,她发表的文集主要有《妈妈,黑鬼的意思是什么?》(Mommy,What Does Nigger Mean?,1986)和《夜晚的儿童:从1967年至今的黑人短篇小说集》(Children of the Night:The Best Short Stories by Black Writers,1967 to the Present,1995)。内洛尔的代表作是其第一部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该小说于1983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之最佳处女作奖,并于1989年改编成电影,轰动一时。该小说采用命运反讽、荒诞幻境和象征手法,叙述了谋生与艰辛、繁衍与生存、爱情与背叛、光荣与梦想、善良与奸诈等与黑人社区生存状况息息相关的事件,揭示人与人之间、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展现美国黑人妇女在后民权运动时期的生活窘境和种族心态。本文拟从命运反讽、荒诞幻境和象征手法三个方面来探索内洛尔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写作手法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命运反讽
文学作品中的命运反讽,也称为情景反讽,不受读者主观意识的控制,通常发生在读者的意料之外,故意使读者的期望值落空的一种写作手法。正如赵毅衡所言,“情景反讽(situa-tional irony)是意图与结果之间出现反差,而且这个反差恰恰是意图的反面。”①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页。此外,在一定场合里,情节的意外转折与意图受阻也会形成命运反讽。“命运反讽包含复杂的元表征推理,它要求对与期待相反或对立的事件进行表征。尽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命运反讽进行了定义,但都突出其本质特征逆期待性。”②葛晓芳:《论〈理查德·科里〉中的命运反讽》,《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3期。小说中命运反讽的恰当运用不仅有助于增强小说的鉴赏魅力,而且还会加深小说的思想内涵。卢卡·里罗(Luca Lillo)将命运反讽主要分为六大类——“戏剧型、毁损型、荣耀型、窘境型、巧合型和二十二条军规型。”③J.Lucariello,“Situational Irony:A Concept of Events Gone Awa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94,(123),p.129.内洛尔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卢卡·里罗的六类反讽,并且根据小说情节发展的需求,设置三类命运反讽:柳暗花明型命运反讽、一见钟情型命运反讽和好意误解型命运反讽。
柳暗花明型命运反讽具有极强的戏剧性,是描写人陷入困境或绝境后意外获得解困机遇或方式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④K.Newmark,Irony on Occasion from Schlegel and Kierkegaard to Derrida and de Man,New York:Fordham UP,2012,p.65.这类命运反讽“以荒诞离奇的背景和事件为起点,在人物、情节‘顺理成章’的进展中,折射出世人的种种心态,凝聚了对人生的感喟与品味、对生命的困惑与追求,淋漓尽致地暴露了现世人生中普遍存在的乖张与谬误。”⑤黄擎:《论当代小说的情境反讽与意象反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玛蒂·迈克尔(Mattie Michael)独自带着吃奶的婴儿巴兹尔(Basil)租住在一间旧房子里,饥饿的老鼠不但咬破婴儿的奶瓶,而且还咬伤了巴兹尔的脸。因此,为了儿子的安全,玛蒂在惊慌中退租房子,背起儿子,拎着行李,满镇子找房子。找了一整天,一无所获,眼看天要黑了,她又住不起旅店。因此,玛蒂打算坐汽车回娘家。正当她去打听汽车站的位置时,路边有人对她说,“如果你想到汽车站,你就走错了方向。你走的方向是火车站。汽车站在另一个方向。”⑥G.Naylor,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New York:Penguin,1983,p.30.本文引自该书的内容,此后只标页码,不另做注。搭话的老奶奶问她昨晚在哪里住的,又探听她是否结婚。正当玛蒂非常反感的时候,那位老奶奶却出乎意料地邀请玛蒂带着孩子到她家去住。这是小说中的第一次转折性命运反讽。玛蒂和孩子入住老奶奶家,老奶奶不提房租和伙食费的事。玛蒂主动去问,老奶奶却说,她的房子不是用来出租的,并叫她把该交的房租积攒起来,便于以后买下老奶奶的房子。这是第二次转折性命运反讽。表面上显得强势冷酷的老奶奶一刹那间变成了玛蒂母子的福星和恩人。玛蒂偶然问路遇到的老奶奶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位老奶奶先是提供了栖身之处,后是解决了房子所有权问题。这个反讽挑战了人间鲜有好人的消极社会心理,有助于消解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感,同时也强化了爱丽丝·沃克关于黑人妇女互助自救的学说。
一见钟情型命运反讽是指男女初次见面后迅速坠入情网,但结局却违背了初衷的情景所引起的讽刺。这类命运反讽“展现人物所面对的人生无法回避的矛盾,如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小说中的人物在挣扎、抉择、奋斗,却越努力越远离希望,越渴望解决矛盾,越深陷于矛盾的漩涡,最终落入种种难以言明的困窘境遇。”⑦黄擎:《论当代小说的情境反讽与意象反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黑人妇女艾妲·梅·约翰逊(Ida Mae Johnson)第一次来到布鲁斯特街聆听玛蒂教堂的布道,一下子被才华横溢的莫尔兰德.T.伍兹牧师(Moreland T.Woods)迷住,觉得自己的白马王子终于出现了。就在艾妲央求玛蒂把自己引荐给伍兹牧师的时候,在台上布道的伍兹牧师也被艾妲惊艳的美貌所吸引。教堂活动结束后,伍兹牧师主动提出开车送艾妲回家,后又邀请她去喝咖啡。他们的情感迅速升温,这对郎才女貌的中年男女很快到旅店开房。当读者期待他们的情感进一步升华的时候,火热的爱情却从高峰一下子跌到了冰点。原来,艾妲追求的是美满的婚姻,而伍兹牧师追求的只是一夜情。当伍兹牧师开车送艾妲回布鲁斯特街时,他几个小时前表现出来的儒雅举止烟消云散,不仅不再对艾妲百般殷勤,更没有了为其开车门的绅士风度。艾妲刚一下车,伍兹就开车一溜烟地跑了。艾妲也一样,连对绝尘而去的小车都没有回顾一眼。内洛尔用一段意识流描写披露了艾妲的心境:“她猛烈地摇摇头,摆脱自己的幻想,但是一股强烈的恐怖感袭上心头,感觉腿像铅一样沉得迈不开步。如果走进这条街,她想到,我就永远不会回头。我再也不去了。啊,天呀,我好累呀——太累了。”(p.73)其实,艾妲的话语不是指身体累,而是指心累。外表华丽而心灵肮脏的男人又一次欺骗了她的情感。这段命运反讽的描写抨击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性剥削,同时也讽刺了女性注重男性外表和社会地位的虚荣心。
好意误解型命运反讽是指在一定的社会语境里某人对他人的好意,却被他人误解,从而遭致磨难或伤害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类命运反讽的作者通常在生活常态的描写中添加某些变异性的情景描写,给人物的行为表现笼罩上了某种神秘、荒诞的奇异色彩,在常态与变态情境的背离中,营造出反讽语境,揭露白人故意不作为所造成的黑人社区恶劣治安环境。在小说的第六章“两位”里,洛兰(Lorraine)参加一个晚会后,刚走回布鲁斯特街,就被以C.C.贝克为首的七个街头流氓拦住并被拖进背街,遭遇到了惨无人道的轮奸。天快亮时,洛兰渐渐清醒过来,艰难地在地上爬行。布鲁斯特街看门人本杰明(Ben)醉醺醺地从家门走出来,蹲在一个空垃圾箱上。满身鲜血、衣衫不整的洛兰一步一步地向他爬过来;洛兰立起身来,本杰明惊讶万分,正要说“天呀,孩子,你怎么啦?”(p.172)。当读者以为洛兰准备向本杰明求救的时候,她却用砖头向本杰明的面部砸去,打掉了本杰明的几颗门牙;未到本杰明反应过来,洛兰又用砖头砸向其头部,使其血溅一地。原来,洛兰被轮奸后,精神恍惚,进入了神经质般自我保护的癫狂状态。当本杰明出现时,她以为又是一名轮奸犯出现了,因此不顾一切地拼死反抗。结果,她把同情她,试图施救于她的看门人活活打死了。这段命运反讽揭示人在精神恍惚状态中可能犯下的悲剧,抨击了美国警察在黑人社区的不作为状态。之前,洛兰和本杰明的关系非常亲密,情同父女,在精神上互相慰藉。洛兰过失杀人的悲剧也加深了这个命运反讽的社会抨击力度。
因此,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内洛尔所设计的命运反讽通过“命运的捉弄”来营造讽刺意境,具有很强的逆期待性,情节发展不仅与故事中人物的期待背道而驰,故事的结局也超越了读者的惯性期待,从而使读者的心理受到巨大的冲击,深化了反讽的伦理寓意。此外,内洛尔作为作者在小说中并不直接表明对某个人物或某个事件的看法,而是借助命运反讽来讲述故事,并将其真正的意图隐含其中,希望读者或听者能够根据其文字表达的字面意义来推断出作者的真正的写作意图。内洛尔笔下的命运反讽与故事情节有机结合起来,给该小说增添了妙趣横生的艺术魅力,消解了以隐喻为基础的传统修辞学理念。实际上,内洛尔所采用的命运反讽手法追求的是一种整体性的艺术效果,在小说的主题立意、情节设置、寓意彰显和虚实结构等方面建构了隐蔽性极强的内在张力,赋予小说以多元化的阐释空间。内洛尔不仅在美学层面的意义上运用命运反讽,而且还使它在哲学层面上得到升华,从而使读者对自我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一种哲理性反思,激发起人们对生存缘由和精神追求话题的新探索。
二、荒诞梦幻
梦是指人在睡眠时身体内外的各种刺激或残留在大脑里的外界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景象活动,有的梦在觉醒前就被完全遗忘或部分遗忘,有的梦在觉醒后仍能清晰地记得。梦的内容可能是过去生活场景的重现,也可能是未来生活的臆想,还有可能是颠覆现实的潜意识幻境。①T.Cˇalovski,Building A Dream,Skopje:St.Clement of Ohrid,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2011,p.65.高松认为,“现实之我的现实境遇与虚构之我的感知对象之间产生了某种冲突。但现实之我不会永远清醒,当做梦时,它便暂时失去了体验现实的能力,自我也就脱离了现实境遇,进入梦境之中。”②高松:《梦意识现象学初探——关于想象、梦与超越论现象学》,《现代哲学》2007年第6期。梦幻描写是内洛尔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叙事全局来看,梦境是插入的话语段落,它发生于小说的主叙事层内部,但又同时在语义和寓意上独立于这第一层面。“这种独立性不是绝对的,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一个支配自由间接引语的叙事者的介入。在讲述梦境时,不管叙事者原来处于全知全能的视角还是以什么样的时态讲述梦境,一旦进入了梦的叙事层,叙事者就与做梦者取得了话语身份上的统一。”③杨铖:《文学现代性框架内的梦境叙事研究》,《法国研究》2011年第4期。内洛尔在这部小说里把现实与梦幻杂糅起来,刻画黑人女性的心理状态,揭示美国黑人妇女的生存现状。这种梦幻描写手法使作品形成一种似梦非梦、似真非真、虚虚实实、真假难分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该小说中的梦幻根据其荒诞性可以分为三类:力比多梦幻、醉态梦幻和解困梦幻。
力比多梦幻是指人的性本能、性幻想和性冲突在受到世俗压抑后在潜意识层里形成的一种本能反应,通常以梦为表现形式来释放人的性臆想或性冲动。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第一个故事“玛蒂·迈克尔”里,玛蒂把儿子抚养成人后,儿子长期在外工作。一天夜里,玛蒂梦到自己在猛烈地奔跑,似乎在躲避高大的竹林和荆棘丛生的杂草里的什么东西。她觉得肚子很饿,总感觉有个看不见的东西一直在追她,其内心恐惧不已。她把一截甘蔗杆拿在手里,放在嘴里咀嚼,竭力想止住肚子的饥饿感。她想在追她的东西抓住她之前,拼命地吃甘蔗杆。她感觉到那个东西正穿过高高的杂草,离她越来越近了,重重的脚步声撞击她的耳膜,她的心也随之砰砰地跳得厉害。当那个东西扒开盖在她身上的草时,她发出了惊叫声。原来那个东西是其前男友布奇。他微笑着,眼睛发亮,他蓝色的眼珠在眼眶里疯狂地转动。他竭力撬开她的嘴,把她嘴里嚼烂的甘蔗渣抠出来。他掐住她的脖子,不让甘蔗汁流入她的喉咙。她张开嘴,叫呀叫——惊叫声在她耳际回荡,使她头疼不已。梦醒后,玛蒂全身发抖,惊叫声似乎仍在耳边回荡,这声音原来是在房间里正响个不停的电话声。这里,内洛尔把梦境与现实的衔接做了完美的描写。房间的电话声诱发了其梦境中的惊叫声,随着梦的渐渐清醒,才发现使她头崩欲裂的惊叫声源自电话铃声。玛蒂的这段梦境与她早年的初恋创伤密切相连。玛蒂第一个情人得到她的身体后就抛弃了她,使她终身失去了再爱其他男人的信心和勇气。但是,性渴求是女人生理上的正常反应。在早年,布奇是用请她吃甘蔗的方式诱奸她的,甘蔗汁就演绎成其性需求的象征。梦中,布奇不准她咽下甘蔗汁的暴行表明了父权制社会里男人的自私和对女人幸福的漠视和践踏。
醉态梦幻是指人受到社会打击或压抑后通过饮酒入醉的方式进入潜意识层的心理活动,产生在清醒时无法生成的潜意识幻境。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本杰明(Ben)是布鲁斯特街上几幢楼房的看门人,也是最早来到这条街道居住的人。本杰明以前居住在美国南方的一个村庄,和妻子伊利维亚(Elivia)居住在一起,生下了一个女儿,由于乡下医疗条件差和医生的种族偏见,女儿在出生时落下跛脚的残疾。本杰明夫妇靠租种地主克劳德(Clyde)的土地为生,本杰明的女儿还未成年时就被好色的克劳德雇为家佣。克劳德时常留宿本杰明的女儿,本杰明觉察到了地主对其女儿的性侵犯,但是为了从地主那里租到地,只好忍气吞声,没有站出来维护女儿的权益。后来女儿不堪克劳德的性折磨,离家出走,到孟菲斯城当妓女去了。她走后也没有给本杰明留下通讯地址。克劳德对本杰明女儿的出走恼羞成怒,拒绝把土地再租给本杰明。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妻子伊利维亚也离家出走,嫁给了他人;本杰明在万般无奈中离开南方,来到北方某城市一个名叫“布鲁斯特街”的地方居住。本杰明深爱自己的女儿,却听凭地主对女儿的折磨,他感到万分的羞愧,觉得自己对不起女儿。女儿被地主侮辱的画面经常出现他的脑海里,他只好借酒浇愁。只有在醉态中,他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只有在醉态中,他才能听到女儿问候他的话语——“早上好,爸爸!”从小说一开始到结束,他一直处于醉态的梦境中,连最后的死亡也是在他醉酒的梦境之中。他的醉态梦境揭示了美国种族主义社会的黑暗,白人不但从经济上剥削黑人,而且还从人格上侮辱黑人,从精神上打垮黑人,导致黑人在神志清醒的时候痛苦万分,只有在醉态的梦境中才能艰难度日。
解困幻境是指人在世俗生活里受到超过其忍耐极限的打击或压力后在潜意识层里形成的消除困境或解放自我的一种心理活动,而这种活动通常是当事人在清醒时想做而不敢做的行为。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洛兰用砖头砸死本杰明的事件给布鲁斯特街的黑人造成极大的震撼。内洛尔在小说里提到,“虽然只有少数人承认,但是布鲁斯特街的每一个黑人妇女在凶杀案发生的雨蒙蒙的一周里都梦到了那个穿着血迹斑斑的深绿色裙子的高个子黑人妇女。她进入到她们的噩梦之中,吓得她们直冒冷汗,或者徘徊在把她们惊醒的边缘。”(p.175-176)在这种沉闷的社区氛围里,每个黑人妇女都知道,洛兰被轮奸不是她个人的不幸,而是所有黑人妇女的不幸,恶劣社会治安环境威胁着每一个黑人妇女的人身安全;洛兰砸死本杰明的事件,不是洛兰对本杰明的误杀,而是不合理社会制度给黑人造成的必然后果之一。白人当局对黑人社区的治安不闻不问;只要受害方不是白人,警察是不会去积极追捕罪犯的。此外,内洛尔还用相当的篇幅描写了玛蒂做的一个梦。在梦里,街区的黑人在街上参加房客联合会举办的一个街头舞会。舞会途中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街头跳舞的人们纷纷逃去避雨,但是跳舞的黑人妇女留了下来,她们认为本杰明被砸死时所倚的那面墙上还留有血迹,于是她们疯狂地把墙砖一块一块地抠出来,把墙砖扔向大街。玛蒂梦醒时,雨天已经结束,阳光灿烂的日子又来到了。黑人妇女们的拆墙行为表明,她们已经开始觉醒。那面墙是一面种族隔离之墙,也是种族歧视之墙。由于这面墙,黑人社区得不到光明,黑人社区的黑人青年无所作为,干下了危害黑人同胞的各种违法行为,这也是黑人在种族主义社会里的一种自残行为。林文静说,“虽然我们读完故事后发现这一聚会只是发生在玛蒂的梦里,但是这个梦境,即社区里所有女性联合起来并推翻那堵发生过惨剧的墙;寓意深刻,所有妇女,异性恋也好,同性恋也好,最终是能够团结起来以反抗男权文化制度的。”①林文静:《姐妹情谊:一个被延缓的梦——解读格罗利亚内勒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内洛尔通过玛蒂梦幻的描写,揭露了黑人妇女的困境,表达了她们的渴望:黑人妇女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可能冲破父权制文化的限制,获得自己的幸福生活。
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内洛尔笔下的梦幻充满荒诞,荒诞映衬着梦幻,折射了黑人社区的苦难与凄凉。黑格尔曾说,“如果我们能把一个时代的人们所做的梦合并起来,我们将会得到最能准确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的图景。”②杨铖:《文学现代性框架内的梦境叙事研究》,第37页。为了展现黑人社区的“神奇现实”,内洛尔采用了这种非理性的、极度夸张的荒诞手法,把梦境和荒诞植根于黑人社区现实生活的描写中,融汇和吸纳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一些梦幻元素;梦幻与现实水乳交融,彰显了内洛尔小说创作艺术的独特魅力。内洛尔在小说情节的建构中借助于梦境与现实的有机拼贴,以亦真亦幻的艺术笔触揭示了布鲁斯特街黑人社区荒诞的生存境遇和梦魇般的心灵图景。
三、象征手法
陈慧说,“象征,即用某种符号代表某种事物。广义地说,在人类生活中,象征无处不在,语言就是一种象征系统。狭义地说,则是一种文艺手法,它用此物暗指彼物,用某种具体形象反映与之相近的现实关系,表达与之相似的思想感情。”①陈慧:《象征手法、象征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河北学刊》1982年第3期。在文学创作中,象征手法是作者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借助作品中某人某物的具体形象,即象征体,以表现作者欲表达的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它可以使小说立意高远,含蓄深刻。作者对象征手法的得体运用可以升华某些比较抽象的精神品质,使之转化为具体的可以感知的意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赋予小说以深刻寓意,给读者留下咀嚼回味的文本空间。个性化的象征是内洛尔在文学作品中用来传达某种精神体验,暗示某种微妙的内心世界或预示人物特殊的命运而广泛采用的表现手法。作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的现代黑人作家,内洛尔对象征的认识是充满洞见的。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内洛尔所采用的象征手法还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诸多表现手法的影响,她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等西方现代主义手法,采取兼收并蓄的积极态度。内洛尔在小说中使用的象征可分三类:多转性象征、启示性象征和寄予性象征。
多转性象征是让读者在作品的不言之中去意会其象征之意,其象征体与本体之间并没有固定的联系。象征体的属性是多侧面的;在不同的场合里,同一事物也可以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布鲁斯特街的大多数居民都是来自美国南方的贫穷黑人,市政建设投资很少,脏乱差成为这个街区的显著特征。白人当局不是采取措施治理布鲁斯特街区的问题,而是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措施,砌一道墙把布鲁斯特街区与城市的其他街区隔离开来。因此,该墙在小说开始部分的象征意义是种族歧视,达到的效果是种族隔离。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布鲁斯特街妇女们生存之路越来越窄,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和性压迫越来越残酷,无论是伍兹牧师对艾妲女士的性剥削和情感欺骗,还是以贝克为首的街头混混对洛兰的轮奸。那面墙不但把黑人与白人隔离开来,而且还导致墙内的黑人自相残害。因此,那面墙又具有了新的象征意义——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该墙的本体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不断衍生出新的象征体。这类象征显得含蓄蕴藉,意味隽永。
启示性象征是指作者在文学作品里直抒胸臆地点示出象征之启示,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或思想感情。作者通过某一具体形象表现出一种更为深远的含意,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从而让读者获得美的感受和艺术享受。这是一种隐晦、含蓄而又能使读者产生体会愉悦美感的艺术表达手法。②M.Ozar,The Epistemology of Symbolism,Ann Arbor,Mich:UMI,1976,p.79.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第一个故事“玛蒂·迈克尔”里,内洛尔采用了甘蔗的意象。黑人青年布奇·福勒(Butch Fuller)用甘蔗为诱饵,花言巧语为工具,成功地把玛蒂从家里骗出来,表面上是热情地带她去砍甘蔗,实际上是为诱奸她寻找机会。布奇主动下甘蔗地砍了两捆甘蔗,对玛蒂殷勤无比,并不断地用言语进行挑逗。布奇教玛蒂吃甘蔗时,说最好的方法是在甘蔗汁被咀嚼完之前就把甘蔗吐出来。他给玛蒂一根甘蔗,教玛蒂按他说的方法吃。在布奇眼里,甘蔗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他的意图是让玛蒂不断把甘蔗杆塞进嘴里,仿佛是男性生殖器进入女性的身体,通过反复的嘴唇和口腔刺激来激发玛蒂的性联想或性幻想,从而引起她的性冲动。内洛尔把吃甘蔗象征为性行为的引诱方式,揭露了父权制社会里男性在与女性交往中的功利性心态,抨击了男性亵渎纯真情爱的肉体占有欲。
寄予性象征是指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某物,使该物成为其理想的象征。在小说第三章“吉斯瓦纳·布朗”里,内洛尔塑造了一名黑人女大学生。她崇尚黑人文化,把自己的名字从“梅兰妮·布朗”(Melanie Browne)改成具有非洲文化特征的“吉斯瓦纳·布朗”(Kiswana Browne)。为了促进黑人社区的发展,改善黑人的居住条件,她专门搬到布鲁斯特街居住。她坐在窗边,看到一只鸽子在天空翱翔,便触景生情,希望鸽子为黑人女性的解放和独立带去新生的希望,这只鸽子是吉斯瓦纳推进布鲁斯特街社会改革理想的象征和载体。就在鸽子随意停在对面楼房一个生了锈的太平梯上的一瞬间,寄予的象征意义马上就崩溃了。“这样的描述也暗示了幼稚的只是接受书本教育但缺乏对黑人命运深切感怀的吉斯瓦纳的最终结局。”①魏永琴,胡笑瑛:《格罗里亚·内勒〈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意象分析》,《安徽文学》2011年第11期。这个象征也表明了吉斯瓦纳社会改革最终失败,以玛蒂的梦幻破灭而宣告结束。
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内洛尔采用的象征手法使象征体和本体有机结合起来,象征体和本体之间产生内在的关联有助于读者产生发散性联想,进而拓展寓意,彰显从象征本体到象征体的相似点和相近点,使抽象的思想、意义、概念形象化和具体化。内洛尔的象征手法一般用来讽刺丑恶的事物,抨击不合理的现象,但有时也用来赞颂美好的事物,体现作者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总而言之,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里,内洛尔很关注黑人妇女的命运,其作品含有丰富的社会伦理内涵和种族文化价值取向。精神的自我拯救是黑人开拓新的人生要义之所在,也是以追问人生意义和捍卫社会正义为己任的内洛尔奉献给读者的一个重要启示。她在沉痛反思美国黑人历史、奋力开凿“文化岩层”的同时,痛感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给黑人带来的灾难;此外,她还从文学美学意义上对黑人民族文化进行重新的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对黑人社区存在的丑陋文化因素进行批判,对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深入地挖掘和剖析。她通过命运反讽、荒诞梦幻和象征手法,将现实夸张、变形,从而更深刻地描绘出布鲁斯特街区的社会状况,进而揭露社会弊端,抨击黑暗现实,展示出鲜明而浓厚的美国黑人文化特色。内洛尔在小说技巧方面的创新和探索,特别是在把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引入黑人小说创作方面,对黑人小说叙事策略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对21世纪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大影响。因此,美国学界通常把内洛尔列为与托尼·莫里森和爱丽丝·沃克齐名的当代美国黑人小说家。
[责任编辑:诚 钧]
Situational Irony,Absurd Dream and Symbolism:A Comment on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Gloria Naylor’s 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PANG Hao-n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The situational ironies in 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include the ironies of way-out surprise,love at the first sight,and well-meaning misunderstanding.These ironies are full of wit and humor beyond expectation or literal meaning.The dreams depicted by Naylor are characterized by absurdity,combined with reality in complete harmony.The symbols of multiple turns,enlightenment and empathy in Naylor’s novel satirize the seamy side of society or glorify the wonderful human relations to highlight the author’s pursuit of a perfect world.Naylor introduces some elements of magic realism to his original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ironies,absurd dreams and symbolism in his work to facilitate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Afro-American novels.
Gloria Naylor;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situational irony;dream;symbolism
I 106.4
A
1002-3194(2014)02-0080-07
2013-09-25
庞好农(1963- ),男,重庆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非裔美国文学史(1619-2010)”(12FWW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