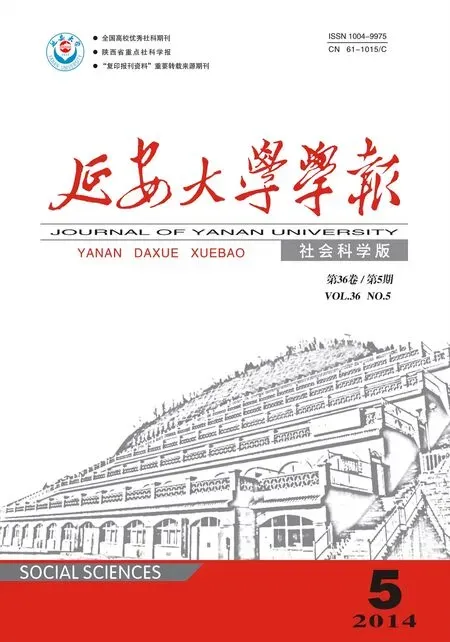翻译与政治的结合及翻译的政治性
呼媛媛
(延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信、达、雅”,注重对原文的忠实,这与西方的翻译理论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翻译并不是中立的,并不是远离政治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与变形。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翻译研究范式出现了重大变革,西方开始吸纳跨学科的学术思想,对翻译研究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如西方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文化理念开始融入翻译研究之中,揭示了翻译所蕴含的政治关系,“翻译与政治”逐渐成为当下翻译界的热门话题。实际上,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形式,从一开始便嵌入了政治的符号,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的影响与制约。所以,从源流上看翻译就是异域文化融入本土文化形态的过程,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当前,翻译界已经逐渐意识到翻译活动并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涉及源语及目的语两种文化,有着复杂交往行为的过程。所以,翻译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行为,渗透着社会文化的政治特性。
一、翻译的政治渊源与译者的政治目的
(一)翻译与政治的渊源
翻译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德国的宗教领袖马丁·路德便对《圣经》进行了翻译。温特在其《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中第一次提出“翻译的政治”这一理念,被看作最早的翻译政治的文章。20世纪90年代,孟加拉国的斯皮瓦克在其《教学机器之外》中对翻译的政治内涵及产生的语境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将其植入女权主义、结构主义的框架之下,对其蕴含的权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逐渐步入科学化的轨道。加拿大的西蒙在其《性别与翻译》中提出了同样的命题,并主要局限于性别的政治之中。以上的这些提法都注意到了翻译与历史、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涉及到了文化政治理念,这便是西方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础与渊源。中国翻译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佛经的翻译,当时的鸠摩罗什倾向于佛经原文的“权力摆布”,以达到政治的目的,唐代玄奘法师更是将政治理念推向极致,他采用灵活的方式翻译佛经,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高度称赞。为了适应近现代社会环境及政治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著名翻译家严复改写了西方大量的社会科学文化著作。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学者王宏志在其《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中提出翻译的政治问题。后来的译者采取对原作删减、做注等形式,增加自己的理念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增加了翻译的政治目的。[1]
(二)翻译活动受制于政治操控
世界上没有一种不受政治影响的话语,翻译便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翻译文本的选择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话语的反映及建构。翻译者并不是中立的,他们往往受某种政治的制约,纠缠于各种权力的网络之中,特别是其主体作用的发挥服从于政治的需要。翻译活动受目的语赞助人的操控,同时翻译更多受赞助人背后的意识形态影响并构成社会上的政治话语。勒菲费尔在其《翻译、改写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提到翻译的三要素,他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并不能真实反映原文的内涵与本质,这是由于翻译自始至终受政治因素控制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的语文化及其诗学特征。翻译者往往服从于政治,有时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如《圣经》的翻译便直接与宗教政治相关。马丁·路德翻译《圣经》并创造出一种适于大众接受的形式而遭到迫害,由此可知“政治话语”便是一种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暴力”。[2]法国著名作家、翻译家雨果曾说:“当你翻译一部作品并将其献给国家时,那么国家将视该作品为对其的一种暴力行为,这种方式并不能取悦于统治者。”特别是当译本与目的语文化相冲突时,译本便自然受到统治者的禁止与打压。所以,译者要想将译文顺利进入目的语文化中,一定要将目的语文化的政治特征与意识形态考虑进去。
(三)译者翻译的政治动机与目的
翻译活动反映着政治斗争,所以翻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传话筒”,也不是远离政治的行为,而是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的行为。清末民初,翻译的“不忠”是当时翻译活动的重要特征。林纾便是当时著名的西方文学的改写者,他通过合作者的口述,以文言的形式翻译了近两百部西方小说,由于他不懂英文,出现了大量的改写、删减内容。作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林纾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民族的安危,并希望通过翻译来唤醒民众的爱国激情,他在《见底鸳鸯》中提到:“今日之中国,衰败之中国也,余不能著书以勉励国人,但有翻译西方英雄之外传,改吾疲敝之习,老怀其以少慰乎。”[3]在他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中,他就特别警醒国人勿忘民族之危机,让国人从黑奴的悲惨命运中看到中国正在遭受的践踏。严复是一位双语翻译家,他主要翻译了八部著作,每部都经过精心挑选,在翻译过程中进行有意的删减、增补,以服务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从中可以看出,翻译者的动机直接影响着对作品的选择,译者往往将翻译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与理想的途径,特别注重作品的意识形态。
二、翻译中政治的内涵及翻译实践过程的政治性
(一)翻译中的“政治”内涵及文化底蕴
20世纪90年代,翻译的政治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界热议的话题,在斯皮瓦克出版的《教学机器之外》著作中,“翻译的政治”一章便集中体现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及结构主义理论等政治主张。她的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去识别与批评将女性贬低的观点,并探索翻译渐进女性化的过程。”她严厉批评了那些主张欧洲之外的女权主义文本都应译成“英文”的女权主义理念,指出这样的翻译就会经常出现“译作腔”的现象。翻译其实就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往往带有鲜明的权力关系。同时,翻译还是一种弱者向强者抗衡的努力,传统的翻译忽略了蕴含于原文的权力关系及历史语境,而探索翻译的建构过程,注重其文化与政治功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外,翻译的文化底蕴直接促成了翻译政治观念的形成,翻译政治逐渐成为西方中心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利器。在现实世界中,好与坏取决于一定的市场与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并构成翻译标准的立法者。例如,金斯堡的诗歌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语言及内容都可以视作资产阶级没落的表现。所以,表面上看翻译活动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实际上是对译体语的创新与探索。
(二)翻译实践过程中的政治性
翻译是两种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翻译活动中的信达雅及正确与错误问题便是一个政治问题,通过良好的翻译来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是一个普遍的愿望。如马可·波罗曾将东方的犀牛看作西方的独角兽,这虽然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而有些学者认为“他既然被传统安排遇见独角兽,那么这种奇特的动物便是‘独角兽’”。这就是说,翻译者应当屈从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及思维方式,并不是真正实现文化双方毫无偏见的沟通。中国著名翻译家冯友兰曾指出:“一种翻译不过是一种解释”,也就是说翻译作为一种活动,不能将译者理解为展开全文的有效渠道。围绕翻译的争论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包含不同文化及主体之间的关系。相对于译体语来说,翻译的作品应该具有一定的新意,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项原创性的活动。然而,“新”的标准则模糊不清,有人认为《易经》中的“变”远远超越西方的辩证法,老子的“道”更说清了海德格尔问题。[4]可见,不同的文化及政治立场,翻译的内容或标准是不一致的。试图通过翻译来改变不平等现状反映出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梦想,这正是翻译的政治性。
三、政治文化与中国文学翻译的政治问题
由于不同年代的政治文化不尽相同,政治文化与翻译文学的结缘形式也不一样。国民独裁政府建立以后,实行文化控制政策,引起了文化界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因为翻译在政治文化传播中有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使得翻译界成为权力主客体之间争夺的重要战场。当时持不同政见的文学群体都特别关注出版与言论的自由。新中国刚成立时期,由于法律本身的不健全,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处于相当主要的地位。翻译活动常常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造的一部分,主要被利用来巩固社会主义文化系统及强化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处于稳定阶段,人们对政府有着高度的政治认同,生产方式也开始趋于同质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及艺术被介绍到国内,人们的思想意识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样,政治文化的多样性便促使翻译选择的全方位性,翻译实践获得空前的活力。
20世纪中国的翻译文学历程中,时代的政治需求成为翻译文学的重要准则。所以,20世纪中国翻译问题的落脚点并不是文本上的文学性,而是在涉及文学翻译时首先摆正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探索政治对翻译的影响程度及在目的语文本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当时翻译文学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并力图以详尽的材料来研究当时政治文化的操作流程,以此形成普遍的政治思想与价值。同时,还应研究20世纪出现的翻译文学现象,根据不同学派译者的反映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对当时的翻译文学进行准确的把握与评价。翻译的政治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翻译行动,翻译也受制于知识的制约。人们虽然意识到了政治性,但并不能真正搞懂政治与翻译的关系。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过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是采取何种方式影响着翻译文学的走向,并构成翻译文学的基本特征。
[1]邵璐.政治文化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三种模式[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9):39-41.
[2]张宁.翻译政治的“三维空间”——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及其他[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07(4):43-45.
[3]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袁赞.翻译与政治的有机结合——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理论基础探源[J].科技咨询导报,2010(29):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