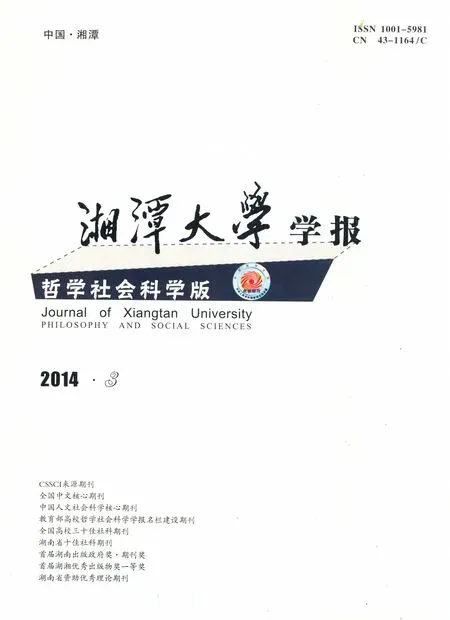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
徐仲佳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小说中的性叙事从1970年代末重新出现在中国文学场之后,历经多次坎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到1980年代末,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与1980年代文学场自主性原则逐渐增强有密切的关联。1984年底,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的核心是试图通过强调创作自由、批评自由来活跃文学创作:“……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1]政治场的这一努力在文学场中被转译为重建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在这一“恩赐”来的创作自由(张贤亮语)的鼓舞下,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和王安忆的《小城之恋》(1986)为代表的性叙事突破了此前禁欲主义文艺政策的惯性,开始展示性叙事狂野的颠覆力量。大胆揭露禁欲时代对人类性本能的戕害与抽空了时代内涵而专门探讨人类性欲望的本质属性,这两种价值取向都不同于政治-文学蜜月期性叙事的共识。同时期的先锋小说中的具有暴力特征的性叙事隐喻意象则试图以此触及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创伤。这些与政治场信仰相异的性叙事的出现,显示出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变为现实。①邵燕君持这一观点,她认为“以1985年‘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的出现到1987年‘先锋小说’成型”是“中国当代文学‘自主性原则’建立的标志”。[2]126-127但是,文学场的独立性进程在1980年代末被政治场风暴强行打断则显示出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的脆弱。
1990年代初的文学场延续了自“十七年”以来的一体化文学场的权力关系。自1992年开始,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成为政治场的共识,[3]文学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艺机构体制改革重新提上日程,出版社、期刊社被推向市场,取消了30多年的版税制度重新实行。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场一直都是一个自主性原则极其脆弱的场域,政治场的等级化原则很容易直接传导到文学场。在1990年代初,经济场的等级化原则也几乎是直接地、未经文学场“转译”地传导到文学场中。由于经济场赢者为王的逻辑与文学场的“颠倒的经济”恰相对立,因此,经济场等级化原则进入文学场,必然要引起文学场原有的集体信仰、文学边界、占位等的激烈对抗。但是,因中国文学场自1949年之后就排除了对经济场的“转译”,加上当时政治场风暴的压抑犹存,所以,经济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识对当时文学场中的占位者却充满着诱惑。“作家下海”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现象,正说明了当时文学场所受到的经济场等级化原则的影响。[4]张贤亮1993年初“下海”便是带着壮士断腕般豪情的:“用小说的形式写政治读物是我对社会改革的行动和参与,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中投入商海也是我的行动和参与。何况我以为,只有市场经济建设方能推动民主与法制的建设,……要自由吗?你必须在经济上独立。”[5]张贤亮的这种说辞很能够说明当时文学场集体信仰的转变:乞灵于经济独立可能带来的自由。许多占位者期望通过新的区分原则颠覆重新趋向一体化的文学场。但是,与这种精英式信仰不同的是,经济场的等级化原则毫不留情地颠覆了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两个次文学场的占位:一方面是造就了像王朔、《废都》这样的适应市场经济的成功者,另一方面则使所谓严肃文学被冷落:文学期刊订数急剧下滑,几乎每一种“严肃”的文艺作品或学术作品的出版都会伴随着出版过程艰难的“抱怨”。这种颠倒评价,说明文学的边界和等级制越来越让位于市场经济的定价权。“图书市场上的‘好卖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好书原则’,并直接、间接地影响了纯文学杂志的发表原则。”相应的,作家们在文学场中的占位也同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2]14文学场的集体信仰、文学边界、占位斗争深深地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
文学场的变化塑造着作家们的习性,并进而将这种习性的改变体现在性叙事中。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可以成为我们观察这一结论的标本。此前,贾平凹在文学场中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象征资本。贾平凹1973年开始公开发表小说。1993年之前他已先后多次获得文学场中最重要奖项,②1978到1991年,贾平凹获得了16项文学奖励,其中包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美孚飞马文学奖等重要奖项。[6]526在国内外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文论集 48种。[7]519-525他在小说、散文等文体的创作都已经被文学场所认可,并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1985年1月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的组成人员。由于这一次名单的公布反映了得票多少,因此,位次可以看出作家在当时文学场中的占位情况。当时,贾平凹位于第50位,远高于许多同代和前辈作家。但是,1990年代之前,贾平凹在文学场中的占位与他在经济场中的占位形成了很大的剪刀差:他在台湾出版的20万字的作品只得到800元,其小说《鸡窝洼人家》被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野山》(1986)也只得了800元。[4]在一个成熟的现代文学场中,这也许会被解释为文学场特有的“颠倒的经济”,不会成为问题。但是,在当时受到经济场等级化原则直接影响的中国文学场中,这被认为是对作家占位的低估。贾平凹的习性也自然会被文学场的这一新的区分原则所塑造。这既表现为《废都》模仿式的性描写,又表现为《废都》的文化工业的“精品”化的生产方式。
1993年《废都》的出现按照商品文化打造“精品”的模式运作。名作家+世情+性描写,是《废都》打造“精品”的主要策略。早在1992年,贾平凹的朋友兼研究者孙见喜(时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就以特有的身份优势披露了尚未完稿的《废都》的三方面信息:一,这部小说是贾平凹(名作家)创作题材转型的作品:“……是贾平凹第一部正面表现当代都市生活的作品。”二,这部小说蕴藏着巨大商业价值:(《废都》)“已有中国作家出版社、天津百花、上海文艺、陕西人民等十几家出版社竞争该书的出版权。有的出版社愿出1000字100元的稿酬,有的则可按15%的版税支付。”三、暗示这部小说在描写上有惊人之笔——直露的性描写:“问及创作思想,平凹说:‘我常常想,《金瓶梅》、《红楼梦》也是写城市生活的,,那就太好了。”[8]孙见喜《身裹羊皮袄,屋点蜡烛灯——贾平凹“隐居”写〈废都〉》103(着重号是引者所加)在随后的炒作中,《废都》的稿费被传为1000150元,其性描写则被比拟为“现代《金瓶梅》”。《废都》中的性描写多处照搬《金瓶梅》,且通过“□□(此处删去××字)”的方式来吊读者胃口。关于性描写的删改,贾平凹的说法是:。”[8]王兰英.《平凹近来做啥》102但这种说辞显然难免商品促销策略之嫌。在1980年代,文学中虽然已经出现了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城之恋》那种直接的性描写,但是,像《金瓶梅》那种大量描写性交动作的性描写还是罕见的。《废都》当时的促销策略很容易会在读者中引起指向《金瓶梅》的性描写的期待视野。这在《废都》之前的严肃文学的广告中是难以想象的。《废都》初版30万册,迅速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被称为“废都热”。当时的一份广告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废都》“精品”建构的要素:“西京城里,四大名人,奇闻迭出;文化闲人,熙攘浮沉,屡见事端;情场男女,恩怨交错,生死纠缠。”[8]陈剑夫,《京城八月:街谈巷议说〈废都〉》11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废都》包括了商业文化对受众欣赏品味塑造的所有元素:过界的性描写、奇闻、窥视欲等等。《废都》的商业文化逻辑使得文学场中批评家对《废都》褒贬不一的评价、《废都》被禁等事件都不由自主地参与了也许它们并不愿意参与甚至是抵触的《废都》“精品”打造的过程。
贾平凹对当时经济场等级化原则的主动适应是那个时代文学场集体信仰、文学边界、等级化原则变动对作家习性塑造的一个鲜明例证。虽然有许多批评家来力图为它搜寻符合精英文化的符码,[8]王富仁.《〈废都〉漫议》.204-205,温儒敏.《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扰》.219但是,这些说辞无法掩盖《废都》作为商品文化“精品”的流行符码色彩。王小波谈论过作为严肃文学的色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性噱头的区别:“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我认为目前自己尚写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学,也许是因为对环境感觉鲁钝。前些时候我国的一位知名作者写了《废都》,我还没有看。有人说它是色情文学,但愿它不是的,否则就有说明意义了。”[9]关于格调83事实上,1993 年的中国,无论是政治场还是文学场都不是最严酷的,其性心理也并不是最不正常的。因此,《废都》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色情文学,而只是一个流行精品而已。“《废都》热”可以证明当时文学场传导经济场等级化原则之后,短生产周期的大规模生产次场已经形成。
当然,经济场的等级化原则进入文学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如许多人所愿,为文学场从对政治场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带来契机。固然,贾平凹、王朔等在短生产周期的大规模生产次场取得的成功对一体化文学场带来猛烈颠覆。另一方面,经济场等级化原则的传导带给拥有“严肃文学家“的身份标示的占位者以新的自信。这表明长生产周期的限制性生产次场也在形成。王小波是这样的代表。王小波与贾平凹不同,虽然他的小说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在朋友圈中流传,但在1990年代之前,他在文学场中几乎一文不名。是小说创作所带来的收入给他带来脱离体制的自信。在致朋友的信中,王小波说出了当时他脱离体制的情形:“我前一段感觉很坏,所幸写小说挣了点钱,又略见光明。人大的差事也打算辞去,以便专营此业;成败尚难逆料,心里也磨得慌。”[10]致刘晓阳(1991年3月22日)150-151如果说,此时王小波还有点游移不定的话,那么,到了当年的9月份,他则更加自信:“不过现在我对微机已无兴趣,因为发现写小说也可赚到钱。这次一个中篇,中了联合文学的奖,奖金比我数年工资还多些。现在正欲辞了职去干这勾当。”[10]致刘晓阳(1991年9月2日)154很显然,这种自信来自于两个方面,一、获奖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象征资本;二、奖金(25万新台币)给他带来足够的经济资本,给他带来了自信:“将来就想吃这碗饭,现在年富力强,挣了钱,将来养 老 不 成 问 题 罢。”[10]致刘晓阳(1992年1月11日)157因 此,他 于1991年9月辞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
成为自由撰稿人之后,王小波选择了以“严肃文学”创作者为身份标记进行占位。由于王小波最初在文学场中几乎一文不名,因此,他亟需在文学场中占据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当时,王小波已经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奖,并在台港出版了小说集。因当时大陆文学场的相对封闭性,他拥有这些资本并不能马上转化为大陆文学场中的资本。他在大陆文学场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占位。这表现为他当时发表的刊物较少,且并没有得到批评界的认可。因此,当时王小波极力想要将自己在港台文学场中获得的资本转变为大陆文学场的资本:“现在中国的风头有利,准备努力写一些,把主战场放到国内。因为没有名声,光靠质量在外面也难有作为……要成名,还是要先在本土打响罢。”[10]致刘晓阳(1992年9月15日)162
王小波试图在当时文学场中获得严肃作家的占位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他小说中的性叙事。《黄金时代》是他最初的象征资本的载体。这部小说因其性叙事而被某些人视为“格调不高”。[9]关于格调80这是“十七年”一体化文学场集体信仰的遗留。王小波一方面对这些遗留进行了颠覆,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性叙事与通俗文学进行了区隔。
关于前者,他在小说集《黄金时代》的后记中对一体化文学场集体信仰遗留进行颠覆:“我曾经就这些作品请教过一些朋友的意见。除了肯定的意见之外,还有一种反对的意见是这样的:这些小说虽然好看,但是缺少了一个积极的主题,不能激励人们向上……我以为自己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教。我的写作态度是写一些作品给读小说的人看,而不是去教诲不良的青年。”[11]后记336王小波以“好看”来颠覆一体化文学场的“积极向上”的“说教”。王小波所说的“小说写得尽量好看”是指其性叙事所蕴含的黑色幽默。他认为,《黄金时代》“真正的主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我觉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气质,是天生的。我小说里的人也总是在笑,从来就不哭,我以为这样比较有趣”。[9]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64王小波将其性叙事定义为其黑色幽默气质的载体。这既是对一体化文学场集体信仰中将性叙事视为“格调不高”的逻辑的颠覆,也是一种与当时通俗文学中的泛滥性描写进行区隔的策略。幽默,从1930年代进入中国文学场起,就被定位为理性高度发达的产物。王小波将自己的性叙事解释为黑色幽默,显然与他一再强调的“理性”、“爱智”是异曲同工的。在这一逻辑下,不仅“十七年”一体化文学场的性叙事标准被老化,而且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教员”式性叙事也被老化。
关于后者,王小波早在他初涉文学场时就有了明确的认识:幽默是区隔雅俗文学的重要策略。[10]致刘晓阳(1992年9月15日)163-164对王小波来说,这种区隔策略不仅区隔了作家,也区隔了读者:“现在严肃小说的读者少了,但读者的水平是大大提高了……小说会失去一些读者,其中包括想受道德教育的读者,想看政治暗喻的读者,感到性压抑、寻找发泄渠道的读者,无所事事想要消磨时光的读者;剩下一些真正读小说的人。小说也会失去一些作者——有些人会去下海经商,或者搞影视剧本;最后只剩下一些真正写小说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9]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64而王小波认为,他的写作是以那些有理性、爱智的读者为理想读者:“我知道,有很多理智健全、能够辨别善恶的人需要读小说,本书(指《黄金时代》——引者注)就是为他们而写。至于浑浑噩噩、善恶不明的人需要读点什么,我还没有考虑过。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咱们国家里前一类读者够多了,可以有一种正经文学了。”[11]后记336另外,王小波也曾经有意地强调《黄金时代》漫长的生产周期以突出它的严肃性与完美性。①王小波在《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中说过,《黄金时代》写了差不多20年,其间数度修改,是他追求艺术完美的尝试。引自《王小波全集》第2卷第63页。王小波对其性叙事的定位随后被文学场所接受。1997年,王小波突然离世,随后他被册封为新的经典作家也进一步加强了其性叙事作为严肃文学的符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990年代的性叙事划开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鸿沟。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经济场的等级化原则提高了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形成了限制性的生产次场和大规模生产次场。
[1]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J].文艺研究,1985(2).
[2]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江泽民.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1992(4).
[4]李纪钊.作家“下海”现象面面观[J].山东青少年研究,1993(2).
[5]张贤亮.也谈文人“下海”和作家心态[N].文学报,1994-04-04.
[6]梁颖.获奖作品[M]//雷达主编.梁颖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7]孙见喜.作品年表[M]//雷达主编.梁颖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8]肖夏林主编.废都废谁[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9]王小波.王小波全集第2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10]王小波.王小波全集第9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11]王小波.王小波全集第6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