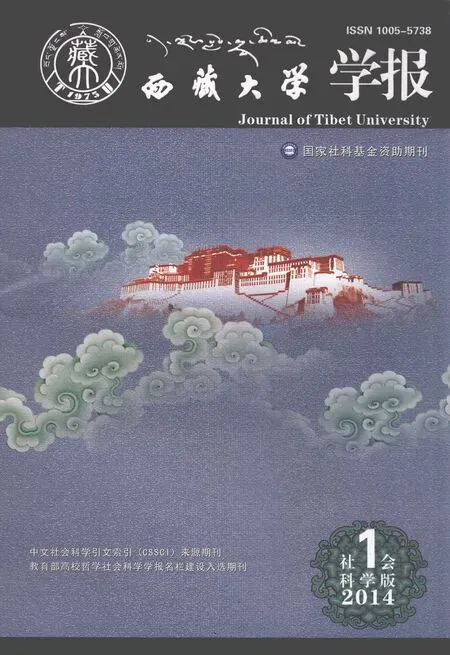明至清初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初探
李晓英牛海桢
(①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②兰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明至清初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初探
李晓英①牛海桢②
(①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②兰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文章以大量的历史文献论述了以饲养马、牛、羊等牲畜为主的畜牧业生产在青藏高原诸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明代至清前期,青藏高原地区的农业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畜牧业生产依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肩负着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明清政府在高原地区和接近高原地区设置的官营茶马贸易和官办马场,客观上对民间畜牧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史为鉴,如何在生态环境脆弱的条件下推动高原地区经济的发展,以满足当地人民日常生活所需也是我们当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明至清初;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
青藏高原地区无疑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自然和地理环境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其地表资源利用的主体方式是畜牧业生产。明代以来直到清朝前期,青藏高原的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并陆续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1]。由于广大高原牧民日常生活和畜牧业息息相关:从饮食方面来说,藏族的许多食物都来源于畜牧业所提供的畜产品;从服饰方面来说,游牧民族主要以牛羊毛、绒和皮等制作各种藏式衣裙、鞋帽、毡褐等;在交通运输方面,牦牛是耐寒负重的高原之舟,马是高原人民远行的坐骑,牛皮制成的船是青藏地区许多湍急河流上横渡的便利工具;从日常用具方面来说,藏族人民使用的许多东西都是用畜牧业所提供的产品制造的[2],因此有学者说:“传统的藏族畜牧业与其说是一种谋利的经济活动,还不如说是一种与家畜共生、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3]明代至清前期,虽然青藏高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畜牧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由于资料匮乏,关于此时的畜牧业经济研究到目前为止,鲜有探究。鉴于此,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明至清初青藏高原的畜牧业生产做一些初步的探索,不妥之处,求教于方家。
一、明代青藏高原的畜牧业生产
虽然蒙元王朝不是特别重视高原地区的畜牧业生产,但是直到明初,青藏高原地区无论乌斯藏还是朵甘地区,大部分藏民仍旧主要以畜牧业为生,马、羊、牛依然是畜牧业的主要产品。明初的史籍中对此多有记载: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邓愈、沐英等征西,俘获“马五千,牛羊十三万”[4]。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邓愈兵至吐蕃,“攻败川藏之众,追至昆仑山,斩首甚众,获马牛羊十余万”[5]。洪武十二年(1379年),沐英等到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平定叛番,“所获牛羊,分给将士,亦足两年军食”[6]。不久,沐英进击“番寇”,大破之,“获马二万、牛羊十余万”[7]。而《明实录》中所载青藏高原地区的贡马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藏高原畜牧业生产之兴盛。从洪武三年到六年仅仅三年之内青藏高原贡马就达数十次之多。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一十三人来朝,进马及方物。”[8]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马梅遣官不失结等贡马及方物[9]。同年八月,“故元宗王子巴都麻失里、沙加失里、院使汪家奴等来降,贡马二十余匹”[10]。十一月,“达鲁花赤赵阿南、赵伯寿、东寨千户唐兀不花、达鲁花赤石添寿等人入朝贡马”[11]。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河州卫指挥佥事朵儿只、汪家奴来朝,贡马”[12]。同月,“西蕃十八族千户包完卜癿等来朝,贡马。”[13]四月,“故元参政阿(陀)失宁自西蕃来降,贡马”[14]。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西宁卫指挥佥事朵儿只班遣人来朝贡马[15]等等,这类记载不胜枚举,而从这些记载中就可以反映出明朝初期青藏高原地区畜牧业生产情况,马、牛、羊等牲畜数量之多。
不仅如此,明初,由于明太祖朱元璋“起江右,所急惟马”[16],加之此时残元蒙古势力给政府造成的军事压力,因此明王朝建国伊始,就把牧马业列为国家头等大事。由于统治者的重视,从而更加带动了青藏高原地区以马为主体的畜牧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明史》载:“西宁即古湟中,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水草丰美。番人环居之,专务畜牧,日益繁滋,素号乐土”[17]。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区由于地域辽阔,水草丰美,是天然的畜牧业基地,因而明初此地即受到了明政府的重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太祖即“诏陕西西宁卫,以征北所获马牛羊万九千三百八十三给诸军牧养。”[18]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政府更在此地建立了甘肃行太仆寺(治所今青海西宁),以发展国营养马业。永乐四年(1406年)九月,明政府设陕西、甘肃两苑马寺,寺统六监。每两司先设两监,监统四苑。“苑视其地里广狭为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圉长,从九品。一圉长率五十夫,每夫牧马百匹……春月草长,纵马于苑,迨冬草枯,则收饲之。”[19]明王朝养马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据《西宁府新志·马政论》载:“拓明朝远稽周唐,大振马政,……置苑马寺,……牧地十七万七千余顷,养马一万四千余匹,牧军三千二百余人。三年两驹,其计利深。……嘉靖三十七年,平固以北,皆为牧地。……后以隙地为牧。”《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记载了苑马寺的职掌:“苑马寺卿一人,少卿一人,……各牧监,监正副各一人,各苑圉长一人,掌六监,二十四苑之马政,而听于兵部。凡苑视广狭为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下苑四千。凡牧地,曰草场、曰荒地、曰熟地,严禁令而封表之。凡马驹,岁籍其监苑之数,上于兵部,以听考课。监正副掌监苑之牧事,圉长帅群长而阜蕃马匹”。
在政府的重视下,民间养马业在西北藏区也有所发展。从洪武(1368-1398年)时期开始,明朝廷就经常派官员到西北藏区采购马匹。据《明史·食货志》载,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政府向西北各“纳马之族”发金牌41面,以此作为纳马凭证。其中河州卫发金牌21面,纳马7,705匹,平均每金牌纳马366匹;西宁卫发金牌16面,纳马3,050匹,平均每金牌纳马190匹。此外,并以茶50余万斤易马13,000多匹。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曹国公李景隆还自西番。“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20]。宣德七年(1432年),“所征河州卫各番簇茶马七千七百余匹,已征六千五百余匹……西宁等卫所属番簇茶马三千二百九十六匹,已征二千三百余匹。”[21]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陕西西宁、河州、洮州番族输马一万三千余匹,当给赏茶一百九万七千余斤”[22]。正统九年(1444年)五月,“陕西西宁、河州、洮州等卫所属番族番民,……一次纳差发马一万四千五十余匹,合用茶偿其价”[23]。正统十二年(1447年)四月,以茶一十二万五千四百三十斤,征收西宁、罕东、安定、阿端、曲先五卫番民马二千九百四十六匹[24]。据《西宁府新志·武备》和《边政考》记载,万历年(1573-1620年)间申中族有300户,每年纳马350多匹;奔巴尔族有100多户,每年纳马150多匹,平均每户每年纳马超过一匹。总计西宁25族,每年共纳马3,170多匹。另据《西宁府新志·茶马》记载,万历十九年(1591年),番僧纳马902匹;西宁祁土司祁德僧纳马625匹。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青藏高原地区人民所饲养马匹的数量是很大的。
实际上,最能反映畜牧业发展水平的是各类牲畜的存栏头(只)数,可惜史书上并未留下相关方面的系统记述,目前我们也只能借助一些零星的资料加以推测。宣德五年(1430),镇守西宁总兵官都督金事史昭等奉命讨曲先卫,“昭等兵至曲先,……纵兵击之,杀伤甚众,获答答不花及男女三百四十余人,马驼牛羊三十二万有奇。”曲先卫是明代“塞外四卫”之一,活动在今柴达木西部地区。仅仅一个卫,拥有牲畜竟达30多万(还不是其全部),整个柴达木盆地以及青南地区此期存栏各类牲畜十倍或十数倍于此数是不难相信的[25]。正统四年(1439 年),“罕东、安定合众侵西番申藏族,掠其马牛杂畜以万计。其僧诉于边将,言畜产一空,岁办差发马无从出。”[26]申藏族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招抚的“纳马十三族”之一,是十三族中的小族,这样的小族也拥有马牛等牲畜万余头,其他诸族一定是此数的数倍。
正德(1502-1521年)以后,东蒙古陆续迁入青海境,在环青海湖等地定居下来。东蒙古进据青海,有其复杂的政治原因,而地旷人稀、水草丰美的青海牧场无疑也是吸引他们的重要的经济原因之一。明人郑洛曾言:蒙古各“部落子女生育于斯,甘泉可饮,茂草堪刍,回视北塞,别是一大漠光景也。盖大海。以西至于大小盐池,又西北至于哈密、斥斤,又西南乌斯西藏,延袤数千里,广漠无际,野牛野马,易于打猎。而西藏之宝刀奇货、氆氇皮革服用,所需种种,皆西海所有,北塞所无也”[27]。
明代,除马之外,羊、牛等畜牧业产业在青藏高原的畜牧业经济中也持续发展着,这一方面史书也多有记载。如宣德元年(1426年)十二月,“乌思藏番僧汝奴星吉……等贡驼、马及羊”[28]。宣德二年(1427年)正月,“陕西洮州等卫土官百户剌麻失宁卜肖(宁)……等贡金银器皿、羊、马。”[29]正统九年(1444年)十月,岷州番僧著即尖昝等来朝,贡马、羊等[30]。此类记载,举不胜举。当时,青藏高原的牛主要有牦牛、黄牛、犏牛三种。《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七年(1384年)十二月庚申条记载,四川都指挥使派兵到松潘安抚司作战时,“获其马一百二十,犏牛三百,牦牛五百九十”。可见明初当地拥有的犏牛和牦牛的数量,比马匹是多几倍的,由此也可见当地养牛数量之多。犏牛是由牦牛与黄牛交配所生,特别耐劳、耐寒、耐饥,且性格温顺,因此尤其适合在青藏高原地区进行运输或耕作。宣德六年(1431年),镇守河州都督刘昭奏曰:“乌斯藏等处使臣往来者,多用脚力犏牛”[31]。显然,当时的犏牛还是青藏高原地区与内地交通往来的重要运输工具。
由于畜牧业生产在青藏高原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加之明政府对青藏高原牧业生产的关注,在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更是鼓励牧民交纳马匹,政府厚给赏赐,因此终明一代,畜牧业生产在青藏高原地区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
二、清代前期青藏高原地区的畜牧业
清初,政府为了推行保护、扶持畜牧业生产的政策,在法律上是严禁在牧区开垦牧场的。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了内地人民“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的禁令。《理藩院则例》中就有“私牧开垦封禁牧场,加等治罪”。因此清朝前期,虽然青藏高原地区农业垦殖规模有所扩大,农业生产相较前代有了发展,但是传统的畜牧业生产在青藏高原地区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清代前期西藏地方从萨迦王八思巴时代设立的“管牛只官,管马匹官”等官职仍然得以沿袭[32]。
由于畜牧业生产旺盛,清初,牛、马、羊等活畜和各种畜产品仍然是青藏高原地区向内地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早在清朝迁都北京的前二年,即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己亥,“图伯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依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藏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使者依拉古克三及同来喇嘛等各向朝廷献驼马”[33]等。顺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达赖喇嘛至,谒上于南苑,上赐坐,赐宴。达赖喇嘛进马匹。”[34]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厄鲁特部落顾实汗遣旦巴温布等贡马及方物。宴赉如例”[35]。康熙五年(1666年)六月,“岷州卫法藏等六寺喇嘛桑节落旦等贡马,赏赉如例”[36]。
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理藩院尚书尼堪在给达赖喇嘛的部分骑用牲畜的安排是:在青海备乌拉马三千匹、驼六百峰[37]。其时,沿途藏区各部落也多次进献马、牛、羊等物,《五世达赖喇嘛传》对此多有记载,“五月初一日,行抵肖莽宗木拉,……霍尔查巴尔达的首领噶玛索南盛情款待我们,并向我奉献了以约一百匹马。……以布玛尔、鄂博、嘉巴日、赞果达、旺杰、衮则一千人为首向我奉献了二百六十匹良马。”[38]九日,“霍尔麦巴拉杰向我敬献了带犊母犏牛一百头、公犏牛二十头。”“此后,我们经过了蒙古人称之为察罕额尔克,藏语称为盖巴噶波的地方,又顺次渡过努克曲、阿克达木河,至曲郭扎西奇巴附近的噶尔巴拉则雄。贝日多达玉杰和曲珍兄妹等人献马七十匹、……牛一百五十头”[39]。六月十四日,“为了迎接我们,达赖巴图尔的属下衮布才旺、扎西、德钦库洛齐等人共送骆驼一百峰,墨尔根济农送马、骆驼等共计一百;……行抵直甫那玛朵时,哲务霍尔仓奉献了马、骡、犏牛、茶叶等各一百。”[40]达赖喇嘛作为藏族居民信奉的宗教领袖,受到崇信而敬献的牲畜数量足可见当地畜牧业之盛。
据《卫藏通志》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前,仅在哈拉乌苏牛羊场内就有“奶牛三千只、羊一万余只。”[41]清代,川西高原饲养牦牛则以放牧为主,多数是随季节迁移牧地,逐水草而居。饲养牦牛主要用于肉食,取毛皮和奶酪。道光《龙安府志》记载,番民“亦养牦牛,多供宰杀。”“番民耕种用双牛耕,其牛呼犏牛,出松潘寨,价颇贵,每头约价十金,犁地有力。”
清初,甘青藏区经济也依然是以牧业经济为主。雍正初年曾任四川总督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在条陈青海善后事宜时曾称:明末清初“顾实汗据占此地,以青海地面宽大可以牧养牲畜。”[42]顺治九年(1652年),青海的塔尔寺曾给达赖喇嘛献马500匹、牛40头,在“给以大小多巴温布为首建的台座上,奉献了以两千匹马为主”[43]的礼品。碾伯的郭隆寺等处也敬献马匹[44]。
清初沿袭明制,所得民间之马送苑马监牧养,
“顺治初,陕西设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茶马司”[45]。据相关档案记载,从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至七月半年内,西宁司易马1,150匹,河州司易马241匹,5司总计易马l,791匹。从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至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西宁司易马1,300匹,河州司易马927匹,总计易马3,079匹。易马数的增加,说明牧区养马数量的增加。[46]
据《甘肃通志稿·物产》记载:“西宁、甘凉一带,附近蒙番地方,产马多而驯良,约分数种:由农家畜养者为孳生马;由番地产者曰番马。由人力之调解,其最良者为走马,次为跑马,青黄红白黑各色均有”。《秦边纪略》记载:今天祝、庄浪一带,少植五谷,多事畜牧,“毳帐当路,畜马弥山”,“番之牦牛、犏牛、马、羊充斥道途”。[47]清雍正年间(1722—1735年)任甘肃布政使的钟保也说:“秦(此处指甘肃)俗以畜牧为生,多有(将山地)留为畜牧之场,比比皆然。”[48]
据《颇罗鼐传》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为剿灭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在收抚那霄六部(nags-shod-tsho-drug)、霍尔四部(hor-khabzhi,均为藏北蒙古游牧部落)、青海玉树(yulshul),上下仲巴(vgrong-stod-smad,今西藏阿里)、穷布白黄黑三部(khyung-dkar-ser-naggsum,昌都39族地区)等部落时,就缴获马羊牛2万余头(只)[49]。
嘉庆年间到过藏区的周蔼联也曾记载:
犏牛最淳,可骑以履冰。牦牛性极野。又有一种无角牦牛,番人呼为“哑”,又名毛葫芦,皆性劣。然番地黑帐房游牧,牛羊以千万计,以乳为粮,以毛为毳帐、衣服,随水草而行,既避差徭且长幼团聚。无耕种之劳。西宁蒙古亦然。所畏者“夹坝”抢劫耳。[50]
除民间畜牧饲养外,清初政府对高原地区苑马监及马场等官营牧场的设置,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青藏高原东缘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康熙四年(1665年)清政府虽然尽撤陕西各苑马监,但是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甘青牧区特别是青海地区的畜牧业经济还是有了发展。正如有学者评述的:“这一点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可资证明,但从青海蒙古势力一度达到极盛,其首领罗卜藏丹津敢于公然与清朝抗衡可以推想,其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实力是相当雄厚的。”[51]
雍正十一年(1733年),陕西总督刘于义因新疆战事紧张,急需补充马匹,遂筹划在河西等地开设马场,委派曾担任过西宁府知府的黄澍赴摆羊戎(今青海化隆县境)等地查勘。黄回报称:“摆羊戎周围约二百四十五里,其间荒地甚多,且饶水草,可牧马六七千匹。”[52]刘于义于是上奏朝廷建议在甘、凉、肃、西宁诸处各设马场一处。此议于乾隆元年(1736年)获得批准并得以实行。是年定制,每场养北马l200匹,以游击1人总理其事。场分5群,每群养化马200、牡马40匹。每群设牧马千总、把总各1人,牧副外委1人,兵10人为牧丁。所牧马不论牝牡,每3匹取孳生马1匹,3年内均齐一次。至乾隆十八年(1735年),甘肃提督所辖马场共达6处:甘肃提标所辖1处,马分5群;提属永固协所辖l处,马分l群;凉州镇标所辖l处,马分5群;西宁镇标所辖1处,马分5群;肃州镇标所辖1处,马分3群;肃州镇下安西协属沙州、靖逆2营所辖1处,马分l群。马场的设置,更进一步推动了牧区马匹等牲畜的饲养。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记载,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西宁镇马场生息繁庶,现有大小儿骡骟马三千七百余匹。”[53]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陕甘总督勒尔谨等奏:‘西宁镇属原设孳生马一千二百匹,因场地不敷放牧,在于镇属大通一带另躔宽厂。后为孳生过多,于乾隆三十四年分拨甘州、凉州、肃州三标营马一千一百余匹,尚存马二千三百余匹。迄今又十余年,除儿、骒交县变价,及补拨营缺骟马外,尚余马三千五百余匹。该厂地窄,水草不敷,气又寒冷,请分拨甘州、凉州、肃州三处马厂放牧。’报闻”[54]。由于管理有方,“至道光间,马大蕃息,多至二万匹。”[55]
清朝前期,官牧除马之外,还设立了牛、驼、羊等牧厂(场),与马并列,专门放牧。这一局面的形成,是由于明代的官牧业只需要马匹,而清代除了马之外,还将屯田用的耕牛,运输等方面用的骆驼,军士食用的牛羊等,都纳入了官牧来解决,从而使清代官营畜牧业的畜牧种类较前代更为广泛。乾隆初年,西宁镇还拥有常备骆驼1000余只,为了牧养好这批官驼,乾隆十三年(1748年)又在西宁设驼场一处,场分若干群。乾隆年间,西宁镇属绿营兵共有额设马4620匹,备战驼500只,又配炮驼100只,额设孳生驼200只,孳生马1200匹[56]。显而易见,清初官办马(驼)场经营状况是明显优于明代的。
清朝前期,由于政府重视,措施得当,青藏高原地区畜牧业生产依然保持着长足发展的势头。
三、结论
青藏高原地区幅员辽阔,河流纵横,水草丰美,自古以来为以藏民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的生息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以饲养马、牛、羊等牲畜为主的畜牧业经济在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明代至清前期,高原地区的农业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畜牧业生产依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肩负着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无论是以汉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朱明王朝,还是以满族为统治主体的清王朝,他们都充分认识到畜牧业经济在当地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而认可和维护这种符合地方特色的畜牧业经济,在高原地区和接近高原地区设置的官营茶马贸易和官办马场,虽然都是为满足统治者自身统治需要而设置的,但是在客观上对民间畜牧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相对于农业经济而言,畜牧业经济本身发展过程中的脆弱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藏高原自然环境本身决定了地表资源利用的主体方式只能是畜牧业生产,而如何基于生态环境脆弱基础上推动高原地区经济的发展,以满足当地人民日常生活所需,不仅是历史时期诸代统治者思考的问题,也给今天的我们关于如何促进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留下了诸多思考的空间。
[1]刘正刚,王敏.清代藏族农业经济初探[J].西藏研究,2003 (3);安平.清代前期藏区经济探析[J].中国藏学,2007(2);张世明.清代西藏社会经济的产业结构[J].西藏研究,1991(1);萧正洪.清代青藏高原农业技术的地域类型与空间特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6).
[2]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63.
[3]南文渊.藏族生态伦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14.
[4]明史纪事本末·卷10(故元遗兵)[M].
[5]明太祖实录·卷112(洪武十年五月癸卯)[M].
[6][17]明史·卷330(西域传二)[M].
[7]明太祖实录·卷126(洪武十二年九月乙亥)[M].
[8]明太祖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辛巳)[M].
[9]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戊子)[M].
[10]明太祖实录·卷67(洪武四年八月癸卯)[M].
[11]明太祖实录·卷69(洪武四年十一月庚午)[M].
[12]明太祖实录·卷72(洪武五年二月壬辰)[M].
[13]明太祖实录·卷72(洪武五年二月壬寅)[M].
[14]明太祖实录·卷73(洪武五年四月庚寅)[M].
[15]明太祖实录·卷78(洪武六年正月乙未)[M].
[16]明史·卷92(兵志四)[M].
[18]明太祖实录·卷202(洪武二十三年六月辛未)[M].
[19]明成祖实录·卷59(永乐四年九月壬戍)[M].
[20]明太祖实录·卷256(洪武三十一年二月戊寅)[M].
[21]明宣宗实录·卷97(宣德七年十二月丁亥)[M].
[22]明英宗实录·卷1(宣德十年正月甲午)[M].
[23]明英宗实录·卷116(正统九年五月丁卯)[M].
[24]明英宗实录·卷152(正统十二年四月丙午)[M].
[25][51]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193,194.
[26][52]王昱.青海方志资料类编[G].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590,858.
[27]郑洛.经略西陲解散群虏疏[M]//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404).北京:中华书局,1962:4388.
[28]明宣宗实录·卷23(宣德元年十二月丙戌)[M].
[29]明宣宗实录·卷24(宣德二年正月戊午)[M].
[30]明英宗实录·卷122(正统九年十月丁巳)[M].
[31]明宣宗实录·卷76(宣德六年二月庚子)[M].
[32][38][39][40][43][44](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上)[M].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14,217,219,221,226,227.
[33]清太宗实录·卷63(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己亥)[M].
[34]清世祖实录·卷70(顺治九年十二月癸丑)[M].
[35]清世祖实录·卷73(顺治十年三月壬午)[M].
[36]清圣祖实录·卷19(康熙五年六月壬寅)[M].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41.
[41]西藏志·卫藏通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484. [42]清世宗实录·卷20(雍正二年五月戊辰)[M].
[45]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41(兵十二·马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6]陈光国.青海藏族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457. [47]粱份.秦边纪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97,106. [48]钟保.奏陈开垦荒山管见折[G]//雍正朝汉文殊批奏折汇编.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49]策仁旺杰.颇罗鼐传[M].汤池安,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239.
[50]周蔼联.西藏纪游[M].张江华,点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33.
[53]大清会典事例·卷524(兵书·马政·牧马)[M].
[54]清高宗实录·卷1105(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丁卯)[M].
[55]刘郁芬,等.甘肃通志稿·军政·马政[M].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64.
[56]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18(乾隆二十七年刻本)[M].
A Brief Analysis on Animal Husbandry Economic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From Ming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Li Xiao-ying①Niu Hai-zhen②
(①North West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②Lanzhou Liberal Arts College School of Tourism,Lanzhou,Gansu,730070)
By presenting great amount of historical reference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animal husbandry which mainly includes raising of horses,cows,and sheep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lives of nomad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From M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although there were certain level of farming industry developed in the plateau,animal husbandry still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in social economics.Animal husbandry bar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official ran tea-horse trade and stud farms establish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helped in promoting local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To draw lessons from history,we have to seriously consider the issue of how can we promo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uch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daily needs of local people.
From M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Qinghai-Tibet Plateau;Animal Husbandry Economics
F326.3
A
1005-5738(2014)01-159-06
[责任编辑:蔡秀清]
2013-11-24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康雍乾时期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研究”(项目号:12XZS02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以制度转型为中心”阶段性成果。
李晓英,女,满族,河北承德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