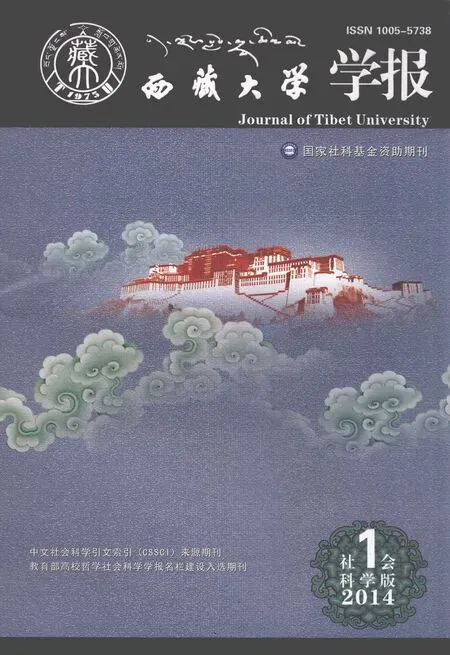“西康女子”涂面习俗考略
——庄学本影视人类学带来的启示
张亚莎 石泽明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西康女子”涂面习俗考略
——庄学本影视人类学带来的启示
张亚莎 石泽明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20世纪30年代庄学本西康考察摄影图片保留了“西康女子”涂面习俗极为珍贵的民俗资料,据藏汉文史料文献记载,这种被称作“赭面”的习俗早在吐蕃时期业已存在,20世纪末期在青海都兰地区发现的吐蕃墓中的棺板画也能见到这类习俗。文章认为赭面习俗更可能流行于“西康女子”及藏北牧区,与古代东氏族有密切关系。
庄学本;赭面习俗;女国;古代东氏族
1941年,时年32周岁的庄学本,将其长达7年(1934~1940年)的西康(今川西北、滇西北、青海西南等地区)考察摄影图片近300幅,以《西康影展》为题,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市举办巡回展览,向内地观众全面展示西部川、滇、甘、青等省区多民族社会的风土人情。这个当时即被于右任先生誉为“中华民族之精神”的“影展”,盛况空前,吸引观众20余万人次。“知君才是摩尔根,学本先生友之良。几度风流三度酒,人人艳羡新西康”,郭沫若以西方人类学鼻祖摩尔根比赋庄学本,对其西康的考察与摄影大为赞赏;而田汉的“何时思得西康去,匹马西风大渡河”,直抒内心豪情之余,对庄氏的西行壮举也是羡慕不已[1]。
学本先生堪称中国20世纪以人类学影像方式全方位记录西南西北诸民族原生态文化的第一人,当年先生所走过的民族地区及考察过的民族,大半个世纪之后,笔者也曾陆续走过或见过,然而先生当年捕捉到的那些真实生动、淳厚古朴,堪称原汁原味的画面,却大多不复存在!
学本先生留下的影视资料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自是难以估量,而其考察日志的重要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先生留给我们的既是原初状态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记述,也是边地考察札记之散文,细细品读庄文,便会随着那简约而略带些诙谐的语句,陶醉在“雪山如玉、野花似锦”、一派“古风盎然”的“美丽的乐园”中[2]。庄文的字里行间荡漾着一种远去了的却引人入胜的风韵,然而如果没有过朴素乃至艰辛的边地行旅经验,很难真正体会到他那简约与诙谐笔触的背后所承载着的厚重与真实,要知道早在20世纪30年代,敢于进入青海果洛藏区,无疑需要极大勇气,过程也一定艰苦卓绝。
先生的摄影作品令人感动,大半个世纪之前,这样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以其质朴而前卫的人类学“他者”的眼光与独特视角,为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些边地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现代化、全球化巨大浪潮的冲击下,还能残存几许?正因为如此,他所留下的那些图片,便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北甘青草原及川滇西北山地诸民族传统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图像资料。对笔者而言,学本先生影视资料中最珍贵的部分可能还是其中丰富的边地民族传统生活的细节,例如,在学本先生影像资料里,尚保留着大半个世纪以前边地藏族妇女的“涂面”习俗(这个发现委实让笔者兴奋不已)。细节本身往往积淀着该民族文化的古老传统因素,看似不起眼,实际上却是极重要的。
一、“西康女子”与涂面之俗
不久前,笔者有幸得到广州美术馆提供的庄学本1941年“西康摄影展”图说资料(“图说”即图片解说词),尽管未能见到与之相匹配的图像,但这部文字资料却已清晰地披露了学本先生1941年西康影展图片所涵盖的内容,其中第102图的文字,引起笔者极大兴趣。
第102图名为“涂面”,在解说词里,庄氏如是说:“涂面——西康女子尚有以赭糖涂面之俗。相传古时藏王因妇女容颜秀丽[3],使喇嘛不能遵守清规,于是下令妇女涂面,以护佛洁。涂面之另一意义谓高原朔风多励,涂之以滋润肌肤云。”
这段解说词有典型的庄氏影视人类学特点:首先,以图像方式真实保留某一民族的生活画面(尤其注重过程与细节);其次,注意搜集与之相关的传说及民俗方面的资料并做记录(这些记录不仅生动而且珍贵)。具体到“涂面”习俗,庄氏不仅记录下该地区妇女的“涂面”图像;与此同时,也并未忘记搜集当地有关“涂面”习俗来源的传说(例如可能与古代藏传佛教的传入相关);另外,庄氏显然还考虑到该习俗可能具有的实用性(因高原朔风多励而用于皮肤保护等)。因之,“图说”文字虽然简略,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其一,西康某些民族妇女尚保留“涂面”习俗;其二,这一习俗的古老至少可追溯到古代吐蕃赞普时期(唐朝)时期;其三,习俗的产生可能与吐蕃时期佛教的传入有关;其四,此习俗还与高原生态环境有关,为当地妇女们护肤的一种方式。
不过,这段文字也留下一些疑问,这里所谓的“西康女子”,究竟是西康地区的哪个民族(戎系?羌系?抑或是彝系?)而涂面民族的族属,正是笔者近年来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庄氏1934~1942年间所拍摄的“西康”,其地理及所涉及民族的范围较广,包括川西北的羌人、戎人(嘉戎)及大小凉山的彝人;川滇的木里番人、麽些、僰夷、白苗;另外还包括青海省境内玉树的“番”人等[4]。上述这些民族当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语族语系,其中属于汉藏语族藏语系的藏族,也分属于不同支系,川西北的嘉戎藏族和川西南的木里藏族属于康藏语支;青海省境内的果洛藏族则属于安多藏语支[5]。
藏族,在学本先生的书中,多以“戎”或“番”人称谓[6],所不同者,川西北或滇西北的藏族多称作“戎”,如他在解释“嘉戎”一词的含义时说,“‘戎’藏语称做‘嘉戎’,他们自称也是‘嘉戎’,意思是‘邻近汉人的藏族’”[7],而对于青海省境内的玉树藏族则明确以“番”人称之,他在考察记里记述道:“玉树的风俗充满了番人浑噩噩的古风[8]”,显然,在他看来,玉树藏族民风尤为淳厚古朴。从学本先生提供的图片看,嘉戎藏族与玉树藏族,其生产经济形态与服饰建筑等,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仅以“西康女子”冠之,很难了解“涂面”妇女属于哪一地区的哪些民族。
所幸笔者最近在由马鼎辉、王昭武、庄文骏主编的《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从文探访》一书里,找到了庄学本先生1937年摄于玉树地区的两幅玉树藏族妇女的“涂面”形象(第161页上的第6、7图)[9],虽然不好断然确定它们就是《西康影展》第102图之一,但至少可以确定“涂面”之“西康女子”确为青海省玉树地区的藏族年轻妇女。
二、藏汉文史料文献中的“赭面”之俗
青藏高原某些古代民族有涂面习俗,早在中古时期的汉文典籍已有记载,近年来,研究者们又发现藏文史料也同样有所涉及。目前已知见诸藏汉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有两个古代部族:一是唐朝初年创建吐蕃政权的吐蕃人(7世纪以前居住在雅砻河谷的悉补野部族);二是可能与苏毗这一藏北古代部族有些关系的女国人(7世纪中叶以前居住在西藏阿里地区)。
先说吐蕃这条线索。“涂面”与吐蕃政权的创建部族雅砻悉补野氏族相关的文献记载,来自汉藏两支不同的史料系统。汉文记载仅见于《旧唐书·吐蕃传》,《吐蕃传》谓文成公主嫁至吐蕃后,因“恶其人赭面”,弄赞(藏王松赞干布)曾“令国中权且罢之”。据此可知,公元7世纪中叶唐朝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吐蕃人尚有“赭面”习俗,因公主不喜欢,松赞干布下令吐蕃国人暂且停止。
藏文史料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却别有一番意味。公元8世纪中后叶,吐蕃政权正值赤松德赞赞普执政,《贤者喜宴》提到,藏王赤松德赞在王室发布的兴佛盟书里曾斥责吐蕃苯教的残渣余孽:“夫吐蕃之旧有宗教实为不善,……故众人沉溺于不善,有人身涂红颜,有人存心有碍国政,有人癖好使人畜生病,有人醉心于招致灾荒饥馑”。这里的“身涂红颜”即“赭面”之习俗。
由此记载看,公元8世纪中后期,吐蕃政权统治者已将“身涂红颜”(赭面)习俗看作“旧有宗教的不善”行为,且其“不善”的程度与有碍国政、醉心于招致灾荒饥馑、癖好使人畜生病等恶行同等。吐蕃政权的“旧有宗教”无疑当指苯教,赭面习俗既然已被列入“旧有宗教”(苯教)传统,,那么它便不仅仅是要被“权且罢之”,而是必须与“实为不善”的“旧有宗教”一起加以摈弃。依此推测,“赭面”习俗至少在赤松德赞时期已不再是吐蕃王族所允许的习俗。
爬梳更多藏文史料,还会发现几乎所有藏文文献在涉及到早期高原古代“赭面”氏族时,都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这个具有“赭面”习俗的部族在青藏高原古代史中曾显赫一时,其强盛时甚至统治过雪域西藏。然而奇怪的是举凡涉及到这段历史,藏文典籍不是惜字如金,便是语焉不详,如此种种,便让这个“赭面”族群显得扑朔迷离,神秘莫测。不过,有一点藏文史料说得很清楚,“赭面”部族显然与创建吐蕃政权的悉补野王族无关。既然“赭面”氏族不是吐蕃人,我们只能把眼光转向汉文史料中记载过的另一个有“涂面”习俗的古方国——女国。
当我们真正聚焦女国时,也才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关于高原女国的记载,只见于汉文史料,藏文典籍可以说是只字未提。换言之,藏文典藉虽然频频提到“赭面”部族,却完全不见女国的记载[10]。与此相反,汉文文献记述女国史实颇详,《隋书·西域传·女国》、《北史·西域传·女国》,另外唐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均提到过这个风俗奇异的女人国[11]。
《北史·西域传·女国》记曰:
“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
其俗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瑜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
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
上述史料里明确提到女国人有“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的“涂面”习俗。概言之,汉文文献里的女国人其最突出的习俗有二:一是女王制,“其俗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二是“男女皆以彩色涂面”[12]。
三、女国人、传说中的罗刹女与赭面习俗
女国与女国人之“赭面”,虽然不明确见诸于藏文典籍,但据笔者考证,“赭面”习俗却与西藏古史中的“岩魔女”传说有密切联系。也就是说,藏文典籍虽然不曾有女国人赭面习俗的记载,却反复强调“赭面”与“岩魔女”(女妖——注意她的性别)的特殊关系。
据藏文典籍记载,藏族是猕猴与罗刹女(又称岩魔女)结合后繁衍出来的族群。五世达赖喇嘛所撰《西藏王臣记》记述,猕猴与罗刹女结合后“生出六婴,其行为各不相同……六婴逐渐繁衍,藏土遂成为人类之邦[13]”。由这个古老的传说推测,今日之藏族至少是由两大族系融合而成,其中父系为猕猴种,母系为岩魔女种。值得注意的是藏文史籍对吐蕃族源父母两系先祖,表现出明显的褒贬态度:对父系的猕猴种极尽赞美之辞;却对母系的罗刹女种系则多批评指责:“具父种性者,心机锐敏,恻隐为怀,小心谨慎;具母种性者,面多赤色,专嗜恶业,秉性顽强[14]”。在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发现母系族人除了专嗜恶业、秉性顽劣之外[15],还有个特点便是“面多赤色”(赭面或涂面)。
事实上,西藏历史文献中大凡提到母系罗刹女(岩魔女)时,都会出现“赭面”的字眼;不仅如此,一些藏文史料还会进而提到,这个有着“赭面”习俗的“罗刹女”部族与西藏早期历史传说中的“神魔统治”有关。
“在吐蕃,……最初被称为有雪吐蕃之国。中间一段时期被神魔统治,被称为赭面之区,后来被称为悉补野吐蕃国,……。”(摘引自《汉藏史集》)
“此后由神与岩魔女统治,西藏遂称神魔之域,并出现了食肉赭面者”。(摘引自《五部遗教·王者遗教》)
根据《汉藏史集》可知,截止到吐蕃政权结束之前,西藏高原早期的历史可大致分为三段:最初的一段被称作有雪吐蕃之国(这里完全没有提及统治者的名号,大抵是指西藏早期的混沌状态)。中间的一段时期,雪域高原曾被神魔统治,这个所谓的“神魔统治”,按《五部遗教·王者遗教》的解释是“由神与岩魔女统治”,这段历史时期的西藏也被称作“神魔之域”。后面的一段是指后来兴起的悉补野吐蕃国,即我们所熟悉的唐代的吐蕃政权,该政权由雅砻河谷的鹘提悉补野部族所建立,其王称作“赞普”。
很显然,“神魔统治”发生在吐蕃政权建立之前,说明在吐蕃政权统治西藏之前,存在过另一个曾经统治过西藏高原的部落政权,而在这个神魔统治政权中,便赫然出现了“岩魔女”的名字。与“岩魔女”相关的记载不是“赭面之区”,便是“食肉赭面者”,可见,“岩魔女”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有赭面传统的族群,而其明确的女性性别特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青藏高原西部曾有过的那个赫赫有名的女国——如前所述,女国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女权制;另一个特点便是它的“赭面”习俗。
拂去历史的尘封,我们发现岩魔女并非只是出现于藏族族源传说系统中的神话人物,在高原早期史里,她更像似某一强族的代名词(或象征)。进一步推论,无论是这一古代民族的“赭面”习俗还是其统治者的女王身份,抑或是“王姓苏毗”的文献记载,均会让我们联想到汉文史料中提到的那个神秘而奇特的“女国”。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许很简单,藏文文献中的“岩魔女”,实际上就应该是汉文典籍中的“女国”。
很显然,“岩魔女”并非只是藏族族源传说中的神话元素,它应该是雪域西藏对某些古老部族的真实的历史记忆。“岩魔女”曾经是西藏高原的统治者,其背后的历史真实则应当是“岩魔女”所统领的族群,也曾经是统治过西藏高原的强有力的部族;该部族甚至先于吐蕃王族之前统治过西藏高原。当然,以后的情形是新兴的雅砻悉补野赞普王族后来者居上,取代其强势,成为7世纪以后整个青藏高原的统治者;而由统治集团主宰的史学体系在创建其族源传说时,势必会留下本氏族重新解释、阐述或改造的痕迹;这也是为什么一涉及到“岩魔女”统治西藏的那段历史,藏史记载不仅稀缺模糊,且多少有些贬低的意味,甚至有些许妖魔化成份的原因所在罢。
客观地说,吐蕃的史官们,承认“岩魔女”部族是构成藏族族源的重要一支,但其褒贬倾向却也曲折地反映出母系部族被后来核心部族战胜并多少有些排斥疏外的情感记忆。虽然在吐蕃时期,该系所代表的旧有宗教势力已被新兴的吐蕃悉补野王族所弹压,且在吐蕃政权结束之前,其势力也很可能已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败北[16],但情感记忆中的某种排斥性尚未被淡化。后世的藏文史料肯定以吐蕃悉补野雅砻赞普谱系为其正统,如此,对“岩魔女”部族祖先或人格特征所附加的贬低或指责的记忆,自然会在吐蕃的神话传说中积淀下来,而“岩魔女”的历史,也就这样被淹没在远古藏族族源的神话传说之中了。
四、赭面习俗与高原古代东族
青藏高原某些古代部族有“赭面”习俗,不仅见于古代汉藏文献记载,难能可贵的是近年来也得到了考古学方面的证据。
2002年8月,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郭里木乡的巴音河畔,考古工作者对两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出土棺木三具,棺木四面均有精美彩绘,那些表现墓主人招待宾客们的欢宴豪饮以及狩猎通商等日常生活场景的棺板画,清晰地记录下吐蕃政权统治后期生活在吐蕃边地的权贵们的生活方式[17]。其中,画面中人物脸颊多有涂红(研究者谓之“赭面”妆[18])的现象,曾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19]。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非棺板画里所有的人物都绘有“赭面”妆,绘有赭面妆者只是其中一部分人,这部分人的服饰与冠帽与其他没有赭面妆的人,似有些区别,例如帽子多为扁平式样,另外,服饰确实给人以“衣服略同华夏”的印象。
青海都兰古墓葬的考古年代大致在吐蕃政权后期,棺板画中参加宴饮的权贵们却仍然保持着“赭面”习俗。如前所述,《旧唐书·吐蕃传》时提到7世纪中叶吐蕃人的“涂面”因文成公主“恶其人赭面”,松赞干布曾“令国人权且罢之”;而8世纪后期赤松德赞时期,“赭面”习俗也已被归类于“旧有宗教”的不善行为而必须加以摈弃;因此吐蕃政权时期,“赭面”至少是不为官方(赞普系统)所提倡的习俗。那么为什么在青海都兰一带的古代墓葬棺板画里的部分人群,仍保持着赭面之习俗呢?对此,笔者以为原因很可能是“赭面”原是青海某些土著民族的古老习俗,即使吐蕃王国腹心地带的卫藏地区禁止赭面,但其禁令似乎对这个远离王都之城的区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换言之,赭面习俗源于青海土著部族,既不是流行于吐蕃全境的习俗,也不是吐蕃政权统治氏族的习俗[20]。
由此不难推测,青海古墓葬棺板画上大量施以“赭面妆”的男女们更可能是生活在当地的土著族群,而这个族群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创建吐蕃政权的雅砻悉补野部族,在文化习俗与历史传统上有明显区别。换言之,有“赭面”习俗的这一族群,当主要生活在被藏史称作“马区”的青海[21],青海省海西州古代墓葬出土文物证实,“马区”与“赭面”习俗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另外,这种神秘关系还会让我们联想到西藏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的出生地,研究者们已基本锁定在藏文典籍中被称作“马区”的黄河上游地区[22],《安多政教史》说“黄河上游全部地区在岭·格萨尔王统治下”[23],而这位赫赫有名的战神格萨尔王便出生于一个古老的“棕色”东姓氏族(“棕色东族”在格萨尔史诗中是一个很常见的藏文词组)[24]。某古代氏族的修饰定语为一种颜色,从字面上看,似乎很难理解(即使是从逻辑上分析,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也不可能是棕色人种),但如果联想到“赭面”习俗,事情便清晰起来——所谓“棕色氏族”实应作“赭面氏族”之解,是以特定的“赭面”习俗作为其突出特征修饰或界定这个氏族的修辞方式。《格萨尔王传》在形容格萨尔时曾明确提到他是一“赭面人”,而《五部遗教·神教》在提到格萨尔的化身马头明王时,也强调他是一赭面人[25]。
以上种种与“赭面”习俗相关的历史元素,无论是汉文典籍中的女国,还是藏文文献中的“岩魔女”传说;抑或是青藏高原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西藏早期文献中提到的青藏高原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区”;尤其是近年来考古发掘成果——青海西部土著民族古代墓葬出土棺木画等等,均向我们证实这样一个史实:早在雅砻悉补野部落建立的吐蕃政权统治西藏之前,曾有过一个有着“赭面”习俗的古代方国,其国“王姓苏毗”,推行一种令中原汉人王朝颇感惊异的女权制;该国曾以强悍武力统治过高原,其统治在藏文史料中被称作“神魔统治”;这个更多与战争和妖魔相关的部族,起源于青海黄河上游地区,由于其尚武的特点,很可能后来被冠以格萨尔王(战神或兵器之神)的名号;而格萨尔出身的古老氏族——“棕色的东族”之“东”(藏文转写“sTong”)姓,显然与藏文典籍记载中普遍出现的东姓苏毗人有关;至于苏毗人的后裔,据至今仍流传于藏地的传说,一般认为青海省玉树地区的藏族,当是古代苏毗部族的后代。
余论
当我们在古史与考古文物中遨游一圈返回时,才发现,关于青藏高原上某些古代族群的“赭面”习俗,尽管我们拥有藏汉文古史的文献资料,并在流传于高原的《格萨尔》英雄史诗中找到了相应的证据;21世纪以后,还进而发现了考古学方面的支持;但我们缺乏的却是至今仍活着的民族学方面的佐证[26]。
正因为如此,此时能够有幸与庄学本先生的人类学影视图片中的玉树年轻藏族妇女的“涂面”相遇,对于笔者近年来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对于研究证据链条的完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于此,笔者在阅读庄学本先生早年的考察日志和他所留下的丰富图像资料时,深为先生客观而缜密的人类学眼光所折服:由于先生当年客观而朴素的记录,让研究者能从中受惠的不仅仅是某些民族传统文化细节的保留(玉树藏人“赭面”习俗的保留);还能够从宏观上廓清,同为“藏族”,但川西北的“嘉戎”、川西南的“木里番人”、青海果洛藏族以及青海玉树“番人”之间明显或不太明显的区别;了解到同为青海藏区,属“安多”藏语方言区的果洛藏族与属“康”藏语方言区玉树地区藏族之间,文化上如此不同;从而更深切地感受到藏族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在此,我们真的应该深深感谢庄学本先生当年非凡的功绩以及他所留给我们丰厚的遗产!
[1]马鼎辉,王昭武,庄文骏.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从文探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231.附录:《1941年庄学本西康影展来宾题词》。
[2]庄学本.西北边荒旅行记之“弁言”。转引自马鼎辉,王昭武,庄文骏.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5.
[3]广州美术馆提供的《西康摄影展图说》这部分的原文是:“相传古死时藏王因妇女容颜秀丽,使喇嘛不能遵守清规,于是下令妇女涂面,以护佛洁。……”“古死时”似不通,大抵还是指古代的吐蕃时期,因出现藏王(赞普)的称谓。——笔者注。
[4]庄学本.西康摄影展图说[M].
[5]庄学本先生1934~1941年期间所拍摄的藏族,主要是康方言区与安多方言区的藏族,这些藏族主要分布于川西北、滇西北及青海省南部及甘肃省南部。四川甘孜州、西藏昌都、青海玉树属康方言区,其余地区为安多方言区。——笔者注。
[6]以今天的人类学视角看,这些称谓似乎不那么含有平等尊重之义,但学本先生考察记中的民族称谓大抵更多来源于当地民族之间的习惯称谓,倒不必苛求之。
[7]庄学本.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48.
[8]马鼎辉,王昭武,庄文骏.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从文探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164.
[9]该书的图片解释为“妇女涂面——玉树藏族有些青年妇女用酥油和上黑灰,涂在面颊上,能超护肤作用,另可以毁容,作为一种装饰,回避坏人的欺辱。”但不知此解释词是否为庄氏的原文。见马鼎辉,王昭武,庄文骏.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从文探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161.
[10]笔者曾在拙著《西藏的岩画》里讨论过这个问题。张亚莎.西藏的岩画[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382-384. [11]玄奘《大唐西域记》记曰:“此国境北大雪山中,……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躁暴。东接土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5:409.
[12]综合唐代多条史料所提供的信息看,女国的地理位置在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境(或札达盆地);国家推行女王制,由女王与小女王共同掌管国家,其俗妇人轻丈夫,国内男人唯以征伐与田业;国内有城池建于山上,方五六里;经济生产以射猎为主,同时靠贩盐获利;虽是女权统治,但国人性情强悍(人性躁暴),“数以天竺及党项战争”;宗教信仰既有来自天竺的阿修罗神,也有可能源于本土的树神信仰,另有“鸟卜”巫术习俗;葬俗是二次葬“贵人死,剥其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于铁器埋之”;该女国曾与中原王朝有过来往“(隋)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吐蕃强大之后,该国很快被吞并,不复存在于史料。
[13]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刘立千,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14]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刘立千,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9.而另一部早期西藏历史著作《西藏王统记》对藏族族源的父母两系人格秉性之优劣,记载的更为详细:“如是此雪域人种,其父为猕猴,母为岩魔二者之繁衍,故亦分为二类种性:父猴菩萨所成种性,性情驯良,信心坚固,富悲悯心,极能勤奋,心喜善品,出语和蔼,善於言辞。此皆父之特性也。母岩魔所成种性,贪欲嗔恚,俱极强烈,从事商贾,贪求营利,仇心极励,喜於讥笑,强健勇敢,行不坚定,刹那变易,思虑烦多,动作敏捷,五毒炽盛,喜窥人过,轻易恼怒。此皆母之特性也。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32.
[15]猕猴与岩魔女结合繁衍藏人这一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是藏民族对其族源构成中存在两大系统的远古记忆,也可以理解为一支系统以猕猴作为本部族的祖先图腾,而另一支系统则以岩魔女为部族的祖先图腾标志,两者的联姻则意味着两大部族后来的融合,整个神话传说是对藏族形成历史过程的形象描述。这一神话传说的内容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究其传说的构成模式,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传说将两大族系按男女两性先祖来划分,父系位于核心位置,而母系则被置于从属地位,从而奠定猕猴种姓在这一组合中高贵的及决定性的地位;二是在对两大系统的人格描述中,显示出明确的褒贬抑扬,父系祖先代表藏民族人性中善良、坚定、诚实、谦逊的一面,而母系祖先则代表着人性中贪欲、善变、狡猾与傲慢的另一面。这样一种传说结构本身,提供了非常有意味的线索和叙事结构。见张亚莎.岩魔女·女国·古象雄——由西藏岩画神鸟“穹”(khyung)引发的思考[G]//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西部西藏的古代历史文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20]“赭面”不完全是吐蕃王族的固有习俗的推测,除前文所提供的史料外,还可补充如下几条:①如前所述,《贤者喜宴》里提到的赤松德赞兴佛盟书,已将“身涂红颜”列入“吐蕃之旧有宗教”之不善行为规范,即苯教的规范。我们知道,吐蕃王族虽然有32代王以佛教治国,但佛教却是外来的。②从棺板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冠帽看,虽然有少数几位身着吐蕃贵族服饰冠帽者有绘赭面妆,但绝大部分的赭面妆者是头戴扁平帽的一类人,这类人也与吐蕃王族的高官贵族有区别。③就吐蕃王朝时期卫藏残存的少量壁画看,卫藏地区的权贵不见“赭面”的习俗。④从在年代上距离9世纪不远的10~11世纪卫藏佛教壁画中出现的供养人(早期供养人多是当地的豪门贵族)的形象看,他们同样没有“赭面”的习俗。⑤古格王国的创始者是卫藏雅砻部吐蕃赞普血统的直接后裔,10世纪前后由卫藏逃亡至西部阿里,从阿里后弘期早期壁画中王室供养人的形象看,他们也没有“赭面”习俗。
[21]《后藏志》提到“藏地三区,古代藏文典藉中划分青康藏地区时说,卫藏为教区,多堆为人区,多麦为马区。”见觉囊·达热那特(觉囊巴·多罗那它).后藏志[M].佘万治,译.阿旺,校订.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97页及第170页注释403。又见《萨迦班智达传》,第126页,转引自(法)石泰安.西藏史诗与说唱艺术的研究[M].耿升,译.陈庆英,校订.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380.
[22]“格萨尔史诗中的地名同时揭示了应将英雄的地区确定在安多和黄河上游地区”,(法)石泰安.西藏史诗与说唱艺术的研究[M].耿升,译.陈庆英,校订.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274.
[23]转引自邢海宁.果洛藏族社会[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193.
[24]同注20,第659页、第663页等。
[25]同注20,第733页、第746页。
[26]古代有“涂面”(赭面)习俗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的西南及西藏自治区的北部与西部(即藏语称之为“羌塘”的地区),青海省西南玉树地区藏族曾流行过赭面习俗的结论,主要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考古文物得来,却缺乏现有的民族学调查资料;而“羌塘”草原上的牧民虽然如今还可见到类似的古代遗风,但该地区民族的赭面习俗,却很可能源于青海省境内的古代羌系民族。
Research on Unique Facial Make-up done by“Xi Kang women”-Inspired by Visual Anthropologist Zhuang Xueben
Zhang Ya-sha Shi Ze-ming
(Central Universty for Nationalities Chinese Rock Painting Research Center,Beijing,100872)
Photos from Zhuan Xueben’s field trip to Xi Kang in 1930s preserved valuable information on Xi Kang women’s unique facial make-up custom.Accord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literature both in Tibetan and Chinese,this unique custom which is called“Zhe Mian”has been existing since Tubo kingdom period.In 20th century,this unique custom of facial make-up appeared also on the coffin painting of Tubo tomb discovered in Qinghai Dulan area.I believe that this custom of“Zhe Mian”was popular among Xi Kang women and in nomadic area of north Tibet which show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Dong Clan.
Zhuang Xueben;Zhe Mian custom;the kingdom of women;ancient Dong Clan
K892.3
A
1005-5738(2014)01-121-07
[责任编辑:周晓艳]
2013-11-24
张亚莎,女,汉族,广东南雄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岩画。
——以《边事研究》刊载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