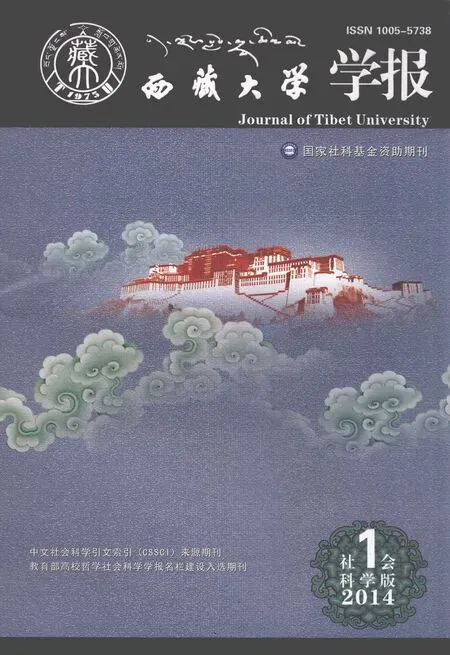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丧礼服制度》写本残卷考索
乔 辉 张小涓
(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054)
唐代礼图之作存世不多,文献可见者仅杨垂《丧服图》(卷数不详)、张镒《三礼图》九卷、杜佑《唐礼图》十五卷。《法藏敦煌文献》P.2967文书载有《丧礼服制度》一卷,该卷是从贞元中淮南节度使杜佑所上新制《唐礼图》十五卷中节选的,此为传世文献中唯一可见的杜佑礼图内容。姜伯勤先生《敦煌社会文书导论》之《P.2967丧礼书对〈开元礼〉的变通》[1]中曾对此件文书有过介绍,吴丽娱先生《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之《丧服制度》(I)[2]对此文书亦有说明,然此残卷依然有不少问题有待考释。笔者不揣浅陋,试结合前人的研究对《丧礼服制度》残卷再行考索。
一、《丧礼服制度》说略
法Pel.chin.2967《丧礼服制度》一卷乃杜佑《唐礼图》之残文。该卷书写体式乃“右图左书”,与传统的“左图右书”式有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命名此卷为“小册子,丧服图”,《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则定其名为《丧礼服制度》。汉魏六朝以来,《丧服图》作大都亡佚,笔者以为杜佑《丧服图》实为唐代大历中杨垂《丧服图》(已亡佚)之后的又一重要礼图文献,对唐代丧服形制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意义。
此件写本为双页对折小册子形式,前后均残。今存七页,但以单页计为十二页,共七十一行文字,每隔数行配有相应插图一到两幅,共有十七个插图。从写卷内容可以知道文字是对丧衣各部所作的制度说明,内容以《大唐开元礼》、《仪礼·丧服》及郑注为主、兼引魏晋六朝礼学家葛洪、崔灵恩、崔凯等作进行说解。这些图文使我们对唐代丧服形制可以进行全面考察。据卷首残存文字,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此卷的来历以及此卷与《唐礼图》的关系:
误为古今服变广狭制,以致差谬。今见淮南节度使杜佑进上新制《唐礼图》十五卷,其有《丧礼服制度》一卷,精麄不差,轻重合宜,当穷本书理,深得其宜。故持此以匡时要。
由残序知此《丧礼服制度》乃《唐礼图》之一卷,据文书行文及残缺的文字内容,其内容非《唐礼图》原文。由“今见”、“故持此”等行文之文辞,文书的撰者当为与杜佑同时代之人。
进上《唐礼图》之人乃淮南节度使杜佑,然考之史志目录及其它文献皆无杜佑撰《唐礼图》说。《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言杜佑出身仕宦,乃中唐政治家,撰成二百卷著作《通典》,其中礼典一百卷,可见杜佑对礼制既精通又颇为重视,实为唐代礼学家。《丧礼服制度》内容所言绖冠裳裙等服制和衣制与《通典》内容接近,故杜佑撰《唐礼图》有理。吴丽娱曾言“《唐礼图》十五卷,顾名思义即知是为礼配图之作,那么,如果是杜佑所作,则与《通典》一书应当是互补和一致的。查杜佑上《通典》在贞元十七年,则《唐礼图》之上也应在此前后,其最晚应不超过贞元十九年。由于《旧唐书·经籍志》乃五代转录开元盛时四部书,不记此书是很自然的。但是宋人欧阳修、宋祁所修之《新唐书·艺文志》也未见记载,说明此书至少五代或宋时已佚。”笔者以为其言有理,宋人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征引六家礼图总图,唯独不引杜佑《唐礼图》,原因亦在于此。《唐礼图》的撰写时间当在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据《杜佑传》、卷一三《德宗纪》言,杜佑任淮南节度使在贞元五年末至贞元十九年之间,即789年到803年之间,《唐礼图》的撰写当在此时。
就礼图性质而言,杜佑新制《唐礼图》十五卷,其卷数和名称显示此礼图当为唐代“三礼”总图,《丧礼服制度》即为唐代《丧服图》别图,此写本《丧服图》与《三礼图集注·丧服图》“倚盧”之“唐大历年中有杨垂撰《丧服图》”并为唐代《丧服图》之重要礼图别图文献。由残序言“持此以匡时要”,可见新制《唐礼图》在当时的地位之高。法藏敦煌文献中的《唐礼图》残卷内容对研治唐代丧服制度及丧服图样有着重要的样本价值,对礼图文献有重要的史料补苴作用,实为礼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礼书。
法藏敦煌文献P.2967《丧礼服制度》言新制《唐礼图》,曰“新制”实相对“旧制”而言,此处的旧制《唐礼图》当为张镒撰《三礼图》九卷。《旧唐书·张镒传》卷七十五言∶“张镒,苏州人,朔方节度使齐丘之子也……交游不杂,与杨绾、崔祐甫相善。大历五年,除濠州刺史,为政清净,州事大理。乃招经术之士,讲训生徒,比去郡,升明经者四十余人。撰《三礼图》九卷。”张镒约在770年左右撰《三礼图》,早于杜佑《唐礼图》的撰作时间,故张镒礼图在前,杜佑礼图在后。《隋志》卷三二载张镒《三礼图》九卷,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屡引张镒《三礼图》,可见唐代礼图的代表作为张镒《三礼图》,其在当时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故杜佑之前的旧礼图即为张镒《三礼图》。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曰“新制”意味着对旧礼图的革新,我们结合此卷具体内容来谈其“新”处。
二、《丧礼服制度》内容考索
丧服制度包括服制和衣制。服制是历来变化最多,亦最为礼家所关注的问题;中古丧服礼之变革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通过服制来反映。衣制则是由丧制和服制所决定,服制轻重和丧制长短以及服丧期间祥、禫变除各节对衣制都有影响。[3]
法藏敦煌《丧服图》写卷中共涉及五服所需的绖、冠、缨武、總、衰衣、负、中、辟领、裳等形制。我们结合相关内容对这些部分择要考索。
(一)绖(首绖、腰绖)
按《开元礼》云:“苴麻首绖大九寸,左本在下,绳缨,十三月小祥,别除之,五分首绖,去一以为腰绖。大七寸二分。绞重两结相去各四寸。”(今人并无制也。)妇人绖如男子,又有绞带。按《仪礼·丧服传》郑注云:“首绖象绳布冠类,以国也。”又云:“苴麻大扼,扼围九寸。谓自中指至大指为扼。”此言中之制,其降杀大小乃通人之形,亦不先九寸为限。如童子当室者亦取小童中指至大指。如之……。
牡麻首绖大七寸二分,半布为绞带(杖周与不杖周绖带与三年同)。大功首绖大五寸七分,长殤及未成人皆九月,绖以绳缨。……葛洪《丧服变除》云:“今之孝子,腰绳即绞带,其来久矣。”郑司农云:“麻在首及在腰皆为之绖。绖,实也。”又《三礼义宗》云:“男子重首,女子重腰。”绖服之法先除重义,具丧礼,此不备载之。
按:据光绪十二年氏公善堂校刊本《大唐开元礼》卷一百三十二,首段“苴麻首绖”为斩衰三年绖带之制,次段“牡麻首绖”为齐衰三年之制。勘之校刊本《开元礼》,“苴麻”后脱“绖带”二字,“绳缨”后脱“五分”二字。“十三月小祥,别除之”为齐衰三年节制,与斩衰之制不符,此乃衍文。“绞重两结相去各四寸”之“重”,《开元礼》作“垂”,据文意,“重”乃“垂”之形讹。“各”字,《仪礼·丧服》郑注、《开元礼》、《通典》皆无,“各四寸”即为“八寸”,与“四寸”相距一倍,文中注言“今人并无制”,“各四寸”说或为唐代丧服制度之例。然唐代《贞观礼》、《开元礼》及张镒《三礼图》辑佚本皆无此说,笔者以为“各四寸”与“垂两结”相砥砺,故“各四寸”说阙疑存之。《仪礼·丧服》“苴绖杖绞带”郑注:“首绖,象缁布冠之缺项。”胡培翚正义:“郑以吉时缁布冠,别有缺项以固冠。”[4]“绳布冠”当为“缁布冠”,“绳”乃“缁”字形误,此乃传抄所致讹误。“以国也”,据《丧服传》胡培翚正义言,当为“以固也”。“苴麻大扼”,十三经注疏本《仪礼·丧服传》“苴绖大搹”郑注:“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围九寸。”“扼”、“搹”乃古今字之别。“此言中之制”当为“此言中人之制”,“中”后脱一“人”字。
“牡麻首绖”乃齐衰绖带之制,“大七寸二分”后,“半布为绞带”前,《开元礼》有“左本在上”语,此与苴麻之制“左本在下”所言相异,“上、下”之异乃“苴麻”、“牡麻”绖之形制相异之处,即:苴绖乃从额前绕项后,复至左耳上,麻尾加在麻根之上;牡麻绖乃从额前向左围向头后,麻尾藏在麻根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然《开元礼》“左本在上”与十三经注疏本《仪礼·丧服传》“齐衰三年”之“牡麻绖,右本在上”完全不同,据郑注及胡培翚正义言“左下为父,右上为母”为男女内外尊卑之别。据古礼言丧服之制先男后女,故齐衰之“牡麻绖”亦当男在先,为“左本在下”,《丧礼服制度》不言“左本在下”实为承前省略。故《仪礼·丧服传》、《开元礼》言失当。“未成人”,开元礼、通典、丧服图、五服图解皆不言“未”;据文辞及文意,“长殇”即17-19岁,其后当为“成人”方符合上下文意,“未成人”实则衍一“未”字。“大功首绖大五寸七分,长殤及未成人皆九月,绖以绳缨”,据《仪礼·丧服》,“绳缨”仅为“斩衰”之制,“齐衰”、“大功”、“小功”等皆为“布缨”。“腰绳即绞带”,“绞带”古代丧制斩衰服所系之带,绞麻为绳而成。《仪礼·丧服》:“丧服,斩衰裳,苴絰杖、绞带。”郑玄注:“绞带者,绳带也。”贾公彦疏:“绳带也者,以绞麻为绳作带,故云绞带。”《礼记·奔丧》:“袭绖于序东,绞带反位,拜宾成踊。”孙希旦集解:“绞带,绞苴麻为之。吉时有大带,有革带,凶时有要绖,象大带,又有绞带,以象革带也。”《晋书·舆服志》:“革带,古之鞶带也,谓之鞶革,文武众官牧守丞令下及驺寺皆服之。共有囊绶,则以缀於革带。”“腰绳即绞带”,文献无说,然与文意相符,腰绳即腰带。“腰绳”乃俗语,此说或与唐代传统的礼学庶民化倾向有关。“腰”,十三经注疏本《仪礼》皆作“要”,“要”、“腰”古今字。残卷征引东晋葛洪《丧服变除》、梁人崔灵恩《三礼义宗》内容各一条,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王谟《汉魏遗书钞》等引二书内容皆无此二条,故《丧礼服制度》所载葛洪、崔灵恩言实为重要辑佚之材料,可补苴清代学者所未备。由上,《丧礼服制度》内容虽较为简略,然在辑佚、校勘方面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武、總
按《开元礼》云:“斩衰之冠,正服、义服冠同六升。右缝通屈之二条绳为武。垂下为缨。所为条属於绖上。”今都无无此绳缕,武之制於义乖。全童子已下当室者则免而仗之也。用妇人以六升布为總。總用束发,今无此制。今幉头或得其义耳。
按:《仪礼·丧服》:“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齐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无爵而杖者何……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故“全童子已下当室者则免而仗之也”之“仗”当为“杖”。《丧服》:“其长殇皆九月,缨绖;其中殇七月,不缨绖。”郑玄注:“绖有缨者,为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绖有缨。以一条绳屈之。小功以下绖无缨也。”《丧服》:“丧服,斩衰裳,苴经、杖、绞带,冠绳缨,营屦者。”贾公彦疏:“云冠绳缨者,以六升布为冠,又屈一条绳为武,垂下为缨。”胡培翚正义:“武,谓冠卷……冠以梁得名,冠圈谓之武……非若后世之帽,尽举头而蒙之也。吉冠之梁,两头皆在武上,从外向内,反屈而缝之,不见其毕。丧冠外毕,前后两头,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缝之,见其毕。”《通典·礼六十五》“丧礼杂制”条曰:“丧冠条属以别吉凶,三年之练冠亦条属,皆右缝。”杜佑注:“别吉凶者,吉冠不条属也。条属者,通屈一条绳若布为武,垂下为缨,属三冠,像太古丧事略也。”《丧礼服制度》言“二条绳”与《丧服》郑注、贾疏,《通典》杜佑注所言有异,胡培翚《仪礼正义》据前人说言武乃一条绳,其两头下垂据丧礼言。武乃二条绳说,当为唐代具体丧服制度内容,此乃古礼“一条绳”说之演变。宋人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十六“冠绳缨”云“冠绳缨条属注云属犹著也。通屈一条绳为武,垂下为缨,著之于冠也”,[5]可见,“两条绳”说当为唐礼图所专有,宋时一仍古礼“武乃一条绳”说。据文意,“今都无无此绳缕”当衍一“无”字。
“總”,《仪礼·丧服》“传曰:總,六升,长六寸”,郑注:“總六升者,首饰象冠数。长六寸,谓出紒后所垂为饰也。”又《礼记·内则》郑注云:“總,束发也。垂后为饰。”《释名·释首饰》:“總,束发也,总而束之也”。《说文·纟部》:“總,聚束也。”段注:“聚束也,谓聚而缚之也。悤有散意,纟以束之。礼经之總,束发也。禹贡之總,禾束也。引申之为凡兼综之偁。”可知,“總”乃女子束发之头饰,其形乃后垂状。《丧礼服制度》“總”之形乃圆形,礼图文献无,唐制“總”图有存图之功。《丧礼服制度》言“總用束发,今无此制”表明唐代“總”制已然消失,与古礼有异。《仪礼·丧服》“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布總”,胡培翚正义:“布總,兼子与妇言之……今案:《檀弓》:南宫縚之妻,为姑總八寸。郑注云:齐衰之總八寸余。”古礼,男、女皆著布總;唐代,该制消亡,以类似于“總”之“幉头”取而代之。据《唐会要》言,唐时幉头为男子的主要首服,明人刘绩《三礼图》卷二之“總”言“幧头也。自关以西秦晋之郊曰络头,南楚江湘之间曰帞头,自河以北赵魏之间曰幧头……覆结谓之帻巾,或谓之承露”,[6]其图类似今之头巾,与《丧礼服制度》“總”之“圆形”完全相异。可见,“總”制在唐代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也是唐代丧礼制度的革新之一,明代礼图“總”之形制或承《丧礼服制度》“幉头”说。
(三)负
负在背上,谓负板也。广一尺,下至胫,适领一寸。又云辟领一尺六寸,谓辟领一边开四寸,量之有八,别一尺六寸也。
按:《仪礼·丧服》“负,广出于适寸。适,博四寸,出于衰。”郑玄注:“负,在背上者也。适,辟领也。负出于辟领外旁一寸。”贾疏:“以一方布置于背上,上畔缝著领,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负名。”胡培翚正义:“负出于辟领外旁一寸者,据下辟领并阔中,總尺六寸,负之,两旁各出辟领一寸,则尺八寸也,此言其广也。”《大唐开元礼》卷一百三十二言“负在背者,适,辟领也。负出于辟领外旁一寸”。由上,负乃丧服背上的一块方布。上端缝在领上,下端垂放,因在背上,所以称为负。然《丧礼服制度》言“负”乃“在背上”、“下至胫”,则“负”之形制由背上至胫部,并非固定在背上。此说与古礼所言有异,当为“负”之形制之延伸。《武威汉简》之“丙本《丧服》”言“负广出于适,寸适,博四寸,出于(衰),衰长四寸,博六寸,衣带下尺衽二(尺有五寸)”,[7]《仪礼·丧服》“衽二尺有五寸”郑注:“衽所以掩裳际。”故“负”之下限亦在“裳”之两旁,非“下至胫”。可见,唐代《丧服图》之“负”图与汉制有异。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第十六《仪礼丧服图式》言“负,亦名负板。用布方一尺囗囗囗六寸,缀於背上,领下垂之”。朱氏所言“缀於背上”与唐代图式大致无二,可见汉、唐、宋三个时期的礼图样式的些微差异体现了礼图的变化。
“适领一寸”后,“又云辟领一尺六寸”前,《开元礼》作“辟领广四寸,则与辟中八寸两之为尺有六寸”,此可补苴“辟领”之广制。据郑注《丧服》“适,辟领也”,故“适领一寸”当有脱文,无“适领”一说。
三、结语
法藏《丧礼服制度》是敦煌卷子中所见关于唐代丧衣制相对规范和完整的著作。此卷与《通典》和《开元礼》相比,图文并茂,解说更加直观形象,较之杨垂《丧服图》,该卷相对完整。就某种意义来说,此《丧礼服制度》为唐中期以后丧衣服制礼式的代表。尽管《丧礼服制度》因传抄乃致文字有部分讹误,其作为目前仅存的唐代《丧服图》的样本价值凸显无疑,宋代、明代《丧服图》或因袭其说,或变更其说。
《丧服图》内容出自杜佑《唐礼图》,就其中的革新内容来看,《唐礼图》当有不少与前代礼图之作相异之处。这种创新,首先体现在其礼图的命名上:《唐礼图》的命名是以朝代取名,言外之意这是唐代专有的礼图,这也是不同于以往礼图的一大创新,是礼书的一大创造。其次体现在礼图的内容方面:《丧礼服制度》残卷中的“绖”、“中”、“武”、“總”、“负”等制与古礼有异,宋明礼图图式与此残卷图式亦有不同,这足以说明其礼图内容、图式均是有唐一代所特有的。吴丽娱先生以为《丧礼服制度》残卷是以唐朝朝廷礼制为核心,辅以吉、宾、军、嘉、凶五礼,给予了本朝特有礼制的一部著作。我们以为其说有大而化之之嫌,《唐礼图》当是一部依托于公礼而又寄情于私礼的一部“庶民化”、“社会化”、“人情交际化”的礼图专著。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就在于唐代重视礼学发展以及“礼学下移”的“全民化”倾向所呈现出的不盲从守旧、勇于革新、与时俱进的精神。随着《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开元后礼》、《曲台新礼》、《元和新定书仪》等的修订,丧服制度作为五礼之“凶礼”的核心内容亦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形成了丧服制度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然相关的礼图著作却是不多,特别是存世的丧礼服图的著作更是罕见,这一现象颇让人费解。日本学者副岛一郎在《从“礼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趋向》中曾言“虽说唐初承续着六朝礼学的传统,但它也随即急速地衰废。那么,六朝以来的丧服学如此急剧衰退,其原因何在?我想其原因之一是唐朝制定贞观礼等而改变了古礼,尤其是增改了丧服。”[8]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需进一步考察。
[1]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22-24.
[2]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17-433,443-449.
[3]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6-19.
[4](清)胡培翚.仪礼正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3.
[5](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19.
[6](明)刘绩.三礼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32.
[7]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135.
[8](日)副岛一郎.从“礼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趋向[J].学术月刊,1999(2):6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