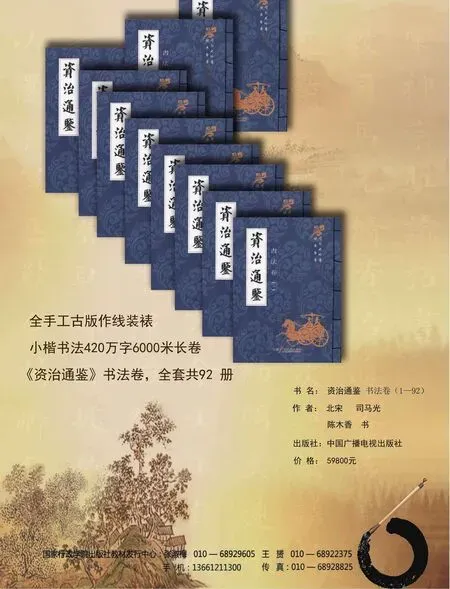探索理想人格的早期轨迹毛泽东批注《伦理学原理》
■ 陈 晋
探索理想人格的早期轨迹毛泽东批注《伦理学原理》
■ 陈 晋
毛泽东读书,有详有略,有经有权。在他读过的书中,有的作了大量批注并推荐给别人阅读,有的在他的著述和谈话中时常引用和发挥;有的是在某个时期集中阅读,有的是从青年时代到迟暮之年多次阅读;有的对他思考和解决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有明显影响,有的则只有放到他一生的经历中品味,才能看出潜在的渊源或关联。
本期选登毛泽东早年仔细阅读的一部书《伦理学原理》,具体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读书的,着重体会一代伟人的学用之道。
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之邀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湖南第一师范老同学杨韶华托他将早年借阅的一本《伦理学原理》,归还毛泽东。杨还在该书扉页上写道:“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人事之“趣”,缘自该命运之“奇”。毛泽东投身革命后,曾将他在长沙求学期间读过的一些书籍和笔记、日记,送回韶山老屋放置,土地革命时期,乡亲们担心它们落入敌手,均烧毁了。这本写满毛泽东批语的《伦理学原理》,却因被杨韶华借去阅读而得以幸免,成为见证毛泽东早年思想探索轨迹的珍贵读物。
《伦理学原理》,是德国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泡尔生是柏林大学教授,康德派哲学家。其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中文本《伦理学原理》,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1909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除序论和导言外,共九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厌世主义、害及恶、义务及良心、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道德及幸福、道德与宗教之关系、意志之自由。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材教授伦理学课程,讲课时,多数同学兴趣不大,不甚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毛泽东还根据书中的一些观点,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先生给打了100分。在杨韶华归还的这本《伦理学原理》上,毛泽东逐句圈点,画了许多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全书共约10万字,毛泽东写的批语即达12100字,批写时间是1917年下半年。毛泽东的批语及原文,已经收录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湖南省委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
毛泽东阅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绝大部分是表达他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一些观点的引申和分析;小部分是对原著论述的赞同语和一些章节段落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也很多,常见的批语是“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等等。批语中还有不少是结合墨子、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联系五四运动前夕的政治国事和文化思潮,对原著观点进行发挥,饱含探索真理真知、塑造人心道德、改革国家社会的热情和沉思。
据周世钊记述,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青年时代拥有一个鲜明主张:要拯救多灾多难的国家,就必须改变人的精神和身体,塑造新的国民。通俗地说,就是要先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去改造客观世界。这种认识,从思想传统看,源于湘学士风的影响,如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都持这样的观点。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倾向,也大体如此。梁启超倡导塑造新民,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代表了当时比较普遍的看法。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既反映了这股思潮,又有充满个性的理解和发挥。
《伦理学原理》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人类先有生活之目的,“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其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毛泽东的批语,大多从这个观点出发,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考,并对他后来建构新的伦理观发生不小影响。诸如,强调事物的运动变化,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消极无为,重视人的行为精神价值,高扬豪杰精神和圣贤精神,追求济世救人,献身崇高理想,等等。这些,都极具理想主义甚至是浪漫主义的个性气质,隐隐然透出其理想人格的影子。毛泽东当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和后来著名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也都强调人们的思想、理想、道德、意志之于人们干事业的极端重要性。
在毛泽东的批语中,“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精神上之利己主义”,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颇为奇异的观点。
青年毛泽东认为,人们的道德评价来源于自身的利益感受,即“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由此,他认可《伦理学原理》讲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观点。但是,毛泽东认为,这只是人格道德的表层内容。社会固然需要个人主义,需要冲破一切压抑个性的东西,但由此解放和实现的,应该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精神上之利己主义”。只有彻底、完美地实现自我的冲动和意志,才算是“遂其生活”,才会是最高境界的“善”。因此,道德上的“善”和精神利益有关,和肉体利益无关,“肉体无利己之价值”。所谓“利己”,应该是“高尚之利己”,本质上是“精神之利己”。这样的利己主义,与平常说的损人利己的自私,不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一般的利他主义更为高尚。毛泽东批注道:
“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只有不顾一切追求崇高理想,仅仅在“精神上”利己的人格,才是崇高的人格。这就是毛泽东年轻时的人格道德理想。
《伦理学原理》典型体现了康德学派“二元论”道德观。读此书,还使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认识: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的转变,常常要经过“二元论”的阶段,要真正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必须要读其对立面的书籍。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说:“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