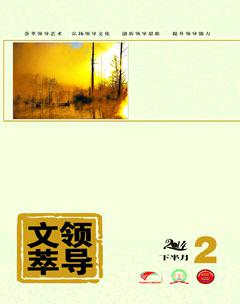仁者之心
张晓林
清早起来,范希文搬一个小木板凳,去院子里的那棵槐树下弹琴。槐花已经开了,一串一串挂满枝头。坐在槐树下,槐花的清香让人陶醉。这样的心境,最适合弹琴。
琴声在槐花间穿越。槐花和着琴的旋律开始舞蹈。这个时候,范希文的妻子李氏开始下厨做饭。李氏对这支曲子再熟悉不过了,这些年来,她都是听着这支曲子做早饭的。这是一支名叫《履霜》的曲子,是她手把手教给丈夫的。范希文只会弹这一支曲子,再教他,他说,会弹一曲《履霜》就行了,会那么多干什么?李氏就打趣他,我看干脆叫你范履霜吧。
李氏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世代书香门第。这样的一个女人,也是打心底敬佩范希文的,在她看来,能遇到这样的丈夫,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刚过门的那些日子,她的婆婆,脸上皱纹多得像几张重叠的蛛网,常常向她谈起范希文小时候的事,每逢谈到儿子,婆婆满脸的皱纹就一下子舒展开来。
婆婆说,希文进京赶考前,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为给家里节省点口粮,他就住进了淄州长白山下的一座寺院里。和他一起住的还有个姓刘的秀才。每天黄昏,等僧人们都消停下来,他们就开始在一口铁锅里煮米。这些米粗糙无比,咽下去刮得喉咙疼。煮好一锅米,倒进瓦盆里面,算是第二天的三顿饭了。过一夜,瓦盆里的米凝结成了一块,希文他们用刀把米切成六块,吃的时候各捞出一块儿用开水泡着吃。
每当婆婆说到这儿,李氏都要插话问一句:“他们也不吃菜吗?”
婆婆瘪瘪嘴,慈祥地看着媳妇,说:“有时吃有时不吃。全凭老天爷了,春夏二季,去山上寻些野葱,七八根,十几根,就着下饭;十冬腊月,雪封住了寺门,就倒上小半瓶的醋汁,加上一小勺盐……”婆婆开始用衣襟揉眼,“这种日子,希文一过就是三年哪!”
婆婆心疼儿子。在李氏看来,这三年未必不是好事,也许因了那三年,范希文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每天睡觉前,都要盘算一下今天花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到底该不该花。如果这些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他就会把双手搭在已经有点发福的小肚子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否则,将一夜不能入眠,第二天一定把昨天不该花的那点钱省回来才心安。
女人嘛,总爱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希文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他的心胸大着呢。李氏很清楚地记得,在苏州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块宅基地,一个堪舆大师看后私下对范希文说:“世代当出卿相。”希文笑笑,说:“若果如此,我不敢一家独享,应为天下人所共有。”于是,就把这块地捐出建了苏州府学。
想到这儿,李氏为丈夫自豪起来。
李氏在想着这些事的时候,范希文一曲《履霜》弹完了。他收了琴。他要简单吃点早餐,然后到朝堂去面见仁宗皇帝。一想起要见仁宗皇帝,范希文的心里就有些堵。前两天西京光化军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如何处理这件事上,他与枢密副使富弼的意见简直是水火不容,争吵得脸都红了。今天就是要到仁宗皇帝那里来见个分晓的。
平日里,他和富弼相处得很融洽,富弼像对待长者一样尊重他, 帮了他不少的忙。范希文还记得那件事。有一次,他给人写了一篇墓 志铭,写好后让富弼看,看后富弼也没说什么。等把墓志铭装进信封, 就要寄走了,富弼忽然说:“还是让师鲁看一看吧。”第二天他专程拜 访了师鲁,师鲁看过,说:“你怎么把知州写成太守了?当今没有这一官名啊,你一定是为了脱俗才这样叫的吧。”
希文诺诺。
师鲁又说:“希文名重一时,文章定会流传后世,你一句与实际不相符合的话,必定会遭到后世人的质疑与争论,将有无数人为你这句话考据论证,喋喋不休,付出惨重代价。写文章不能不慎重啊!”
师鲁就是尹洙,当朝文章大家,与希文亦师亦友。
事后希文想想,当时富弼应是也看出了这一问题的,他不点破,却让师鲁指出来,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啊。
但希文也深知富弼的脾气,犟得很,他认准的事,八匹骡子去拉,他也不会轻易回头。
这年暮春的一个上午。范希文和富弼一同站在仁宗面前。仁宗问:“光化知军弃城逃跑一事如何处置,二位爱卿可商议好了?”富弼率先往前迈了一步,口气决绝地说:“应按军法处置,斩了他!”仁宗看了看范希文。范希文不慌不忙地向仁宗行了君臣之礼,然后说道:“光化城既没有城郭,也没有兵卒,强盗来势凶猛,光化知军不逃匿躲藏,他又能如何呢?望陛下从轻发落。”仁宗沉思了一下,说:“准范爱卿的奏。”
走出朝堂,富弼的火气还没消。范公太宽容犯罪了,这让仁宗如何治国!他第一次对范希文说出不恭敬的话:“参政是想修炼成佛的啊!”范希文笑笑:“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想成佛。但我的话有道理。等到政事院再给你细讲。”
富弼显得愈发不高兴。
到政事院,二人坐下来,范希文从容地问:“你希望把皇上教唆成一个暴君吗?”停了停,他放缓了语气:“仁宗还年轻,我们岂能动不动就教他杀人,等他杀得手滑了,不但我们做大臣的会有杀身之虞,天下百姓也会因此遭殃啊!”
富弼猛然警醒,额头的汗水纷纷滚落。
(摘自《小小说选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