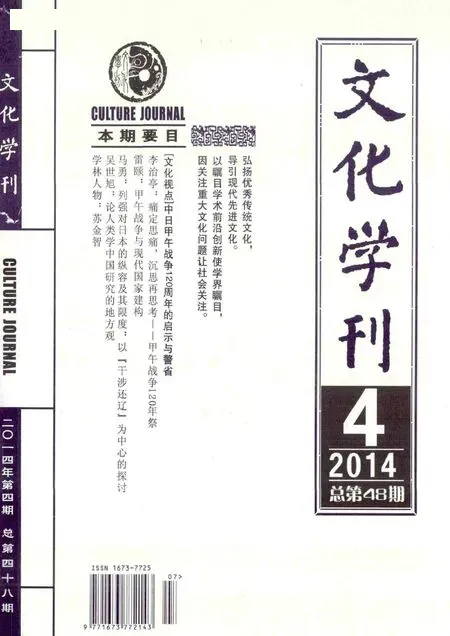“性本爱丘山”与“刑天舞干戚”
——论李铭的短篇小说创作
李春林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李铭是一位新锐作家,其小说、散文、影视剧创作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作品被《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多家报刊转载,由他编剧的电影《磨剪子戗菜刀》被评为2006年十大优秀国产影片,《村官李八亿》获第十届数字电影百合奖优秀影片奖。
读罢李铭大部分短篇小说,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他有点像陶渊明。虽说他早已离开乡土,但他内心深处却始终挚爱着乡土的丘山,渴望回归自然与人性的本真。同时,他又对假恶丑有着几近本能的仇恨,很有些“刑天舞干戚”的战斗风姿。
我首先抄录一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其一》,看看诗人的理想世界: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抒写其脱离官场、归隐田园的惬意生活。在他心目中,唯有田园才是生命与生活的理想乡,而官场则是樊笼,正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老先生确实归返自然了,去“诗意地栖居”了。
当下,成千上万离开了自然又想重返自然的人们,却难以真正地登上“幸福的火车”,欣赏大自然的“幸福的雪花”,收获“幸福的麦穗”了。这就是李铭的短篇小说所表现的重要内容。
李铭来自底层——乡村的底层,他又在城市的底层摸爬滚打,尝尽了底层的辛酸苦辣。他自述道:“五味杂陈以后,方能炼化成功的灵丹。”[1]他的灵魂受到了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甚至不把底层的人当人、不把来自乡野的人当人的社会现实的深深伤害。蚌病成珠,种种伤害作用于他自幼即非常“丰富的情感世界”[2],其结果便是一篇篇塑造了虽然未免“粗粝简单”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是富含诗意的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说,通过他们开释自己的思乡情结。
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李铭笔下的许多人物虽然身已进城,但心犹在乡。由于“日益严重的阶层贫富分化、消费社会中新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导致的冷漠、算计、猜疑和敌对等负面情绪在人群中扩散”[3],因此他们觉得城市有如樊笼,羁縻着自己的身心,他们只能将城市当作暂时栖身之地。回返旧林与故渊,成为他们的终极目标。
《幸福的火车》中的大姐巧玲和小妹水玲,为了供养二妹完成学业,来到城市打拼,她们出卖自己的劳力,而为了使得自己的出卖劳力 (经营一小饭店)获得保障,不得不向官员们和黑势力出卖肉体。她们本想“堂堂正正干干净净地活着”而不能,被迫为改变整个家庭的处境而牺牲自己的肉体。她们在备受肉体折磨的同时,也承受着精神的苦刑。因为她们本系来自纯净的乡野的纯净的人啊!小饭店的掌勺者“大哥”对故事叙述者帮工小李所说:“她们是小姐也是好小姐。”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社会。作品比较细致地描写了姐妹俩的道德与良知的挣扎,她们对摆脱现状,重回乡野的向往:“我们不属于这个伤心的城市。……我每天晚上听着火车的声响 [按:她们开的小饭店在火车道旁],我都觉得那是多么幸福的火车啊。因为它通往家的方向。”这城市是她们肉体的炼狱,精神的樊笼。其实她们最初的离家也是为了回家,出卖肉体正是为了保卫自己。此种悖论,正是城乡矛盾、强者与弱者矛盾、有权 (钱)与无权 (钱)等诸种矛盾的折射与衍化。
倘若说《幸福的火车》还仅是一种回乡的向往或准备,那么《幸福的雪花》却是一种回乡的行为——一种悲壮的心理回乡。
《幸福的雪花》主人公胡长锁与李凤芝是一对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经过自己的打拼,胡长锁当上了包工头,但他们仍不属于城市,并面临着开发商欠薪的苦恼。他们也曾算计过下属的民工 (与开发商相比,只能说是小算计,决不可同日而语);李凤芝尤表现得未免俗粗,甚至用非常手段找老板索要工钱 (到老板家撒泼)。但在关键时刻,她却用大智大勇援救身受重伤的民工柴三玉——其实他之受伤与胡李夫妇并无关联。为了使得柴三玉有钱看病,李凤芝以一种赴死的勇气爬上塔吊向开发商索薪。她在冰雪侵袭的塔吊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但她落下来时却“感觉自己是一朵幸福的雪花”。此种感觉恐怕不独是因为获得了救人的快乐,体验到了自我存在价值的欣慰,主要是获得了归乡的幸福。“回家是他们共同的心愿。”此处的他们亦不仅仅是胡李夫妇,而是包括着柴三玉在内的所有农民工。“李凤芝就纳闷成天给城里盖楼,楼都让谁住呢……”不管谁住,都没有楼房建筑者的份。这就是城市剥削乡村的现实,城市欺凌乡村的现实——连她们的孩子都受城市孩子的欺负。泼辣的李凤芝毫不掩饰地唆使孩子对欺负者进行复仇,所以,笔者认为,李凤芝在自由落体的那一刻,其实也获得了“切腹复仇”(以自杀的方式进行复仇,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娜斯泰谢是个典型)似的快意。被欺凌与被侮辱者以抗争与复仇昭示出与城市的决绝,以自由落体的姿态享受到了自由回乡的快乐。
至于《幸福的麦穗》的回乡主题的表现则更为曲折和复杂。麦穗作为一个农村女孩想离乡念书却遭到母亲的阻拦。被迫穿着低俗、暴露的服装在母亲开的饭馆打工,换得工钱,好去师专上学。她终于获得了上学的机会,有了幸福,然而,她幸福吗?“幸福的麦穗”其实是个反讽。并且,最后她能否上学,仍是未知数:故事叙事者“我”本是来饮马池 (麦穗的家乡)搞文化调研的,却被乡政府判为来调查矿难 (麦穗之父亦死于矿难)的,他受到了乡政府派来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大奎的种种威胁,乡政府通过大奎告知,只要“我”不报道矿难 (其实“我”根本不知此事),那么乡政府替麦穗付学费。可是在“我”离开饮马池时,路遇前往饮马池的警车,从而留下悬念:这是抓捕那造成矿难、隐瞒矿难的一干人犯吗?倘如此,谁来保障麦穗的学费?开放的结尾,含有多种意蕴及情思,正义的伸张,很可能成为麦穗上学的危机;麦穗如能上学,矿难就可能得不到伸冤。这是一种两难,更是一种尖锐的矛盾。其实也是一个象征,昭示出当下社会的种种困惑。“半个月后,我还能在城市里遇见那个叫麦穗的女孩吗?”麦穗能否成为大学生,对“我”来说,真的成为了一个谜。那么如何理解作品的回乡主题呢?首先,麦穗的具体生活环境业已非乡村化,开矿已经成为那里的主要产业,而麦穗的家庭也已非农化,都已染有城市的特征。所以,麦穗欲离的已不是本色的乡土。其次是麦穗的命名,这样一个青春而清纯的少女名曰“麦穗”,就使得她更富大地自然的气息,使得她本人成为纯净的乡土的象征。她要离弃龌龊不堪的乡村里的“城市”,到学校读书——学校在麦穗的眼中无疑尚属理想乡,是陶冶人的灵魂之所在,是城市里的“乡村”,亦是保证麦穗本真之所在。所以,麦穗的上学,乃是回乡的别种方式。“我转身,在麦田深处的毛毛道上行走,原野上的麦穗向我迎面扑过来,在我身前身后摇曳起丰收的舞蹈。”这是麦穗之舞,是回乡之思,是返归自然之情。然而,紧接于此的一句话:“大路上,警车的鸣叫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使得麦穗的上学——回乡——回归本真成了未知数。“复得返自然”?离乡人只有期待再期待。
看来,李铭委实是一位有点残酷的作家,他让人们受苦,又使得人们的期望的实现分外艰难,或者看着火车隆隆驶过,却仍未上车,抑或仅是一种精神的飞翔。而惟其如此,才更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
二、寻找人性本真之旅:返归自然的另一种路径
托尔斯泰幼时喜作一种游戏:与兄弟们寻找“绿棍”——那上面有解救人类苦难的药方。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寻找的旅途,哲人和先知寻求的是与整个人类命运相关联的正确之途,芸芸众生寻求的是自己的人生幸福之路。幸福有种种样态和层级,有浅近与高尚。有时恰恰是在初看起来是寻找浅近的过程中,发生了质变,实现了浅近向高尚的升华,抵达了人性的本真世界。《寻母》讲叙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
一般说来,李铭的作品不喜欢煽情,《寻母》或许是个例外,此作在貌似平静的叙述中却能催人泪下。女主人公刘桂香为给父亲治病,出来骗婚。不成想,逃跑没有成功,反而生米煮成熟饭。又不成想,她的欺骗对象也就是她现在的丈夫老满死于矿难。而老满有临终嘱咐:财产全部给刘桂香,他与前妻李秀秀所生之女臭妞交给其亲母抚养。刘桂香于是带着臭妞踏上了寻母之路。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李秀秀,但此时的她早已另组家庭。她担心臭妞的到来会破坏这个家庭 (她的新夫不知她以前有过婚姻),拒收臭妞。于是两个女人在推拒臭妞上展开了拉锯战。在这过程中,刘桂香与臭妞间的感情日增,业已产生了带臭妞返乡的想法。不料臭妞出了车祸。给臭妞做手术时,刘桂香与李秀秀两个女人争相在家属栏签字:两人的母性都被强烈地激发出来。由互相抵拒变为互相争抢臭妞的抚养权。其实李秀秀是被人贩子拐卖给老满的;被公安部门解救之后很想带走与老满所生臭妞,但遭到老满之母猛烈地抗拒,她的母爱权利被无情地剥夺。“寻母”不独是臭妞的寻母,而且是两个女人对母性的寻觅,或曰复归与苏生。作品在一个拐卖人口、买婚骗婚的故事框架内,以人性(母性)的丢失为起点,以人性 (母性)的激活为归宿,细腻地描写这样一个由人性异化到人性归化、探寻人的本真之旅,其实也正是人的返归自然,是人的精神还乡。
《寻找马东山》同样是寻找和实现人的本真之旅。牛老倔是一个兼职的民办教师 (他还要务农)。他之所以有了此种角色,是因为他所在的深山沟刘杖子穷乡僻壤,沟外的教师无人肯来授课,有关部门于是决定聘请沟里的一位老农牛老倔代课,其报酬则由沟外学校每个老师从各自的工资中抽出30元共330元来解决。但某次有人反映有一个学生没有参加考试,应是逃学,建议少发30元。校长担心倘若如是为之会影响牛老倔的积极性,于是从自己的工资拿出30元补上。牛老倔闻知后,便开始寻找那个其实当时没有逃学只是出去打工的学生马东山,让他向学校说明真情,好证明自己所拿的330元是完全应得的,并无照顾成分,不是任何人的施舍。他为此而历尽曲折、艰辛。但他却执意寻找下去,终于找到,事实得以澄清。寻找马东山,就是寻求真相,寻求本真,这种执着、认真的精神,恰恰是我们的国民性格中所缺乏的。鲁迅先生曾多次指出这一点。其实,牛老倔的寻求真相,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为了彰显自己的人的本质,为了回返自然的生存状态,尽管他也带有农村小生产者难以避免的某些缺点,如有时让学生帮助自己干农活等。但被别人以为自己拿了不应拿的东西,在他看来则是一种大是大非问题,是一种人格侮辱。被别人施舍,使他产生了屈辱感。为此他片刻不宁。他认为“人活着啥?活的是人性,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为寻求而备尝劳累乃至饥寒的毅力正是由此而发生。在底层文学中以如此方式剔挖小人物的自尊心、坚守自己的本真而自然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实为罕见。此作可能受启发于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但影片侧重表现的是人的责任心,《寻找马东山》昭示的是人的尊严的不可侮。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更深刻。
在李铭的笔下,偶有“大人物”也在追求重返本真自然的生存。《星星点灯》中的县长杨长生当是典型一例。尽管他也有缺失,对老婆经济犯罪制止不力,也有一个情妇,甚至利用老婆的关系为情妇买了一套房子,但他内心深处还葆有一定良知,做了许多好事。作品比较细腻地展开了杨长生本真自然的一面,甚至是富有诗性的那一面。他喜欢君子兰;他能够在大会上正式宣布,老婆的事情是她个人的私人行为,有关部门不要给她开绿灯、开口子;他在山区吃请,然后掏钱;他听说残疾孩子上山抓蝎子卖钱维持学业而眼睛湿润,并去他家慰问;他在山野的夜色中萌发了诗心;他会因与肖丽娇的初次云雨而“心存愧疚”;他会记得“第一次”时“蒿草的气息”“满天的星星和灯光下像星星的蝎子”;他会对肖丽娇的放荡“不寒而栗”;他“宁可不要政绩,也不想做罪人”;他想在自己没下台之前把农民卖菜难的事情解决了……他的死亡是最富有诗意的一笔:在倾听了一位卖菜老人的大吐苦水后,他给了这位老人100元钱,将老人的萝卜全部买下,装进自己的汽车,最后被郑副县长发现“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当是多种焦虑引起的心脏病发作导致的猝死。这也是别一种方式的死在岗位上。他离开了贪污的老婆,不忠的情妇,回归到真正公仆的角色,回归到自己人性的本真自然。
此处有必要谈谈小说的题目《星星点灯》的寓意。作品是这样将《星星点灯》这首歌引进的:
……杨长生观看了山区孩子们的表演,肖丽娇上台演唱了一首歌曲,是跟一个残疾孩子一起合作演唱的。杨长生记得很清楚,歌曲是台湾歌手郑智化演唱的《星星点灯》。
为了比较深入地分析此歌在这篇作品中乃至他的全部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寓意(他以此歌曲名不独命名了一篇作品,而且命名了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有必要引用一下此歌歌词:
抬头的一片天 是男儿的一片天
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 做梦的少年
不知道天多高 不知道海多远
却发誓要带着你远走 到海角天边
不负责任的誓言 年少轻狂的我
在黑暗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
看着你哭红的泪眼 想着远离的家门
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盏希望的灯火
星星点灯 照亮我的家门
让迷失的孩子 找到来时的路
星星点灯 照亮我的前程
用一点光 温暖孩子的心
现在的一片天 是肮脏的一片天
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 再也看不见
天其实并不高 海其实也不远
人心其实比天高 比海更遥远
学会骗人的谎言 追逐名利的我
在现实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
看着你含泪的离去 想着茫茫的前程
远方的星星请为我点盏希望的灯火
……
多年以后一场大雨惊醒沉睡的我
突然之间都市的霓虹都不再闪烁
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
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守候
副歌部分未全引用。有人认为此歌是一首励志歌曲;有人认为是表现希望之后的失望、无奈,以及仍存在的微茫希望。我认为,都对,但都不全面。此歌有着比较丰赡的情感内容和社会内容。倘若说首段是抒写梦想的美好,那么第二段则是梦想破灭后的自省、不甘;第三段在原词中是叠唱的副歌 (此处只引用一段),也是全篇的主旋律,这主旋律却是“回家”,是将“来时的路”作为“前程”,而这要用“星星点灯”来照耀,星星又是不可能点亮人间灯火的,所以这只能是梦想破灭之后的美好想象和精神自慰;第四段回到现实世界,天空肮脏,星星不见,更为深刻地自省梦想与现实的天壤之遥;第五段是痛苦的自我解剖和微茫的希望;末段比较昂扬,抒发了自省后对城市的厌弃和对“星光”的向往,仍将此“星光”作为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星星点灯业已成为一个意象。
那么,应当怎样理解歌词与作品的耦合关系呢?
就《星星点灯》这篇具体作品而言,歌词应是杨长生内心的写照。他本来自乡村,也曾有过美好的理想 (从他为官之后所作的种种好事即可证明)。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往往使他感觉到自己的脆弱,一个环卫工人被撞死,他想伸张正义却因肇事者属于官二代、肇事的车属于公安局长而不了了之。每当这样的时刻,他必然怀念乡土,怀念自己的家,希望“星星点灯”给自己带来温暖与光明。他将貌似正义感强烈而又富有诗意的山区小学校长当作了能够点亮自己疲惫的心灵之灯的“星星”,最终才发现这“地上的星星”却是“蝎子”,星星只有天国才有。他在临逝之际,或许真地看见了“星星点灯”,作品没有写明。当“物质压倒精神的欲望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4]时,就作品本质而言,其所写的就绝非是一个官员的肉体死亡悲剧,而是写的在当下人的本真难以寻找的悲剧,写的是时代的精神悲剧。
就《星星点灯》这部小说集而言,歌词又是作家本人内心世界的抒写。他同样来自乡野,对于底层世界有着更为深切的体验,因而也有着更为强烈的改变自己、改变环境的热望。这在他的《我与小说,不得不说》一文中有着充沛的表现。他的希望与执着,他的永不言弃,他的直面现实的种种苦难时勇敢地生存和奋斗下去的毅力,恐怕也来自“星星点灯”的鼓励,来自用天上的星星来点亮地上的灯光的美好甚或未免浪漫的理想的召唤。可是来自底层的他,更多地感受到“现在的一片天 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 再也看不见”,更多地体验到“多年以后一场大雨惊醒沉睡的我/突然之间都市的霓虹都不再闪烁”,所以,一方面他塑造了巧玲、李凤芝、麦穗、刘桂香、牛老倔、杨长生等寻求自然、寻求本真、寻求理想之光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寄予着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在使得他们获得诗意的同时,亦实现了自己的诗意的栖居;另一方面,他以鲁迅的批判精神为楷模,对那“肮脏的一片天”——当下社会的不良方面,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三、扫描社会病状,哀悯多艰民生
鲁迅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写道“……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李铭同样如此。他的短篇小说,极写弱者的种种不幸,饱蕴着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愫。
李铭对当下社会的城乡二元对立有着独到的体验和深切的会心,许多作品的主题即是此。
《坚硬的水》书写城乡的严重对立,并在此格局中表现官与民、富与穷等的尖锐矛盾。城里人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农民工,甚者蚊子都变成了势利眼,专门叮咬农民工。若是仅仅将此理解为此事是由于农民工的生活条件所决定,那么就是没有很好地理解作家的寓意:他是以蚊子作为城里人的象喻。而农民工们拉的屎都整齐划一,则明显地是对他们的生活条件(饮食)之恶劣的曲折表现。此作对于社会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进行了全面抨击。一句“张金发以前在武浅浅眼里的缺点现在都成了优点”,道出了人们的价值观业已发生了180度的逆转。“这个时代,还会有撒谎脸红的男人吗?”当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已经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撒谎恐怕成为人们的本能。《城市黄昏里的一只候鸟》中的二燕子在进城后却又不被城市接纳,融不进城市中,最后跳楼自杀。她最后被城乡严重二元对立的社会所吞吃。《民工大嘴》写的是大嘴和锤子给王科长装修卫生间时狗的丢失而引发的悲喜剧。大嘴最后宁可在拘留所呆着也不愿到王科长家干活。作品的主旨即是大嘴这样一句话:“我是琢磨过味来了,拿我不当人呢。什么老板,什么王科长,……看他们城里人表面正经,办的事脏着呢。”这是大嘴的觉醒,他认识到,不独是王科长不把他当人,事实上是整个城市不把他当人!作品的丢狗寻狗的故事相当曲折,处处所昭示的都是“人不如狗”这样一个主题:一方面,农民工的生活和地位不如“公仆”的宠物;另一方面,公仆的“人性”不如狗性。
那么,农村本身的情况又何如呢?也绝非理想乡。
《娘家侄儿侯赛寅》同名主人公因超生备尝人间苦难:罚款,扒房,老婆和大女儿先后被村长逼奸,且大女儿被强制为其妻,而他本人在饥荒年代脚落残疾,在当下又被汽车碾压了一只手。《血案》则是以闹剧形式写的悲喜剧。作品系复线结构。黄土梁子村主任郝大炮被李德力用镰刀砍倒,乡派出所派许警官调查,最后发现郝大炮逼奸人妇,猥亵幼女,贪污公款。原告成了被告。原来李德力在夜间以为一头驴偷袭他的白菜地,施了杀手锏,结果却是伤了对其妻有不轨之图的郝大炮。后来他又以为是郝大炮来偷袭他的妻子时,真开杀戒,并误以为自己此次真地杀了人,畏罪喝药自杀。不料此次杀死的却是郝大炮的驴。郝大炮与驴就是这样实现着角色互换。另一线索是许警官同时还在处理张寡妇的猪被劁死案。为迫使劁猪匠赔偿张寡妇,许警官特地保存一枚猪卵以证明劁猪匠的过失。结果此卵被猫叼走,许妻龚丽丽 (亦为警员)拼力追猫抢卵,不幸摔倒流产。猪的绝育与人的流产又发生了干系。作品借两个案件相当丰沛地展现了农村的日常生活,官民矛盾由于日常纠葛的烘托更显尖锐,闹剧笔法又引发读者对某些政策的反思。
农民除了受到地头蛇们的种种欺凌迫害外,还每每经受着急于出政绩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形形色色的折腾。
《乡间排球赛》写的是基层干部如何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名声”坑民扰民的故事,亦颇富戏剧性。三道弯乡李乡长听说缸碗沟出了个女排队员徐红丫,所在球队要代表市里参加省运会的比赛,他想借此为三道弯亦即是他自己扬名,于是灵机一动,要在徐红丫的家里搞电视现场直播及庆祝活动。结果徐红丫根本没出场。弄虚作秀,瞎折腾一气,使得徐红丫家里债台高筑。一场庆典,徐红丫家无钱再供她上学,被迫离开体校,退学结婚。徐父也因之疯狂。作品是写乡间的贫困:学校除玻璃球外再无其他任何球类;全村只有村长一家有一台黑白电视,且信号不好如此等等。
李铭的作品的社会批评所向是相当宽广的。有人认为,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大师艾丽斯·门罗的创作是“‘碎片故事’中的大千世界”;笔者以为李铭的短篇小说创作亦可作如是观: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阵痛”。
对下层人们看病难的批评即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看病难甚至成为某些作品故事发生的原点。如《寻母》中刘桂香之所以骗婚,就是因为无钱给父亲看病,“要不是我们家有病人,我能走这步吗?老百姓活着就活着,不想活了就喝点药死了算了,做手术能做得起吗……”在她看来,医院“是最黑暗的地方”。《城市黄昏里的一只候鸟》的二燕子的无爱婚姻的造形,同样是为了给亲人看病。
教育乱象也是李铭指斥的重要内容。《幸福的麦穗》中的曲折故事正是生发于学校的高收费。《幸福的雪花》中一个班级居然有104个孩子,“比工棚还挤”的现象由人物之口进行了批评。《失声》写一对艺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被迫相互背着对方到歌厅讨生活。不料在彼处邂逅相遇,双双“失声”:李宝看见了女友被歌厅老板猥亵,女友看见了李宝看见了自己被猥亵。此处的“失声”乃是一种无言的抗议:主人公如是,作家亦如是。《飞翔的锅炉》写的是家庭内部冲突,却以工厂倒闭、平民取暖困难以及社会的道德堕落为背景,批评了某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扯皮能把你扯休克了”矿难频发,政府隐瞒(《幸福的麦穗》)。矿难还成为“寻母”故事的第二次起点:老满死于矿难,刘桂香不得不携臭妞为其寻母。
文人也在堕落,《文人那点事》可谓一篇文人的百丑图。他们没有崇高理想,亦无社会担当,争名夺利,争风吃醋,比一般百姓表现得还要下作。只有夏小芸尚有少许责任心,但结尾写她与王馆长偷情,又被李局长撞见、冲散后,给王馆长发短信那一桥段,不独损害了人物形象,而且冲淡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尽管增添了喜剧色彩。在《坚硬的水》中,某些作家看到少数民族吃香,就给自己“整个少数民族的名字”。
性解放的泛滥使得人们将男女私情看得随随便便,更给各级官员的性腐败、性欺凌提供了贲张的社会氛围。城乡无不如此,而乡村的基层官员对于普通村民的性欺凌尤烈。在《坚硬的水》等篇中对此都有表现或道及。然而,农民工最基本的心理要求和生理要求却难以得到满足(《春草》),弱势群体的性饥渴与强势群体的性泛滥也已经成为一种反差与对立,尤其是前者的女性成为后者的男性的泄欲工具时,那么此种反差与对立事实上就成为当下社会失去了公平与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家还将自己的笔触上溯至历史生活,但着力批判的却仍是当下。《石匠·铁匠》是典型之作。《石匠》主要写抗战史,对烈士后代与普通百姓都忘记了烈士、忙于发家致富进行了批评。《铁匠》主要写“文革”史,最后却落脚于对领导干部为招商引资而刻意讨好日本人的批判:日本遗孤铁锤不忘中国人的养育之恩,生前决定一切遗产捐给中国,而县长大人却嫌烈士坟前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太扎眼。《父亲的情人》抒写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对早年恋人的怀念,引出了过去年代发生的悲剧。虽说给悲伤制造了喜剧色彩,但仍保有历史纵深感。
《寻母》蕴含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批判内涵:究竟是谁剥夺了女人的母性?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句刘桂香的口头禅,不单带有其精神自慰的质素,更是她观照社会的思维方式。作品在显层上以此表现社会人心毕竟有美好的一面,而这促使事件的良性发展;然而此语也会引起人们的诘问:“人心都是肉长的吗?”倘如此,为何还有偌多不幸?那些隐在后面的不幸的制造者的人心是肉长的吗?当刘桂香得知臭妞由于车祸记忆基本丧失时,“苦笑着说,丧失就丧失了吧,过去那些事情哪有值得孩子记住的。”不值得记忆的不仅有种种不幸,而且有种种不幸后面的种种罪恶。在《寻母》中,拐卖人口、制造矿难的黑恶势力均未现身,如同曹禺《日出》中的金八——那还是有具体所指,而在《寻母》中,则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无主名杀人团。不应忘记:老满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两次婚姻都与人口买卖相关联,都带有买婚性质,而李秀秀本是一个大学生都惨遭买卖,这个社会的黑恶势力岂不是太猖獗了吗!
《风中的驴子》另有一番寓意。在社会剧烈转型期,原有的驴子其实也就是李庆山老汉自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地位,失去了生之权利。他被迫向心爱的驴子举起屠刀,杀掉的也正是他自己。《风中的驴子》正是万千被改革掉了饭碗的底层人们的写照。按照工具理性的思路,人与驴子均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为了利润最大化,是可以被减掉的。千万不要小瞧这篇或许初读时感觉平实之作,其实它是可以作为民族寓言来读的。
当然,李铭也未将社会写得毫无希望,如《娘家侄儿侯赛寅》主人公虽历经种种苦难,由于他的自强不息,终于将女儿培养成高考状元,生活也有了转机。在猛烈地暴露与批判中,又闪现出一缕生之阳光和人间温情。《乡间排球赛》中给徐红丫一家折腾得不轻的李乡长也还葆有少许人性,他为此而受到良心谴责。《血案》结尾处是派出所毕所长背着龚丽丽去医院,许警官则送李德力去医院。上下级之间、警民之间,又有着和谐与温馨:曲终奏雅。这也还是“星星点灯”的希望吧!
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着“仇官”“仇富”心理,这在李铭的作品中都有着不同的反映,而且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的某些作品还比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工的“仇城”心理,《春草》当为最突出者:四奎以专门“日”城里女性作为对欺凌乡村的城市的报复,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日”了一位农村女性,则自责不已。作品对此没有明显的批评意绪。事实上,以四奎的身份能接触到操皮肉生涯的城市女性,以下岗女工居多,她们与四奎一样是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弱者。四奎没有认识到此,但作家对此应当也必须有所超越。
四、刑天舞干戚:杂文体小说
如上所述,李铭对假恶丑的批判十分勇猛,令人想起“舞干戚”的“刑天”。那么什么是他的“干戚”呢?笔者以为是与鲁迅一样的杂文笔法。
鲁迅说过:“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6]。这其实是鲁迅为杂文所规定的基本功能。不知李铭是否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运用鲁迅杂文笔法,但从本人接受的角度来看,至少在客观上他的小说创作在此方面确有与鲁迅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鲁迅有时是将杂文笔法溶进了小说创作中的,如《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社戏》等,都不乏其例。在李铭这里,其杂文笔法主要在于以语言的幽默、锋利,一笔揭穿人间世相本质,时有一剑封喉之感。
《清白》中女主人公在寻找民工时有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哪里有民工出现,哪里就会有市场了,好象这个城市专门为民工服务的。”初看起来,似乎是说民工好找,其实是借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昭示出城乡对立情绪,再深层剔挖,则是对于城市排斥农民工的反讽。这正是杂文笔法。
《血案》是写村官诬告村民的故事。长期欺凌普通村民的村官郝大炮在向民警陈述案情时,语曰:“我死了倒不要紧,那村里的大事小事可咋整啊。”“‘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7]此例正是如此。此处虽说是以一个小小的村官之口,道出其自以为是救世主的心态,其实正所谓“别拿村官不当干部”,其权力大着哪!这也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公仆们都有的心声①笔者20世纪80年代曾亲耳聆听某大学党委副书记讲过:“我们不是学校的罪人,我们是救星!”我当时的感触即是“一星陨落,众星升空。”后来也知晓某位学者称颂自己单位的所有领导都是救星。呜呼!无法可想。。所以,这句再“朴实”不过的话语却真实地道出了许多官员的共有心态。不着一贬词,而其性伪行丑毕现。可谓不见血的匕首。
有时李铭的讽刺也未免直接甚至颇有点刺刀见红的意味,如《寻找马东山》中牛老倔看到了基层公仆们在他们经常光顾的饭店的房后墙上撒尿,而那墙上又有几块黑色的蘑菇,便大声喊道:“这都长狗尿苔了!”此处委实不够含蓄,但牛老倔对于这些所谓“公仆”确实已经表现出愤怒了,他如是为之,倒也符合其性格真实。若是说此处略微还是拐了一点小弯,那么《情愫三咂》中对官场中汇报材料特点的概括——“就是不说人话”——可谓直刺要害、一剑封喉了。
李铭善于用夸张的手法放大恶相,使其本质得到更为清晰的昭示。在《寻找马东山》中有这样的小桥段:牛老倔问二蛋为何不找老板要工资,二蛋回曰:“没用。啥办法都想过。有一回俺去爬塔吊,爬半路发现上面蹲着一个人。跟俺说,兄弟,你还有个先来后到吗?等俺爬完了,你再来吧。”虽说此处未免有点夸大,但却写出了农民工遭遇欠薪和艰难索薪的普遍性,从而对此种历久而弥坚的社会不良现象给予了冷嘲。
有时则描述和叙写现实生活中的荒诞与悖论,让事物或物事的实有样态与应有样态发生强烈的碰撞,而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乃至闪电,使得假恶丑无所逃遁,读者也会于笑声中获得了向其复仇的快意。这样的例子在《幸福的麦穗》中俯拾即是,如:“……乡政府,倒是跟庙宇建筑有些相似了。”鲁迅讽刺过“洋服青年拜佛”,而今作为无神论奉行者的共产党基层政权的衙门宛若庙宇,就深刻地揭示了其“假”,其“丑”,姑且不说其“恶”吧。“麦穗的胸部刺激了他们[按:公仆、老板们]的食欲。”在这些社会达人那里,原来性欲与食欲是相通的,这也许是“通感”的作用?饮马池乡的文化站站长大奎其言谈举止无不像个涉黑人物,他对自己工作内容的介绍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谁家老娘们不结扎,我带人喊话,不投降就抓;还有,提留款啥的有不交的,我带人抄家。在我们饮马池,文化站干的是派出所的活,职能大了。” “文化”与“武化”发生了名实颠倒。这是十足的“恶”了。在饮马池,政府建筑 (所谓硬件)与政府官员 (所谓软实力)等都发生了情状与情态的异样,荒唐到使得人们不能不发生种种质疑和慨叹!
《愤怒的鸭子》则全篇都是讽刺,不独表现为语言,整个故事架构都是讽刺了,完全可以作为杂文来读了。作品写三道弯乡历任的赵、钱、孙、李、周、吴六位乡长都想整出点“动静”(政绩工程),这“对以后的仕途发展是有好处的。”赵乡长在曾有孩子被大水冲走的缸碗沟修了一座“连心桥”,“动静”很大,“惊动了市里和省里的注意”,赵乡长因之得到升迁。但河的上游发现了铁矿,放炮平山,河水改道,不再流经缸碗沟,“连心桥”遂成为村民晒牛粪的地儿。钱乡长则另辟蹊径,他是“懂艺术的人,早些年靠写诗出道”。任三道弯乡长后,“雷厉风行地建设各村的文化站。”家家都得装大喇叭,“强制性地安排,每个喇叭四十块钱”,要求大家及时收听国内国际大事,他通过大喇叭传达精神,“顺便播送他写的古体诗什么的”。还在集市上塑了一个“女神”像。钱乡长又写了一本关于三道弯的民间故事集,自费出版,销量很好,再版三次。当然,旧书摊上此书也很畅销:各摊主都是在顾客买一本别的书时,免费搭上一本民间故事集子。钱乡长却因之成为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而女神塑像则“大大方便了很多上厕所的赶集乡亲。都到塑像后面拉屎撒尿,天暖的时候臭气骚气熏人,冬天后面摞起了冰山,金黄的屎橛子立在冰山顶上,老远看好像冰雕一样。”孙乡长“干实的”,组建养殖基地,“集团式地稿大‘动静’”,要养羊致富。可是由于脱离实际,猫腻甚多,再加上包活的孙乡长的小舅子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结果弄得半途而废。遭罪的“最主要的是那群羊,哪里是种羊啊,一个个面黄肌瘦,像难民似的。自己活命还困难,更别说给你生儿育女发展地方经济了。”作者简直以羊的口吻进行抗议了。李乡长为了出名则搞了一场乡村排球赛的闹剧。周乡长制造了一个“辣椒节”,搞了三件“动静”,一台演出,一次辣椒厨艺大赛,一部三十八集电视剧。周乡长亲自为其命名:《三道湾的娘们》。吴乡长则搞养鸭致富,下边为了加大鸭子的数量,竟然从别处租鸭子。真可谓六仙过海,各显其能,然而给百姓带来的却是灾难。阅读此篇,让人忍俊不禁,读者在获得了愉悦和休息的同时,抒发了愤懑,引起了对此种现象和如何改变此种现象的深沉思索。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用《愤怒的鸭子》,因其实为李铭的鲁迅风代表作,可谓批判力度最大的一篇,有如鲁迅那样对恶浊喷吐着愤火与毒焰。就此篇结构而言,有点与鲁迅的《社戏》相似:《社戏》开篇是现在时,是对当时戏院等的批判,后来才是对童年时所看的社戏的怀旧,前面不要,后面也完全可以独立成篇;《愤怒的鸭子》前面是对赵钱孙李周诸位乡长政绩的介评,后面才是故事中心——吴乡长与“愤怒的鸭子”之缘,前面亦可不要,完全不影响后面故事的完整性。两者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在鲁迅那里前后比例大体为一比八,而李铭这里则为约一比三而已。两作的前面均系杂文笔法,均是社会批评。作家之所以如是为之,甚至不惜破坏小说的连贯性、整体性,就是为了凸显所写的主要故事的意义,在鲁迅那里,是一种对比,而在李铭这里,是一种铺排;前者是为了抒写已逝韶光的美好与不再,后者是为了书写现实生活的荒诞与绵长。杂文笔法或曰杂文部分 (两者的前半其实也可作为独立的杂文篇章来读)与故事主体的焊接,确实在有限的篇幅中扩大了作品的社会容量,加强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另外,《愤怒的鸭子》的赵钱孙李周吴六位乡长的姓氏安排,亦有点与《阿Q正传》中赵钱二位太爷的姓氏安排类似。选择百家姓的头几个紧密挨着的姓氏作为作品中人物姓氏,自然绝非随机为之,而是要向读者暗示此类人物的普遍性与绵密性。这一点,在李铭这里更为突出。诚然,李铭的讽刺有时也是针对弱势者本身的缺失的,如《我和岳母大人的内部战争》中对岳母的某些行为举止的讽刺,但此种讽刺是微温的,是满含善意的,与对假恶丑的讽刺全然不同。
写至此,又想起了陶潜的《读山海经》之十: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李铭对腐恶的批判精神真有点“猛志固常在”的意味呢!“良辰讵可待”,他期待着终有一天,良辰美景到来,然而什么时候到来,亦难以判定。希望高远而微茫,亦正如“星星点灯”。所以,李铭的“刑天舞干戚”仍是与“星星点灯”这一意象相纠结的。

泥模艺术——打花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