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地走在进步的道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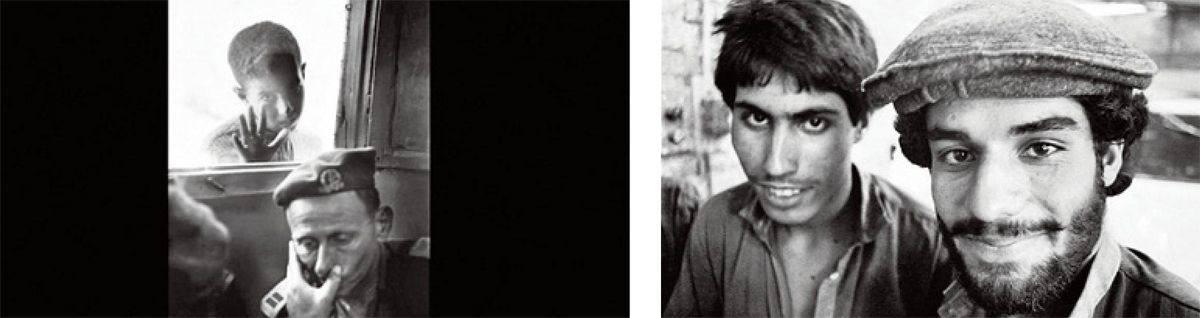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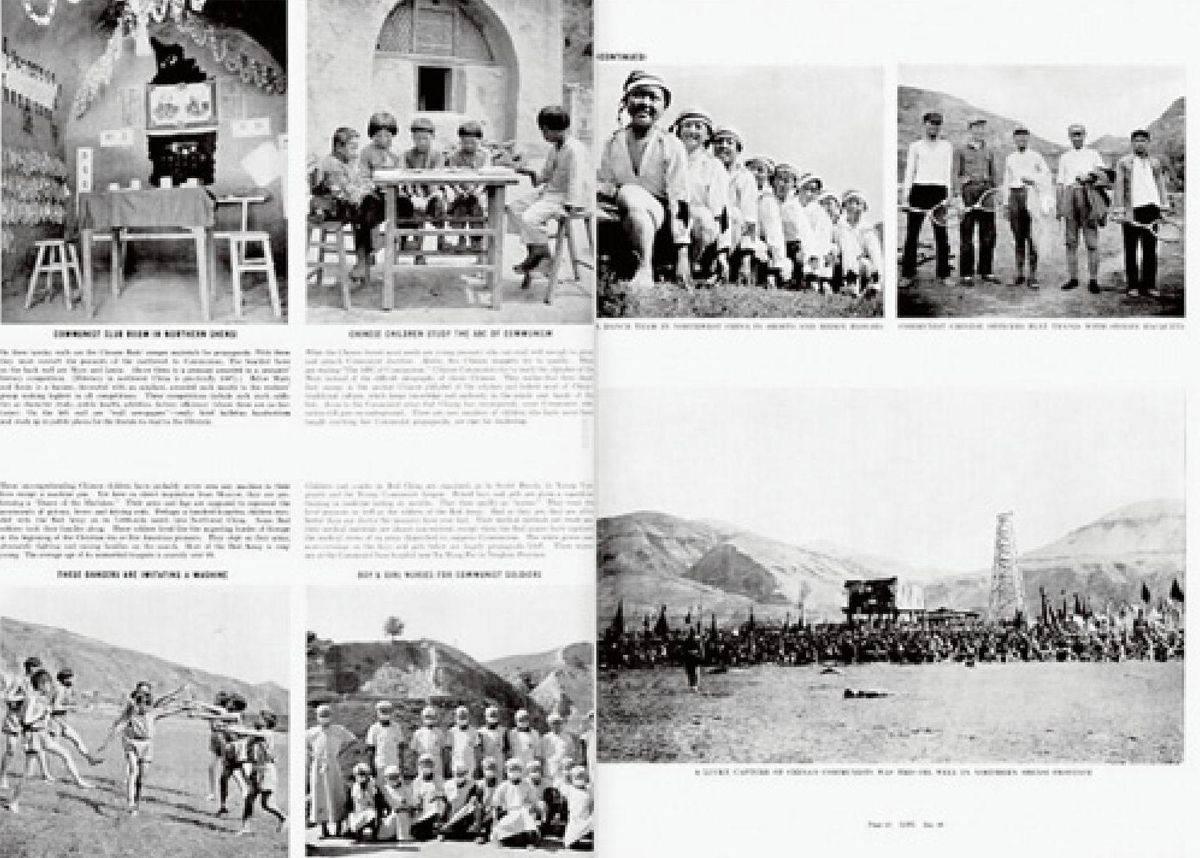
1980年代初期,我在美国初次读到约翰·伯杰1的Ways of Seeing(中译本名为《观看之道》,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受启发。这本激进地改变了几代学生对艺术观看方式的书,其文字之简炼、观点之犀利,让我敬佩不已。1995年秋天我在英国,刚好碰上当时已年近七旬的伯杰,于伦敦的ICA(当代艺术中心)出席他新出版小说To the Wedding的发表会。那次我心理上完全像个朝圣的粉丝,听完他的讲话后,买了一本书,兴奋地排队等着请他签名。
记得他在书上签名题字后,我告诉他,Ways of Seeing在华文出版界已经有三种不同的译本。2他亲切地微笑着,很有力地握着我的手。那双大而粗砺厚实的手,像是移居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农村20多年、跟农人们一起下田的结果。但伯杰努力不坠的,主要是笔耕。
2005年春天,伦敦“南岸”(South Bank)的国家电影院,为伯杰在电影、电视、小说、剧本、散文、评论等丰沛之创作成就,举办了长达一月的盛大回顾活动。英国《观察家报》的肖恩·欧海根(Sean OHagan)在一篇访谈长文《激进的返乡》(A Radical Return)里,描述伯杰具高度感染力的充沛能量与具创造性的强烈好奇心,使他拥有从不疲惫的理想主义昂扬情操,与浇不熄的乐观主义精神。
受《另一种影像叙事》译者张世伦与《诚品好读》之托,我有幸与这位英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左翼作家与艺术批评家,进行了80分钟的电话访谈。伯杰在接受访谈时,已迈入八旬高龄,而话筒彼端传来的,是一位言词清晰、语气诚挚、思考问题专注、批判立场坚定的声音。那种诚挚与坚定是熟悉的,一如1995年在伦敦ICA他那只厚实的大手,传递给我的讯息与温度。
郭力昕(下面简称“郭”):在《另一种影像叙事》中《照片的暧昧含混》这篇文字里,以及在更早的《影像的阅读》3一书的《摄影术的使用》、《痛苦的照片》等文章里,您都提到关于摄影里的“时间断裂所造成的惊吓感”(shock of discontinuity)4,认为照片里那些瞬间的、断裂的信息或事实,无法构成意义,也无法产生有意义的政治行动,例如您描述的麦库林的战地照片。然而,在2001年BBC的电视节目《希望的幽灵》(The Spectre of Hope)5里,您与萨尔加多对谈他的全球移民摄影作品时,似乎非常肯定他的写实主义摄影,对全球化产生的恶果有着批判性的意义。请容我引述苏珊 · 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里对萨尔加多的批评意见。她说,萨氏的移民群像,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原因与类型不同的流离现象,笼统地归纳在一个“人性”的标题与“全球化”的概念下;并且,在这种呈现下,观者可能感到人间的苦难过于巨大而无法逆转,而任何地区性的政治行动亦因此无济于事。虽然桑塔格在此书最后,似乎又自我矛盾地认为视觉效果耸动的战争摄影,仍有激发人们认识问题与产生行动的可能,并从而相当地否定了她早年在《论摄影》里的批判观点。您如何响应这些问题?
约翰·伯杰(John Berger,下称“伯杰”):首先我想表示,对于桑塔格最后这些年里,针对几个重要国际政治事件所发表的意见,或自我修正、转向的看法,我是非常尊敬的。像她或我这样的评论写作者,有时会在书写当时的特定氛围与热度上,为凸显某个重点而损失了客观的话语,但回头检视时的自我修正是可能发生的。
然后,关于照片意义的问题。总的说来,摄影不像绘画,它没有自主性的陈述形式。哥雅(Francisco Goya)版画里的意义,很难被读者误解成别的意思;但摄影的第二层语境(second context),则可以因为不同的使用方式或情境,而削减或扭曲了照片的意义。照片的意义与阅读效果,取决于它们如何被使用、在哪里发表/出版、伴随的图说与文章,等等,这些都不是摄影者可以控制的。问题在于摄影这个媒介本身。我对麦库林的照片,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来谈论的;对麦库林的作品与他本人,我有着很大的敬意。
最后,关于萨尔加多的作品。单张战争摄影里的战地现场,确实无法呈现关于战争的完整历史叙事;但萨尔加多的作品不太一样,不能从任何他的单张作品来比较或评断。他的照片是以系列的方式呈现,因此作品里有着比单幅照片更多的叙事功能。我知道有一些批评者认为,萨氏的作品有美感化其拍摄题材的问题,但我不这么看。问题不在于他想要把照片拍得太美,而是他试图透过这些视觉上强烈的影像,将那些在艰苦中之幸存者的尊严与神圣性呈现出来。
郭:我同意照片本身是否很美并不是问题,但我仍比较认同一种批评萨氏的意见,就是让那些劳工或流离者陷入如此困境的结构性因素,并不在他的作品里;因此作品剩下的,是否就只能是美丽的构图与摄影感了?
伯杰:因此我与萨尔加多在《希望的幽灵》节目里,并不特别着墨在他的摄影本身,而是希望观众能思考这些影像所带出的一些更复杂的问题,让萨氏的摄影,可以开始提供一些关于政治、经济等结构性的问题意识。这也是为何在此节目里,有许多静默无语的时刻。
郭:但我实在觉得,不从美感经验阅读萨氏作品、而会从其中暗含的对全球化之批判讯息来阅读其作品意义,会不会只是您的主观意愿?因为这可能来自您本人对移民与流离问题的长期关切。萨尔加多在此节目中,呼应着您对全球化议题的批评意见;他在拍摄劳工与移民的两部摄影作品书里,也确实提供了大量的图说与数据。请原谅我的多疑,但我实在看不出,传递如此之政治批判讯息的摄影书,为何需要如此精美厚重如古典画册的巨大制作成本、和一般人难以付得起的书价?
伯杰:我个人同意你的看法。我与尚·摩尔(Jean Mohr)在制作《第七人》(A Seventh Man)时,即主张此书的印制成本一定要愈低愈好,使那些我希望阅读到此书的普罗读者能买得起,即使必须牺牲一些照片的质量也当如此。不过,我也不想说萨尔加多的坏话,摄影集印成那样是他的事情/生意(his business),我无可置喙。
郭:或许从前面的讨论继续请教您,写实主义摄影究竟如何可以传递政治讯息。霍尔(Stuart Hall)在1983年的一篇访谈里,曾批评左派摄影创作者缺乏有力的摄影语言,仍旧以实证主义式的纪实影像作为言说方式。他鼓吹例如摄影蒙太奇(photomontage)作为更有政治话语能力的影像语言。您的看法呢?
伯杰:我对摄影蒙太奇或拼贴合成等的图像处理方式,都持开放的态度。但如我前面所说,摄影并非一个有着自主话语意义的媒介,它必须要与其他媒介合作,来传递政治讯息,例如文字与图片说明的书写。摄影者与文字作者应该一起工作,使得两者能够充分互补、彼此强化,而非重复同样讯息。
郭:从《观看之道》到The Shape of a Pocket(《另类的出口》)6,从您对资本体制下广告影像的剖析与批判,到全球化经济“新秩序”里的野蛮主义,与它创造的全球劳动力的强迫性移动与买卖,您批判资本主义之“极权主义”逻辑的政治立场,从未改变过。您在许多作品中,长期书写发生在欧洲地区的移民问题;华文作家或视觉艺术家,可以如何响应目前台海两岸的这个现象?
伯杰:我也许不合适给华文创作者特定的指导性意见,不过我可以谈谈自己看待写作的一点通则。我认为一个写作的人,应该勤于见证身边正在发生的重要事情;即使书写所立即产生的力量,可能看似微不足道,或一时被人忽略,但不要顾虑这些,还是要写。“书写”有着一种非常潜沉的生命(a subterranean life),它蓄积着能量,在某个时刻,会对读者产生一些微小或不小的改变。我引用刚过世不久的一位重要的波兰记者瑞扎尔·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的话,他谈到记者这个角色时说,“一个记者必须要知道,对于他有机会看到的事情,他也只能看那么一次。”我觉得这句话重要极了,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写作者必须发言的迫切义务。
郭:您出生、成长于伦敦,但在1970年代起就移居法国南部山区的农村至今。您曾于其他访谈里说过,这个移居是您的主动决定,而非被迫流离或放逐。我好奇这个定居农村的主动选择,是否或如何有助于您抗拒伦敦主流文化圈的氛围,并保持一种批判的距离?
伯杰:其实,我不是为了要保持对伦敦文化的批判距离而住到法国山村,也不是一种从都会/中心的退隐;我住到农乡里,是为了要向农人们学习,而我也学到了很多。7 至今世界上多数人仍是农民,其中大部分人仍一无所有、或者只拥有很少的物资。在中国,这就是十分真确的事。对于我们的现代世界,农民的存在,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与议题。这才是我要离开都市、跑到农村居住的原因。至于要有效抗拒都会主流文化的影响或诱惑,可以用阅读的方式。我经常读诗,全世界各地的诗,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很难在晚上的电视或隔天的报纸上看得到。
郭:高夫·戴尔(Geoff Dyer)在《讲述之道》(Ways of Telling8)一书里,推崇您是一位能够拒绝被体制化与被分类的“异类”作家。《旧金山纪事报》的艺评人肯尼斯·贝克(Kenneth Baker),描述您从不靠近有政治权力的人。另一位作者苏德福·珊度(Sukhdev Sandhu),称您延续了从劳伦斯(D. H. Lawrence)到肯?洛区(Ken Loach)的英国异议传统。
伯杰:我对肯?洛区十分尊敬,劳伦斯则是我在十四、五岁学习写作时,唯一认同的英国作家。这个异议传统,也许还可以追溯到布雷克(William Blake)。而我不与政治当权者靠近的原因,其相当简单:我发现他们实在太无趣了!(大笑)他们在许多地方都极其无趣:说话内容太可预期、或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的话、或总是说一半真话—但那比谎言还糟。相反地,在没有那些权力的人们身上,则常充满了谦虚,与令人启发的神采。
郭:您在《卫报》网站上,有个人的博客。您对博客做为激进政治行动的空间,有何看法?
伯杰:那是《卫报》帮我架设的,我忙于新书的写作,实在没有时间去管理它。但我是支持博客的,它是另一种横跨全球之“潜沉话语”的方式。当然也许它已经被某种程度的滥用,但是无所谓,无所谓的。因为,论坛(forum)功能的出现,是极为重要的。另类论坛在此时肯定规模不大,但重要的是彼此的连结,以形成一个交换想法的网络。在全球资本垮台的时候,这个网络应该有道德与行动上的准备,而我毫不怀疑资本主义终将垮台—不必然是由什么巨大的外在运动,而是源于它内在的矛盾和愚昧。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领袖,能像今日世界的统治者们这么愚昧无知。
郭:您80岁了,目前还骑摩托车吗?在1994年BBC关于您的纪录片里9,您骑在那辆本田摩托上穿梭于农村巷道的样子,简直像个青少年……
伯杰:还骑呢。我的体质不错,不是我的功劳,只是运气好。不过,也许有个听起来意思矛盾的生活态度,多少让我保持了精神:打从我从十五、六岁起,我就经常以一种“这将是我生命最后一刻”的概念,活在当下。矛盾的是,也许这个态度,反而激发了生命力。
(本文选自郭力昕的新作《再写摄影》, 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