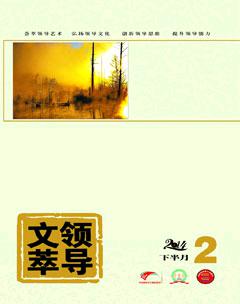父子无情亦有情
唐宝林
1921年、1922年,陈独秀两次被捕,此事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需要加强保密和保卫工作。于是,党的工作机构进一步隐蔽化,特别是对陈独秀,决定让他单独隐蔽起来,其住址不告诉任何人,包括党中央和其家里人。平时陈独秀自己到党中央机关来办公,阅看和签发文件,他走后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这样,他就与高君曼和两个孩子——陈鹤年、陈子美隔离分居了。
当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冒天下之大不韪,姐夫与小姨子结合,曾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二人真心相爱,又一直生活在远离家乡的环境中,而且终日忙于救国救民的大业,因此二人的爱情生活曾相当甜蜜。在高君曼方面,过去不知道她的感受,现在也有人从一份稀有刊物上发现了高君曼约在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前写的两首组诗,其对陈独秀的感情,也是感人肺腑的。
由于史料湮没,关于高君曼的为人,鲜为人知,甚至至今没有找到一张她遗留下来的照片。只知道她的儿子陈鹤年在香港观看《日出东方》电影后,对女儿陈祯祥说:“你奶奶长得比电影中的‘高君曼还要漂亮。”这应该是可信的。而且高也是一位贤妻良母,1920年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移居上海后,君曼为了让独秀全力从事党的工作,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劳作,还在陈的帮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
但是,真如世界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一样,世界上也少有恒久的爱情。二人的裂痕最早缘于对子女的教育。
1913年反袁革命失败时,陈独秀被通缉,逃亡上海。接着,因抄家,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也千辛万苦逃到上海,投奔父亲。这两兄弟之间的情谊与陈独秀少年时与其兄的情况相似。延年个子高高,浓眉大眼,皮肤较黑,平时沉默不爱说话,一天到晚看书,无书不看,一目十行,记忆力很好,尤其古文写得好。安庆老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后说:“可惜现在科举废了,要不然延年是翰林之才。”参加革命后,特别在大革命中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期间,忙于紧张的革命工作,无暇写文章了。但由于他的博学深思与聪慧,演讲和口述整理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他从广州到上海向总书记陈独秀汇报工作,一时没见着,就由他讲,郑超麟记录整理下来后,十分感叹地钦佩他的这种才华。陈延年受母亲影响,对父亲的薄情颇有怨气。弟弟乔年则相反,个子比延年稍低,但长得清秀。他“长大后讨论问题时,则一本正经,毫不放松,辩论批评,绝不马虎,是则是,非则非,正义凛然也”。
陈独秀与高君曼在对待子女的教育观上,发生尖锐分歧。陈独秀见两个儿子是可造之材,从孩子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对延年和乔年实行所谓“兽性”教育,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就是要把他们造就成他心目中的“新青年”,而不是旧教育制度培养的纤弱无用之人。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复批判旧教育制度戕害青年的罪恶,指出:对比西方强国,我国青年“甚者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凤毛麟角”。陈独秀认为这样的青年将来不能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成为优秀的政治家、军人、实业家等。
陈独秀决心按这样的思想来塑造自己的两个儿子,以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只给他们很少的生活费,让他们勤工俭学,并且不让他们俩在家里住。学业上则出于他对法兰西文明的偏爱,安排他俩与当时同陈独秀关系密切的辛亥革命志士潘赞化同在法租界学法文。延年兄弟俩“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要外出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
君曼更是竭力反对这样做。她本有母性之爱,善良之心。见此情景,实在不忍。她本来就自觉对不起姐姐,再这样对待姐姐的两个儿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两个孩子这般受苦,她与独秀多次争吵,说不拢,就“流涕不已”乞求潘赞化:“姐姐不在,小子无辜,我是姨妈,又是继母,他们也很训实。我以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于我所生。他兄弟失母无依,视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不知者谁能谅我?”希望至少让他们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独秀如此严格要求儿子,看似“父子情薄”,实则望子成龙。尽管如此,君曼对独秀和延年、乔年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尽量缓和父子的紧张关系。
不久,延年、乔年勤工俭学进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读书。接着,陈独秀北上,出任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后,君曼也携鹤年、子美来到京城,过起相当优裕的生活。陈的月工资是300元,但是,对上海的两个儿子还是那样“刻薄”,只让亚东图书馆老板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两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费。
两兄弟从小见父亲不顾家庭,对于妻子即他们的生母如此薄情寡义,现在又如此严酷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自然不能理解和接受父亲的良苦用心。因此,二人在参加共产党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以后,父子同在共产党内,他们也一直直呼其“独秀同志”,毫无亲情可言。
然而,兄弟俩毕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都成了中共优秀党员和杰出的革命领导人,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人在1927年、1928年先后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杀害时,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愧为将门虎子。
1936年,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时,“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当时在场的濮清泉回忆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点菜……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了!把酒洒在地上。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流泪。”这时,他藏在心底的对儿子的深情才像洪水一样倾泻出来。
(摘自《陈独秀全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