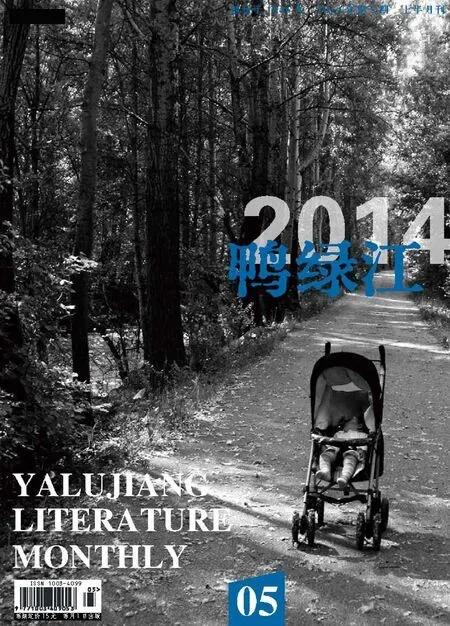幸福在招手
舒 袖
幸福在招手
XING FU ZAI ZHAO SHOU
舒 袖
一棒子的小儿子景德水抢劫被抓了,这消息一清早就在幸福小区传开了。
啧啧,没想到,他老实巴交的,怎么去抢劫了呢?
嗨,人啊,看皮看不到瓤。
哼!随根儿,心黑着呢。
一棒子蔫蔫地呆若木鸡般耷拉着脑袋倚在床上,老伴儿张小人抹一把眼泪,老头子呀,你别难过了,小二走到这一步啊,也是命中该着啊,报应啊。当初动迁时,我就说别把钱分给他们那么多,咱俩多留点养老的,你不听啊,你说得让孩子们投资干点啥,自个当老板,比给别人打工体面,赚钱。可到了啊,坑了他们了。
一棒子有气无力的,目光却透着恶狠。我养俩儿子,就他妈是养俩冤家!
张小人听罢,手捂脸大哭,这可怎么办啊,我的天啊!啊啊,老大德鱼腿残了,俩崽儿啊,念书成家的怎么办啊,老二又这样,呜,呜,呜呜……
德水媳妇赵香菊已经没有眼泪了,搬到幸福小区这几年,她几乎天天流泪,丈夫景德水不哼不哈的闷有主意,动迁时分得的50万元,让德水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几年他把香菊折腾得死的心都有,德水被抓了,她心里反倒有些轻松,是疖子早晚得流脓,出了头或许就有好转了。香菊做了早饭,催儿子快吃,吃完上学去,别想你爸的事,把你的书读好,就要中考了,考上重点班是真格的,将来长出息远走高飞,让妈妈借你光在人面前抬起头。儿子一声不吭吃了饭背上书包走了。香菊开始收拾屋子,嘴里嘟囔,这孩子跟他爸一个脾气,不哼不哈的,闷有主意。抹布抹到柜子上的相框,她看着德水那张文雅淡笑的脸,往事一桩桩浮上心头。
德水搂着小菊亲嘴,嗯——哪,媳妇,咱也买车,还要比别人的好,他们买十万元以内的,咱买十八万的,明儿个我带你去沈阳4S店看看,那儿的车款比辽阳的多,一样的车,提车还便宜五千元,咱开车回娘家,小菊你多有面子啊。开车送孩子上学,孩子多有面儿啊,老师也得高看咱儿子一眼不是。咱在市府广场,闲遛时,你不也看到了吗,那市政府工作的一些人美其名曰说步行上班绿色出行,其实就是养不起车嘛,咱啊,命好,还是咱爸说得对,“这党啊,就是对咱贫农好!”香菊撇撇嘴,你爸这话是传辈了,什么年头了,还贫农贫农的,咱娘家是富农,那现在还有谁敢斗咱家啊,都是村民,平等待遇。德水说那倒是,要不平等,我们家还能要你呀,等着跟你家受连累一起挨斗啊,咱爸头一个反对。香菊嘿嘿地笑,难不成你爸上咱家抡一大棒子呀!
香菊这句话捅到了德水的痛处,他的脸一下子就撂了下来,从阳光灿烂转到乌云密布。从小他就知道村里人都喊他爸“一棒子”,这外号在阶级斗争那年代,虽然不乏嘲讽却似乎有点荣耀,后来改革开放了,“一棒子”几乎就是凶狠残暴的代名词,一听到有人喊“一棒子”,德水的心里就像油煎一样不得劲。

舒 袖,原名王秀英。辽宁省灯塔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省作家协会会员,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情非得已》、 中短篇小说集《风淳巷口》、网络长篇小说《一路风尘》等六部。在《中国文化报》《时代文学》《北方文学》等多家报刊发表作品约百万字。有散文、小说数篇分别获《散文选刊》杂志社、《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宣部、文化部等多部门联合举办的征文奖项。多篇作品被收入年度文学集。
话说土改斗地主的时候,德水爷爷是贫农代表,带领一伙穷棒子队在斗地主现场,那是首当其冲,带头喊口号,在那群情振奋有些混乱的场面,有人开始往地主身上扔东西,结果,一石头砸在了德水爷爷的头上,德水爸那时才十多岁,他见父亲满头是血,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眼睛都红了,拾起混乱中别人丢在地上的棒子冲进人群,高声喊,叫你欺压人,还指使人打俺爸,俺打死你,狗地主!照着浑身筛糠哆哆嗦嗦低头耷肩的地主头上就是一棒子,地主应声倒下,死了。德水爸的外号“一棒子”从此诞生了。
德水爷爷之后便成了贫农代表,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村小学的专职农代表,经常给学生做忆苦思甜报告,在村里很有名气。直至一年春天,生产队牲口不够用,大伙儿拉纤往地里送粪时,他被绊倒了,被绳子裹住,压在了大马车的胶皮轮下,成了烈士。
德水爸爸顶着父亲的荣誉,也红得发紫,读书时,学校大会小会台上发言,被各种形式的活动推在前边,后来到生产队又当小队长,能说能干,敢打敢骂,是村民眼中的硬人红人。 改革开放后,承包了三十亩稻田地,在村里依然是好使的人。他从心里感谢党,他说他家是党养活的,要不然还是穷棒子。村里动迁,一棒子分得了三处七十多平方米的楼房,外加百余万浮钱,他跟俩儿子三三开。他对俩儿子说,钱给你们了,你们要用好,记住别让人家眼了,人活一张脸啊,别人有的俺也置上,让孩子老婆抬头做人。
大儿子德鱼买个车办了出租手续,骂骂咧咧地对父亲说,这办手续的钱是车的两倍,还得挂靠出租公司,妈的,这点浮钱没剩什么了,以后啊,就得天天奔命了,车轮子一停,就没进项了。唉,这城里的生活啊,逼得人心惶惶的,没底。真不如在农村时踏实。
一棒子“啪”一合掌,不如让你弟入一股,你俩黑白班倒着开,车轮不停,成本就减少了呀。要不你弟还能做啥嘛。
德鱼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我宁可雇个夜班工,也不能跟他合着干。兄弟间别再闹出口角反而不美了。
一棒子把德水叫过来,德水啊,你哥干出租了,你打算干啥呢?
德水低头摆弄手机,再说吧,我也想买车,但我不出租,我想买好点的,跟婚庆公司挂挂钩,赚点油钱,自己用着方便。
一棒子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盯着小儿子的脸。那你靠什么养活老婆孩儿?
德水继续在手机上玩游戏,找份工打呗,干点什么还挣不出个工资钱啊。
张小人洗了几个苹果端到茶几上,德水啊,别一门玩手机了,那眼睛不要了啊,吃个苹果吧。老头子,你不用跟德水操心,德水从小到大没让你操过心,他还不知道挣钱养家糊口啊,倒是老大德鱼,你得跟他多嘱咐,以前在堡子里他跟谁都说上句,这脾气啊得改改了,开出租啊,什么人都能碰上,别气儿粗,和气生财。
嗯,是得说说他了,到哪儿随哪儿,进城了,得看看人家城里人都怎么处事的,要不吃亏的是个人。
一棒子对小儿子买车的事没有表态,他心想,村里不少人家都拿动迁款买了不错的车,用上方便,也体面,咱这一大家子有辆好车也成。
德水领着香菊从沈阳提回了丰田车,送儿子上学心情特爽。他是不想干脏累的活了,琢磨着找个体面的工作。他去网吧玩游戏玩上了瘾,日子久了就跟网吧老板混熟了,网管不在时,他也帮着解决小问题。一个网管小伙儿回老家结婚不回来了,德水就接了网管的差,月薪2000元,他觉得可以,另外加上每月十来次的婚庆出车,比得上机关干部的月收入了。香菊去饭店打工了,每月也挣一千多元呢,这样的日子紧着过,略有节余,可以了哈。
德水觉得生活真美好,如今咱农民也过上了市里人的生活。渐渐地,他本就文雅的气质更加突显,脸皮越发白皙细腻,网吧里的大事小事他都处理得当,小女生以为景哥哥是大学毕业呢,好仰慕他哦。一日他在后面休息室休息,年龄不过二十的小姑娘白玲也进来了,一进门就躺到沙发上。白花花的大腿和小腰都裸给了景德水。德水体内有股冲动,他眯缝着眼睛瞧一会儿,再也坐不住了,起身想出去,却见白玲捂着肚子呻吟起来。他哈腰看着白玲的脸,怎么了,不舒服吗?不行就去医院吧。
白玲佝偻一下腰,使劲捂着肚子,嘴唇发白,却在摇头。她说能挺住,一会儿就没事了。
德水却发现白玲的短裤下边汪了一摊血,他掏出手机打了120急救,急忙回吧厅,谁和白玲是朋友?有没有啊?上网的人有的摘下耳机,有的抬头看看德水,副副茫然相,无人接应。吧台的登记管理员锁好抽屉,跟德水到休息室看白玲,妈呀,大出血呀。120急救车几分钟就到了,德水只好跟着白玲到医院。
白玲被护士从手术室推出来,躺在病床上不说话。德水帮忙交了住院费后,手里只剩几十元零钱。白玲死活不说家人的电话,德水只能替代家属陪护。
德水帮白玲在医院食堂订了一碗热汤面,白玲只吃几口就放下了。德水给媳妇香菊打电话,香菊啊,你在你们饭店弄点鸡汤,送医院住院处来,再带点钱。
德水打电话时,饭店正好是午饭高潮刚过,香菊得以腾出空,她急三火四地跑到医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唉呀,这可大意不得,这种事可容易落下病根了。这么的吧,德水你回去上班吧,我在这儿陪她一会儿,等到饭点了我再回饭店。
香菊说傻孩子,谁碰你了,你得找他负责啊,不能白便宜他了。这事你一小丫头怕是弄不明白,还得让你家大人出面。
白玲抽泣,我奶奶岁数大了,怕她上火,不敢跟她说。我爹妈在我读小学时离婚了,都有自己的家,又都去外地做生意了,他们只给我点生活费,不管我别的。
那你出这么大事,你得告诉他们,他们肯定能管你的。你看我们都是外人,也没能力帮你什么。
白玲呜呜地哭,不用,谁也不用,我的事只能靠自己。姨,我没事,您忙您的吧,不用管我,等明天我能下地了,就把钱还你们。
香菊和德水照顾白玲两天后,白玲就出院了。几天后,白玲到网吧,还了德水的钱,说要离开这里到外地打工。德水可怜这孩子,她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几岁。劝她没有可靠的人不如在家这边打工,咱这超市、饭店、工厂总招人的,有奶奶照应也能安稳点。白玲低头说不爱在这儿待了,太没意思了,他走了,我其实要去找他。
德水明白白玲说的这个他是谁了,便关切地问她,能告诉我他是什么人吗?找到他会是什么结果?我还是很担心你。白玲咬咬嘴唇,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在歌厅认识的,那时我在那儿当服务生,他跟一伙人去唱歌,我陪他唱过几回歌,我们就好了,他比我大一轮,有媳妇。
德水说他做什么生意?白玲说不清楚,反正他跟矿山老板挺好,经常往外地跑,看样子能赚点钱。
那你能找到他吗?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帮你打听打听。
他叫计铁,大伙都叫他老铁。我昨天跟他通了电话,他说在山西呢。
你打算跟他混?
要不我还能怎么的,去看看再说吧。
嗨,你一个小丫头,挺让人担心的,别再让人给你卖了。德水流露出怜惜之情。
嗨,除了我奶奶,只有你这样担心我了。德水叔,我会一辈子记住您的好,比我爸对我都好。
那你有什么事可得联系我,不行就赶快回来,别让奶奶担心。
德水叔,别拦我了,只能这样,老铁答应我了,他说在那儿待不服再回来。
半年后,白玲回来了,老铁出资开了一个酒吧,白玲当了老板娘。这是县里第一个专业酒吧,生意逐渐兴隆后,白玲找德水来帮忙,工资比在网吧多一千。白玲信任德水跟信任自己一样,逐渐地越发依赖德水。
德水在酒吧工作不免沾染上了酒,有时也滑下舞池发泄一通。老铁信任德水,也醋德水,白玲总是口不离德水,老铁哪能甘心让德水抢了白玲的心呢!可是酒吧还真离不开他。于是,老铁动了歪心眼儿。
一天,老铁在酒吧为朋友庆生,特意把德水喊过来。德水啊,跟我的朋友认识一下吧,都是铁哥们儿,以后他来酒吧,德水你照应点儿。那几个朋友中一个叫大力的说德水你碰上麻烦,不用通过老铁,直接找我大力就行。于是,德水就跟大力他们经常碰杯,经常下舞池摇摆,德水越来越上瘾,不喝不跳就难受。
白玲骂大力,你他妈太不地道了,德水叔是我的恩人,你也坑。大力嘿嘿地笑,玲子,你是老铁的人,我也是。我不听老铁的能行吗!那个傻子他活该,谁让他看不出眉眼高低呢。
白玲心情沉重地说,德水叔,您别在这儿干了,要不还回网吧吧。德水说白玲你没良心,我现在回那地方还不得憋死呀。
可是德水叔,您再在这儿干,就是死路一条啊。
德水摇着头,混一天算一天吧,也不知怎么的,我一天不喝不跳就浑身难受。
德水几天来喝了酒还是难受,浑身乏力,抓心挠肝的死的心都有。大力又来了。哥们儿,难受了吧?给你这个,吃上就好了。大力拿两粒药片塞到德水手里。
德水确认这就是传说的摇头丸。他瘫在沙发上,完了,这辈子完了。
大力斜着眼说,之前你已经吃了一万多元的了,就算小弟赞助你了,从今天起,想吃就得拿钱了。
德水愤怒,你们还是人不?就这么对待兄弟?算我瞎了眼,把你们当哥们儿!

愤怒归愤怒,德水还是吃下了药片,几分钟他就恢复了常态,又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照顾生意之余,滑下舞池,整个人轻松地摇晃,感觉好爽。
几个月之后,德水开始从香菊手里掏钱,一个谎接一个谎地撒,香菊觉得不对劲,交朋好友的也用不着花这么多钱啊。香菊打电话给白玲,白玲说交际是多点儿,可以劝劝德水叔尽量收敛些。
白玲已经借给德水两万元了,这么下去德水非出大事不可。白玲说德水叔,送您去戒毒所吧,对香菊婶说送您出去学调酒,只有这一条路能救您。
德水戒毒一周时,简直跟一个活鬼一样作人,他嗷嗷地叫,拽着刀条脸看守乞求,给我一包耗子药得了,这么活着不如死了的好啊!
刀条脸见四处无人,贼眉鼠眼地捏起拇指和食指,有这个吗?
德水连忙点头,有有,我肯定不少你的。德水从兜里掏出两张红票递过去。
刀条脸鄙夷地撇撇嘴,推了回去。
德水又掏几张递过去,刀条脸把钱揣进兜里,随手给德水一小袋药粒。恶狠狠地说敢卖了老子,让你不知道咋死的。
白玲再去探视德水时,发现德水根本戒不了,心知肚明有人往戒毒所贩毒,可自己小老百姓有何能力去拯救呢?她也没有更多的钱填给戒毒所,索性把德水接回了酒吧。德水靠工资根本不够开销,白玲也苦恼得不行,她在心里揣着对德水极大的歉疚,可她也没有能力供德水日复一日加量地吸食毒品。德水车也卖了,他知道媳妇香菊手里也没存什么钱了,他再不好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地跟白玲索钱。
深夜归家路过一小区,巧遇一老板模样的人挺着大肚皮挟着手包从小车里钻出来,按了遥控器欲往楼内走,德水两步冲过去抢了手包撒腿就跑,被抢的大肚皮边喊边追,眼看着追不上,大肚皮按响了车的遥控器,报警声声,他又按了手机报了110,小区里有夜归的人帮忙撵德水,德水被抓了。
一棒子没脸跟以往一样在小区里跟闲人们闲聊,他无法接受别人鄙夷的眼神。就去彩票中心买彩票,福彩、体彩他都买,开始买几十元的,小赚一点,尔后加大投入,几百元及至上千元,小奖没少中,却抵不住投入多,他一门心思想中大奖,却始终无缘。在彩票中心结识了一个卖六合彩的庄主,走火入魔般地加入了六合彩的行列,大半年工夫,一棒子手里的动迁款全军覆没,老伴儿一上火中了风,瘫在床上等人侍候,香菊侍候婆婆,又要侍候儿子,无法再去打工,一家人生活成了问题。
老大德鱼出租车肇事腿残后,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个小百货,勉强维持四个人的生活,供俩孩子上学。他只能给父母提供米面油盐之类的生活用品,治病及其他大的开销,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棒子坐在卫生间的坐便上,捂着脸号啕大哭,那哭声像狼的哀嚎一样凄惨。活到七十多岁,竟然活到这份上,给祖上丢人啊。他想买包耗子药,跟老伴儿一起死了算了,个人没能力管孩子们,也别拖累孩子们了。
一棒子一大早就到农贸市场转悠,那些卖小药的摊贩还没上来,只是青菜批发摆摊的挺火龙。他看到一些农民推车送来新鲜蔬菜,便怀念起在农村生活的日子,那日子虽比不上城里的悠闲,也是有滋有味的啊,如果一直过那样的生活,该多好啊,咱乡下人就没有福气待在城里,可老天非让咱进了城,现在是手插磨眼里,拔不出来了啊,唉!
一棒子忽然听到一辆三轮车里传出歌声: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一棒子听了这歌词,心情豁然开朗。对呀,毛主席共产党才是俺贫农的大救星,俺活到这份上了,找党啊,看看党这阵子还能管俺不?电视里老是讲扶贫帮困,俺得想办法找党啊。
一棒子进了市政府的院子,发现政府门前有几十人在上访。他站到上访人群中,问身边的老头子,老哥,你们为啥事上访来了?老哥说还不是动迁那点事啊。
一棒子心想,俺先看看动静,看上级政府咋对待上访群众的,俺再考虑俺的事咋办。
上访群众几次欲进办公大楼,都被几个保安拦下了,上班的政府工作人员侧着身子在保安的护佑下进了办公楼,然后门又被关上了,保安站成人墙把门口挡得严严实实。有几个中年妇女起哄,一声接一声地高喊,我们要见市长,见市长,男人用身子往前拥,保安往外推他们,一时乱作一团。这时有警车长鸣,十几个特警全副武装拨开人群冲到办公楼门前,群众愣在那不知所措。
一位信访干部站到人群前,各位老乡,请你们选三位代表跟我到信访办谈,好吧,你们都在这里影响政府办公。上访要走程序是吧,大家都是懂法的吧,快,谁跟我去信访办,快走。其余人散了散了。
人群中没人回应。
信访干部问,这里有村干部没?
一个女人尖叫,干部没吃亏,他们还能来呀。
信访干部又说,那你们也得有人出来跟我们走程序不是,都在这儿闹有用吗?
你们要是选不出来,我点谁谁跟我走吧。就你了,这位老哥,还有你、你跟我走。
信访干部指着一棒子身边的俩老头,还有那个尖叫的女人,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发现他们没动静,便站住脚,再不跟我来谈,警察就把你们都带走了。
警察开始驱逐人们。那女人一挥手,走就走,我跟你们去谈。俩老头也跟着信访干部向办公楼后边走。警察指挥其余上访人员到办公楼侧面静候。
一棒子向楼内走,保安拦住他。大爷你上哪个部门,登个记。一棒子说俺找市长。保安说那可不行,找市长得有预约,你有吗?
俺没有。但俺是有困难的贫农,俺活不下去了,俺要找市长。保安说有困难找当地乡村干部,市长哪有时间接待这小事。一棒子被保安请到楼门外。
一棒子心想,俺才不找村长呢,让他笑话俺。顶多弄个低保户,那点补助不够塞牙缝呢。他思虑,得怎样才能见到市长呢?他一个电话,指使民政局或联贫办,一包到底,把俺的困难麻溜地解决了。他决定就在楼门外等,市长的车牌号肯定是小号,对,就这么办。他靠在门旁边坐在石板砖铺的地上,点燃一支烟。
保安来扶他起来,大爷,您别坐这儿啊,到院里花园或马路对面的广场休息吧,一会儿有车上来撞了你怎么办。一棒子顺势站起来,正好一辆车牌号是辽K005的黑色小车停在楼门前,他几步走到车门口,对着正欲下车的一位稍微发福的中年人喊:你是市长不,俺找你有事反映。
发福的中年男说我不是,找错人了,我也是来办事的。
一棒子歪着脖子看看车内还有什么人,车里只有司机。司机已经把车开动了。保安过来推着一棒子,大爷,你快走吧,认错人了,再说,市长不是天天来这儿办公,开会下乡的,能在屋里待着吗?你别在这儿了,有事还是回村里走程序吧。保安拽着一棒子下了台阶,一棒子嘟嚷:别拽俺,俺又不是无赖,这多难看。
一棒子觉得还是找到大官好办事,等着村里往上报,没啥指望。他回家用绳子捆了一个行李卷,太阳快下山时,背着行李来到市政府门前,把行李往地上一铺,坐在那儿等大官,此时办公楼内的工作人员已经寥寥无几了。保安说大爷你要住这儿了?一棒子说,小老弟,别轰俺走,俺真是活不起了,等村里往上报,俺就死好几回了。俺要直接找大官,管事的。俺家三代贫农,都受党的恩惠,党不能不管俺们,你别撵俺,俺在这儿不影响什么。俺听说大领导白天下乡,有时回来得晚,让俺在这儿等吧,俺不影响领导工作,也不影响普通干部办公。保安没有再撵他。
一棒子连续在政府办公楼前睡了一周,那天市长下乡回来遇个正着,问秘书这老头哪村的?秘书说水景村动迁户,可能来好几天了,天天下班后来,睡一晚上,第二天大伙都上班后他才走。
市长嗯了一声,你去问问他什么情况,如果真有困难,让扶贫办帮忙解决一下,这么大年纪了,别在政府门口出点什么事,就麻烦了。
一棒子看戴眼镜的干部来询问,他就嗷嗷地号起来了,然后是泣不成声的样子,秘书一再安慰劝解,大爷别激动,有啥困难跟我说说,我们好商量解决不是。一棒子可算稳定一点情绪了,便抹着眼泪说,俺啊教子无方啊,到如今落得个生计无从的下场啊……
秘书说大爷我记下你的联络方式了,回头我跟领导汇报一下,看怎么能快点帮到你。你回家照顾老伴吧,你这样天天晚上在这儿睡会落病的,老伴不也担心嘛。
秘书朝保安一挥手,自己上了楼。保安过来拉一棒子,起来吧大爷,这可是市长的秘书,你回家等信吧。
一棒子回家左盼右盼,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消息。他拿了一瓶农药,又来到了市政府门前。对保安说,俺要进去找那秘书,糊弄俺贫下中农啊。保安拦着说不行,他伸手打了保安一记耳光,保安没有提防,被打愣在那里。旁边俩保安一起扭住了一棒子,一棒子连踢再叫地骂,看门狗,不让俺贫农见到党,俺踢死你们,你们不知道俺一棒子的厉害,当年俺十多岁就一棒子打死了恶霸地主,俺们全家跟党走,听党的话,在村里是有头有脸的,现在你们几个看门狗就挡着俺,不让见党,真是,衙门好进,小鬼儿难搪,小鬼儿难搪!松开俺,俺不进去了,俺走。
保安把一棒子扭扯到台阶下放开他,一棒子便从兜里掏出了农药,指着保安叫嚷:小兔崽子,俺死给你们看!挨一个耳光的保安指着一棒子,老不死的,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打我嘴巴子呢,要不是有纪律,我削死你!你吓唬谁啊,死不死的又不是别人逼你,你喝吧,糊弄谁呢,还农药,灌的水吧。三个保安转身往台阶上走,他们刚回到保安站岗位置,就听台阶下“啪”一声闷响,一棒子倒在了地上。一个保安跑下台阶,走到一棒子跟前,闻到了刺鼻的农药味。不好了,真喝药了,快打120急救。
一棒子没有死成,可他没有力气再到市政府闹了,他还是不想活了,他晓得了,落到如今的下场,不赖政府,动迁款给那么多,政府已经对俺们不薄了。别人家都过得愈发红火, 是俺自个儿家没那命啊。俺还去找政府,其实就是憨脸皮厚,这人啊真是丢到家了!他琢磨着等身板硬实点了,干脆走得远点儿,投了大江大河算了吧,省得让人耻笑,谁耻笑俺俺也听不见了。正在一棒子胡思乱想、病蔫蔫地趴在床上寻思怎么死的时候,德水焕然一新地从戒毒所归来了,这让一棒子一下子打消了寻死的念头,他感觉生活有了希望。
德水发誓再不进网吧,再不进酒吧。他应聘到水泥厂当上了拉罐车司机。
一棒子的眼睛开始放亮,他要重树自己的光辉形象,不能让人耻笑到百年,俺,一棒子,就得跟棒子一样,立起来是直的,躺下去还是直的。他到小区物业当上了保洁员,专管小区的花草园、甬道和健身器材的卫生。每月800元,对一棒子家虽然是杯水车薪,但一棒子心情有了改善,他把健身器材和休闲椅擦得干干净净,花园里少有一根杂草,甬道上不见一块污迹。幸福小区的人们见了他也不像德水刚被抓那阵子那么指指点点了,而是不带一点歧视地喊他“老景头”。
其实,小区里大部分是原来他们水景村的人,一开始对一棒子家有那么点幸灾乐祸,现在看到德水洗心革面了,一棒子这么精心地做他的工作,便转向了同情,不管咋说,一棒子家以前在水景村也是有头有脸的贫农代表,咋的也得让人活着啊。原村委会把一棒子家上报了贫困户,逢年过节的就有市里的领导来对接,送些生活用品和一沓钱,这让一棒子一家感到十分温暖,据说来扶贫的领导送的钱物都是自个儿掏腰包,这让一棒子很是过意不去,要是过去在农村,自家还能有点土特产回报给人家,现在住进楼房了,无以回报。一棒子对老伴说,张小人啊,你这一病啊,俺就没了主张,硬要讹党来管俺们啊,这是不对的啊,可没想到啊,党还真没抛弃俺,你说那领导们虽然工资高点,可人家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啊,凭啥就得年节的来孝敬俺们啊,俺们花人家的钱这心不安啊,张小人啊,你快好起来吧,你好了呀,香菊就能出去打工了,俺们的日子就不比别人差了,俺就撤了那贫困户的户头吧,贫困户这顶帽子啊,是耻辱啊!一棒子说着说着就老泪纵横了。张小人张开嘴,啊啊地点点头,香菊惊奇地发现,婆婆那只总是端着不听使唤的手活动起来了。一棒子攥紧了老伴的手,淌着眼泪,咧开嘴,哈,哈哈,哈哈哈……
责任编辑 王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