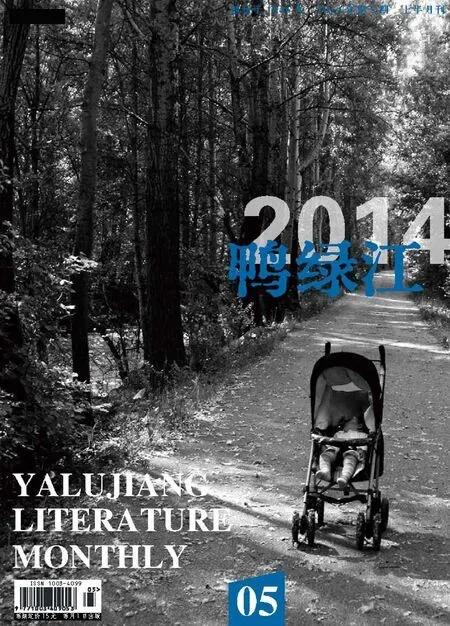浅春
赵淑清
浅春
QIAN CHUN
赵淑清

这个春天来得有点突然。人们还没从几十年不遇的寒冷中缓过神来,春风就热乎乎地一拨一拨吹来,吹得人们有些晕头转向。小村跳动起来,年轻人纷纷掀开电话本,向远方问询打工的消息。初春的小村被这些消息搅得慌慌的。
院子里,母鸡也叫得欢了,脸涨得通红,一到晌午就在院子里踱着方步,有节奏地“咯哒咯哒”地叫,见了主人,又羞涩地甩着小碎步跑开了。主人到鸡窝旁往蛋窝里瞄,除了一枚种蛋啥都没有。又去仓房,在柴草间发现有个窝儿,把手探进去是温热的,他赶紧进屋拿来一枚种蛋放进去。主人做着这一切,很认真很亲切,像在温习一个旧梦。因为他知道距离出外打工的日子不远了。
从仓房转出去,整个小院明晃晃的,阳光有些刺眼,到处都暖烘烘的,院子像蒙着玻璃罩子。进园子里看看,羊角葱还干枯着银白的叶子,扒开才见里面裹着胖胖的绿葱芯儿。菜畦里的小葱却钻出了绿锥锥儿,脸俯下来,眼前是一片小“森林”,一眼望不到边,这感觉真好。旁边的韭菜畦里,韭菜也拱叶了,紫褐色的窄窄的一小截,像是眯缝着眼儿。这些小东西真是精明,让人感觉不到是啥时候睡醒,打个哈欠伸个懒腰就冒出来了。风这么暖,阳光也像个顽皮的娃娃,在小院里欢快地跳跃着。
主人情不自禁出了院子。院外的白杨树上,长满了黑乎乎的杨树狗儿,此时还紧紧地长在树枝上,再过几天就该松松垮垮地垂下来了,成千上万的紫红色的杨树狗儿迎风飘荡,那是一树的春旗,招摇着,舞蹈着,像喝醉了似的,渲染着春的热烈,春的喧腾。小村里这样的杨树到处都是,那时候,整个村庄全被这一树树的紫红笼罩起来,阳光透过枝丫的间隙,在屋顶上、院子里、村街上洒下斑驳陆离的花影,人们就踩着这一地的花影背着农具上山犁地,心情也格外地美。可惜这样的场景有十年没见了。
主人又漫无目的地走上了村街。如今的村街真是漂亮!那条灰白的水泥路直通到村边,然后是红红的砖径曲里拐弯通到各家门口。此时,那些等待着开花的树也都迫不及待地将头伸出院墙。杏树的花蕾在枝丫间鼓着,有的藏在紫色的花萼里,有的隐隐露出点白,偷看这个春天。梨树花的花蕾隐蔽得挺严实,它们准备在杏花开后再登场,时间还来得及。榆树钱儿有点急了,高粱米粒似的,一串串地在春风中摇曳,仿佛有股甜丝丝的榆钱儿味袅袅地袭来。榆钱儿状似铜钱,开放时像樱花一样一嘟噜一嘟噜的,这种绿色的花朵在辽西的春天很罕见。村街就这样被这些要开花的树木打扮着,拥挤着,在白墙灰瓦的房屋间穿行着,走到哪儿都好看,熟悉而亲切。
从村街折回来,他站在小村口,沿着公路望去,那两排垂柳正舒展着腰肢,伸开手臂,散开长发,迎风而立。她柔嫩的枝条饱蘸春墨,将叶芽均匀地点缀在身,像一排排流动的音符,用莹莹绿意,谱写春的乐曲。远山望上去还没啥动静,但灰蒙蒙的色彩上有了浅浅的草色。松树更绿了。山下好多人都在忙着备耕,有拉粪肥的,有刨茬子的,还有燎荒的……
就在他的目光恋恋地流连之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口,原来是附近镇上的老板来招工了。刚才还静静的春气被这个信息搅活了,人们兴奋地围拢上来,问工种,问工薪,问待遇,问保障……一个小时后,他和十几个年轻人签约了。
这些常年奔波在外的人们总算可以在家里过一个完整的春天了。他浅浅地笑了。
可是,这个来得挺早的春天却因为连绵不断的雨雪天气给推迟了。往年清明一过,阳坡的杏花就迫不及待地开了,今年却迟迟不见踪影。天阴沉沉的,不停地孕育着一场又一场雨夹雪,男人一遍一遍地唠叨着:这杏花咋还不开呢?
天终于放晴了。阳光暖暖地照在喧腾的田垄上,照在小院里:小嫩葱冒着高地长,羊角葱挺着身子,韭菜舒心地展着细叶。地角那墩菜母也拱包了,露出嫩黄的小脸儿。井台边的芍药伸出了粗壮的莛子,叶子像婴儿的拳头紧紧地攥着紫红色的莛子。家燕在房檐下筑巢,它们时而落在畦子里衔泥,时而到鸡窝旁啄几片细小的羽毛,忙碌而欢悦。男人的目光落在邻家伸出来的杏枝上,那枝红红的杏蕾在温润的春光里像一团流动着的火焰,男人心旌摇摆起来。他的目光蹦跳着,越过邻家的杏树,越过那些绽放着丝丝甜味的榆树,也越过那些高大的杨树,此时树杈上的杨树狗全都炸开了,万千条小旗子摇摇摆摆。他的目

赵淑清,60年代中期出生于辽西农村。现供职于喀左广播电台。省作协会员,省散文学会会员。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在《辽宁日报》《海燕》《鸭绿江》等五十多种报刊发表散文、小说作品两百余篇。著有散文集《月亮泉》《在梦与醒之间》。光像一只拖着长尾巴的鸟儿最后落在杏树坡上。那里绵密的杏树红红紫紫的一片,宛如没熟透的火烧云。男人忍不住对女人说,这杏花怎么像个难产的婴儿,露个面真难。女人笑了,笑得他莫名其妙。
女人也跟着他立在了院子里,满眼笑意地看园子。这个春天,因为男人在家,整个小院多了许多生气:大蒜早钻出了葱绿的幼芽,春菠菜刚播种,豆角、黄瓜、角瓜畦子早做完了,就等着天一转暖就挖埯点种。院墙周围也都暄了土,准备东墙边种几棵南瓜和冬瓜,南墙边种一溜葵花,等这些小家伙都长起来,那才是献给春天的一份田园清供呢。想到这儿,某种诗意的东西在女人心头荡漾开来。
是啊,这杏花怎么还不开呢?女人也说。
真是不禁念叨,就在这天下班,男人骑着摩托车往家赶时,迎面山坡上的杏花波浪般向他涌来,打了他一个冷不防。他嗅到了杏花的芳香,一股热热的暖流涌上心头,那个久违的梦又清晰地在眼前展开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不停地升腾、升腾,遮盖了要干的农活,遮盖了给牛铡饲草,也遮盖了帮媳妇做晚饭——这是他在十多年的打工岁月里无数次回味和憧憬过的,也是他在这个春天里最期盼的。
他回到家,先把儿子安顿到父母那吃晚饭,说自己和媳妇有点紧活儿要干,就扛把镐头带着媳妇径直奔杏树山去了。媳妇说咱家的地没在那儿,你去那儿干吗?男人说你到那儿就知道了。路上有扛着农具回家的人,问怎么都黑了还上山干活啊?男人支支吾吾地回答着。
两人一前一后到了杏树坡,雪白的杏花犹如一位身着嫁衣的新娘,热情地向他们扑来,浓浓的芳香瞬时包围了他们,黏黏的,稠稠的,有花的苦味,也有蜜的甜味,他们都有些半醉了。此时夕阳正红,给杏花涂上一层淡淡的胭脂。往远处望去,山坳里,田角边,村庄周围全是杏花,一团团,一簇簇,一坡坡,都羞红着脸拥着挤着往眼里钻。这情景让他们想起了恋爱时的甜蜜,也是在这片杏地,也是满天杏花的时候,爱情的花蕾绚丽地绽放了。男人回眸的一瞬间,看见了女人甜甜的笑容,他就幸福得顶天立地了。他喊声:快跑,后面狼来了!便小跑着进入杏林。女人嗔怪道:瞎咋呼啥啊!也跟着小跑起来。男人边小跑边抖动杏枝,让洁白的花瓣慢天飞舞,女人只觉得月亮的碎片从天而降,花香愈加浓稠了,她的心里也如杏花盛开着,那个芳香四溢的梦多少次在她的梦里上演,却因为男人在遥远的异乡打工难得重温。那时候,他们躲避着人们的视线,让两颗彼此倾慕的心跳跃在春意盎然的杏花里。回到家,村里人还是从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杏花味嗅到了秘密,拿他们开涮,让两个人脸红心跳……
月亮渐渐升起来,丛丛簇簇的杏花上笼罩着一团白蒙蒙的雾。男人背着女人在杏树趟子奔跑着,他要把这月色调均调亮。果然,月色如银盘般亮起来,男人手舞足蹈,不断有如雨似的杏花瓣飘落,像一只只白蝴蝶的翅膀,也像无数飞舞着的鱼的鳞片,落在女人头发梢上,眉毛上,衣襟上。女人羞答答地抖搂着,怪男人老大不小没正形,男人看女人越发漂亮,妩媚,索性弯下腰把女人扛起来,在亮地上转起圈来。女人的眼里,杏花如巨大的银白的旋窝旋转起来,一仰脸,一轮金黄金黄的月亮慈爱地看着他们,“别疯了,月亮笑我们呢!”
男人一愣,果然也看见月亮眯着眼在笑他们呢,他也笑了。
此时,万籁俱寂,月光幢幢,花影扶疏,整个世界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了。不必说十年的牵挂,也不必说十年的思念,更不必说十年聚少离多的艰难,只管尽享眼前的杏花月色就是了。
回家的路上,男人又像孩子似的发了疯,他把镐头往前撇出去老远,然后背起女人小跑着追镐头,逗得女人咯咯笑。这笑声撞到月亮盘上,撞到月色镶着杏花的大瓷碗里,也像杏花一样漫天飞起来……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