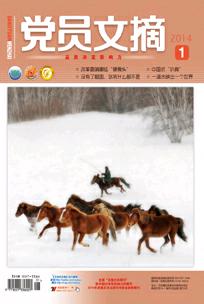高贵的“文化快乐”
张小黑
快乐有很多种。但有一种快乐,却是必须建立在一种文化的、文明的、有教养的基础之上,它是一般人难以拥有的真正的快乐。
“文革”中,季羡林先生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开始时,他几乎每天都要被拉出去批斗,后来,造反派安排他在女生宿舍的门口打铃,还兼管传呼电话,就是有人来了电话,他就站在门口喊几声“几零几室,某某同学的电话”。这件事如果搁在别人身上,一定会有满肚子的怨气,季先生却居然感觉很快乐,说是“上天对自己的恩赐”。因为他终于可以有机会能每天偷偷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悄悄带到女生宿舍门口的传达室里,琢磨着怎么将它翻译出来。《罗摩衍那》的汉译版,就是季先生在那段时间里完成的。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季先生就是依仗着一种人文的滋养,一种文明的积淀,最终度过了那段非人却快乐的时光。
与季先生一样,杨绛先生的快乐同样充满着文化的快乐。
杨绛先生也没有逃脱那个疯狂年代的迫害,被发配到单位厕所做清洁工。她置备了几件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了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子,每天在厕所里认真地清洗,将所有便具都洗出了本来的面目。所有人都赞叹她的活干得漂亮,厕所不像厕所,倒像一座温馨的小宾馆。忙完工作后,杨绛先生便悄悄坐在厕所里看书。有时候她出去,远远看到外地来京的红卫兵,为防止意外,她便进入女厕所,那里成了庇护她的宝地。在忆起那段经历时,杨绛先生这样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
而钱学森先生所具备的文化快乐,却有着另一番意境。
在钱学森的图书馆,有一个老式写字台,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小椅子。写字台是钱先生每天做完研究之后剪报专用的,小椅子则是夫人蒋英女士用以陪伴钱先生的专座,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其间两人甚至连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默默地坐着。一次,蒋英对儿子钱永刚说:“你去陪陪你爸爸。”钱永刚说:“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他是搞导弹的,那些机密的东西又不好跟我说。”蒋英就笑了,说:“去吧,你爸爸看见你陪他会很高兴的,陪他不一定要说话,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钱永刚后来说:“陪了父亲几次后,我这才知道,快乐是可以很安静的,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说话的。这就是难以言喻的文化快乐。”
(摘自《意林·原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