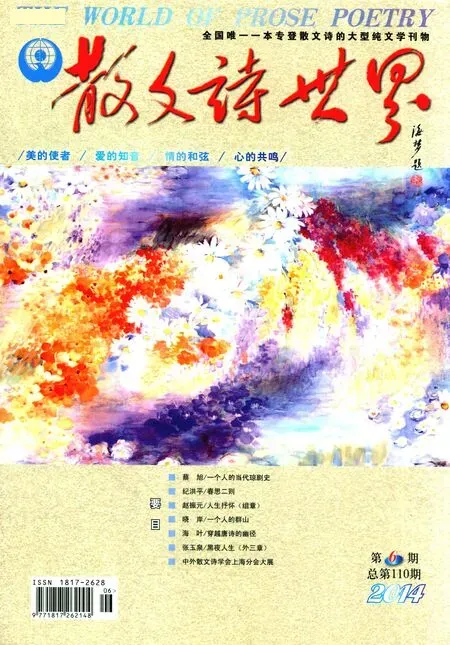我是一条消失的弄堂(外一章)
朱锁成
我是一条消失的弄堂(外一章)
朱锁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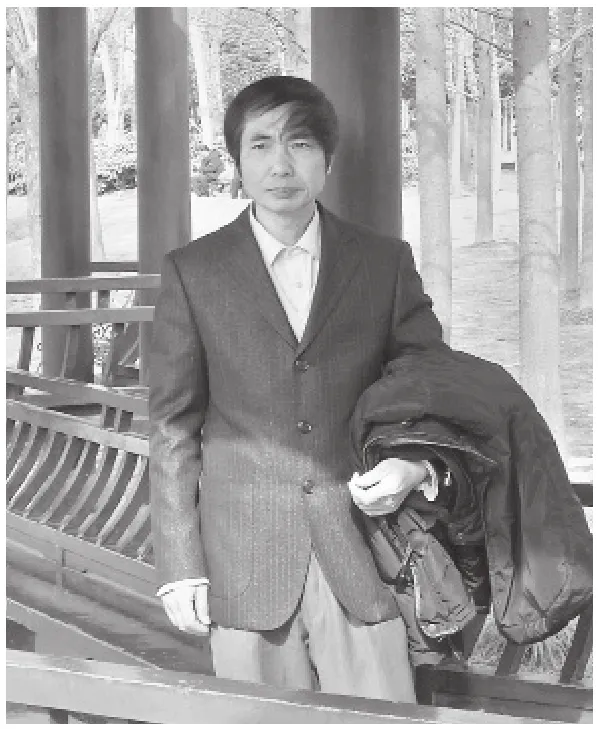
朱锁成,上海人。插过队,当过矿工,做过记者编辑。1992年出版散文诗集《最后的倾诉》。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鱼鳞瓦、黑砖墙、白炽灯,这个城市最具特色的记号消失了。
黄浦江、轮渡、万吨轮,这个梦里常常拥在枕边的声浪离我远去了。
因为一个并不了然的动词,我这条滚过铁圈、萦绕过煤烟、响过粪车摇铃,炸响过除夕鞭炮的弄堂消失了。
消失的是繁华背后的身影。消失的也许是底层的潮湿和嘈杂。但我是这个城市组成的最广大最普通的系列。
我举过十月的手臂,和鲜花红旗一起挥舞在人民广场。
我舞过五月的银镰,响应过黄昏的那一次潮涨。
我这条窄窄的弄堂开始远离城市,远离生我养我的摇篮,第一次孤单地瑟缩在异乡。
我自信,我是一条精选的弄堂。虽然我的手掌有点稚嫩,虽然我从没出过远门,可我以一代人的誓词握紧了锄把,以浦江之水浇灌了我的饱满和忧伤。
弄堂,许许多多的城市的种子,是摇曳在小村的大面积播种,匍匐在小村的另一种偎躺。
如今,我又一次告别,不再有痕迹。
这里会是一座公园,有我栖息的长椅。
这里会是一间教室,有我旁听的灯光。
这里会是一张病床,有我询问的诊筒。
可这里又崛起一幢住宅、酒楼和咖啡吧。
悬挂的窗帘溅满了灯红酒绿,这里原不是车铃的停车场。
我只是隐隐约约听到,地毯亵渎的地方,举行过一次开业典礼,被邀请的席卡当然不会有弄堂。
我是一条消失的弄堂。
也许,城市就是在一次次消失中变得美丽和强大。如若那样,我不也消失得其所,消失得还有分量。
而我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走廊,我倾听这个城市每天的潮声,收集这个城市一样美的阳光。
城市已经没有我的狭长。
我只是希望,我这个分散的走廊,有一天会变得更加的敞亮……
抚 摸
抚摸是最初的哺乳。
背上生出痱子,手碰破了皮,母亲的抚摸是滑润的痱子粉,清凉、消毒。
暑假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老师的家访是抚摸的清风,飘拂在瘦瘦的小弄堂。
即使到农村插队,大嫂端来的手擀面是一碗抚摸,乡妹子给我缝的夕阳是丝丝缕缕的抚摸,老队长的旱烟袋也是抚摸。空旷的不坠的篝火,夜,不再漆黑,思念,由暗转红。
来到高高的井架,来到黑尘和硝烟丛生的掌子面,培训是一种抚摸,矿帽和矿靴是一种抚摸,老书记坐在床沿的谈心是一种抚摸,培育卑微的种子更是一种抚摸。
抚摸无处不在:房子漏了,瓦赶来抚摸。被絮破了,闻风而动的棉花伸出洁白的纤手。不幸躺倒的手臂,白色的床单和罐头笑吟吟地抚摸我胸口。
即使大地冰冻,还有月色抚摸。
即使大雾锁江,还有城市轮渡。
即使电闪雷鸣,还有彩霞等待飞虹。
抚摸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母乳。是天空辽阔的甘霖,是弄堂拐弯处一盏路灯,是开启心灵之锁的一把钥匙,是恋人的一记轻吻,是垂危时亲人的一声抚慰。
只要岁月有淤积和堵塞,人有跌倒和低落,就期盼抚摸。
浪抚摸船,歌抚摸夜,爱抚摸心。
现在还有抚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