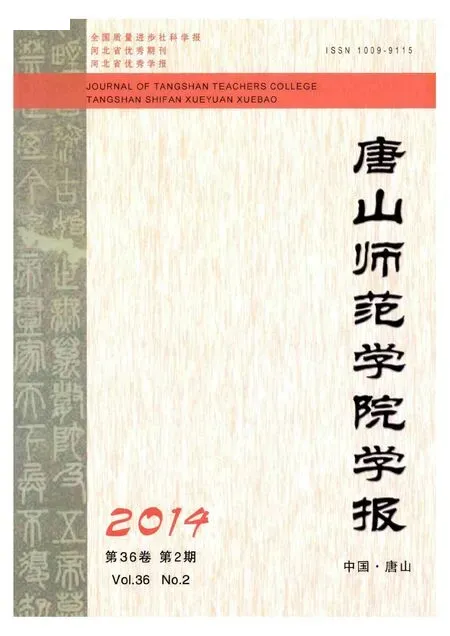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差异及变化的统计分析
田 立,冯 丽
(1. 福建农林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2. 安阳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福建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差异及变化的统计分析
田 立1,冯 丽2
(1. 福建农林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2. 安阳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选取了福建省2011年和2003年9个地市农村居民的8个生活消费指标。首先对8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了3个代表性因子:基本生存需求因子F1、改善生活因子F2和健康生活因子F3;其次利用对3个因子加权平均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分析,把9个地市分成了3类,并且计算了同类别内部的平均因子得分、平均综合得分和8个生活消费指标所占总消费的平均比例,最后比较了2011年相对2003年同类别内的平均综合得分和8个生活消费指标所占总消费的平均比例的变化特点,并进行了讨论分析。
消费结构;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不但反映了居民消费的具体内容,更能体现居民的消费质量和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消费结构是否合理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增长速度[1,2]。对于福建这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省来说,研究其农村消费结构特点并掌握它的消费需求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2011年统计分析结果
根据福建省统计年鉴共选取了2011年9个地市农村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服务、其他支出8个生活消费指标。由表1可见,各个指标存在比较严重的相关关系,说明各指标重叠严重,不利于分析消费的内在结构,有必要对数据进行降低维度处理,使得消费结构能够简化明了。
经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得卡方值为89.257、自由度为28、p值为0.000,表明8个变量比较适宜进行压缩降维,可以进行因子分析[3]。为使得因子具有比较明确的含义,需进行方差最大化的因子旋转。因子分析和旋转结果见表2、表3。
由表2可知,前3个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0.942,即反应了原来8个指标的94.2%的信息。
由表3可知,食品、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其他支出在第一主因子上有接近于1的大载荷,交通通讯在第一主因子上有0.773相对大的载荷。食品、居住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面对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阶段家庭设备及服务中的电视洗衣机之类的设备也是日常必需品,同样交通通讯中的电话及话费,代步工具也是日常必需品,所以第一个因子反应日常生活中经常性发生的基本生存需求的因子F1。衣着和文教服务在第二主因子上有绝对大的载荷,交通通讯在第二主因子上有0.577的稍大载荷。现在生活单纯出于保暖目的的衣着费用降低,因美感、舒适感等改善型需求所占的衣着费用的比例比较大;文教服务属于提高个人文化修养充实内心的精神需求;交通通讯中也有相当比例的是改善型的,如交通工具的改进等,所以第二个因子反应的是非经常性的改善生活因子F2;医疗保健在第三主因子上有0.992的载荷,由于现在农村中的医疗特点仍然是小病在基层医疗点就诊,花费非常少,对于偶然的大病,即使现在有农村医疗合作社,由于覆盖范围、指定医院和自费比例的限制,花费比较多,在总医疗保健花费中占有绝对大的比例,而单纯的保健费用支出基本可忽略不计,所以第三个因子反应的是日常生活中偶然发出的健康生活因子F3。

表1 相关系数表

表2 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表

表3 因子载荷矩阵
可计算得出3个因子各自得分,但是由于3个因子所涵盖的信息量与地位不同,直接利用3个因子的得分对9个地市的消费结构进行比较存在比较大的误差,所以对3个因子进行加权平均,构造综合因子得分,其中每个因子前的权重值为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3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的比值。利用综合因子得分对9个地市进行排名并进行聚类分析[4],结果见表4。

表4 2011各因子得分、综合得分及聚类分析结果
对同一类别的地市分别计算3个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的平均值,结果见表5。

表5 2011年各类别的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的平均值
计算同一类别地市8个生活消费指标占总消费的比例,结果见表6。

表6 2011年各类别内的生活消费指标占比
2 2003年的统计分析
类似于2011年数据分析过程对2003年福建9地市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服务、其他支出8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所得3个因子及其含义与2011年的相同。结果见表7、表8和表9。

表7 2003各因子得分、综合得分及聚类分析结果

表8 2003年各类别的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均值

表9 2003年各类别内的生活消费指标占比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由表4和表7可知,厦门、泉州两市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一直明显高于其它地市,处于第一类;福州一直处于第二类;宁德与漳州、龙岩,南平、三明一起处于第三类。莆田在2003年处于第三类,但是在2011年处于第二类。
由表5和表8可知,第一类的综合得分由2003年的1.140 5变为2011年的0.945 0,导致2011年三类别平均综合得分的差距比2003年的变小。
由表6和表9可知,在衣着所占总消费比例上,第一类地市由0.046 1提升到0.058 3;第二、三类地市也分别由0.050 7和0.052 8提升到0.058 2和0.058 5;在交通通讯所占总消费比例上第一、二类地市分别由0.122 8和0.099 4提升到0.141 7和0.105 2,第三类地市也由0.099 6上升到0.104 2;在文教服务所占总消费比例上第一类地市的由0.094 4下降到0.087 1;第二、三类地市也分别由0.101 1和0.123 3下到0.072 5和0.090 7;在医疗保健所占总消费比例上第一、二类地市分别由0.046 1和0.059 0下降到0.034 9和0.055 7,第三类地市则由0.042 6上升到0.045 0。
在居住所占总消费比例上,第一类地市是由0.196 4下降到0.171 3;第二、三类地市却是上升。在家庭设备及服务所占总消费比例上,第一类地市由0.059 9下降到0.057 7;第二、三类地市分别由0.053 4和0.042 9上升到0.057 2和0.050 6。
由表6可知,第一类地市在食品和医疗保健方面所占比例明显低于第二和第三类地市;在居住和交通通讯方面明显高于第二和第三类地市。
进一步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厦门、泉州两市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一直明显高于其它地市,但是2011年各地市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比2003年有所缩小。
(2)随着经济的发展,福建省的农村居民花在衣着和交通通讯所占上的费用所占比例都保持增加,但是文教服务所占总消费的比例上却呈现下降的现象,原因是随着经济水平和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额在增加,但由于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取消、非义务教育所需的学杂费未增加和政府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大了投入导致了在文教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未增加;
(3)在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所占总消费比例上,第一类地市是在下降,第二、三类地市在上升。由于农村居住是以集体土地作为宅基地并自建为主,所以与城市房价的模式不同,受城市房价飞涨的影响有限,与此同时由于收入的增加,总消费也在增加,在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所占总消费比例上不应该上升,另外第一类地市属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所以在居住和家庭设备上的消费行为比另外两类地市提前,第二类和第三类地市在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所占总消费比例上的变化有滞后效应。
(4)在医疗保健所占总消费上体现出的第一、二类城市下降的原因是现在实行的农村医疗合作社政策,缩减了农村居民在医疗方面的支出;第三类地市没体现出下降的原因是,2003年时比较低的医疗支出的低起点和现在农村医疗合作社在第三类地区推广覆盖范围的约束。
(5)从各类别的八个生活消费指标占总消费的比例的变化上看,2011年较2003年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在医疗保健、文教服务、家庭设备及服务上一直比例较低,在食品和居住上一直都占很高的比例,尤其是第二和第三类上的食品比例,一直都大于0.46,明显高于第一类的0.41左右的水平,说明福建农村消费,尤其是厦门、泉州之外的其他地市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消费水平。
[1] 张小勇,李培峦,常志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数学理论与应用,2009,30(2):53-56.
[2] 罗彦平.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对应分析[J].北京:经济研究导刊,2010(19):32-35.
[3] 朱建平.应用多元统计分析[M].科学出版社,2006:62-128.
[4] 马欣.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和水平的聚类分析[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9(2):211-211.
[5] 段小红.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国际比较[J].世界农业,2010(8):20-25.
(责任编辑、校对:赵光峰)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of Fujia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TIAN Li1, FENG Li2
(1. College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2.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yang 455000, China)
Eight rural consumption indicators in nine cities of Fujian province in 2011 and 2003 are selected. Firstly, three representative factors are obtained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of the eight indicators: basic survival needs factor F1, living Improvement factor F2 and healthy living factor F3. Secondly, nine citi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by cluster analysis based on composite score which is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three factors. Furthermore, average factor scores, average composite scores and average proportions of eight living indicators to total consumption are computed in the same categories. The changes of average composite scores and average proportions of eight living indicators to total consumption in the same categories between 2011 and 2003 are compared and commented.
consumption structure;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O212.4
A
1009-9115(2014)02-0025-03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2.007
2013-06-06
田立(1982-),女,山东冠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应用概率统计与数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