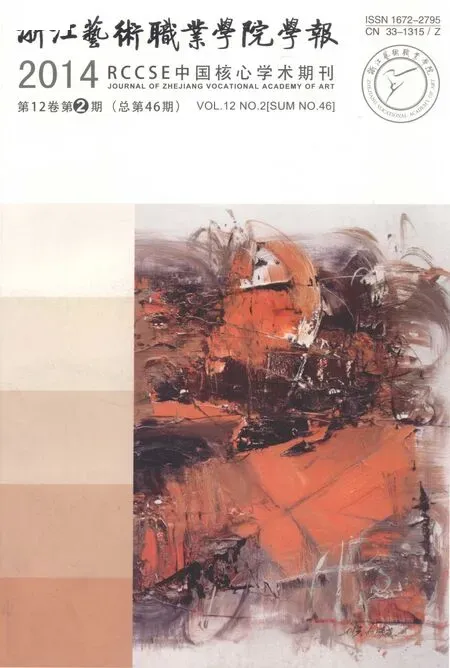本体回归与现代化追求——近年来中国戏曲的发展与趋向
刘 祯 江 棘
这是一个多元共生的新时代,中国的戏曲既面对着日新月异的时代浪潮和日益紧密的全球联动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也正在凭借其民族民间文化优秀代表的存在价值获得更多的尊重、敬畏与珍视。昆曲、藏戏、广东粤剧、京剧先后成功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些古老剧种也在上海世界博览会和国内外各类艺术节、戏剧节的广阔舞台上,不断彰显着民族文化穿越时空的不朽魅力。伴随着文化多样性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概念的深入人心,民族文化传统和特色的保持与回归被视作当下整个民族在现有世界格局中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理论界也展开了对西方话语长期主导戏曲研究的反思,呈现出力图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戏曲本体并呼唤理论回归的集体性诉求。另一方面,上述对于传统的继承与尊重,对戏曲本体回归的呼唤,在今天又是与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型这一时代命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本体回归与现代化追求之所以成为近年来中国戏曲发展中两大焦点,既是文化自觉的一重体现,也反映了传统在当下以及未来的生存中诸多矛盾关系的交汇与辩证。
一、理论研究的本体回归与表演理论体系建构
戏曲本体回归的呼声,其前提是对文化传统的珍视。中国的戏曲文化与以欧美近代以来戏剧为代表的剧场形式,有着诸多差异,这已成为比较文学、比较戏剧领域老生常谈般的共识。在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期以后,中国的戏曲与海外的交流越来越主动和频繁,一方面是随着新知新学在清季民初的生成和国家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兼具中外学养且与海外汉学界关联紧密的学人,以近代学术的史学架构开启了近代戏曲理论构建之门 (这一构建是从古典戏曲文学开始的),同时,欧美戏剧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知识界与剧坛,易卜生、戈登格雷、阿皮亚、爱尔兰戏剧运动等都曾在五四新旧剧论争、国剧运动、戏剧大众化运动等阶段被反复提起、讨论、呼应,成为民众启蒙和新艺术实践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梅兰芳、韩世昌等戏曲表演艺术家在日本、美国、欧洲的公演引发了许多有意义的对话,吸引了布莱希特、梅耶荷德、斯达克·扬、青木正儿等众多海外著名戏剧家参与其中,中国戏曲也在与异质戏剧形态的比较对话中,获得了更广泛的认知,这不仅是指外部认同的获得,同时也包含自我认知的深化。中国近代戏曲艺术理论的构建与归纳也同样是在这一跨文化视野的观照之中进行的。对于戏曲艺术一系列“写意性”“虚拟性”“象征性”“程式性”“流动性”等特征归纳,无疑都是设定了一种与之对立的异质戏剧形式作为参照的。借助比较,我们看到了戏曲艺术的独特性,而来自异域的评价也让处于新旧剧变中压力重重的戏曲重拾自信,得到了证明自己并加深自我认知的机会。
然而这一进程中也蕴藏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它们成为了今天戏曲研究与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和新的起点。首先,珍视文化传统虽是一大普遍共识,但落实于戏曲之上,却又要求重视其内部的具体的复杂性。中国的戏曲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单一的存在,而是有着多元的脉络。今天当我们继续在 “中外” “东西”的脉络中进一步发掘戏曲独特的文化价值的时候或者以 “国粹” “传统文化”笼统称呼概括戏曲的时候,其实也容易陷入一种认识的误区,那就是以几种形式看起来最为精美、历史影响最为广泛的剧种 (典型的如昆曲、京剧)其某一方面最为鲜明的特质来囊括中国的戏曲文化与戏曲精神。从有利的一面说,中国戏曲理论中很多概念基础离不开这种基于代表性的选择、归纳与概括;但是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理论视野的拘囿和惯性视线,使得中国戏曲的丰富性缺乏应有的关注,某些地方戏曲、少数民族戏曲等戏曲宝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趋向边缘化,成为 “弱势戏剧”而被漠视。正是基于此,当下戏曲界呼唤对于剧种偏见和单一汉族戏剧史观的突围,只有真正将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使京剧、昆曲等大剧种、古老戏曲声腔剧种和各地方戏曲、民间戏曲以及少数民族戏剧都能得到保护,都有机会生存、发展,才能让戏曲回归其民间本质,实现中国戏曲真正的百花齐放。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国家的政策扶持,也需依靠艺术家们的高度自觉,归根结底则离不开发自内心的精神体认与人文关怀。
另一个问题是在学术话语方面。毋庸置疑,跨文化的交流为近代戏曲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术语等多方面的资源,然而与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学术领域的整体背景相一致,中国戏曲并不是以在自身悠久历史中形成的语言进入国际对话的符号生产和流通体系的。虽然古代有很多相关著述,但中国古代文论、曲论中重视主观情感体验的诸多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 (如 “意境” “气韵”等概念与鉴赏、评点式著述),面对今日的国际学术对话,陷于“失语”之境。国际学术对话中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强势文化垄断、文明优劣论的阴影长期笼罩,使得近代以来对戏曲理论体系表述的努力,实际上总是难以摆脱用西方的 “语法”来 “说话”的事实。如何用本土的语法,清晰、完整、有逻辑支撑地阐述自己的戏曲理论 (尤其是独特的表演艺术),而不是用强势文化制造的语法、术语做类比性的描述和定义?如何夯实民族戏剧基础理论研究,寻求积极平等的对话?这些问题在当前的戏曲界,汇聚为在对中国戏曲自身美学思想内涵加以审视和研究的基础上,科学阐释和构建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集体性努力。在中国戏曲中,表演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而今天戏曲舞台上的 “转基因”和异化现象也突出且直接地反映在表演环节, “话剧化”的表演,对其他艺术形式的模仿跨界,以及一些名曰创新、实验、现代、后现代的表演正侵占着戏曲舞台和动摇着戏曲演员的表演根基,其中良莠不齐,有基于深入思考的尝试,也不乏跟风效颦之举。市场的繁荣与舞台的创新当然是戏曲发展的动力,然而这绝不应当以演员丧失灵活巧妙运用戏曲程式手段塑造角色的能力为代价。戏曲表演的核心价值与存在本质,亟待得到更深刻的认识,形成自己的理论语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筹划多年,即将着手的 “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这一课题,也因此受到了学界广泛而热切的关注。借这一集体性的关注,人们不仅反思当下,同时也获得了有利的契机,去重新总结和认识诸如张庚等当代前辈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戏剧史家的理论贡献和中国戏曲理论、戏曲学科现代化的历程。应当说这是一项开放式的系统工程,它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既是戏曲表演理论的引领,也是表演实践的汇通。
二、见证与发扬:经典魅力与传统意蕴的当代抒写
戏曲理论研究的本体回归是与舞台实践 “原汁原味”的追寻互为表里的。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已过了十个年头,藏戏、粤剧、京剧也相继跻身其中。古老剧种和传统剧目是戏曲悠久历史和丰厚积淀的最有力代表者,也在真诚守候民族传统文化的戏曲知音者心中占有着最重的分量。古老剧种与传统剧目在当代舞台上的大放异彩,无疑是对传世经典其穿越时空的魅力的见证与发扬。今天的戏曲人和戏曲观众,仍渴望在经由厚重的历史而沉淀凝香的传统意蕴之中滋养身心并反哺于戏曲自身进一步的发展,呼唤人们怀一颗敬畏之心去面对的,是戏曲传统中那厚重悠远的美学意蕴、深沉隽永的历史意识与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民间情怀。
近年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10年在上海举办第41届世界博览会时,作为 “世博会文化展演活动”之一,上海昆剧团联合重庆市川剧院、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山西省高平市上党梆子剧团共同策划, “古戏薪传——中国四大古老剧种世博展演”,把中国东、西、南、北四方地域中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古老剧种首次聚合在一起,川剧、昆剧、梨园戏、上党梆子四大古老剧种同台亮相上海舞台。数十位 “非遗”传承人与剧种代表人物汇聚一堂,演出昆剧 《借茶》 《偷诗》,梨园戏《大闷》《公主别》,上党梆子《杀庙》《惊疯》,川剧《醉隶》《思凡》《逼侄赴科》等多个经典折子,“碰撞”出一个古老戏曲的博览会。演出的成功既源于海内外观众对民族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也说明了传统戏曲在社会心理层面所拥有的深厚根基。
与此相关,传统经典或经典整理改编剧目在当今舞台和戏剧市场所受到的欢迎同样引人注目,如上海昆剧团的精华版昆剧 《长生殿》、重庆川剧院的川剧 《李亚仙》、浙江昆剧团的 《虹霓关》等。尤其具有代表性同时或许也是最具有舆论热度的事件,是白先勇团队打造的 《牡丹亭》 (也被称为“白牡丹”)等 “青春版”昆曲的演出及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剧目演出宣传中, “白牡丹”被深深打上了 “原汁原味”、“只删不改”、“串折本而非改编本”的烙印。但是究其创演的目的和舞台呈现,事实上并不同于传统戏曲,如白先勇本人所言,“制作青春版《牡丹亭》的目的就是想做一次尝试,借着制作一出昆曲经典大戏,举用培养一群青年演员,而以这些青春焕发、形貌俊丽的演员来吸引年轻观众,激起他们对美的向往与热情”,并 “将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制作出一出既古典又现代,合乎二十一世纪审美观的戏曲”[1],可见这是一次力图符合现代审美的尝试。白先勇在演讲授课等场合曾将这种尝试比拟为将原有的博物馆展品放置在新的更加悦目的展示环境中予以呈现,但事实上这当然不仅仅是 “环境”的置换,其背后是一整套不同以往的整体性的美学意图。当代昆曲编剧张弘先生在谈其创作心得时曾提到 “舞台时空就好比一杯水,此长彼消,容量只有那么多,我希望这杯水的八成以上,都是表演艺术”[2],以 “小” “少”“虚”“空”的舞台凸显出对于 “演员血肉之躯”的“信任与欣赏”、凸显出表演的第一性,其实这正是传统优秀昆曲表演的宝贵经验财富。不过, “青春版”演员们尚显稚嫩的表演当然还不足以承担如此的信任,如白先勇先生所言,他们更多是以青春靓丽的形象气质迎合目标观众 (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审美并吸引他们。“白牡丹”更着意营造的,是以现代舞台技术手段抽取中国古典文化的符号元素(如书画的水墨丹青、古琴的形与意等),形成以当代艺术思考和特质为内核的凝练的古典意境空间,“青春”的表演更多成为这一美学意图的一个有机部分被安放在此空间,一般观众对剧中表演本身的期待也往往并不是第一位的。借助白先勇的文化名人效应,更借助其团队在全球化体制背景中的现代运作, “白牡丹”作为一种具有衍生性的文化“品牌”,其文化推广方面的价值与成功或许是比起艺术本身的价值更大的。不可否认,海内外很多观众,尤其是年轻人,正是以 “白牡丹”为契机,进而成为传统昆曲的拥趸;从被某种舞台环境氛围和整体性的意境所吸引,进而认识到真正优秀成熟的昆曲表演本身所具有的无限性和惊人魅力。
三、本体回归中的“现代性”追求
(一)敬畏·悲悯·反思:返本开新的古今对话
相比舞台美学的营造而言,当代戏曲舞台上的新编剧目在剧本层面更突出地体现和承载了对于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问题的思考。中国戏曲的古典题材有许多震撼人心之处,但是它独特的与漫长中国前现代的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的题材理解和处理方式,与所谓的 “现代”视角着力关注和挖掘的方面不无抵牾。早在18 世纪,中国的元杂剧《赵氏孤儿》经由传教士马若瑟翻译进入法国并在欧洲各国产生广泛影响,伏尔泰的 《中国孤儿》更是这一系列影响中的高潮。自那时起,关于中国戏曲传统与欧洲古典戏剧规范之间种种差异的比较就层出不穷,但这些声音进入中国学者和剧界视野并被关注还是要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陈受颐、范存忠、范希衡等学者先后较集中梳理了这一系列关于 《赵氏孤儿》的中外比较言论,从中可见对于戏剧本质认识的中外差异在18世纪的欧洲已是一大聚焦热点。钱钟书先生在他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吾国古剧中之悲剧》(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里,也含有从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高乃依的戏剧理论 (尤其是悲剧理论)角度来批判中国传统戏曲的基本态度,认为即使像 《窦娥冤》《赵氏孤儿》这样被王国维推崇的可与世界悲剧杰作相颉颃的作品,也因为因果报应的宿命观和求偿心理、道德判准中公义相对私利的绝对优势地位,以及元杂剧结构的设置 (余波不绝、团圆解决、对主唱行当的限制)等,导致本来可以彰显出内心强烈冲突的人物、情节被冲淡,更趋于 “行动”而非 “命运的”、“内心的”,因此影响了戏剧的内在力量。冰心先生在20年代 《中西戏剧之比较》一文也曾以内心冲突和自由意志的强烈来区分“悲剧”与 “惨剧”,论述中国戏剧中 “悲剧”精神的缺乏并表达了热烈期待,相关的认识不仅在近代中国的比较戏剧研究开创期占有主流地位,其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视之为戏曲剧本创作对于现代精神自觉呼唤的先声。当然,这种自我批判的产生有着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和针对对象,也有着时代的限定性,随着时代与思想的变迁,所谓东西方模式之间的套用思维在今天也早已受到广泛而严肃的反思,今天优秀的戏曲创作,尤其是古典历史题材的创作,正是基于种种历史的经验和当下的思考,形成了新的思考和追求,即熔铸反思、批判的思想精神内涵于古典题材和传统表现,但又不因精神思想方面的 “现代性”追求而取代戏曲自身表现的特质,在敬畏、悲悯的文化立场和态度中返本开新,实现有价值的古今对话。
以在当代剧坛受到广泛关注的魏明伦、郭启宏、郑怀兴、王仁杰、张弘等一批优秀戏曲编剧为例,他们的创作体现出一些共同的关注点,例如在他们所关注的题材人物方面,一些具有边缘性的人物和题材被深入细腻挖掘:被以往的叙述压抑或描述为 “淫妇”或旌表为 “节妇”的苦难女性 (如《潘金莲》中的潘金莲、《董生与李氏》中的李氏、《节妇吟》中的颜氏),两难于做人与为君、不幸生在帝王家的 “庸主”与亡国之君 (如 《南唐遗事》中的李煜),“夷夏”交变、江山易代之际身处文人节操、皇权压力与自我功业期许夹缝中的知识分子(如 《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傅山进京》中的傅山),等等。在情与理、爱与欲、权与道、利与节、家与国、公与私之间的分裂和挣扎都在或明或暗中呈现出作者借剧中人与历史、与当下、与观众对话的严肃人文思考和情怀。在历史的真实精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中,也体现出精英高蹈的文化姿态与戏曲中深厚的民间思维意蕴的结合。既体味到广大观众的审美需要,也有对流行观念进行挑战,引领时代思潮和艺术风尚的勇气与担当。
而在对戏曲表现的尊重方面,这些剧作家往往对某一传统或地方的珍贵剧种有长期的专门研究与深入了解,并在长期的浸润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轨迹和风格,因此他们对此剧种语言文字和艺术特质各方面的把握不仅有自信和自如驾驭的基础,并且有广泛的公信力,例如魏明伦之于川剧、郑怀兴之于莆仙戏、王仁杰之于梨园戏等;另一方面在编剧语汇处理上,虽然作品在精神层面流露出鲜明的现代意识和探索,但是语言风格仍然或古雅精致,或有民间自然情味,整体上都具有写意的诗性特质;再者相比较事件的悬念性或行动性冲突,作者更凸显人物身居其中时内心的天人交战,并有能力以戏曲本身所擅长的唱念等抒情叙事形式而不是场面的逼真再现来表达前事,进入内心。这无疑是将作为戏曲核心的演员表演予以放大,尊重珍视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为之留足舞台空间的有意之举。
(二)针对现代戏创演的集中思考
与传统戏曲相映成辉的,是近年来活跃在舞台上的一批现代戏,这些剧目或贴近现实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或是革命历史题材的 “红色经典”。京剧 《江姐》《生活秀》 《飘逸的红纱巾》,秦腔 《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评剧 《宰相胡同》,滑稽戏《顾家姆妈》,河北梆子 《女人九香》,陇剧 《苦乐村官》,琼剧 《下南洋》,豫剧 《铡刀下的红梅》《村官李天成》,花灯戏 《梭罗寨》,粤剧 《刑场上的婚礼》,黄梅戏 《风雨丽人行》等都是近年来较有影响的现代戏。尤其是201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针对现代戏创演的思考和讨论趋向集中、热烈和深入。以现代意识切入现代、现实题材,从中体现出创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体生命和精神的人文关怀,是人们赋予当前现代戏创作最显见的期待,现代戏也因此在戏曲的当代占有重要意义和地位。
从题材内容上,现代戏无疑能够更有力地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改革进程,直面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戏发展的线索,今天的现代戏编演相较以往有了新的关注和共识。不仅仅在塑造英模人物、弘扬时代思想等方面丰富了戏曲文学的语言,其优秀的剧目也并非一种简单的歌颂,而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并触及一些现实矛盾,折射出时代变迁中现代人精神流变的历史。从现代戏题材最为主要的两大方面来看,其当代题材日益关注在大时代巨变中的底层生态与小人物的苦乐,在渺小、卑微中挣扎闪烁出的人性光芒;从革命历史题材剧来看,这一趋向表现为颠覆高大全的人物塑造和过于简单的定性划分,回到历史现场和人物内心来重写活生生的、可信的英雄,重写历史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现代戏的现代性也同样表现为艺术形式和舞台呈现的 “现代”,以及其与内容题材之“现代”的结合和统一。与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目的当代编演,或者说与戏曲当代生存的总体性诉求相一致的是,这种表现形式上所体现的 “现代性”,恰恰应该是在继承戏曲艺术传统、尊重戏曲艺术本质的规定性和民族美学原则基础上,在向戏曲艺术本体的回归中,所展现出的古典戏曲融入时代新质后呈现出的崭新形态。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戏的创作也只有把握对戏曲艺术本体的继承,重视发挥戏曲自身的表现功能和对戏曲化的身段、语汇的运用,运用艺术的、审美的方法,才能进行属于戏曲的真诚、深情的表达。然而,因为题材对表现方式的限定,现代戏正在沦为 “话剧加唱”或者说 “话剧化”表导演的重灾区,重内容而轻形式,或者在形式上缺乏办法,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直接影响到现代戏的艺术品质,进而影响到其观众的认可。在现代戏的领域中更加呼唤以传统为根基的重要性以及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强调艺术形式与美学品格,不仅是基于严峻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因为正是现代戏,承载了戏曲当代发展和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极为深切的一重寄托。
[1]白先勇.《牡丹亭》还魂记 [M]//白先勇.牡丹还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2]张 弘.半 树 枯 槐 吊 君 王 [EB/OL].(2012-06-10)http://blog.sina.com.cn/s/blog _4a7f4b4d01015fz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