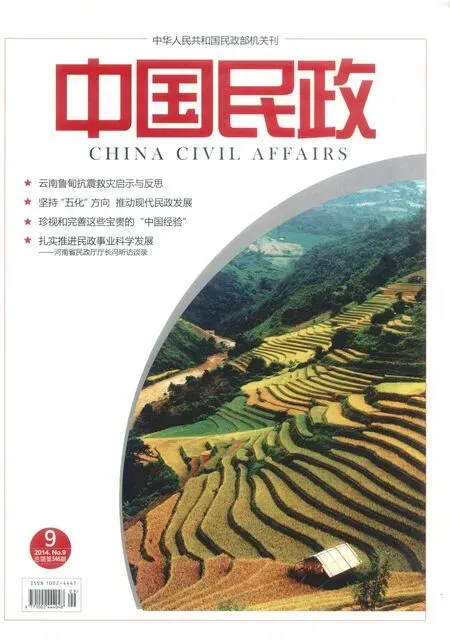甘肃:如何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靳生喜
甘肃:如何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靳生喜
城镇化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四化同步”发展。“四化”之中,城镇化地位特殊、位置关键,而行政区划调整是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要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具备行政区划调整的县可以有序改市。这是关于行政区划管理工作和改革的决策型意见,从其释放的信号来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频率有望进一步加快。民政部门作为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职能部门,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应积极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充分发挥行政区划调整的“杠杆”作用,主动探索行政区划优化设置和合理调整的新路子。近年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甘肃城镇化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优化甘肃的行政区划设置?笔者认为,重点在县改区上找突破、乡改镇上做文章、县改市上下功夫、驻地镇调整上求创新。
一、破冰县改区,确立区县新体制。多年以来,县改区一直在进行着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推进,但各地效果并不理想,特别在甘肃这样一个贫困省份,可以说步履维艰,进展缓慢。目前,全省86个县市区中,市辖区有17个,占19.8%,城市承载能力严重不足,发展空间受限。调研发现,尽管国家在行政区划管理中支持和鼓励对设置一个区的市增设区,使一个中等城市有两个以上区来承载,但各地对县改区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究其原因,一是现行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没有包括区,区财政受制于市上统筹的程度较高,资金使用没有县灵活,各县不愿意放易求难,再找一个管事的“婆婆”;二是改区后,一些人权、事权由市里直管,区里在干部任用、项目安排、资金分配等方面的话语权将弱化和虚化;三是甘肃有58个县属国扶贫困县,在扶贫开发等方面享有国家特殊优惠政策,“含金量”较大。各地担心改市后不能享受优惠政策,不利于争取国家和省级的项目、资金和专项政策扶持。要破解县改区难题,打消种种顾虑,笔者认为,首先,要搞好顶层设计,着眼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国家和省级应制定县改区的统一规划,既设定硬性“杠杠”,又体现软性“指标”,先易后难、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其次,在政策层面为县改区“亮灯”“松绑”,强化区一级的人、财、事权,并适当给予政策创制、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优惠激励,赋予区更大的政治、经济话语权。如此,县改区则会冰消雪化,步入正轨,渐成气候。
二、发力县改市,树立市治新理念。市与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同级不同性。从功能定位来看,县的工作以农村为主,兼顾城市;县级市的工作以城市为主,兼顾农村。甘肃作为一个农业省份,长期以来工作重心放在“三农”问题上,城市建设和管理关注相对不足,县改市一直不被各级重视,目前全省86个县市区中只有合作、敦煌、玉门、临夏4个县级市。随着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县的城市承载能力明显不足,城市规划滞后、管理能力较弱等问题日益凸显,市州所在地单市(区)已无法支撑一个地级市的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区位带动和中心辐射作用被限制。县改市形势所需,势在必行。笔者认为,要推动县改市工作,首先要转变各级过去对县、县级市的模糊认识,树立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现代思维。过去,在传统的农业形态社会,我们讲“郡县治,天下安”,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城乡加速变迁、城市高度扩张的时代,我们应树立“城市治,天下安”的现代治理理念,实现由“县治”到“市治”的转型。其次,要注重研究政策,对县改市的标准和内容进行反复论证,在试点推广的基础上,对符合县改市条件的20个县进行优先排序,率先支持指导积极性较高的陇西、成县、临洮、华亭、秦安、高台6个县启动改市工作,到2020年实现全省县级市和市辖区达到40个、比例达46.5%,达到或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三、提速乡改镇,优化乡镇新布局。甘肃自2002年至2006年期间开展大规模的撤并乡镇工作以来,乡镇区划调整相对趋于稳定,再无较大动作。但随着新型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乡改镇再度升温,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目前,全省1228个乡镇中建制镇有482个,占比为39%,要实现到2015年建制镇占乡镇总数比重接近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目标,乡改镇工作应按照“积极审慎、适度放宽、严格程序、有序推进”的原则加速推进。笔者认为,乡改镇工作,各地认识明确、积极性很高,且具备实践经验,在保证数量的前提下关键要把好质量关,严格按照乡改镇的人口、经济等标准执行,成熟一个、报批一个,乡改镇后真正起到辐射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目的。绝不能违悖乡改镇初衷,以牺牲质量换取数量,使乡改镇“新瓶装旧酒”、轰轰烈烈流于形式。目前,已完成兰州、张掖、陇南3市18个乡的撤乡建镇工作,按照计划年内乡改镇可达40个以上、5年内乡改镇382个、2019年全省建制镇总数达到860个占乡镇总数的70%以上。从当前乡改镇实践效果看,基本起到了优化乡镇布局、辐射带动发展的作用。例如,山丹县陈户乡改镇后,其汉明长城“露天博物馆”的优势显现,文化产业发展前景看好;临泽县鸭暖乡改镇后,其特色产业发展优势明显,“中国枣乡”的品牌日盛。同时,在乡改镇工作中,应注意总结和发现问题,广泛征求当地群众意见,适时修正解决上一轮撤并乡镇引发的遗留问题,做到“科学、合理、群众满意”。
四、调整驻地镇,赋予管理新职能。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设立街道办事处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由于该规定没有包括县,因此,自建国以来,县政府驻地行政管理体制一直实行的是县—镇—村管理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县政府驻地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区规模明显扩大、居住人口显著增长。据庄浪县政府驻地水洛镇党委书记罗彦鹏介绍,现在的水洛镇由2004年前的水洛乡和水洛镇合并而来,总面积已扩大到74.28平方公里,人口达3.4万多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水洛镇的管理服务重点已逐步由农村转变为城市,但因缺乏相应的职能、机构设置和健全的城市基层管理服务体系,无法有效地对城乡实施管理和服务,甚至在城市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与县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撞衫”现象,降低了行政效率,急需进行调整。像庄浪县水洛镇这种情况,在全省乃至全国都较为普遍,是当前县政府驻地镇实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对于解决这一难题,广东、深圳等地早已有成功的实践模式,即撤销县政府驻地镇级行政建制,改设街道办事处。笔者认为,我省对于县政府驻地镇行政管理模式的调整,应坚持试点先行、鼓励创新,即可先选择几个综合条件较好的县政府驻地镇开展改设街道办事处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后全面推广,以期达到“点上开花,面上结果”的成效。同时,借助县政府驻地镇行政管理模式调整,积极探索开展“村改居”社区建设工作,推进“村改居”社区基层治理机制改革,加大对“村改居”社区的公共财政投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村改居”社区延伸。
行政区划调整,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政策性强、政治性高、影响面大,不论是相对成熟的乡改镇工作,还是寻找突破的县改区工作,亦或是需要创新的县政府驻地镇调整等,目的都是服务服从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成熟实践的推进。我们相信,随着行政区划调整“杠杆”作用的不断放大,城镇化水平将日益提升,如何适应城乡一体化、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提升养老服务保障、社会救助、社区治理水平等,民政部门还将迎来新一轮大考。这也是开展行政区划调整的应有之义,是需要我们当下综合考虑的现实而迫切的重大问题。
(作者单位:甘肃省民政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