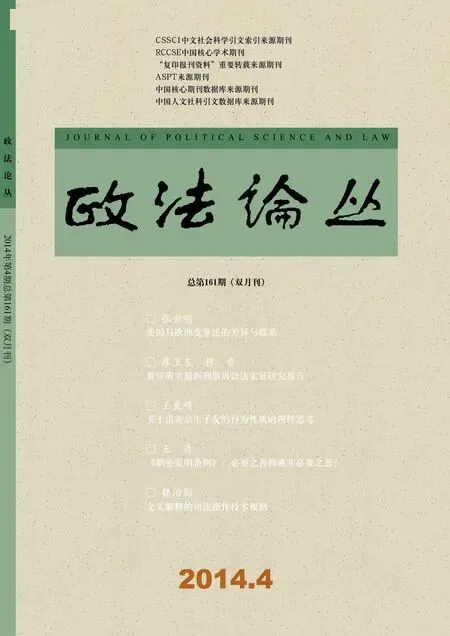自己决定权的确立与保护*
——从武汉数千男生被集体采血验DNA事件切入
李菊明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2013年11月中旬,湖北武汉某校一位女大学生身亡,法医鉴定为他杀。为方便寻找犯罪嫌疑人警方要求附近的武汉大学珞珈学院、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武汉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湖北银河信息技术学院等四所学校的数千名男生抽血验DNA。①而之前(2013年10月下旬)刚刚发生了滨州学院因集体宿舍盗窃案,让5000余名男生被采血验DNA的新闻。两则类似新闻引起社会关注,有学者从刑事诉讼角度批评公安局做法不合法,有学者从公安机关侵犯身体权隐私权角度讨论,②各有道理。笔者认为,从公安机关侵犯个人权利的角度,身体权、隐私权的侵害固然是存在的,但从被迫集体抽血角度,侵害的是当事人对是否参加抽血验DNA的自己决定权。私事的自己决定权作为重要的人格权,在我国宪法、民法上尚未确立,③在学理上对于自己决定权尤其是患者的自己决定权有一定研究,④实践中类似前述案例侵害自己决定权(尤其是公权力侵害自己决定权)的案件屡有发生。本文对自己决定权的起源、内容、正当性、相对性予以探讨,研究公权力为公共利益限制自己决定权的条件以及自己决定权受到侵害时的法律救济,以期对完善相关立法与司法、保护人权有所裨益。
一、基本人权与重要人格权:自己决定权的确立
(一)自己决定权的起源与内容
自己决定权这一法学术语来自日本,而日本则是受美国关于隐私权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启发。1890年美国的两位法学家Samuel D. Warren和Louis D. Brandies将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定义为“不受他人侵扰的权利(right to be let alone)”。[1]后著名的侵权行为法学者William L. Prosser 1960年发表了论隐私 (Privacy)的论文,整理分析实务上案例,将隐私权的侵害分为四类,⑤并为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采纳,构成美国侵权行为隐私权的基本体系。[2]美国宪法对隐私权未做规定,通过判例来创设是个人隐私不受公共权力的侵害而使得其成为宪法保护的人权,是其路径选择。日本学者研究认为,美国的隐私权又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私生活领域,提倡“自己决定权”;二是提倡“个人信息的控制权”。[3]美国关于私生活领域自己决定权的隐私权经典判例有:一是Griswold v. Connecticut(1965)案,⑥当地州立法禁止避孕,Griswold认为侵犯自己的权利,于是上诉,最高法院强调联邦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含蕴有使隐私权不受政府侵害的晕影,正式宣告隐私权系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二是Roe v. Wade(1973)案,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无论是权利法案第九修正案确认的“人民保留的权利”,还是第十四修正案确认的未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个人“自由”,都隐含着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因此,“隐私权的广泛性足以涵盖妇女自行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权利”,[4]P114最高法院确立了对个人私生活秘密保护的确认,判决干预避孕等私域的公权力违宪。[5]后来美最高法院多是以“正当程序”条款和“保护平等”原则作为判决此类案例的理论支撑,据此达到保护公民隐私领域,如同性恋、拒绝治疗的尊严死、堕胎等与他人无涉的自由。[2]且理论界越来越倾向于将个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也囊括在个人私域的保护之内。[5]
日本学者受美国处理隐私权的判例实践的启发,并结合本国宪法理论,在处理相关判例中,建构出一套“自己决定权”的理论。[6]P187日本著名的与自己决定权确立有重大影响的判例是花子输血案。花子是一名虔诚教徒,她信仰“耶和华的证人”教派,拒绝接受他人的血液。医生在为她实施肝脏肿瘤摘除的手术时,违背她明确表示不输血的意愿给她输血。花子手术后知道自己被输血,精神受到打击,非常失落难受,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一审认为,医生迫于拯救病人的职业需要而为的行为是正当的。花子不服上诉,二审认为,医生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使得花子对于是否输血的自己决定的权利受到侵害,构成侵权。医生不服判决,上诉。终审(即最高法院)认为,病人明确表示输血违反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自主意思的权利(即自己决定)作为人格权的内容之一,应该得到尊重。本案医生应对患者说明输血在医疗过程中的必要性,但是否同意、是否接受手术方案关乎患者的自己决定的权利。被告未行使说明的义务剥夺了花子决定是否接受有输血可能性手术的权利,侵害花子的人格权,因此,应该承担给花子造成精神痛苦的责任。此案首次指出患者自己决定权属人格权内容之一,在促进人格权之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7]如今,日本医学临床、司法实践中已经广泛运用该原理,这对减少医疗纠纷、协调医患关系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关于自己决定权的概念,有日本学者认为,是“自己有决定与他人无关的事情”的权利,[8]P3简言之,就是自己的事情由自己决定。我国有学者认为,自己决定权是意志以发展、控制、塑造人格的抽象人格权。[9]还有学者认为,自己决定可以作为人格自由的内容,以弥补具体人格权规定的不足。[10]P167总之,自己决定权与人格联系密切,是对私事自己决定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它强调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是一项基本人权。
虽然自己决定权来源于美国关于隐私权的学说,但自己决定权与隐私权是有极大区别的。如果把隐私权作为掌握自己信息的权利来理解,那么此外的那些可被认为是私生活上自由的东西,可视为自己决定权的内容。例如自己决定留什么发型、穿什么服装,自己决定是否生育子女、是否避孕、怀孕后是否堕胎、生育后是否采取避孕措施等,自己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医疗、是否采取安乐死、尊严死等,这些均为处分与个人外观、兴趣、好恶等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权利。[11]P394人格要素的保护是与社会进步相关联的,其发展程度受限于科技、物质、理论等,如隐私权的发展从无到有、再到完善一样。随着客观条件限制的减少,人格越来越受重视,自己决定的权利保护越来越周延,其“内容会越来越丰富 ”。[9]
(二)确立自己决定权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人格的表述在早期罗马法中就有表述,而近代哲学的发展,使得人的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得以提倡。康德非常崇尚人格之内的尊严,他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利仅把他人作为实现主观目的的工具。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为目的本身。法律可以运用强制力量来对付那些不适当、不必要干涉他人自由的人。理性的自我决定能力亦即自由,自由意识是近代伦理及近代法的根本要素。自己决定权的确立,主要是基于对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等价值的尊重,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人格利益。自己决定权是一种基本人权,关于人权概念的定义,有观念说、生存条件说、人性说等。[12]P1-2人性说对于自己决定权的确立更为妥当,人性说是以自由为前提,即认为人权是指人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在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度。保护人权源自尊重人的尊严性,即人权是作为构成社会自律性质的个人,为确保自由和生存,维护其尊严性,因而作为前提得到承认,人为此当然固有的一定必要权利。[13]P71在日本,自己决定权是为构成宪法上“幸福追求权”的一部分,幸福追求权与“个人之尊重”原理结合,以个人的人格价值本身为重要的保护法益。[14]P100
经过宪法学学者研究认为,自己决定权主要凸显自主、自决,强调个人的自由,并认为其为一项基本人权。[5]自由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是指与人身和财产相关的公民依法自主决定个人精神和行为空间的权利,而保护自由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共识。[12]P35《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3条又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均在第1条规定了所有人民的自决权,得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得为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其所拥有的天然财富和资源。
就公民自由权的形式而言,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可以分为五类:一是政治自由或意志表达自由,二是人身自由,三是宗教信仰自由,四是文化活动自由,五是婚姻自由。我国宪法中还没有自己决定权、自主权的表述,而在我国确立自己决定权更为必要。中国的社会结构,内部秩序的主要支柱是整体性的权威主义,因此,应从全部结构体系上来把握此种权威主义,以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结构。[15]P8而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 没有个人权利这种东西。而没有个人权利,实际上就等于一般地没有权利。正如无私权的个体不能算为 “个人”,没有“个人”的权利同样是不可想象的。[16]P231我国古代由于权威主义影响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人格的保护是不足的,更谈不上人本主义精神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想残留,人格权和人格尊严没有得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以致在文革期间,出现“架飞机”、“剃阴阳头”、擅自抄家、揪斗等严重侵害个人人格权、践踏人格尊严的现象,使亿万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灾难。[10]P30而现在,我国人权保障仍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公权力的侵害尤为严重,诸如暴力拆迁、上访“被精神病”“被劳教”、重庆“黑打”等现象,都突显私权遭遇公权侵害的现状。世界越文明,世人越知国家最主要目的是保护人民自由,国家应保护人民自由,即应以宪法规定一切人民基本权利。凡人们自由权利,是国家所不应侵犯、必须禁止侵犯的。[17]P904自己决定权作为人权和宪法权利,国家有义务通过立法确认、保护该权利。
同时,自己决定权是自然人对于生命、身体、健康、姓名等具体人格要素享有的控制与塑造的抽象人格权,作为重要的人格权,也是民法上的权利,笔者赞同学者提出的在制定我国人格权法时明确规定自己决定权的建议。[3]自己决定权应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例如在医疗领域,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医疗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自主原则(principle of autonomy)。英文中“自主”(autonomy)一词是由希腊文autos(自身)和nomos(控制法则)组成,是指人们对自身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既不受其他人的影响,也不受个人条件(如个人不能充分理解等)的限制。在医患关系中违背患者自己决定的意愿实施的医疗行为,从后果上看可能是对患者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但因侵害了患者自己决定权的人格权利,也应构成侵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作为患者自己决定权主要内容的患者知情同意权已做出规定,如1999年我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但患者的同意权仅规定为对实验性临床医疗的同意,将普通检查与治疗排除在外。国务院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患者知情权、同意权的范围有所扩大,但关于同意权的规定,同样仅限于手术和特殊检查,对于普通的检查与治疗是否应经患者同意,没有明确规定。2009年我国《侵权责任法》设专章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第一次在民事立法中明确规定患者知情同意权。其中规定了患者知情权的范围,完善了知情同意权代为行使、不能获得患方同意时医疗处置的情形,对侵犯知情同意权的法律责任予以明确规定。但还是存在着患者同意权范围过窄、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例外情形规定不够完善等缺憾。当然,侵权责任法未对医疗领域之外的自己决定权予以保护,这也是滞后于社会发展要求的。在没有明确规定自己决定权为独立人格权前,在侵权领域可通过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把自己决定权作为一般人格权来保护,从长远看,在民法典人格权编明确规定自己决定权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公共利益:自己决定权的相对性
和其他权利一样,自己决定权也具有相对性。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由此言之,权利不是绝对的,宪法上对个人权利的行使有其限制,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权利行使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正是密尔所言的经典自由理论,人人都有自主行事的自由,“只要其行为不对他人的自由造成限制”。基于这个理念,当个人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 即影响了别人享受自由的权利) 时,政府应该插手监管;当个人行为的后果仅仅作用于自身时,政府应该保持缄默放任。二是为了公共利益可以限制个人权利。为什么公共利益可以限制个人权利?主要是个人所处的社会的需要,按照孟德斯鸠的论述,社会的形成是一种契约,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是由个人权利的集合,而这些权利是由于公民个人自愿让渡的。既然这些自愿放弃的权利组成了公共利益,公民个人权利是受其制约的。[18]P20自己决定权的界限即是公共利益。
什么是公共利益?理论上有人数说、地域说、圈子说等等,不同学者意见不一,各有道理。公共利益是针对某一共同体内的少数人而言的,共同体的规模小到某一个集体,大到国家、社会。其实,公共利益的关键在于谁来主张公共利益。在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主张者就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公益组织等组织机构。但新的问题是,主张者作为共同体中大多数人的代表,其对公共利益的认识是否可能与大多数人的认识一致。德国学者将公共利益分为主观公益和客观公益两类,主观公益是基于文化关系之下不确定之多数所涉及的利益。客观公益是基于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重要目的,藉着国家机关、地方自治团体,以合乎目的性考虑即可达成公益之需求。[19]P185例如和平社会秩序的维护、人权的保护、文化教育经济环境的条件和促进等。正是由于存在谁来主张公共利益以及主张者认识不保险性的问题,由法律来确认客观的公共利益成为现代社会的解决办法,通过法律将一些普遍性的公共利益确定下来,作为对主张者的诫条。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的程序性(即民主的立法过程)保证了公共利益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的明确性,使得公共利益主张者得以藉此来积极地主张公益,以促进公益的实现。因此,现在所谓的公共利益,往往就是指实定法上的公共利益。[20]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Jacobson v.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⑧被视为美国公共健康法的里程碑,迄今仍是平衡公共利益与自己决定权冲突的典范。该案中,马萨诸塞州(作为一个当时美国主要的海港和移民登陆地)政府为预防天花制定法律,授权地方政府“当公众健康和安全需要时”可以进行预防接种牛痘,当地剑桥市政府即通过了“居民进行疫苗接种,凡是不接受接种的人必须缴纳5美元的罚金”的地方法规。本案原告认为强制接种侵害了其受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个人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中论述了个人自由的相对性:“联邦宪法赋予的自由,并没有对个人授予绝对权利。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个人都没有不受限制和享有完全自由的绝对权利。宪法规定了多种限制,个人在公共利益面前必须服从这些限制。否则很难形成和谐社会,更不用说保护社会成员的安全。”判决中同时论证了公权力制约个人自由权利的诸多条件,最后认定被告强制接种的行为并不违宪。法院在本案中对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关于“保护个人自由”的解释,为现代美国审理涉及公共健康与个人权利的案件铺平了道路,不仅为强制疫苗接种法提供了宪法上的法律支持,还为其后许多有关公共健康的法律提供了支持,例如要求人们在汽车内使用安全带、要求摩托车驾驶者使用头盔的法律,[21]P441973年美国法院对娼妓必须接受性病治疗的支持判决和1988年对于监狱强制接种白喉破伤风疫苗行为的正当性支持都说明了公共健康利益限制自己决定权的情形。
为公共健康利益限制自己决定权已成为公认的法理,日本对于传染病防治的法律规定对于接种的强制性规定需以“加强公众卫生”为目的。[22]P256除了传染病的强制医疗外,有时在一些特殊场合,如军事、侦查、管理等领域。美国法院通过判决确定在取得证据可被采纳和有义务施行限制公民个人权利的强制措施是有必要的。而在1979年一个判决中对于监狱犯人拒绝透析的犯人权利的不支持体现了为了监狱管理的利益可以限制个人拒绝治疗的权利。[23]我国相关法律也规定了强制医疗制度。我国《刑法》、《人民警察法》有相关散落条文规定,《传染病防治法》更是详细具体规定了强制医疗的对象、实施措施等。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1条规定,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对被依法逮捕、拘留和在监狱中执行刑罚以及被依法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和劳动教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防止艾滋病传播。同样,我国《强制戒毒办法》对戒毒做了强制规定。
三、法律保留原则与多维度救济:自己决定权的保护
(一)公权力限制自己决定权的条件
为了公共利益,公权力在法定条件下得限制自己决定权。在前述美国雅各布森的判决意见中,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政府为公共健康目的行使公权力限制个人决定权的有效条件是:第一,公共健康行动应有必要性,即为了公共健康或公共安全,不能通过任意的、不合理的方式来执行。第二,公共健康行动应具有非伤害性。如案例中的强制接种疫苗,如果有医生证明儿童或成人如不适合接种(接种后会导致人身伤亡)则可不必接受强制接种。第三,公共健康行动应具有适度性,法院有必要采取合理的手段来防止出现不公正、压迫性或荒谬的后果。⑨这几点对于评估平衡公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很有借鉴价值。
笔者认为当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公权力需要对自己决定权限制时,需满足以下条件:(1)法律保留原则,即限制自己决定权,需法律明确授权。毕竟,人人生来皆有自由平等之权利,而在国家中,公权力掌握大量的暴力机器和资源, 人权在公权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对公民人权之限制,需法律之授权,这也是公法中“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法理所在。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也有明确规定。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尊重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身体不受非法搜查”,“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权的规定。(2)符合法律程序。美国宪法上有“正当程序”条款,英国法上也有“自然正义法则”,德国基本法上有正当程序权,台湾地区宪法上第8条也明定“宪法上正当程序”。强调、注重程序正义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因为程序的价值有利于纠错,且益于防止权力滥用。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自由平等之观念更受重视,人们对侵犯自己人权的容忍度降低,再加上社会分工趋于复杂化,各种人权组织增多,为公共利益对自己决定权的限制更需符合法律程序。
在本文所涉数千男生被集体采血验DNA事件中,公安机关所依据的是我国《刑事刑诉法》第130条“侦查阶段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强制检查”之规定。本事件中,公安机关是把被采血的数千师生当作犯罪嫌疑人,并行使对其行使检查的权利。本事件中公安机关将被采血的数千师生都当作犯罪嫌疑人是不合法的。嫌疑对象与犯罪嫌疑人是有区别的,显然,本事件中,公安机关并没有对二者进行区别。公安机关正常的侦查过程是接到举报、控告后,第一步是进行现场的调查,认定事实,收集证据。对犯罪分子进行第一次的判断,显然这是大体的、模糊的判断,主要是确定侦查方向,将犯罪分子可能具备的条件列出来,以减少盲目的排查。而认定犯罪分子应该具备的条件后,再进行排查,找出符合条件的人选,这就是犯罪嫌疑人。往往在实践中,排查出的嫌疑人有多个,甚至数十个。但他们都有一共同点都与本案件有或多或少的、直接间接的联系,通俗来说他们有极大可能、并有合理依据确定其涉嫌犯罪。所以不能把所有嫌疑对象当成犯罪嫌疑人,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如火车上发生犯罪事件,把火车上所有人都当成犯罪嫌疑人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先要确定对嫌疑对象进行调查时的标准,然后依照这个标准所筛查出来的人员才是犯罪嫌疑人。[24]本事件中,公安机关没有在确定的侦查方向和范围内摸底排查,而把所有这些嫌疑对象都当成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把初查时的嫌疑对象当作犯罪嫌疑人进行强制检查,这是不符合法律授权的实质要件的。
退一步说,即使公安机关符合条件之一,公安机关的做法也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公安机关完全忽视了当事人的受告知权(也称当事人的知情权)。“受告知权”即行政程序当事人与利益关系人,有及时获悉与其利害攸关的事实及决定的权利。本案涉及身体检查,世界各国对身体检查是极其慎重,法律程序是及其严格的。根据侵害公民个人权利的程度来说,身体检查分为一般的与重大的。重大的就是对个人权利严重侵害的检查。此种区分意义在于适用条件与适用程序是不同的,如重大的身体检查相当于强制措施,德国就把抽验血液、脑波检测当成强制措施,在重视个人权利保护与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重大的身体检查是慎重的,不仅条件严格、程序正当,还要求其对于公民个人权利侵害限于必要且最低。而一般身体检查对于个人权利的干预较轻,适用较为轻松。[25]在美国,无论是一般的还是重大的身体检查都必须有法官签发的令状。在极少数情况下,只有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进行检查: (1)使用方法合理,不能不人道,需重视尊重人的尊严;(2)应必要即具备充足的、正当的、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证据;(3)情况需急迫(来不及走正当程序申请令状),不能等待,对案件影响巨大。⑩同时,美最高法院在判例中确定,要以取得对方同意为原则,确实需要强制时,需采取侵害性小的方法,以期达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平衡。[26]在英国,是通过另一种路径选择来限制身体检查。相关法律规定,经警长或级别以上的官员的授权,警察可以使用“合理的武力”收集隐私样本。这与德国的进行“收集指纹、身体测量”等非侵人性检查时可以不经法官的批准的规定有“异曲同工”之妙。[25]而在本事件中,公安机关对几所大学的师生进行采血这个重大的身体检查,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条件,也没有遵循一定法定程序,未告知被采血人。被采血人是在采完血后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这是对被采血师生自己决定权的侵犯。
(二)公权力侵害自己决定权的救济
自己决定权是基本人权,是宪法上的权利,也是民法上的人格权的内容,公权力侵害自己决定权的救济方式可从以下四个角度考虑:
1.违宪审查与宪法诉讼
针对国家公权力对基本人权的侵犯,普通法系的英美国家是通过违宪审查的方式进行,这与德国宪法法院审查方式不同,英美是只要个人权利受到公共权力的侵害,普通法院就可以进行,也可以称美国违宪审查是“私权保障”型,更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其具体过程是,当公民发生具体案件诉讼时,普通法院审理时可以附带的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这是与大陆法系提供宪法救济方式是不同的,宪法法院既可以针对具体案件审查又可以直接针对法律进行抽象审查,这也说明大陆法国家不光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更强调对于宪法秩序的尊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民个人是可以提起宪法诉讼的,这与英美法系相同,但与接近大陆法系的我国只能通过国家机关审查是不同的。即公民在发生具体案件时可以提起,公民个人不可以自己提起对政府行为或法律进行原则性、抽象的审查。[25]我国现行《宪法》关于违宪审查的主体的规定是不完善的,同时在具体部门法的规定上没有违宪审查的诉讼制度,法官也不能以宪法作为判案的依据,[27]因此,在我国自己决定权受到侵害是不能利用宪法提出请求权的。
在我国,宪法诉讼已成为法治建设中不可避讳的隐伤,其中原因很复杂,有生产力水平欠发达的原因,有政治体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权利文化氛围的原因。而对于法治实践层面的原因,有学者分析:首先,宪法诉讼缺失可存在性根基。中国宪法自立法之后便被束之高阁,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6年的两个批复,更使得宪法不具有可适用性。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既不能直接引用宪法审查、判断法律法规的合宪与否,也不能受理当事人依宪法提出的权利主张。其次,违宪审查权力主体模糊不清,宪法监督机制不合理。依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实施,但此二者并非我国违宪审查权的唯一享有主体,根据宪法有关条款及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国务院、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及地方政府亦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违宪审查权。而后者都没有宪法解释权,该权力只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宪法解释权就无法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事实上,我国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并不负责法律的适用与执行,其自身不可能主动发现及裁决违宪案件。[28]
2.行政诉讼
政府守法是实现法制的首要的关键问题,在现代社会,诉讼因为其公正性与中立性,自始就肩负监督政府权力运行、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维持公权力与私权利平衡的使命。而在中国的诉讼体制框架内,能够承担此职责的唯有行政诉讼。如前文所言,对于行政权力侵害自己决定权,在我国不能提起宪法诉讼,只能转向行政诉讼。很多国家都是以行政诉讼作为宪政诉讼的突破口,我国行政诉讼亦可称为中国宪政的试金石。但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仅有权对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被告仅限于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实践中存在的诸多行政侵权行为就被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因此笔者赞同有学者提出的观点,除具体行政行为外,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还应扩展到抽象行为诉讼、内部行为诉讼、准政府行为诉讼、事实行为诉讼、准行政行为诉讼五类,[28]以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行政权力侵害自己决定权场合,除具体行政行为可能侵权外,在另五类行为中都有可能存在侵犯自己决定权的情形,因此,在无法请求宪法救济诉讼的背景下,应扩大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允许公民就上述多种公权力行使中的侵权情形提起行政诉讼。
3.请求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力
对于行政权力的侵权可提起行政诉讼,而类似本文案例中是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时侵害公民自己决定权,对于侦查权侵权的防范,我国可以借鉴他国经验。在俄罗斯,侦查搜查活动由来已久,有其悠久历史渊源。而检察长对侦查搜查活动中执行法律的情况实施监督,以符合社会的需要,以有效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于1996年8月9日签署的《关于组织对联邦法律侦查活动法执行情况监督第48号命令》中有所反映,检察机关主要监督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侦察活动中实施机关是否恪守个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第二,是否遵守实施侦查措施的法律和进行侦查的法定程序;第三,侦查搜查活动中实施机关所做决定之合法性。显然这种制度是有明显的作用的,有利于对规定侦查搜查法律法规的漏洞、瑕疵予以检查与完善,还有利于完成检察任务。最重要的是有利于公民权利之保护。我国完全可以借鉴此种制度,尽管我国检察机关有权力监督法院、公安机关的行为,但这种监督在全面性和有效性方面尚待提高。在被集体采血事件中,对于公安机关强制采血的非法行为,受害人可向检察院提起请求,检察院应发挥监督作用,有效制止公安机关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合理的侵害。
4.民法上的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
自己决定权是民法上人格权的内容之一,即使现在法律尚未明确规定自己决定权,对于自己决定权的救济,仍可按人格权的保护主张民法上的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9]自己决定权所具有的人格权请求权包括排除妨害请求权和停止侵害请求权。除妨害请求权和停止侵害请求权产生于人格权遭受侵害的场合,但也可产生于物权等权利遭受侵害的场合,故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请求权非人格权所专属。不过,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的请求权落实的结果,的确能使受害人格权恢复原状,人格权若想保持原状,缺少不了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请求权的运用。因此,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请求权属于人格权的有机构成因素,与人格权不可分离。人格权遭受侵害的场合,人格权自身受到创伤,人格权人也受有精神损害。救济方式的运用,有时只能平复权利人的精神损害,不能使人格权本身恢复原状;有时可以使人格权、人格权人两方面都得到同时回复;有时分别针对人格权和人格权人,各自发挥特定的功能。在自己决定权受到侵害的场合,为方便和经济,依据请求权基础理论,受害人宜考虑首先选择排除妨害请求权和停止侵害请求权,使自己决定权自身得以恢复。如果实现这些请求权后,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得到平复,就不必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若其精神创伤未得到平复,则可继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至于侵权请求权,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了国家机关侵权责任,规定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害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4条也规定了用人者的责任,规定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用人单位,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这些法律规定都表明当国家机关的公权力侵害自己决定权时,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国家机关承担侵权责任。在自己决定权受到侵害的场合,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体现为精神损害赔偿。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了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虽然在其列举的人格权种类中并未明确列举自己决定权,但规定了兜底性的“其他人格利益”受到侵害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因此依我国现行法律,自己决定权受到公权力侵害时,受害人可主张国家机关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至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的确定,可依据自己决定权受到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情节、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
综上所述,自己决定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应被确立为宪法权利;作为民法上的重要人格权,在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确立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国家公权力为了公共利益,在法律明确授权、符合法定程序的前提下,可以对自己决定权有所制约,但在我国当前法治环境下,公权力的合法有效运行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正如丹宁勋爵所说:“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而成的……社会需要采取手段惩治犯罪分子,而这种运用得当的权力才能保卫自由。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假如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会甘拜下风。”[29]P117-118让我们期待类似本文所讨论的公权力侵害自己决定权的案例会越来越少,如不幸发生,更期待受害人能得到宪法、行政法及民法上等多维度的救济。
注释:
① 参见南方周末编辑部:《命案必破》,载《南方周末》第32版,2013年11月28日。另见杨京、戴维:《女大学生返校时遇害 数千男性师生配合验DNA》,载《武汉晚报》2013年11月20日。
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显东认为,公安机关至少须告知被采样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认为,侵犯人格权中的身体权还可能侵犯隐私权,任何人都可以拒绝采集。参见郭丝露:《被忽视的身体权和隐私权:宿舍失窃,全校男生验DNA》,载《南方周末》2013年10月10日。
③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患者自己决定权的重要体现。
④ 参见杨立新、刘召成:《论作为抽象人格权的自我决定权》,《学海》2010年第5期;夏芸:《患者自己决定权和医师裁量权的冲突——评“病人基于宗教信仰拒绝接受输血案”》,《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春季号;段匡、何湘渝:《医师的告知义务和患者的承诺》,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李燕:《患者自己决定权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7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
⑤ 涉及四种不同的利益,构成四个侵权行为。即:A.侵害他人的幽居独处或私人事务(侵犯隐密: Intrusion upon the plaintiffs' seclusionor solitude or into his private affair):例如:侵入住宅、窃听电话、偷阅信件等。B.公开揭露使人困扰的私人事实(公开揭露: public disclosure of embarrassing privatefacts about the plaintiff):例如公开传述他人婚外情或不名誉疾病。C.公开揭露致使他人遭受公众误解(扭曲形象: publicitywhich places the plaintiff infalse light)。D.为自己利益而使用他人的姓名或特征(无权在商业上使用他人姓名或肖像, appro-priation, for the defendants' advantage, of the plaintiffs' name or likeness)。前揭四种侵害隐私的侵权行为(torts)各有其要件,其所共通则的,系不受干扰的独处。
⑥ 381 U.S. 479 (1965).
⑦ 410 U.S. 113 (1973).
⑧ 197 U.S. 11 (1905)[0].
⑨ Jacobson v.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197 U.S. 11 (1905)[0].
⑩ U. S V. Lafayette, 462 U. S. 640(1983).
参考文献:
[1] Warren, Brandies. Right to privacy[J]. Harvard Review, 1890,(4).
[2] 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上)[J].比较法研究,2008,6.
[3] 刘士国. 患者隐私权:自己决定权与个人信息控制权[J]. 社会科学,2011,6.
[4] 焦洪昌,李树忠.宪法教学案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 [日]松井茂记.论自己决定权[J].莫纪宏译.于敏校.外国法译评,1996,3.
[6] [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M].[日]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 夏芸.患者自己决定权和医师裁量权的冲突——评“病人基于宗教信仰拒绝接受输血案”[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3,19.
[8] [日]山田卓生.私事与自己决定[M].日本评论社,1987.
[9] 杨立新,刘召成.论作为抽象人格权的自我决定权[J].学海,2010,5.
[10] 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1] [日]芦部信喜.宪法学l——人权总论[M].有斐阁,1994.
[12] 林喆.公民基本人权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 [日] 芦部信喜.宪法(第三版)[M].高桥和之增订,林来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 [日]阿部照哉等.宪法(下册,基本人权篇)[M].许志雄教授增订,周宗宪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15] [日]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M].牟发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6]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7] 何孝骥.法国人权宣言之研究[A]. 何勤华,李季清.民国法学论文精粹(第二卷,宪政法律篇)[C].法律出版社,2002.
[18] [法]孟德斯鸠.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9]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 (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20] 胡棉光,王楷.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J].中国法学,2005,1.
[21] 汪建荣等.用法律保护公众健康[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22] [日]植木哲医疗法律学[M].冷罗生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3] 李燕.未经同意的治疗:知情同意权的相对性 [J].法学论坛,2011,5.
[24] 刘梅湘.犯罪嫌疑人的确认[J].法学研究,2003,2.
[25] 瓮怡洁.我国刑事身体检查制度之反思与重塑[J].公安学刊,2004,3.
[26] 陈光中,陈学权.强制采样与人权保障之冲突与平衡[J].现代法学,2005,5.
[27] 胡锦光.论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原则[J].法商研究,2003,5.
[28] 胡肖华.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之治[J].中国法学,2007,1.
[29] [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