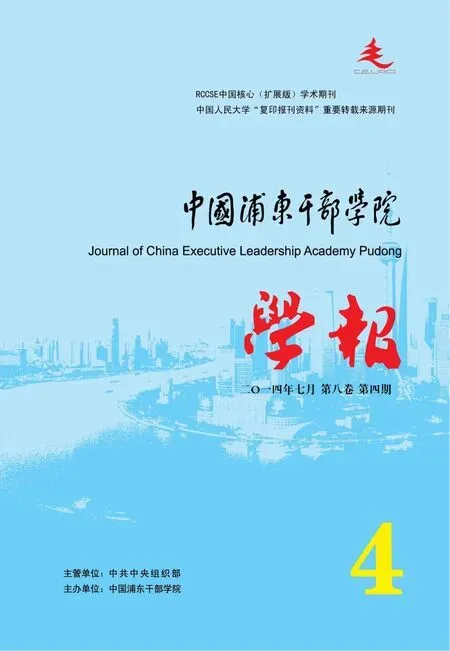建设西南次区域经济走廊的地缘战略思考
王志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北京100029)
建设西南次区域经济走廊的地缘战略思考
王志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北京100029)
西南周边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及其走势蕴涵着对外开放模式的创新。建设西南次区域国际经济走廊,实行东西双向开放战略,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先行一步,有条不紊地致力于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并赋予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新内涵,打通西南国际大通道,进而拓展自身地缘经济政治空间,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抉择。
地缘经济政治;次区域;西南周边;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
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对外开放就曾经历了从东南沿海到内陆地区,再到西部周边梯次展开的三个地缘层次。如今,中国正在调整自身地缘经济政治战略,为平衡美国“重返亚太”的所谓“再平衡”,应对东海和南海岛礁争端,“向西开放”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既定战略,同时构建出东西双向开放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已与西南周边国家达成共识,进行“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背景下的经济走廊建设。本文试图以西南周边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及发展态势为视角,探讨西南次区域经济走廊的对外开放模式创新。
一、经济走廊战略设计:对外开放模式的新突破
次区域经济走廊,是以地缘上相邻国家的部分地区为依托,以铁路、公路、航空、航运线为纽带,建立以交通沿线为辐射的优势产业群、城镇体系、口岸体系以及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分工、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走廊。[1]西南周边次区域国际经济走廊概念,最早提出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8年9月30日至10月2日,第十届大湄公河次区域部长级会议提出“三纵两横”经济走廊概念。①“三纵两横”,其中“三纵”为云南昆明——云南大理——云南德宏——缅甸曼德勒——缅甸仰光;云南昆明——云南西双版纳——老挝——泰国曼谷;云南昆明——云南红河——越南河内——越南海防。“两横”为缅甸毛淡棉——泰国彭世洛——老挝沙湾拿吉——越南岘港;缅甸仰光——泰国曼谷——柬埔寨金边——越南胡志明市。1999年,中印缅孟四方在我国云南昆明举行第一次经济合作论坛,首次提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这一概念,得到印缅孟等国有关方面的响应。如今,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流域经济走廊建设已经成为中国西南周边对外开放的战略抉择。
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将是当今世界上容纳人口最多的次区域经济走廊,对次区域经济合作有着示范和引领作用。2013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期间正式提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得到印度、孟加拉国、缅甸三国政府的积极响应。中印两国共同倡议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目的在于连接中国和印度两大新兴市场,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扩大双向投资,启动两国区域贸易安排谈判,开展在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各领域的大项目合作。2013年5月20日,中印两国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对孟中印缅地区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进展表示赞赏,将研究加强该地区互联互通,促进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并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2]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随即成立,并于2013年12月18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四方联合工作组会议。云南省省长李纪恒、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穆哈迈德·阿兹祖尔·哈克、孟加拉国驻昆总领事沙哈纳兹·噶兹、印度外交部东亚司司长班浩然、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高志远、缅甸国家计划和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杜钦桑伊出席会议。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涵盖我国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等省、市、自治区,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等东北部各邦,孟加拉国、缅甸两国的大部分地区,总覆盖面积约165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达4.4亿。自1999年召开第一次中印缅孟四方经济合作论坛,至今已经轮流举办了11届,已初步形成由智库主导、政府和商界参与的制度化的交流平台。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对建立中巴经济走廊意愿更为强烈,地缘经济政治意义更为深远。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提出,加强战略和长远规划,开拓互联互通、海洋等新领域合作,并着手制定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稳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2013年7月,上任不久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访问中国。谢里夫总理访问期间就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行实质性商讨,两国决定成立联合合作委员会,制定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和短期行动计划,重点实施交通基础设施和沿线经济开发区等支点项目建设,积极拓展能源合作。根据巴基斯坦2013-2014财年预算草案,巴政府将投入725.88亿卢比资金,将用于现有的35个项目以及将启动的新项目,包括喀喇昆仑公路的改线工程。高速公路建设将对发展相关工业、储油设施以及油气管道产生积极影响,巴政府希望以此拓展和建设与中国、中亚国家、印度、伊朗以及西方国家的贸易新领域和新枢纽。[3]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境内起点是南疆铁路的起点喀什,经红其拉甫进入巴基斯坦的苏斯特-洪扎-吉尔吉特-白沙瓦-伊斯兰堡-卡拉奇-瓜达尔港全长4625公里的交通大动脉,不仅涵盖“通道”的建设和贯通,而且在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开展重大项目、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水利、信息通讯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创立更多工业园区和自贸区。
大湄公河(中国境内称澜沧江)流经中国、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等6个国家,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涉及地区总面积(中国部分为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为256.86万平方公里,人口3.2亿,又称“陆上东盟”,其合作机制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1994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前期研究协调组”。2012年,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5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318亿美元。截至2012年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共筹集超过150亿美元资金投入次区域交通、能源、信息通信、农业、环境、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等重点领域的合作项目。第十届大湄公河次区域部长级会议提出“三纵两横”经济走廊设想,其中“三纵”均以中国云南省昆明为开端。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与投资、私营部门参与、人力资源开发、环境保护5大战略重点,开展了包括交通、能源、电信、环境、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旅游、贸易与投资、禁毒、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果。广西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实际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延伸,直至马来西亚、新加坡,以泛亚铁路为基础。
建设西南次区域经济走廊,是依托中国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在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模式的创新。西南次区域经济走廊的建成,既能实现中国向西开放与印度东向战略的对接,为世界上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奠定基础,同时加深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地缘经济政治合作。建设西南次区域经济走廊,不仅推动我国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又将刺激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最不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从而提升其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达到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和政治整合的双重目的。就地缘经济而言,西南国际经济走廊只涉及相关国家的局部地区及经济领域,不牵扯国家核心利益,对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具有试验性质和窗口作用,会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就地缘政治而言,西南次区域国际经济走廊不仅能促进我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国家相关地区的经济崛起和社会发展,还有利于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由此形成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相关国家在地缘经济政治上的相互依托发展之势,有利于相关国家建立政治互信,促进安全领域的合作。
二、西南周边地缘态势:经济走廊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区域经济合作呈强劲发展势头,成为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不确定性的基本策略。而中国所在的亚洲地区却在区域经济合作大潮中不仅落后于欧洲和北美,甚至落后于非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涉及经济问题,“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中国西南周边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复杂,但拓展余地广阔,区域一体化潜力巨大,机遇与挑战并存,推力与阻力同在。
(一)中印地缘政治复杂敏感,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任重道远
中印两国双边关系敏感而复杂,缅、孟两国甚至包括南亚其他国家均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中印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印两国的地缘经济政治战略决定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成功。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历史境遇,都抱有实现大国崛起的梦想。无论中国还是印度的战略家,都认为中印存在共同利益(如在气候变化谈判和经贸规则等方面),中印还在2013年签署“中印边防合作协议”,边界矛盾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中印恶性竞争无疑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带来风险。[4](P238)中国有发达的制造业,印度则以服务业见长,两国经济互补很强。2011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为739.2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计划在2015年实现贸易额1000亿美元的目标。印度是世界铁矿石的主要提供商,已成为中国第三大铁矿砂来源国。金砖国家正在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为中印合作提供制度化平台。
然而,印度社会对中国一直存在瑜亮情结,至今对1962年中印战争心存芥蒂。如今,中印仍存在着边界纠纷、水资源争端等问题,直接导致政治互信不足,偶尔还出现军事对峙,特别是印度对中巴合作抱有戒心。印度东北部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必经之地,却是印度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这直接制约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建设。该地区的人均GDP为2.1万卢比(约合2900元人民币),仅为印度人均GDP的一半。该地区分布着200多个民族,加之贫穷落后等原因,致使民族与种族冲突频频发生,20年来,已有1.4万多人为此丧生。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是中印两国如何解决藏南问题。藏南地区(印称“阿鲁纳恰尔邦”)属于中国领土,现由印度实际控制,被印度媒体称为“禁止中国进入的地区”。[5]因而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建设任重道远,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是连接亚洲各次区域的重要枢纽,入有中、印、缅广袤腹地,出有加尔各答、吉大港、仰光等著名港口,有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明显区位优势。[6]印共(马)曾多次在印度东北部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执政,为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奠定了良好社会基础。印度学者约书亚·托马斯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发达,缅甸有丰富的资源,印度的服务业和医疗业上有优势,孟加拉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中印孟缅经济走廊可以充分发挥各国的优势,同时将印度东北这一‘闭锁之地’变成‘联结之地’。”[5]而作为不发达国家的缅甸和孟加拉国对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更是寄予厚望。印东北部及缅、孟等国工业基础薄弱,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在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需要进口大量机器设备。而中国产品适合当地的消费层次,这就为中国机电产品、农机具、交通运输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对该地区的出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7]
(二)地缘经济政治相互依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势必先行一步
巴基斯坦是中国全天候的朋友,在地缘经济政治领域相互依托。新世纪新阶段,中巴两国全面合作关系向规范化、法制化发展。2005年4月,中巴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巴基斯坦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的能源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巴基斯坦还是中国进入中东的大门,中国从波斯湾进口石油的路线大致经过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同时,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牵制印度的重要战略力量,始终是中国南亚战略的优先选择对象。中巴经济走廊北部起点中国新疆的喀什是中巴经济走廊与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点,有着极强的地缘经济政治价值。而巴基斯坦国内政局持续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又处于反恐第一线的压力,这不仅影响着巴经济发展,而且制约了巴的地区影响力。中巴经济走廊穿越巴境内基础设施最差、安全局势最动荡的西北部和西南部落后地区,这无疑增加了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难度。
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2005年,双方同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2006年,中巴签署《中巴自由贸易协定》、《中巴经贸合作五年(2007-2011)发展规划》等18项合作协议。巴基斯坦还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和海外重要工程承包市场。2012年,中巴双边贸易额超过120亿美元。巴基斯坦人力资源丰富、高端人才英语优势明显,中国企业到巴基斯坦投资设厂,不但有效促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促进就业,还能提升巴基斯坦制造业水平。[8]
巴基斯坦有着离中国西北地区最近的内陆出海口,中巴双方建设经济走廊可以有效发挥区域经济的互补性。巴基斯坦发展经济需要借力中国,期待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中国南亚问题专家马加力认为:“巴基斯坦十几年来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反恐上,国内经济发展受影响,巴基斯坦新一届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工作重心,而中国经济向西开放,寻找新的出海口,双方合作意愿很强,一拍即合。”[9]包括东突在内的中国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也正是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为藏身之地。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客观上要求巴基斯坦必须下大力气抑制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内安定的外部环境。中国作为巴基斯坦全天候的伙伴,与巴基斯坦有着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强烈共识,加之中巴有着良好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势必比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先行一步。
(三)强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赋予其合作新内涵
中国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国家,积极发挥该地区第一大经济体的优势,推动次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起步较早且已经机制化,共同目标是建设更加一体化的、繁荣的、公正合理的次区域合作。目前,中国所参与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主要有三大合作平台,即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湄公河委员会(MRC)。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最高决策机构为领导人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各成员国按照国名字母顺序轮流主办。部长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下设专题论坛和工作组。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至少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该地区地缘环境复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落后,且成员国差距较大,其中缅甸、老挝、柬埔寨3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处在东盟第二层次,虽然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具有开发潜力,但目前开发难度仍然较大;二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中除中国外都是东盟国家,而东盟对外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域外大国如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甚至欧盟都通过东盟合作机制,参与大湄公河开发,它们均从自身地缘经济政治战略出发,与该地区国家就政治、经济、环境甚至军事等方面展开合作,大国博弈无疑压缩中国的地缘空间;三是该地区安全形势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2011年10月,东南亚特大武装贩毒集团“糯康集团”因收“保护费”遭拒便勾结几名泰国军人射杀13名中国船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湄公河惨案”。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强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制度化合作机制,应出台更多具有互利共赢的合作项目,加速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经济整合,推动次区域一体化进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十年(2012-2022)战略框架》为未来十年合作制定了三大战略目标,即推动次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繁荣、公平的发展;在完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为跨境贸易、投资、旅游等合作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关注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促进次区域可持续发展。2011年,中国发表了《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家报告》,加强与相关国家经济贸易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中国还可以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互相推动,相互对接,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同时,中国为保证地区安全提供国际义务,与老挝、缅甸和泰国开展联合调研与情报交流,联合打击跨国犯罪。2011年12月9日,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指挥部成立。截至2014年4月30日,中老缅泰四国已经在湄公河流域进行21次联合巡逻执法,保证了湄公河航道的安全,促进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有序发展。
三、打通西南国际通道,拓展地缘经济政治空间
打造西南国际大通道是建设次区域经济走廊的客观要求,但西南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贸易方面,还将全方位拓展中国地缘经济政治空间。要打通西南国际大通道,必须从地缘经济政治现实出发,为对外开放和国家总体战略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
(一)携手西南周边国家和地区,构筑互联互通国际大通道
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也被称为“新茶马古道”、“新驼峰航线”。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第一步是互联互通,尤其是要展开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研究工作,研究通关便利化措施。[10]云南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最近的陆上通道,从腾冲猴桥口岸出境,经过缅甸密支那就可进入印度东部,路程只有300公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2013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暨中国-南亚和平发展论坛”时指出:云南与南亚国家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人文相通,商缘相连,利益相融。……继续推进互联互通,探索公路、铁路、航空、电信等领域的互联互通,积极推进通关便利化,以交通、通信的畅通带动全方位各领域交往合作的畅通。[11]云南省提出,加快建设国际大通道,构筑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互联互通的交通、通信、物流等国际通道和枢纽。下一步是积极打造特色优势产业基地,努力把云南打造成为资源深加工基地、清洁新型载能产业基地和特色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不断完善开放合作平台,积极融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水平,不断深化与东南亚、南亚的全方位合作。[12]广西北部湾通往越南、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地出省出边的6条高速公路现已全部打通,通往广东、湖南、云南的高速铁路在加快建设,北部湾经济区内正在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二)构建大西南沿边经济开放带,连接和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
中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西部沿边省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落后于内地,特别是落后于中国东部地区,但与我国周边国家的接壤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领先水平。由于自然禀赋差异,各有比较优势,经济互补性较强。同时我国与周边国家接壤地区民族相近甚至相同,有着无法割舍的人文联系,且边境贸易从未中断,完全具备建立西南沿边经济开放带的条件。中国政府已明确承诺,鼓励企业参与东盟东部增长区、大湄公河、泛北部湾等次区域合作,给予金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有力支持,推动形成若干经济增长极。[13]云南昆明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枢纽,是中国、南亚与东盟三大市场的连结点。昆明作为国际性中心城市,以曲靖、玉溪、楚雄为节点城市,以瑞丽、畹町、河口为前沿城市,打造与东南亚、南亚陆地接壤区的经济走廊现实可行。云南正在发挥自身陆上通道的优势,与相关国家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2013年,云南省与东盟贸易额为109亿美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与缅甸贸易额就达41.7亿美元,增长83.6%。再以广西北部湾为例,拥有1600多公里海岸线的北部湾,正悄然崛起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高地。北部湾的优势在于,对内,可互动东中西部;对外,一湾相挽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地处我国华南、西南和东盟三大经济圈结合部的广西,是我国与东盟之间唯一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区域,区位优势得天独厚。[14]与越南接壤的广西凭祥边境自由贸易合作区正在形成“边境特区、境内关外、自由贸易、封闭运作”的新模式。
(三)破解“马六甲困局”,拓展陆海能源和贸易通道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贸易通道安全不容忽视,并且正在为此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军舰索马里海域护航就是明证。但中国的主要海上贸易通道的宫古水道和马六甲海峡,均存在安全忧虑,特别是马六甲海峡。中国自1993年首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2009年突破50%的警戒线,2012年达到58%,而中国石油进口80%来自中东和北非,而这部分原油进口只能靠海运并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海军却对马六甲海峡鞭长莫及,加之区域地缘政治关系复杂,中国不得不直接面对“马六甲困局”。2013年投入运营的中缅石油管道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能源通道安全困局。中缅石油管道不仅保证了中国能源安全,降低了石油运输成本,还与缅甸实现了经济上的互利共赢。该能源管道起自于印度洋东部的缅甸西海岸皎漂市,从云南瑞丽进入中国境内,分别通往重庆和广西。中国还积极倡议并与其他国家合作,积极筹划开凿泰国克拉地峡运河。克拉地峡运河开通后,东亚国家和欧洲、非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将不再通过马六甲海峡,直线缩短1000多公里的航程,东盟、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因此受益。中国作为贸易大国,还需要多个印度洋出海港口来支撑,最终实现太平洋出海口和印度洋出海口互动的“两洋出海”战略。同时,中国必须将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作为重点战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通信网络的规模与能力,全方位拓展地缘经济政治空间。
[1]李平.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20年综述[J].东南亚纵横,2012,(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3-05-21(3).
[3]2013-14财年巴基斯坦政府将为高速公路建设投入725.88亿卢比[EB/OL].http://pk.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6/20130600161268. shtml,2013-06-13.
[4]Strobe Talbott.U.S.Interest in Sino-Indian Cooper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0L.64,No.2,Spring/Summer2011.
[5]在印度东北看中印孟缅走廊[N].环球时报,2014-04-22(7).
[6]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助力中国南亚合作[EB/OL].http://intl.ce.cn/ specials/zxgjzh/201305/31/t20130531_24438122.shtml,2013-05-31.
[7]胡国财.抓住机遇开拓南亚市场[J].经贸世界,1996,(5).
[8]述评:构筑中巴经济共同愿景[EB/OL].http://news.xinhuanet.com/ 2013-05/22/c_115862606.htm,2013-05-22.
[9]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步入“快车道”[N].解放军报,2014-02-20(8).
[10]学者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EB/OL].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10-25/5426786.shtml,2013-10-25.
[11]中国-南亚和平发展论坛在昆明开幕[EB/OL].http://www.yn.xinhuanet. com/newscenter/2013-09/22/c_132738792.htm,2013-09-22.
[12]构筑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互联互通的国际大通道[EB/OL].http:// www.y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1-06/05/content_22940716.htm, 2011-06-05.
[13]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繁荣[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10-22(1).
[14]壮乡崛起国际区域合作新高地[N].人民日报,2012-03-09(21).
[责任编辑 闫明]
Geopolitical Strategy of Building Sub-Regional Economic Corridor of Southwest China
WANG Zhi-min
(Institute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Innovation of opening-up model is imbedded in th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rend of southwest China. It has become a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 to build sub-regional economic corridor,to adopt the strategy of mutual opening-up of east and west,to promot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to build China-India-Burma-Bangladesh corridor,to innovate the sub-region of Mekong River for broadening the regional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ace with the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passage of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geopolitical economy;sub-region;around southeast region of China;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China-India-Burma-Bangladesh corridor
D822
A
1674-0955(2014)04-0074-07
2014-05-0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设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经济政治环境研究”(项目批准号14BGJ003)的阶段性成果
王志民(1960-),男,山西运城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中巴建交七十周年主题推广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