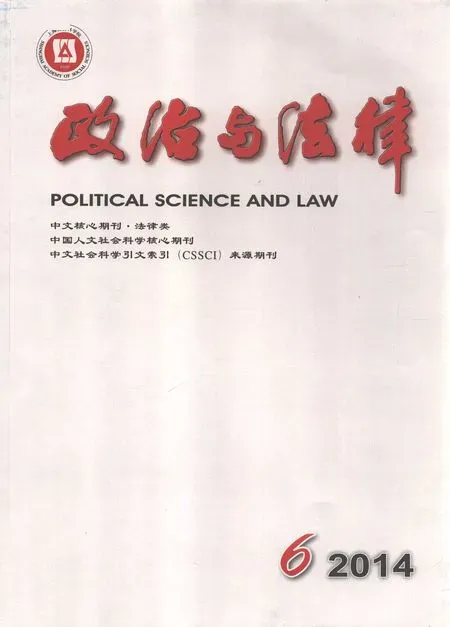兼有欺诈与勒索因素的刑事案件之司法认定*
——从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因果分析结构转向以被告人为中心的事实认定结构
潘星丞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兼有欺诈与勒索因素的刑事案件之司法认定*
——从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因果分析结构转向以被告人为中心的事实认定结构
潘星丞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行为兼有欺诈和勒索因素的案件,实践中认定分歧较大,同种情形却存在五种判决结果。各种理论无法自圆其说:一罪说各执一端却说理片面;两罪说兼顾二者却不符合罪数形态之法理基础。诈骗与勒索实是互斥关系,两罪不可能同时成立,也不可能竞合。界分之困境源于传统理论对诈骗与勒索的犯罪结构的理解,应放弃这一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因果分析结构,改采以被告人为中心的事实认定结构。定性时应区分“欺诈——胁迫”、“胁迫——欺诈”、“欺诈+胁迫”等不同类型具体认定。
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罪数形态;互斥关系;犯罪结构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同为财产犯罪,而且均有“诈”的成份,对于行为兼有欺诈与勒索因素的案件,究竟应认定为诈骗罪,还是敲诈勒索罪,抑或同时成立两罪?司法判决莫衷一是,“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比比皆是。理论学说亦分歧较大。因此,厘清二罪之界限殊有必要。
一、引论:由“虚构事实勒索财物”类案件的同案异判说起
行为人同时采用欺骗手段与恐吓手段,从而不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这是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例如,对于以虚构事实勒索财物的情形,从判例观之,就有五种结论,这五种结论可分为两类:一罪说与两罪说。
(一)一罪说
一罪说认为此种情形只构成一罪,或为诈骗罪,或为敲诈勒索罪。
1.只构成诈骗罪
案例1:女大学生张某毕业后与已有妻室的郭某同居,并怀孕生子,但郭却不愿意离婚娶张;于是,张与家中保姆于某合谋,让于某将孩子带到乡下住几天,再冒充“绑匪”打电话给郭,向其勒索100万元,后被警方侦破。法院认为:被告即孩子的母亲张某和保姆于某虚构绑架事实,使孩子的父亲郭某产生错误认识,并向郭勒索100万元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法院最后以共同诈骗罪判处张某5年有期徒刑,判处于某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①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003/105081.shtml,2014年3月1日访问。
2.只构成勒索罪
案例2:2007年3月5日,张某给李某打电话,谎称已绑架李母(其实李母因有事外出),要求李某交付8000元赎人,张某收钱后被警方抓获。法院认为,张某虽未实施绑架,但其威胁内容的程度足以使孝顺的李某产生恐惧心理。李某是受精神强制产生恐惧,不得不交付财物。故此案应定敲诈勒索罪。②章正华:《谎称绑架他人母亲索财该定何罪》,中国法院网:http://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707/04/254905.shtml,2014年3月1日访问。
(二)两罪说
两罪说认为此种情形同时构成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但对于两罪的关系,又有不同观点。
1.想象竞合说
案例3:陈某在已经死亡的李某的手机中查到李某丈夫赵某的手机号,以李某被绑架为名,发短信要求赵某交20万元“安全费”。由于赵某及时报案,陈某未得逞。对陈某如何定罪呢?
这是我国2011年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题,司法部给出的参考答案是同时构成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两罪是想象竞合;而且连续几年的司考均有类似题目,答案也均是想象竞合。对此,陈兴良教授表示赞同,理由是:被告人虚构绑架事实,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而处分财物,构成诈骗罪;同时,被告虚构的事实对被害人也有一种精神威吓作用,被害人交付财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精神受到强制,所以被告的行为也符合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两罪是想象竞合。③陈兴良、陈子平:《两岸刑法案例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2.包括一罪(吸收犯)说
张明楷教授则认为:“行为同时具有欺骗与胁迫性质,被害人既陷入认识错误又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处分财产的,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形成狭义的包括一罪,从一重罪论处。”④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99页。其“狭义的包括一罪”其实就是吸收犯,所谓“从一重罪论处”就是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因而在处断结果上与想像竞合相同。我国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敲诈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仅为10年有期徒刑,因此处断结果应为诈骗罪。
3.法条竞合说
对于上述情形,有学者认为,由于只发生了一个危害结果,不是想像竞合,而是法条竞合,但不应简单地按特殊法优先或从一重处的原则,而应根据刑法规定处断;由于刑法第266条诈骗罪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诈骗与敲诈勒索因素交织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应属‘另有规定’的情形,故此种情形应按敲诈勒索罪处理更妥”。⑤张少会:《论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分》,《人民论坛》2012年第14期。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同时采用欺骗与恐吓手段不法有占财物的情形,不止我国内地出现争议,在我国台湾地区及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也存在分歧(下文详述)。从现有裁判文书来看,不但定性之结论各异,而且对定性之理由均语焉不详,莫衷一是。
实践分歧往往源于理论片面或瑕疵,为此,笔者的研究思路是先“破”后“立”:首先,从反面对现有理论观点进行评析,检讨其缺陷,是为“破”论;其次,再从正面对诈骗与勒索的关系进行分析论证,是为“立”论;最后,将由“立”论所得出的原理加以推演,用于分析此类案件的各种具体情形,是为结论。
二、破论:各种学说竟成“没有办法的办法”
(一)一罪说:诈骗罪说与敲诈勒索罪说各执一端、说理片面
从前述案例1、案例2可看出,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结论都只是从自身犯罪构成特征来说理,各执一端;无视此类案件既有“诈骗”因素,也有“勒索”因素,难免陷于片面。注重“诈骗”者,主张以诈骗罪定性,但被害人虽“陷入错误”,却并非“心甘情愿”地交付财物,这就与诈骗罪特征不符;注重“勒索”者,主张以勒索罪定性,但没有对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进行评价与界分,亦不完善。
为了兼而评价诈骗与勒索两个不同因素,司法实践多转向两罪说。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判例曾认为:“恐吓取财罪(相当于内地刑法的敲诈勒索罪)与诈欺取财罪(相当于内地刑法的诈骗罪),其性质并不相同,如其所用之手段,仅使人陷于错误而交付财物者,为诈欺取财;如使人心生畏惧而交付财物者,则为恐吓取财,两者在理论上,根本无低度行为与高度行为之可言,亦无其他足发生吸收关系或吸收犯之情形。”⑥台湾地区最高法院73台上3933(决)。但这种说法过于简略,甚至可以说是缺乏论证的,因为,在虚构事实勒索的场合下,被害人既“陷于错误”,又“心生畏惧”,这时,应当如何在诈骗罪与勒索罪中作出选择呢?由于一罪说缺乏论证,未能真正解决问题,稍后台湾地区的判例便改变了这一态度,⑦台湾地区最高法院84台上1993(决)。转而承认两罪之间有低度行为与高度行为的关系,并排除诈欺罪法条的适用,仅适用高度之恐吓罪的法条进行定性。⑧甘添贵:《刑法各论(上)》,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65-366页。实是认为该行为构成两罪,两罪之间是法规竞合中的吸收关系或包括一罪关系。
(二)两罪说:兼顾诈骗与勒索,但不符合罪数形态之法理
在兼有诈骗与勒索因素的场合,两罪说主张同时成立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这种观点,表面上同时评价了整体不法内涵与罪责内涵,满足了厘清功能,但该说无论主张哪一种罪数形态,都不符合该罪数形态的特征,因而面临无法理根据的悖论。
1.想象竞合论之悖论:只存在一个法益侵害事实
多数观点认为,虚构事实勒索财物的行为同时成立诈骗罪与勒索罪,两罪是想象竞合关系。前述案例3与我国学者多持此观点。
想象竞合论在日本也是“有力的观点”,例如,大谷实教授认为:“不利后果的告知中包括有诈骗行为的场合,例如声称‘你儿子强奸了我姑娘’,要求他人赔偿精神损害,不赔偿就告发,威胁他人交付财物的时候,因为对方的处分行为的原因中,具有错误与恐惧的竞合,因此,成立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观念上的竞合。”⑨[日]大谷实:《刑法各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山口厚教授对此表示反对:“由于只有一个法益侵害——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交付,认为属于想象竞合,并不妥当。”⑩[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二版)》,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页。
然而,山口教授从“法益个数单一”来否定想象竞合的观点实难成立。因为,想象竞合犯的成立条件乃在于“触犯数个罪名”,“法益乃系抽象社会秩序的理想生活价值,是立法者创设不法构成要件的基础,也是司法者在解释构成要件是否该当的重要参考因素,但法益本身并非描述不法内涵的事实情状的构成要件要素,由于构成要件是否该当,以及其该当是否多次的问题,判断的关键乃在于构成犯罪事实,故不能以抽象的法益概念作为判断标准”。①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增订十版)》,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15页。
想象竞合说仍然存在法理悖论。一般来说,同一行为触犯了法益相同的数个异种罪名,往往是该行为侵害了“多数的独立行为客体”,②同前注②,林山田书,第316页。从而形成多个“法益侵害事实”,如一枪打死甲、打伤乙,则为杀人罪与伤害罪之想象竞合,或一个诈骗行为,同时骗了A和B,仍可说是两个诈骗罪的同种罪名的想象竞合。但在一行为同时具有诈骗与勒索因素的场合,则属于:同一行为针对同一法益主体、侵害同一法益的事实,却触犯两个罪名,这就是“针对一个法益侵害事实可能适用数个刑罚法规”,③同前注⑩,山口厚书,第368页。实际上是法条竞合,而不再是想象竞合。具体而言,是两个罪名的法条规定之间存在重合之处,使得同一行为可用两种不同的刑罚法规进行评价。
2.法条竞合论之悖论:两罪的行为不存在补充与交叉关系
不少学者持法条竞合说的观点,这主要是基于法益事实同一,无法构成想象竞合犯的考虑。但是,究竟是何种关系的法条竞合,却不统一。
具体而言,所谓法条竞合,是指针对一个法益侵害事实可能适用数个刑罚法规,但从这些法条的相互关系来看只可能适用其中一个法条,并排除其他法条的适用。法条竞合常常被分为四种类型:(1)特别关系;(2)补充关系;(3)吸收关系;(4)择一关系。④同前注⑩,山口厚书,第369页。就诈骗与勒索而言,除特别关系外,补充关系、择一关系、吸收关系均有学者主张。但对于吸收关系,近来有不少学者认为,既然其能够肯定存在着复数的法益侵害事实,就应该将其理解为并非法条竞合而属于包括一罪。⑤[日]大谷实:《刑法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2008年版,第433页。为论述方便,笔者将吸收关系放在包括一罪中讨论,在法条竞合中仅讨论补充关系与择一关系。
(1)补充关系说
所谓法条竞合的补充关系,是指一个行为同时符合的两个构成要件处于基本法与补充法之间的关系。此时,“基本法拒绝补充法”,只有不适用基本法的场合才适用补充法。如伤害罪是基本法,暴行罪是补充法。适用伤害罪时,就不再适用暴行罪,只有在不适用伤害罪时,才认定为暴行罪。
我国台湾学者甘添贵教授曾认为:“恐吓取财罪之保护法益乃个人财产兼个人意思自由,诈欺罪之保护法益则为个人财产。因此,二者间具有保护法益之同一性,恐吓取财罪与诈欺罪应属法条竞合之补充关系,最后论以恐吓取财、得利罪。”⑥甘添贵:《体系刑法各论Ⅱ》,台北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409-410页。
该观点将诈骗罪视为补充法,恐吓罪视为基本法,显然不妥。因为,具有补充关系的基本法(主要条款)与补充法(辅助条款)均是在保护同一法益,主要条款描述法益侵害较为严重的行为样态,辅助条款则描述法益侵害较轻微的行为样态。因此,在具体个案中只要能够适用主要条款,辅助条款即无适用的意义。⑦同前注①,林山田书,第338页。例如,一行为构成伤害罪,往往也同时构成暴行罪,但适用伤害罪法条后,就没有必要再适用暴行罪法条了。而诈骗罪与恐吓罪的行为样态是“质”的不同,而不是“量”的差异;就法益侵害性而言,诈骗罪多数情况下轻于勒索罪,并非因为勒索罪对财产法益侵害更严重,而是因为勒索罪另外侵害了人身法益。所以,二者根本不存在补充关系。后来,甘添贵教授自己也放弃了这一观点,改持择一竞合说。
(2)择一关系(交叉关系)说
所谓择一关系,指可以同时适用于一个行为的数个构成要件之间处于排他性关系的场合,只适用其中的一个构成要件,排除其他构成要件的适用。
甘添贵教授放弃补充关系的法条竞合说后,指出:“恐吓取财罪与普通诈欺罪之保护法益,均在保护个人财产安全,具有保护法益之同一性。惟恐吓取财,系使人心生畏惧而交付财物;诈欺取财,则系使人陷于错误而交付财物,两罪之性质不同。成立法条竞合时,因两罪在构成要件上,并不具特别、补充或吸收关系,应依择一关系,选择最适合之恐吓取财罪处断。”⑧同前注⑧,甘添贵书,第365-366页。
择一竞合实是交叉竞合,因为,若两个构成要件不存在重合,则不属法条竞合范畴,应该适用哪一个法条只是事实认定问题;从而,作为法条竞合的择一关系仅指两个构成要件处在交错关系的场合。⑨同前注⑤,大谷实书,第434页;同前注⑩,山口厚书,第369页。例如我国刑法的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就存在交叉关系,交叉部分为: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数额较大的钱财,此时应择一重罪适用。然而,诈骗罪与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之间并不存在交叉竞合的可能。从立法者设立犯罪的逻辑看,所有侵犯财产法益的犯罪都具有相同的结果无价值,但基于构成要件的类型性和明确性要求,刑法不能笼统地规定一个“侵害财产罪”,而是考虑行为无价值,根据其侵害行为的样态区别为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勒索罪等。这些具体罪名相当于逻辑划分中的“子项”,相互不能有重合部分,即不能“子项相容”,否则,立法就违背了逻辑的划分规则。例如,抢劫罪与勒索罪虽然都可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但其程度不同,抢劫罪应足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而勒索罪不能达到排除被害人反抗的程度,二者界限可谓泾渭分明,不可能存在重合部分。诈骗罪与勒索罪之间也是如此,诈骗罪是被害人陷入错误后认为“应交付”财物,从而是“自愿”的,而勒索罪是心生畏惧后虽认为“不应交付”财物,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交付之,其主观心态是“不自愿”的。“应交付”与“不应交付”,“自愿”与“不自愿”处于对立的两极,诈骗与勒索的构成要件如何能存在重合部分呢?
实际上,在按行为样态划分具体财产罪罪名的立法逻辑下,规定诈骗罪与勒索罪行为样态的构成要件之间的界限应该是泾渭分明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重叠部分,也就不存在法条竞合的问题;而且,就同一法益侵害事实而言,也不可能同时符合两种要件,即不可能存在想象竞合关系。
3.包括一罪论之悖论:两罪法定刑差别不大,无法“吸收”
所谓“包括一罪”,是指“虽然存在着复数的法益侵害事实,但在能够通过一个法条的适用将其包括地评价的场合”,⑩同前注⑩,山口厚书,第374页。易言之,包括一罪存在着数个单纯一罪,在此意义上虽属数罪但却作为一罪处理。包括一罪存在两种情形。其一,同质的包括一罪,即行为在外形上似乎数次符合相同的构成要件,但只概括性地认定为一罪,如集合犯、接续犯等,亦有学者将此视为狭义的包括一罪。①同前注⑩,山口厚书,第379-380页。其二,异质的包括一罪,即行为外形上分别符合不同构成要件,但从被害法益来看,将其整体概括为一罪,轻罪为重罪的刑罚所吸收,因此也称为“吸收一罪”,如伴随行为,用手枪将他人杀害的同时子弹还损坏了被害人的衣服,可理解为,损坏器物罪的事实被杀人罪的刑罚所吸收了;另外还有共罚的事前行为、共罚的事后行为等情形。不难看出,吸收关系的两罪法定刑轻重差别较大,轻罪基本上相当于重罪的预备行为,如两罪轻重差别不大,则不能成立吸收关系。“吸收一罪”长期以来是作为法条竞合的类型之一的“吸收关系”,但既然能够肯定存在着复数的法益侵害事实,就应该将其理解为并非法条竞合而属包括一罪。②同前注⑩,山口厚书,第369页。因此,笔者在法条竞合之外对此加以讨论。
日本学者山口厚教授指出:“同时实施欺骗他人的行为与恐吓行为,对方由此交付了物或者财产性利益之时,如果欺骗也是使对方感到畏惧的因素,被害人因畏惧而交付的,仅成立恐吓罪;反之在陷入错误的同时,因畏惧而实施了交付行为的,有力观点认为,成立诈骗罪与恐吓罪的想象竞合。然而,由于只有一个法益侵害——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交付,认为属于想象竞合,并不妥当。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认为两罪属于包括的一罪的观点,事实上也存在疑问,但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③同前注⑩,山口厚书,第335页。
由于诈骗罪与勒索罪显然不属“同质的包括一罪”(或“狭义的包括一罪”),只能认为该两罪是“吸收一罪”,但两罪之间又无明显的轻重关系,谁吸收谁并不明确。尤其是日本刑法,诈骗罪与恐吓罪的法定最高刑均为10年有期徒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成立吸收关系的。④同前注⑤,,第439页。
那么,是否在两罪法定刑相差较大的刑法制度下,可依包括一罪(吸收一罪)来解决此问题呢?
答案仍是否定的。首先,法定刑配置与不同立法者的评价相关,而不一定完全符合社会价值观念。例如,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的刑法中,杀人罪都必然重于毁损财物罪,这就是合乎社会平均价值观念的刑罚判断,而诈骗罪与勒索罪则不然,既可能勒索罪重于诈骗罪(如我国澳门刑法),也可能二者相等(如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甚至可以出现诈骗罪重于勒索罪的立法例(如我国内地刑法),这说明,勒索罪重于诈骗罪并非“必然”,从而使得对虚构事实勒索财物的定性,完全取决于不同刑法典的法定刑配置,而不是取决于构成要件的定型,否则有侵蚀罪刑法定根基之虞。其次,吸收一罪也以“复数法益侵害事实”为前提,是实质的数罪,只是在刑罚评价上,可以一罪的刑罚包括评价之。但如前所述,在虚构事实勒索财物的场合,只有一个法益侵害事实(行为、行为客体、被害法益都是单一的),根本不可能存在相互吸收的两罪。
另外,我国台湾地区之司法实务曾用“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来解决这个问题,判例谓:“恐吓手段若以虚假事实为内容,此含有诈欺性之恐吓取财行为,足使人心生畏惧时,自应仅论以高度之恐吓取财罪,不再适用诈欺取财罪。”⑤台湾地区84年台上字第1993号裁判要旨。“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是判例中最常出现的说法,行为的高低度由行为该当之罪的法定刑来决定,即法定刑高者为高度行为,法定刑低者为低度行为。这在我国台湾地区“判例”中较为常见,却往往缺乏说理,因而被批为“浮滥致极的吸收”。⑥同前注①,林山田书,第372-374页。实际上,这与包括一罪(吸收一罪)的概念并无实质区别。但台湾地区“刑法”中,诈欺罪与恐吓罪的法定刑几乎等同,因此,有学者亦指出:“两者在理论上,根本无低度行为与高度行为之可言,亦无其他足以发生吸收关系或吸收犯之情形。”⑦同前注⑧,甘添贵书,第369页。更为关键的是,虚构事实勒索财物的场合,本来就只有一个行为,并不是同时存在一高度行为、一低度行为。因此,台湾地区判例的这一态度难以得到认同。
可见,现有理论对于兼有欺骗与勒索的情形,一直难以得出妥当答案,正如山口厚教授所说,学界现提出的各种观点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三、立论:两罪互斥说之证成
(一)立论之基点:两罪是互斥关系
实际上,诈骗罪与勒索罪之间是互斥关系,不存在重叠也不可能竞合,理由是:第一,从案件事实看,在兼有欺诈与勒索的场合(如虚构事实勒索财物),只存在同一法益侵害事实,不可能是想象竞合,也不可能是包括一罪;第二,从立法原意上看,由于立法者对侵犯财产罪是按行为样态的不同划分为各个不同罪名,各罪名的行为方式就不可能存在重合,从而各罪名之间不可能是法条竞合关系;第三,从构成要件的内容上看,两罪都是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而处分其财产(即向被告人交付财产)的犯罪,所不同的仅在于手段(行为方式),一是欺骗,一是恐吓或胁迫,性质迥异,诈骗罪是智能犯之代表,而勒索罪为暴力犯之代表。⑧[日]前田雅英:《日本刑法各论》,董璠舆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56页。被害人的心态也分别处于“自愿”与“不自愿”两端。
(二)界分之前提:由“因果分析”转向“事实认定”
在兼有欺骗与勒索的场合(如虚构事实勒索财物),被告人既有“欺骗”的成份,又有“威胁”的因素;被害人则既“陷于错误”,又“心生畏惧”,这就给定性带来困难。诈骗罪与勒索罪的界分困境,与传统刑法理论对二者的犯罪结构的理解有关:这一结构的功能是对被害人行为进行因果分析,却被用于对被告人行为进行事实认定。
1.以被害人为中心的犯罪结构:因果分析
传统理论认为,诈骗罪与勒索罪具有大致相同的犯罪结构,都呈因果递进关系的四个步骤。⑨参见上注,前田雅英书,第256页、第230页。诈骗罪:欺诈行为——错误——处分——财物、利益之移转。勒索罪:恐吓行为——畏惧——处分——财物、利益之移转。
对于虚构事实勒索财物的场合,既有欺诈行为又有恐吓行为,既有错误又有畏惧,两罪的结构要素(四个步骤)都齐全了,故而难以区分。
然而,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四个步骤(子项)的地位并不是等同的,以诈骗罪为例,“欺诈行为——错误——处分——财物、利益之移转”分别对应:“被告人行为——被害人之主观——被害人之客观——结果”。
在划分逻辑上,这四个“子项”是不能并列的,否则就是“划分标准不同一”。可见,这种犯罪结构是以被害人为中心的,注重被害人的主观心态与客观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其功能是因果分析:被害人因被告人欺诈而发生主观错误,并因主观错误而作出客观处分。
这种犯罪结构不能适用于犯罪事实认定:一方面,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以被告人为中心,以被害人为中心的犯罪结构只适用于被害人学,而非刑法学;另一方面,事实认定时,主客观是无法分离的,例如,如不结合主观,我们就不能认定客观上的“不告而取”究竟是盗窃、借用还是取回自己的物;被害人的主观“错误”与客观“处分”也不可能分开,主客分开的犯罪结构只适用于概念上的因果分析,而非事实认定。
2.以被告人为中心的犯罪结构:事实认定
在犯罪事实的认定中,被告人行为是研究对象,被害人行为只是认定被告人行为的辅助手段;而且,不但“被告人行为”应从主客观两方面判断,被害人之主观与客观也应结合在一起考察,成为与被告人行为相对应的“被害人行为”;被告人行为与被害人行为是整个案件的两个“子事实”。这样一来,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因果分析”结构就转变为以被告人为中心的“事实认定”结构:“被告人行为——被害人行为——法益侵害结果(不法占有)”。在这个结构中,法益侵害结果也是广义上被告人行为的一部分;处于中间的被害人行为是认定被告人行为的辅助手段,它是被告人主观必须认识的内容,在广义上也是被告人行为的组成部分,而且它是一个主客观结合的整体:被告人的“欺诈”不仅对被害人主观“错误”有因果关系,而且对被害人的客观“处分”行为也有因果关系;被害人“处分”行为不仅是被害人“错误”引起的,更是被告人“欺诈”所追求的;如果“欺诈”不指向“处分”,就与法益侵害结果无关,就不是诈骗罪所要求的“欺诈”。
(三)事实之认定:“被告人行为——被害人行为”
由于勒索罪与诈骗罪是互斥关系,具体是构成哪个罪名,就完全是事实认定问题了,就应当依据“被告人行为——被害人行为”的犯罪结构来考察。
1.被告人行为的认定
本体论认为,行为的性质由其目的性决定,即行为人预设一定的目的,选择实现它的必要手段,有计划地指向目的实现,这就是目的行为概念。在诈骗罪中,其“欺诈行为”要达到不法占有的目的,就不能仅以被害人主观上“陷入错误”为满足,而需将被害人客观上的“处分”作为其目标,这样才能最终“不法占有”。客观归责论也能得出同样结论:如果“虚构事实”虽使对方“陷于错误”,但并未产生使对方财产损失之风险,即未“制造风险”,则诈骗罪之客观构成要件并不该当;只有被告人的行为产生了使被告人“处分”的可能时,才产生了法所不容许的危险。即“欺诈——处分”的关系才是更重要的。而传统的“欺诈——错误——处分”的因果结构,人为地割裂被害人行为中“欺诈”与“处分”之间的联系,容易误将“错误”视为“欺诈”的目的。例如,被告人仅仅虚构事实“你小孩在我这里”,虽然被害人也产生了错误认识,但这并不能促使被害人交付财物,就不是诈骗罪的“欺诈行为”;只有当被告进而实施勒索行为:“你不给钱,我就杀了你小孩”,才能达到目的。在此之前,虚构事实“你小孩在我这里”仅仅是为了勒索行为更容易达成创造一定的条件而已,可以认为,这只是勒索的预备行为,只有说“你不给钱,我就杀了你小孩”才是勒索罪的实行行为,从而应作为勒索罪处理。
2.被害人行为的认定
被害人行为只是被告人行为认定的辅助手段,但将其独立出来分析,有助于揭示传统的因果结构在事实认定上的不足。
(1)被害人主观(错误/畏惧)之认定
以诈骗罪为例,“欺诈——错误——处分”的因果结构中,分割主客观两面,对被害人主观“错误”的认定,容易忽视客观的“处分”,仅从“欺诈——错误”来判断,从而扩大“错误”的范围;如果从整个“被害人行为(错误——处分)”来判断,就能较合理限制“错误”的范围。例如,当被害人听到“你孩子在我这里”时,虽然也产生了“错误”,但这个“错误”并未驱使其作出“处分”决定,就不是诈骗罪中要求的“错误”。当然,被害人主观上的“错误”使其处于一个更容易被胁迫的境地,如被告人进而实施胁迫行为,被害人就可能在“畏惧”的驱使下客观“处分”其财产,这就是勒索罪而不是诈骗罪了。
(2)被害人客观(处分)之认定
表面上,被恐吓者与被骗者都实施同样的“处分”,但二者并不相同:由于被害人行为只是认定被告人行为的辅助手段,因此应从与被告人的关系上理解“处分”行为。勒索罪之被恐吓者知道自己的处分,相对于被告人来说,是一种具有“牺牲”性质的配合行为,是“不得已的损失”;相反地,诈欺罪之被骗者在处分财产时,并不认为自己系“牺牲者”,而系一种心甘情愿的处分财产,⑩黄惠婷:《刑法案例研习(一)》,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版,第196 页。是对被告人“应履行的义务”。
四、结论:两罪互斥说之个案适用
基于以上分析,诈骗与敲诈勒索两罪处于互斥关系,对于欺骗与胁迫兼有的场合,只能构成诈骗罪或勒索罪一罪,而不可能出现任何竞合,具体结论可区分以下几种典型个案来确定。
(一)“欺诈——胁迫”型
前述案例1至案例3均属此类型,即以虚构事实的方式勒索财物,欺骗行为一般不直接指向被害人的处分行为,这种欺骗实际上是勒索罪的预备行为,被评价于敲诈勒索罪中;胁迫行为才是产生侵害的实行行为,因此,只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胁迫——欺诈”型
如A、B赌博,A赢钱后想离开,B说“继续玩两把,不然你赢的钱我不给你”,A无奈继续赌博,此时B用诈术反赢A的钱。此案中,B的胁迫行为只能视为诈赌的预备行为,被评价于诈骗罪中,只构成诈骗罪一罪。又如,甲强迫乙拿钱来买古董,称系真货,但实是不值钱的假货,乙付款虽有被迫的成份,但却没有“损失”的认知,因而不属勒索罪的“处分”行为;甲的胁迫行为只是诈骗罪之预备行为,本案只构成诈骗罪。
(三)“胁迫+欺诈”型
严格说来,胁迫与欺骗是不存在竞合的两种行为样态,因此,不可能出现胁迫与欺骗同时进行的例子,但以下案例仍有迷惑性:行为人冒充治安联防队员或者冒充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抓赌”、“抓嫖”、没收赌资或者罚款。表面上看,这是诈骗与勒索同时进行的例子,有学者因此认为这种场合“同时触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与招摇撞骗罪,应从一重罪论处”。①同前注④,张明楷书,第899页。实际上并非如此。治安联防队员无权没收赌资和罚款,人民警察即使没收赌资和罚款也要符合一定的程序要件。一般情况下,赌客对此是明知的,因此,被告人除了冒充行为外,还需实施勒索行为(如“不交罚款就送警察局”),才能使得赌客交付赌资和罚款,因此构成勒索罪,假冒行为系勒索之预备行为,被评价在勒索罪中,假冒与交付财产并无因果关系。如果被告人通过其他行为(如假公章)与冒充行为相配合,使赌客误以为其当场罚款是合法的,则被告人根本无需另外实施勒索行为,赌客即会“按规定”交付赌资和罚款,此时仅仅构成诈骗罪。当然,就人民警察而言,还有成立招摇撞骗罪之可能,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之间存在交叉竞合关系。
(四)不作为的“胁迫+欺诈”
由于敲诈勒索罪不仅侵害财产法益,还侵害了人身法益,所以,其暴力、胁迫手段以行为人本人实施或行为人本人能控制为限,只有这样,才能让行为人对人身法益侵害承担责任。我国台湾学者亦认为,“恐吓内容所通知于被害人的恶害,应以人为或人力所能支配的恶害为限,若以妖魔鬼怪之事相告,则非人力所得左右,判例上认为即非恐吓行为,被害人若因出于迷信而信以为真,乃竟交付财物与行为人,则属陷他人于错误的欺罔行为,应成立诈欺取财罪”;由于被告人根本无能力以“作为”形式实施胁迫行为,因此,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以“不作为胁迫”进行的场合,如,“你不给钱,我就不帮你祈解”一案中,“被害人惑于被告所云,见其宅有三种不同色彩灵魂,断定其家最近死了二人,可能再有一人死去之谎言,信以为真交付财物,求其祈解,是被害人之交付财物,乃不过仅基于实行之欺罔行为,陷于错误所致,自与恐吓罪之要件不合”。②廖映洁:《刑法分则新论(修订三版)》,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702页。
日本刑法虽然也认为,勒索罪中的“胁迫”,“以告知足以使他人恐惧的不利后果为内容”,这一不利后果不一定是行为人亲自实现的,但是,在由第三者实现该不利后果的场合,行为人必须处于能够影响该第三者的地位。因此,“告知天地变异或预测祸福凶吉之类的警告,原则上不是胁迫行为”。但是,“使他人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左右凶吉祸福的时候,能够成为胁迫。某甲被某乙请求为其母亲祷告,以消除其病,某甲借此机会,对某乙说,你母亲为鬼魂附体,为了驱除该鬼魂只有向神求助,但是得要10万日元,否则,你母亲就有生命危险。某乙等感到恐惧,于是,分数次向某甲交付了32万7千余日元。本案成立敲诈勒索”。③同前注⑨,大谷实书,第205-206页。
这一结论值得商榷。这实际上是将行为人的“不作为”视为勒索行为,即“你不给钱我就不帮你母亲祷告”,但是,即使其母真的被鬼魂附体,在甲并无“祷告”之义务时,“不祷告”也没有使这种风险增加,因而不能和制造其母生命危险的“作为”同等对待,甲就不能成立勒索罪,而是诈骗罪。
再如,乙见自己的小孩落入水中,但自己水性不好,求甲相救,甲要求10万酬金,乙不得已应允之。本案中,甲本无救助义务,即使不救助,也不成立刑法上的“不作为”,让乙产生恐惧的是孩子落入水中的事实,而不是甲的勒索。所以,甲不构成勒索罪,而只是乘人之危的行为。在我国民法中,“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三种行为被并列规定,都是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我国刑法并未规定见危不救罪,因此,这种行为不宜以犯罪论处。当然,如果甲有救助义务(如甲是小孩的游泳教练),其“不救助”就是相当于“杀人”的“不作为”,以这一恶害相告知,就构成勒索罪。但如果甲骗乙说“你的小孩落入水中”,乙信以为真,求甲相救,甲要求10万酬金,乙不得已应允。本案中,乙被甲欺骗,因而产生错误,认为小孩处于“危急”之中,但这个“危急”的内容不是甲施加的,因此,不能认为甲实施了胁迫行为,甲在虚构的“危急”上,仅实施了乘人之“危”的行为,乘人之“危”不构成犯罪,但甲的欺骗行为可以构成诈骗罪。
(责任编辑:杜小丽)
D F625
A
1005-9512(2014)04-0036-10
潘星丞,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刑事判决书中法理诠释之实证研究”(项目编号:GD12XFX10)的阶段性成果。
——兼谈集体法益的类型
——美创科技“诺亚”防勒索系统向勒索病毒“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