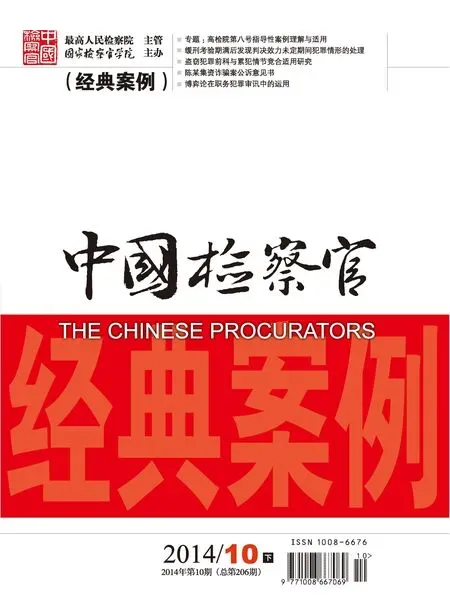是“偷”还是“捡”
文◎孙涛
是“偷”还是“捡”
文◎孙涛*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期间,天津某高校多次发生下课时间学生手机在教室被盗案件,后学校保卫处干部刘某查看监控视频,发现一名学生模样的男子形迹可疑,刘某在巡逻期间抓获此名男子——犯罪嫌疑人韩某,并报警。经查,犯罪嫌疑人韩某于东北某大学肄业,现无业。公安机关在韩某家中搜查出大量手机、笔记本电脑、MP4、充电宝、钱包等物品。犯罪嫌疑人韩某承认这些物品均为在天津某高校教室内所得他人物品,但其辩称这些财物均为学生遗忘在教室,自己只是拾得这些物品,并非盗窃。后经公安机关查找,寻得丢失手机的学生五名,其中学生A是上午下课后去吃饭时将手机遗忘在课桌抽屉中,走下教学楼后即想起,返回教室寻找时已经丢失;学生B是下课后去吃饭时将手机遗忘在课桌抽屉中,到了食堂想起,但由于下午的课还在同一教室,认为不会丢失,就继续吃饭没有返回寻找,饭后回到教室手机已经丢失;学生C是使用书包占座,而手机放在书包中,待上课时,发现手机丢失;学生D是上下午的课在同一教室,中午吃饭时未将桌上的书本等物收起,书包放于座位上占座,手机在书包中,待其吃饭后返回教室时发现手机丢失;学生E是周六没课时去教学楼找人,中途去厕所时将书包随便放于一无人教室课桌上,手机放在书包中,待返回后手机已经丢失。经鉴定,涉案手机总价值为人民币2260元。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韩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因为在大学校园中用物品占座的行为极其普遍,犯罪嫌疑人韩某作为上过大学的人,对此应有所了解。因此韩某应当认识到此物为他人占有,韩某的辩解不能采纳,对于学生A和学生B的手机,即使确为遗忘物,犯罪嫌疑人韩某也是以盗窃的故意,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同样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于被害人用以占座的物品以盗窃罪认定,而对于确属被害人遗忘的物品则不能以盗窃论处。因为虽然韩某对这些物品为他人占有应当有所了解,对其辩解不予采信,但客观上学生A和学生B的手机确是遗忘物,如以盗窃罪定罪,与客观事实不符,因此对韩某取得这两部确为遗忘物的手机的行为应认定为侵占行为,但由于数额不足立案标准,对取得这两部手机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
第三种意见认为,对于被害人放置于包内的手机以盗窃罪定罪,而对于单独的手机则认定为侵占行为。因为取出包内的手机并把包留下体现出了犯罪嫌疑人韩某对手机为他人之物的明知,此时韩某辩称从他人包内捡东西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这体现出了韩某盗窃的故意,且从包内取出手机把包留下的行为方式属于秘密窃取的手段,因此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而单独的手机更容易被认为是遗忘物,韩某“捡”的主观认识就合情合理了,且本案中单独的手机均确为遗忘物,因此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只是因为数额不足不构成犯罪。
三、评析意见
韩某的行为应认定为侵占行为。在本案中,将手机取得的行为既可以认为是秘密窃取的行为,也可以认为是捡拾他人遗忘物的行为,在行为模式上没有分别。根据犯罪嫌疑人韩某供述,其对财物占有状态的认识为他人遗忘物,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其以侵占他人遗忘物的故意实施了一个捡拾他人遗忘物拒不归还的行为,应当定性为侵占,而因为其侵占数额不够而不构成犯罪。
(一)理论界观点及其问题与改进
本案中行为人对脱离占有人的财物的占有状态所做的判断可以归纳为遗忘物或遗留物。遗忘物是物品非基于原占有人本意而脱离占有,处于占有人不明状态的财物。遗留物看似不在任何人的占有之下,但实际上遗留物并未脱离原占有者的实际控制,而是占有者有意将其留在某处。在当前理论界对将遗留物误认为遗忘物的行为定性大多采取“合情合理”的标准认定行为性质,即如果行为人对财物占有状态的认识是合情合理的,是有一定依据的,即按照行为人主观认识定性;如果行为人对财物占有状态的认识是不合常理的,是毫无依据的,则按照财物客观占有状态定性。例如,有观点认为“将他人占有物误认为是遗忘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实际上属于客观事实是重罪(盗窃罪),主观认识是轻罪(侵占罪)的情况,当行为人的‘误认为’合情合理时只能成立轻罪,即侵占罪,反之则应成立盗窃罪。”[1]前述第三种观点认为从包内取出手机为盗窃,拾取单独手机为侵占的理论即是采用的这种标准。那么从包内捡手机是盗窃,从桌内捡手机是侵占的观点是否正确呢?笔者认为,此种观点看似有些道理,但却难以解释由此引发的一个悖论:如果捡拾单独的手机可以认定为侵占遗忘物,为什么捡拾单独的包就不能认定为侵占遗忘物呢?如果行为人认为整个包都是他人遗忘的而将其捡走,按照这种观点该行为仍是可以认定为侵占的,而且在行为人侵占了整个包之后将其中值钱的财物据为己有,然后将包和书本等物随手丢弃只是侵占财产之后的处分行为,没有定罪上的评价意义。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将整个包拿走就是侵占,将包里的手机拿走就是盗窃;行为人将包拿出教室再取走手机丢弃包是侵占,当场拿走手机将包丢在原地就是盗窃。这显然是荒谬的。
笔者认为,要对此类案件给予一个准确的定性,需要分两步进行分析: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分析当行为人对所取得财物占有状态的认识与客观情况不符的情况下应以主观判断还是客观状态作为定罪标准;然后需要从实务上分析如何判断行为人对所取得财物占有状态的认识。前述如主观认识“合情合理”即依主观定罪、如主观认识“不合常理”即依客观定罪的观点无疑混淆了刑法理论上认识错误下的行为定性原则和司法实践上对行为人主观心态认定的证据标准。产生此种混淆是因为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案例模式不同,学术研究案例多为虚设,多不涉及证据问题,行为人主观心态已提前预设好,无需通过证据予以认定。而在司法实践部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不明确的,不能仅凭行为人自述,需要办案人员结合各种证据还原出一个法律事实,尽管这个法律事实只能力求接近客观事实,而无法等同于客观事实,但最终予以定案的依据是这个法律事实。
(二)两步分析法在本案中的应用
本案中产生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认定犯罪嫌疑人韩某是“捡”他人遗忘的手机还是“偷”他人遗留的手机。捡拾遗忘物拒不归还的行为符合侵占罪“合法占有转变为非法所有”的核心,而取得他人遗留物的行为不存在合法占有的前提,应以盗窃罪而非侵占罪进行评价。本案犯罪嫌疑人韩某声称对涉案财物的占有状态的判断是遗忘物,而部分财物的客观情况是遗留物,在此种情况下无论是盗窃还是侵占客观上都是将时空上脱离物主的财物占为己有的行为,因此依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应以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认定其行为性质。即是说行为人以捡拾他人遗忘物占为己有的主观故意实施此行为即构成侵占,行为人以趁无人之机秘密窃取他人遗留物的主观心态实施此行为则构成盗窃,与此物实际上是遗忘物抑或遗留物无关。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标准是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得出的,此时尚未接触证据,仅在理论层面分析,因此这条标准是不以具体案件证据情况、行为人自述的主观认识、行为人的认识是否合理等因素为转移的。
至此,对脱离物主的财产的占有状态认识错误下的取财行为定性的标准已经找出,即以行为人主观故意为定性标准。下一步就是该确定如何认定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故意。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不能仅凭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要根据其教育背景、行为模式、客观环境、财物大小等因素综合予以认定。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韩某辩称其去往教学楼是为了上自习准备考研,因并非本校学生,所以每次都是在用餐时间进入无人教室学习,每次捡拾手机均是临走时无意间发现课桌内有他人遗忘的手机,桌上没有其他物品,也从未从他人包里取得手机。按此说法其当时认为“所捡”手机是遗忘物属于所谓“合情合理”、“有一定依据”的认识错误。
但经过办案人员询问高校保卫处,发现学生B和学生E两起案件案发教室门前有监控探头,经调取查阅案发时监控录像,发现两次案发时韩某进入教室到离开教室的时间均不足一分钟,说明犯罪嫌疑人韩某进入教室并非是去自习,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且录像显示案发时为周末,教室无人,学生E进入教室时背着书包,离开教室时未背书包,其回到教室之后即发现手机被盗跑出报警,说明要么学生E的手机当时是在包里,要么手机被拿出来了但附近的桌面上还有包等其他物品,不可能只有手机没有包。经办案人员询问被害人学生C及与其一同占座的同学,均证实学生C当时确将书包放于桌面上占座。经询问被害人学生D及与其一同上课的同学,均证实案发前后两节课均为同一班在同一教室的课,学生D及班里很多同学均未将书本收起,学生D前去吃饭时他的书包确实放置于座位上。且学生C和学生D的同学均证实,学生C、D回到教室发现手机丢失后曾仔细翻找自己书包,且对其他同学说过手机原本就在书包里。
至此,综合分析证据,可以认定学生C、D的手机确为从包内取出,学生D的桌上还有书本等学习用品,学生E的手机要么是从包内取出,要么周围有书包等其他物品。犯罪嫌疑人韩某的辩解已有多处与其他证据矛盾。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定韩某作案时对涉案手机明知是他人遗留物呢?笔者认为此时可以运用前述所谓“合情合理”的标准了,即综合各种证据看韩某作案时认为这些手机是遗忘物是否合情合理,如合情合理则可采信韩某的辩解认定其作案时认为手机是遗忘物,反之亦然。但怎样才算合情合理呢?恐怕没有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笔者认为,对于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辩称所取财物是遗忘物是否合理,需要结合现场情况考察财物是否足以引起人的注意。如果财物在所处空间内极为显著,足以引起人的注意,那么对财物原占有人来说同样是非常显著的,也应当引起原占有人的注意,将其遗忘于此就不甚合理;如果财物在所处空间内并不显著,不足以引起人的注意,那么对财物原占有人来说同样不显著,也很难引起原占有人的注意,也就极易遗忘。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刑法理论通说为何认为路旁未上锁的车辆仍为车主占有——车辆以其体积和与车主的紧密联系而且非常显著,因此几乎不会有任何人将车辆遗忘,行为人如若声称其认为车辆是遗忘物也就不合常理了。回到本案,学生A、B的手机放在课桌抽屉中,以手机的体积并不明显;学生C、D的手机放在书包中,且放在桌面或座位上,以书包的体积非常显著。至于学生E,由于没有证人能够证实E在进入教室之后是否将手机拿出,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所说也相互矛盾,因此无法判断案发时手机与包的位置关系,也就无从判断当时手机是否明显。因此,学生A、B的手机由于放置位置不显著,犯罪嫌疑人韩某称其认为是遗忘物合情合理,没有相关证据对其证伪,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只能认为犯罪嫌疑人韩某当时确是以侵占的故意实施捡拾他人遗忘物的行为;学生C、D的手机由于非常显著,犯罪嫌疑人韩某称其认为是遗忘物不合常理,对其辩解不能予以采信,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韩某是以盗窃的故意实施了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而学生E的手机虽无法判断是否显著,但根据监控录像可以证实被害人E的书包当时必定在案发教室中,手机即使不在书包内而在书桌里,由于有书包的存在,在高校的行为模式中应认定书包为占座之物,所谓占座即是对外宣称此座位已被某人暂时占有,在此期间此座位不具有公共属性,因此此时手机为置于某人独占的空间内,应为空间占有者所占有。犯罪嫌疑人韩某作为曾上过大学的人,应具有此知识背景,应当知道占座所代表的含义,因此学生E的手机对韩某来说也不可能是遗忘物。
综上所述,本案涉案五部手机中学生A、B的手机确为遗忘物,犯罪嫌疑人韩某所称认为其为遗忘物的说法也合理,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应定性为侵占行为,由于数额不足不构成犯罪;学生C、D、E的手机为所有人占有之物,犯罪嫌疑人韩某的辩解与其他证据不符,不予采信,根据其他证据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韩某作案时明知这三部手机是他人占有之物,而趁无人看管之机秘密窃取,是盗窃行为,虽数额不足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属于多次盗窃,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注释:
[1]蔡雅奇、徐梦萍:《将他人占有物误认为是遗忘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定性问题探析——兼论盗窃罪与侵占罪的界分》,载《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1期。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300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