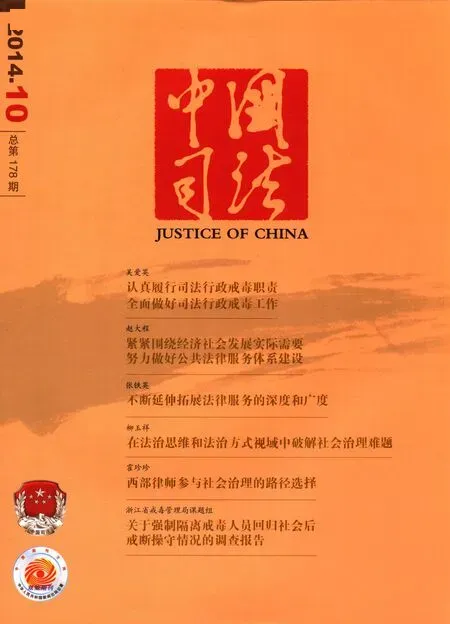律师“死磕”的理性解读
邓 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律师“死磕”的理性解读
邓 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近期,发生在广西北海市银海区法院的律师“绝食抗议”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律师给法官“送红薯”事件,再次将 “死磕派”律师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加之此前的律师在法庭上“集体沉默”等事件,不得不引发人们对律师“死磕”现象的深度思考。
互相尊重、各司其责、共同追求司法正义的目标是法治国家中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最基本的应然关系,尊重法官、张弛有度、公平有序的法庭秩序是法治社会的最基本场景。然而,在我国当下的现实中,总是存在种种因素困扰着法庭上控辩审三方的应有关系。如何在互相独立中互相牵制,如何在互相牵制中互相独立,这不仅是立法者应该考虑的问题,也是司法者应该反思的问题,还是学者应该研究的问题。
律师文化,是一种根植于律师心中的修养,是一种承认约束并强调自由的自觉,是一种设身处地为当事人利益着想,并秉持法律公正的信仰。然而,从一开始,律师文化在我国并没有得到顺利的发展,我国古代法律中并没有“律师”概念。早期庭审过程中,律师的地位是低下的,律师在法庭上对检察官和法官会有所忌惮。伴随着法官中立、控辩平等对抗规则的建立,在法治建设成绩显著的同时,也出现了控方打击报复律师、律师“死磕”法官检察官等不正常现象。冀祥德教授认为,律师“死磕”现象是中国司法制度转型时期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及法治建设现实碰撞交织的一种综合反应,是一种“司法乱象”。
“技术派”、“学院派”、“艺术派”、“死磕派”等等,是近些年对刑事辩护律师的一些分类。其实,有“技术”的刑辩律师不管是不是来自于“学院”的,在辩护代理的过程中都要讲究辩护的“艺术”,而这项“艺术”绝对不应该是“死磕”,因为“死磕”是“磕”不出司法公正和法治中国的。律师“死磕”现象是传统的“非讼”文化与当代司法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所形成的“矛盾综合体”。“死磕”派律师的兴起和壮大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社会及体制原因。
其一,古代“厌讼”文化盛行。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是一种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文化,强调宗法伦理,秉承礼教中心,实行比较严格的刑罚强制措施,重伦理轻法理,个人权利被淹没在特定的伦理要求之中,成为义务的另外一种形式,这是一种恪守本分的政治法律关系。在如此“厌讼”的法律背景和情势之下,以权利为本位的律师职业与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文化很难和谐发展,所以,律师的社会地位之低也就可想而知。在一个对“人治”信仰多于“法治”信仰的时代,古代的讼师只有据理力争,依靠自己的法律知识为受害者争取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律师“死磕”现象产生的文化原因。
其二,国内法律本身的夹缝和空隙较多,矛盾之处有待完善。立法活动不能全然地洞察所有社会问题,其滞后性、孤立性、不确定性的特点不能完全对应社会中复杂性、动态性的案件事实,当介入法官主观思维判断时,律师可能就会存在有不满情绪。例如新刑诉法中,对“重大刑事案件”和“下级人民法院因案情重大、复杂,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其确认标准,因不同法官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审判结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造成法官在处理案件时,由于考虑不周全,进而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从而激发起律师“死磕”的动机。同时,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的变异也会造成法律运作机制的不顺畅,进而使得律师“不得不”通过“死磕”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三,当前,司法机关人员与律师接触过多,其职业威严有所下降。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是代表国家形象,体现法律公平和正义的化身。法官与律师是接触比较多但又必须保持一定距离的两种职业,二者不能“亲密接触”,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群众的信任。可是目前,法官与律师频繁的接触,甚至有很多的“关系案”爆发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律师的“优越感”。只有当内心信奉法律,律师才会更加尊重法官,进而尊重法庭秩序。
“死磕”派律师是目前律师群体中新出现的一种力量,其行为方式之过激已经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和理论界的讨论。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认为,“死磕派”律师“不像律师”,但是“律师不像律师,首先是因为法官不像法官”,他认为“不可否认,死磕派律师在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推动法治的进步”。纵观一些西方国家,由于判例法的盛行,律师会在一些案件中“追求细节”、“挑战传统”、“不择手段”地追求案件的胜诉,并且产生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经典判例,推动了国家法治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无视法治文明建设,突破法律底线,以“死磕细节”来掩饰自身能力的不足。对于“死磕”派律师的行为,有人认为,其行为可以促进诉讼程序更加严谨,促进立法的不断完善,可以使审判活动顾及舆论,进而更全面的实现社会公正。而批评者认为,“死磕”是律师成名的一种途径,是一种牺牲当事人利益以达到自身利益的私立化行为,其过分追求程序,忽视诉讼效率,忽视司法公正,无法兼顾法律的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是中国法治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绊脚石,是法治文明中的一种阻碍力量。笔者认为,律师是法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其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尊重法治精神是其职业道德的首要要求;尊重事实与尊重法律应该并重,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只有平衡法律的严谨和事实的复杂,才能构建和谐文明的法治图景。
对于如何解决律师“死磕”问题,笔者有以下建议:
第一,着力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就其职业道德的基本价值蕴涵来讲,理性平和是律师应具有的基本素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其主要目标,合理的运用法律是其基本手段,其必须在理性和守法的精神导引下,以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为依据,进行合理的判断和理性的思考,这是成为一名合格律师的基本要求。一名合格的诉讼参与人,应该以尊重法治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底蕴,以促进法治社会发展为目标。“死磕派”律师无视自己的职业道德,无视当事人的权利和自身的义务,无视行为的风险和代价,“死磕”司法机关,这是控辩关系的一种扭曲,律师应该不断地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构建“律师文明诉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庭审顺畅”三位一体的律师诉讼模式,实现司法共赢。
第二,完善律师执业纪律与规则。如果不能坚定地维护法治社会,那么又如何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的追求?律师“死磕”是司法活动运行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从短期来看,其行为方式似乎实现了维护当事人权利的目的,实现了法律公正;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行为对法治文明的建设将是极大的毁坏,对于构建结构清晰、功能明确的法庭秩序将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对抗制”模式已经势在必行,但是这种“过分”的对抗只会使法治社会的建设更加困难,更加混乱,只有在规则内进行辩论,以妥当的方式实现法庭秩序和谐,才能真正地实现法治中国。
第三,公安司法人员要尊重律师、善待律师。律师是社会矛盾化解、风险控制、法治进程进步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律师在法律活动中的主动参与使其具有前瞻性,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和法律视角,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各种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因此,不仅当事人要尊重律师,公安司法人员也要尊重律师。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规律,法治建设离不开公安、检察院、法院、律师的共同参与,缺少任何一方,都将是对法治规律发展的一种极大破坏。因此,公安司法人员应当在互相独立的基础上,尊重律师并善待律师,使律师无须通过“死磕”程序来达到对正义的追求,这将会大大促进法治社会建设。
第四,建立尊重法庭的强制性规则。良好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是保持法律实现规制机能的基本要求,“死磕派”律师不尊重法律事实、超越法律底线的行为应该受到一定的惩罚,其藐视法庭、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应该被刑事法律进行规制。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看,可以考虑规定限制“申请回避”、“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次数,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兼顾司法效率的实现。
法律是有着严格要求的规范性规则,蕴含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双重含义,任何法律参与者都不能只偏袒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利益。律师“死磕”这一法律乱象严重地冲击了司法技术合理化的实现,利用“追求程序公正”这一“外衣”实现其本不正当的目的,“控辩冲突”、“辩审冲突”就是最直接的后果。法治中国的建设是社会多元合力的结果,法官要依据法律、依据事实,居中裁判,公正断案;检察官要全面搜集证据材料,履行客观义务,尊重“对手”;律师应该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尊重法律,尊重法庭。中国法治社会的成功转型必须多种社会力量的不断整合和全力合作。“死磕”则两败,和谐则共赢。在规则下进行辩论,在辩论中追求公正,绝不可以牺牲法律尊严为代价进行“死磕”。
(见习编辑 朱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