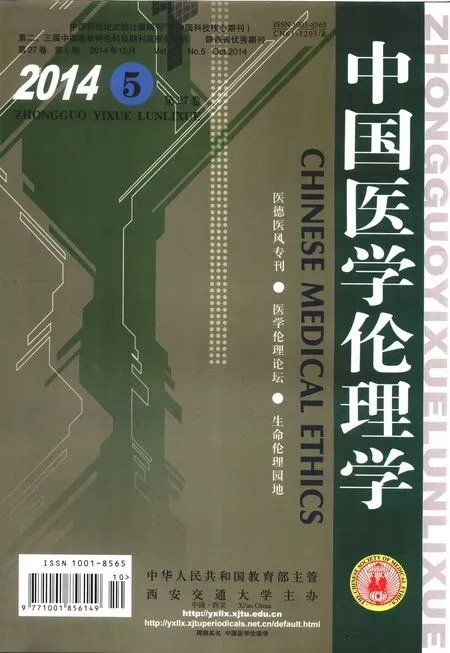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从技术理性走向生命伦理
陈 芬,纪金霞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chenfen66@163.com)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从技术理性走向生命伦理
陈 芬,纪金霞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chenfen66@163.com)
从技术理性角度分析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对社会、家庭、个人的伦理挑战;从医学目的的层面分析说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是一种医学本体实践方式,有其自身的伦理价值;从对生命伦理的思考中总结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确证与规制,需要保持适度的宽容、遵循伦理原则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用“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技术理性;医学目的;生命伦理
辅助生殖技术给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福音,但是在技术理性和医学目的的双重制约下,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也面临着诸多伦理挑战。这些挑战或涉及法律,或挑战传统伦理,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人文主义生命伦理来更好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1 技术理性:挑战传统伦理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技术理性是指人类以科学技术为工具改造世界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实践理性,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自身的实践活动。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是指人类运用现代医学高科技手段来代替自然生殖过程中的某一过程或全部过程。
人类的生育发展进化史经历了自然选择生育时期,又走过了计划生育时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提倡“少生优生”,而现在,由辅助生殖技术引领的选择生育时期却陷入了伦理困境。
1.1 对社会伦理的挑战
技术作为科学知识向实践转化的手段和技能,在实践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正面能量和负面因素,辅助生殖技术也不例外。
1.1.1 分配公正性及生殖技术滥用问题。
在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和经验最丰富的医疗机构开展此类辅助生殖手术,成功率也只能达到20%~30%左右,费用也极其昂贵。如此昂贵且成功率又相对不高的技术,并不是每个不育家庭都会选择的,而辅助生殖这一高科技带来的福音仅有少数人能享受,这显然不利于社会公平。
由于某些辅助生殖技术的操作并不复杂,一些没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或个人在利益的驱使下私自开展此类技术,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
1.1.2 名人精子库危机。
“名人精子库”能否决定优生一直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名人精子库”只允许部分成功男性供精,将大部分男性排斥在外,既无科学依据,又否定了生命平等观。由于过分夸大基因决定性,片面强调先天的遗传物质基础,忽视后天成长环境中家庭、社会、教育等因素的作用,名人精子库容易导致人类基因库缺乏多样性,实际上事与愿违。
1.1.3 精子商业化问题。
人工授精具有很大的市场,极易导致精子的商业化,继而引发一系列问题。首先,商业化将导致无法确保精子质量等问题。精子的市场化可能导致供精者出于经济的压力而隐瞒自己的身体疾病去供精,有可能把病情传给通过人工受精出生的子代;精子库也可能为了追求利润或实现垄断竞争,而忽视对精子质量的监测,结果使人工受精产生的后代缺乏基因多样性或有先天疾病,这对社会是危害极大的,对于子代也是极不公平的。其次,商业化也会引起管理不到位,同一个人多次重复提供精液,未来近亲结婚的概率也由此增加。
1.1.4 代孕商业化的伦理困境。
代孕的出现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时间,但是从目前来看,代孕已经形成一种非正常的人类交易行为,即代孕的商业化。在这一交易过程中,接受代孕委托的女性把自己的子宫当作了商品租借给了他人,这就辱没了人的尊严,亵渎了生命的神圣性。“代孕妈妈”的出现,它与“供精、供卵”等技术相结合,更会造成子代拥有多个父母,给社会伦理带来强力冲击。
此外,代孕还引发了一系列让法律感到棘手的问题,比如计划生育、抚养权、继承权,生殖犯罪等问题;另外,如果穷人都迫于经济需求来为富人代孕,无形中就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有失社会公正。
1.2 对家庭伦理的挑战
费孝通认为在传统社会伦理环境下,男女结婚组成家庭,共同孕育抚养孩子成人,这是传统的生育制度。[1]这种传统的生育制度形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传统的婚姻模式下,夫妻双方通过自然生殖将双方的基因遗传给后代,人类得以生生不息。然而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淡化了婚姻与血缘传承之间的紧密联系,孩子也不再是婚姻的结晶和纽带。
1.2.1 父母子女关系多元化。
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会导致多父母家庭的出现,违背了传统的家庭模式。自然生殖情况下,一个人生来只有血缘关系上的父母双亲。但是,随着供精人工受精和代孕等这些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一个孩子可以同时拥有几个父母亲,比如遗传学父母亲、代孕母亲、社会学父母亲。假设出现父母离婚后又再婚现象,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1.2.2 代际伦理关系的混乱。
代孕技术的应用,使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比如,当妹妹可以为姐姐代孕、母亲选择为女儿代孕,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母女、姐妹以及他们与代孕出生的子代之间的关系?直系血亲之间的代孕,造成家庭伦理尤其是代际伦理之间关系的混乱。
1.2.3 未婚单亲家庭及同性家庭的出现。
辅助生殖技术可以帮助独身主义者成为未婚父母,只需借助人工受精或者找人代孕,由此产生未婚的单亲家庭;甚至男同性恋者可以雇佣代孕妈妈、女同性恋者可以通过人工受精来获得孩子,这就产生同性恋家庭。
1.3 对个体伦理的影响
1.3.1 代孕母亲的权益。
代孕母亲在怀孕过程中身体出现问题需要流产时,该如何处置?生下的孩子若有先天性疾病时,若委托方不愿负责,又由谁来抚养?假如代孕母亲对腹中的胎儿不愿割舍,又该如何?代孕合同是不是存在贬低人性尊严的嫌疑?代孕母亲具有哪些权利和义务?代孕母亲是否受到了剥削?
1.3.2 胚胎的地位如何确定。
无论是“精子库”、还是“代孕”,无一不牵涉到配子、胚胎问题。如何确定胚胎的道德地位,学术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胚胎就是生命的开始,实际上就是人的开始,我们不应该把他们作为工具来使用,应该尊重他们的生存权利,更不该随意扼杀它们。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胚胎不是人,它只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哲学上的观点认为不能利用潜在的人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工具及手段。由此可见,配子和胚胎的商业化是违反他们的固有价值的。
1.3.3 子代是否享有知情权。
每一个应用辅助生殖技术成功孕育孩子的家庭都必须面对一些问题:是否应该告诉孩子他的真正出生方式;孩子是否具有寻找自己遗传性父母的权利;如果选择隐瞒,是否剥夺了孩子对生命基本权利的知情权;如果揭开真相,又是否影响家庭亲子关系的和睦?[2]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普遍强调保密原则,但也有观点认为,人工授精的孩子成年以后对自己的身世应该享有知情权,包括寻找亲生父母和其他相关信息的权利。
2 医学目的:作为医学本体实践方式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医学目的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概念,是特定的人类群体或个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医学的理想和期盼,是人类希望通过医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对医学目的的考察是为了帮助辅助生殖技术更好的符合医学本身的要求。
作为一种医学技术理性,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是实现医学目的、体现医学科学知识的一种技能和手段,具备成为医学本体实践方式的价值。辅助生殖技术攻克了不孕不育这一难题,维护了不孕不育患者的生育权,提高了他们的生命质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认为在女方不能怀孕的前提条件下而“代孕母亲”又不是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时,那么,在道德上是容许代孕行为的发生的。[3]配子或胚胎冷冻技术则可以帮助准备采取绝育措施的夫妇保留生育能力,为他们打消后顾之忧,因而辅助生殖技术可以作为生育调节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而存在,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顺利实施。
无论是人工授精、还是体外受精,它们都是实现医学目的强有力的手段和形式,两者共同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保障不孕不育者的生育权、维持不孕不育者的家庭圆满。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为不孕不育者提供了生育的可能,为他们的生命延续带来了希望。人类生命质量的提高,离不开医学的不断发展,医学的不断发展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自身的存在状态,所以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生命的存在状态和人类的延续是医学之所以存在的根本价值。因此,辅助生殖技术作为一种医学本体的实践形式,获得了自身的伦理价值,它的存在也就有了独特的意义。
3 生命伦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确证与规制
邱仁宗认为生命伦理学以问题为取向,其目的是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生命科学或医疗保健中提出的伦理问题。[4]生命伦理学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的伦理难题。作为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致力于更好的平衡技术理性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力图通过伦理的正确引导,调整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促进医学技术理性与生命伦理的进一步融合。在技术理性与生命伦理学两者相互靠近、相互融合的尝试中,辅助生殖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两者的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辅助生殖技术正是这种技术理性的实现形式。技术理性并不会自觉地走向与伦理价值的融合,因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某些层面上甚至对立而存在。而生命伦理学又是以价值理性为重点,因此,医学技术理性与生命伦理学之间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还必须经过漫长的不断尝试。辅助生殖技术会产生一系列的伦理问题,但其应该获得人类的伦理认同。
3.1 保持适度的宽容
人类的进步史给了我们明确的指引,当面对伦理道德的困境时,我们应该保持心灵的平静和适度的宽容,勇于应对伦理难题的挑战。比如,输血技术和器官移植刚出现时也曾掀起轩然大波,遭受强烈的质疑与反对,但事实证明当初饱受诟病的技术迄今为止拯救了不计其数的病人,造福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虽然在当下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是未来它对人类的贡献也将是不可估量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平静应对挑战,规范引导技术的理性发展,避免技术异化。
3.2 遵循伦理原则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
实施辅助生殖技术更应遵循相应的伦理原则,如有利于患者、知情同意、保护后代、社会公益、保密、严防商业化、伦理监督。妥善建立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也是监督医护人员伦理原则实施的必要手段。只有医患双方各自都能遵循这些伦理原则,才能从道德层面上更好的规范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
道德层面上的规范管制只是手段之一,我们更需积极探索技术的正确导向和法律调控原则的多重手段。原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引导辅助生殖技术实施工作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
3.3 用“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善”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自身善,其二是手段善。作为一种科学技术,辅助生殖从本质来说是“善”的,它是人们实践各种知识能力的技能和手段,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外在表现和理性形式。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理性形式,而技术作为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是知识向实践转化的必备工具和技能,它的出现同时反映了客观规律和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善的价值属性是它的固有属性,技术本身就蕴含着善的向度。辅助生殖技术弥补了人类的生殖缺陷,实现了它的工具理性即功利价值,更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属性,对社会和个人来说,满足了人对自身的生命价值、生活意义的追求,提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韩跃红.护卫生命的尊严—现代生物技术中的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邱仁宗.生命伦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邱仁宗,翟晓梅.生命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
〔修回日期2014-10-04〕
〔编 辑 李恩昌〕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From Technical Rationality to Bioethics
CHEN Fen,JI Jinxia
(College of Marxism,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6,China,E-mail:chenfen66@163.com)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ethical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to society,family and person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From the level ofmedical purpose analysis shows that artificial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is a kind ofmedical practice of ontology,have their own ethical values;Summed up from the ethics of life ethics confirmed and regulation of artificial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the need tomaintainmoderate tolerance,follow the ethical principles,and improve the corresponding legalmechanism,using"goodness"to regulate people's behavio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Technical Rationality;Goals of Medicine;Bioethics
R-052
A
1001-8565(2014)05-0625-03
2014-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