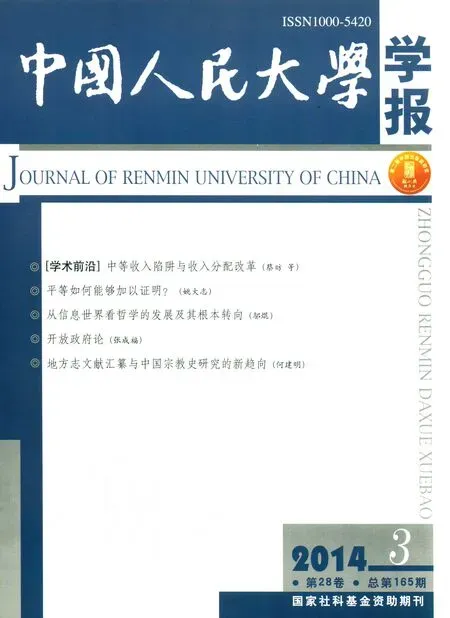权威式整合
——以杭州市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实践为例
康晓光 许文文
权威式整合
——以杭州市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实践为例
康晓光 许文文
为应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化挑战,杭州市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机制——权威式整合,即政府依托其绝对主导地位,对社会中的多元主体、机制和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区域与国家的整体发展。“权威式整合”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管理模式和西方主流的公共管理模式,是适用于整个中国的新型公共治理模式。
公共治理模式;多元整合;权威式整合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经济基础的巨变引发了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一元化体制”被打破,政府之外的主体(非国有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人)、机制(市场机制、非营利机制)、资源(上述主体掌控的资源)开始出现。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政府管理体制无法适应这种多元化的现实。中国政府需要探索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以回应多元化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杭州市政府不断探索,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适用于新环境的公共治理机制,并将其命名为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战略方案。社会复合主体的“多元主体参与、多元机制并行、多元资源共存”的特征与当代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的主流模式较为相似,因此被贴上了治理、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参与式民主、公民社会等标签。然而,通过深入观察可以发现,杭州市的公共治理模式绝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二者存在着本质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对杭州实践进行解读,恰当解读杭州实践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有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杭州市的实践,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建立能够忠实地反映杭州市创新性实践的新的公共治理理论。
一、描述:杭州市政府的实践
杭州市政府的探索并没有一个事先存在的“蓝图”,社会复合主体是在回应现实挑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①杭州市案例资料来源于:《培育社会复合主体研究与实践》、《民主民生战略研究与实践(上、下)》等杭州市政府资料汇编、期刊文献以及笔者实地走访调研获得的一手资料。
第一阶段,杭州市政府创建了社会复合主体的基本框架——党政界、行业界、媒体界、知识界四界联动[1](P2),并将其运用于经济建设领域。
这一阶段的杭州面临着历史文化资源衰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传统产业“文化空心化”等问题,以风景人文著称、以旅游产业为主要支柱的杭州失去了原有的核心竞争力。[2]为解决上述问题,2000—2002年,杭州市政府规划上马了数个旨在开发传统优势资源、推动重点行业发展、带动城市整体发展的大型公共工程。运河综合保护、女装丝绸行业发展、西泠印社改制三个项目即是其中的代表。
运河综合保护工程是集生态环境治理、旅游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于一体的大型公共工程。该工程地域范围广,项目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涉及利益主体众多,任务十分艰巨。其中,最紧迫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解决政府内部各级机构及各职能部门相互扯皮的问题;二是如何筹措巨额资金。为解决上述问题,杭州市政府发挥“整合”的力量,充分利用了政府内部及外部多元主体、机制及资源。首先,成立了市政府直属的局级事业单位——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综保委”),并规定运河流经城区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如交通局)也相应成立工程指挥部,隶属综保委领导。综保委负责工程的统筹规划,解决了各部门扯皮的问题。其次,注资成立了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与综保委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其法定身份使工程能够借力市场机制,吸引资本进入工程的开发。此外,在工程实施中,政府还建立了一种对话协商、汇集民意的社会合作架构[3],广泛地与媒体、专家、市民进行工程方案论证等工作。总之,该工程形成了以综保委和集团公司为核心的、网络式的对外整合多方优势资源的运作架构,社会复合主体的概念也在此架构中得以体现。
西泠印社也是历史赐予杭州的宝贵遗产。然而,命途多舛的西泠印社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接近沉寂状态,面临着社团登记受阻①由于一直隶属于地方政府管理,西泠印社只能注册为地方性社团,无法注册为全国性社团。但注册为地方性社团,会在法律上限制社团的活动范围,影响社团发展。、社团活动基本停止、高级人才流失、社员退社、产业经济效益严重亏损等一系列问题。杭州市政府认为,社团、事业、产业混为一谈,全部在行政机制下运作,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明确症结后,杭州市政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制。首先,成立全额拨款的副厅级事业单位——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社委会”),统辖社团和企业。社委会下设社团事务部和产业发展部,社团事务部主管西泠印社社团,产业发展部承担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职能。其次,将西泠印社注册为全国性社团。社团和社员是西泠印社的灵魂,法律身份的解决使社团能够独立运作,保证了社团的独立性。最后,成立集团公司,整合西泠印社所有的文化产业。该公司由社委会单独出资设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接受社委会的授权,负责对西泠印社品牌进行产业化运作。上述多元机制的整合和运用决定了西泠印社改制的成功。非营利机制提升了社团声誉,吸引更多的精英文人入社;市场机制可为社团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而行政机制则确保了政府对社团和产业的掌控。
进入21世纪以来,杭州丝绸产业陷入了发展困境。为此,杭州市政府成立了由政府办公厅、市经委等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组成的丝绸与女装行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推动产业发展。其重要举措是搭建了用于整合行业内“产、学、研、商”等各类资源的平台——“杭州丝绸与女装行业联盟”。行业联盟集合了行业内来自党政界、行业界、媒体界、知识界的利益相关者,其主要工作包括行业研究、市场拓展、人才培养、产业宣传等。上述工作由行业联盟内各领域领军人物统筹协调,如市丝绸行业协会会长负责市场拓展工作,资金由杭州市政府提供。行业联盟吸引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加入,以虚拟网络型组织的形式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各方资源,是社会复合主体的典型代表。
经过多年努力,上述骨干型、战略型项目或已完成,或进入常态化运行,杭州市的经济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强调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视。在此背景下,社会复合主体实践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实践以“社会主体参与”为核心特征,将普通市民、社会组织纳入社会复合主体,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拓展了适用范围,并将社会复合主体的战略方案运用于社会领域,以解决民生问题,完善社会管理。
在这一阶段,杭州市政府主要从舆论引导、市民居住环境基础设施改善、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社会管理等领域入手,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拓展政府与市民的交流渠道,提高市民的生活满意度。庭院改善工程、我们的圆桌会、凯益荟等案例充分地展示了这一阶段社会复合主体的特色。
庭院改善工程是杭州市政府实施的一项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惠民工程。与第一阶段的工程项目相比较,该工程涉及的资金规模小,工程实施技术简单,难点在于涉及数千栋房屋、数十万市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仅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项目,不会让市民满意。因此,杭州市政府设计了“四级联动”与“民间庭改办”相结合的运作机制。首先,成立庭院改善工程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庭院改善工程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办);各区、各街道也设立工程办公室,其中区办公室设在区城管办,街道办公室由街道领导负责。这种工作机制充分运用了层级型的政府组织架构,为工程的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其次,为弥补行政机制的不足,创建了“民间庭院改善办公室”(简称民间庭改办)。民间庭改办由街道办公室负责培育和管理,成员由各社区居民自愿报名,社区内公开评选产生,主要职责包括汇总居民意见和建议,组织居民对庭改方案进行听证,对施工情况进行监督,对结果进行考核等内容。民间庭改办直接与街道庭改办对接,保证了工程实施过程中居民利益的表达。
我们的圆桌会是由杭州市政府发起、杭州市电视台主办的谈话类节目,目的是主动引导舆论、促进公众对政府工作和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节目以演播室谈话为主,参与节目的人员包括主持人和由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代表、企业代表、市民代表组成的嘉宾。杭州电视台主要负责提供媒体平台和技术支持,而核心工作,如节目规则制定、话题设定、嘉宾确定及邀请、节目评审等工作全部由杭州市政府负责。为此,杭州市政府设立了“市民主民生媒体互动平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政府通过我们的圆桌会节目,借助媒体优势搭建了一个整合专家学者、政府、企业、公众的平台,以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
现阶段,中国基层政府面临建立社会化基层公共服务体系的任务,民间社会组织成为政府能够整合和利用的力量,凯益荟①凯益荟的含义是凯旋街道公益组织荟萃的地方。即是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街道为整合民间社会组织力量而成立的。凯益荟的法定身份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但本质上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该部门主要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1)管理、孵化凯旋街道内活跃的社会组织,使其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力量; (2)有选择地购买街道外的社会组织的服务,使其进驻凯益荟,为凯旋街道提供公共服务。为吸引社会组织的进驻,凯益荟将为其提供资金、办公场地以及在社区开展活动时的背书。值得强调的是,凯益荟的功能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整合,它还通过备案、培训、孵化等制度实现了对民间社会组织的监管。
经过两个阶段近10年的努力,杭州市创造了城市综合发展的出色业绩。我们没有充分的论据将杭州的成功全部归因于社会复合主体的实践,但在上述案例中,社会复合主体的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本文所选取的案例覆盖了地方政府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大领域的所有职能,包括民主政治建设、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发展、城市综合发展、发展教育、发展文化事业、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社会管理等,可见在杭州,“社会复合主体”不是孤立的、零星的现象,而是全局性现象,几乎在政府所有的重要活动领域中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
二、归纳:权威式整合
在上述案例中,社会复合主体的主要策略是对政府内部及外部的多元主体、机制、资源进行“整合”。为系统准确地对杭州市政府的实践进行归纳,本文围绕“整合”这一核心概念,建立了包括整合维度、整合框架、整合机制、参与主体角色四个维度的描述框架。“整合维度”旨在考虑整合发生在哪些“对象”之间,这些“对象”可以是主体、机制,也可以是资源。一般情况下,主体、资源、机制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因此对主体的整合往往伴随着对相应的资源和机制的整合。“整合框架”用于描述“整合维度”中涉及的各种“对象”通过何种组织结构进行互动。“整合机制”是指能够把参与主体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参与主体角色”旨在分析各参与主体在共同行动中发挥的作用。
(一)整合维度
最易于理解的整合是主体之间的整合,此种整合常常伴随着相应的资源和机制的整合。上述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主体之间整合的多种类型: (1)政府内部的垂直整合,即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整合,如各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办公室之间的整合,或者四级庭改办之间的联动;(2)政府内部的水平协作,即政府平行部门之间的整合,如“女装丝绸行业发展领导小组”;(3)政府与其他主体,如企业、媒体、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之间的整合,该类整合在上述案例中随处可见,但不同的案例侧重的整合维度有所不同,运河综合保护案例展示了政府与企业、研究机构、媒体之间的深度合作;对社会组织的整合在凯益荟中得到了凸显;而在庭院改善工程中,普通公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主体之间的整合,还存在着一种“另类”的整合维度,即政府通过成立新的附属主体或改变既有主体的运行机制,实现对其他机制的整合。运河综合保护工程以及西泠印社改制都展现了此种整合维度。在运河综合保护工程中,杭州市政府为综保委增添了公司的身份,将市场机制引入工程运作中。尽管集团公司拥有法定的企业身份,也按照市场机制运行,但无论从所有权还是从人力资源构成来看,该公司都仅仅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西泠印社改制的案例更加典型。无论改制前还是改制后,西泠印社的所有权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改制的核心并不是新类型主体的加入,而是对市场机制和非营利机制的借用。这一另类的整合维度,使政府能够超越行政机制,顺畅地进入市场领域或社会领域,自如地运用市场机制或社会机制实现自己的目标。
(二)整合框架
为了保证整合的实现,杭州市政府加强了相关的制度建设,无论是设立正式的组织体系,如成立综保委,还是通过制度构建虚拟组织,如组建女装丝绸行业联盟,都体现了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杭州的实践中,层级型组织不再是唯一的组织形式,网络型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与层级型组织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杭州市政府在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组织形式。层级型组织在运河综合保护、庭院改善工程等案例中发挥了骨干作用。然而,一旦整合超出政府范围,层级型组织便不再那么有效。政府外部的各类主体拥有独立的法人身份,而且遵循各不相同的运行机制。层级型组织赖以维系的垂直命令链、等级节制的组织结构,既不能容忍参与者的独立性,也不能容忍参与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因而不适合为彼此平等的独立主体之间的合作提供组织支撑。而网络型组织既可以保留各类主体的独立性,又可以使它们按照自己的本性运行,也可以支持它们之间的有效协作。因此,网络型组织在杭州市政府的实践中广泛存在,女装丝绸行业发展、凯益荟等案例中都存在发达的网络体系。
实际上,单纯地依托层级型组织实现垂直整合或依托网络型组织实现水平整合的情况并不多见,常见的是两类组织形式的混合运用。在多数案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同时出现,整合既发生在各政府主体之间,也发生在政府与外部主体之间,因此,层级型组织和网络型组织都是实现整合的必要元素。
(三)整合机制
根据韦伯的支配理论,支配地位的建立或是借助强制,或是通过满足,或是通过劝说。[4](P235-238)反映到整合中,则或凭借行政命令,或通过利益交换,或基于价值认同。在杭州市政府的实践中,最核心的机制是行政命令,最普遍的机制是利益交换,最隐秘的机制是价值认同。
行政命令在整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无论是政府内部的整合,还是政府与外部主体的整合都是如此。在政府内部,垂直的命令链使各主体之间整合的实现十分便捷。庭院改善工程中的四级联动机制、运河综合保护委员会组织体系、女装丝绸行业发展领导小组,行政命令对政府内部主体的整合可谓一呼百应、令行禁止。而在政府对外部主体的整合中,虽然行政命令的强制作用不再如此直接,但仍十分有效。尽管企业和社会组织拥有法律上的独立性,但政府仍能够对它们施加有力的影响。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政府能够自主地决定它们能否获得正式的法律身份,能否得到法定的税收优惠,能否在某个领域开展活动等等;对于企业而言,政府在执法中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决定了“是否配合政府工作”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强制虽然可以保证“形式上”的整合的实现,但无法保证参与主体积极投入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而“利益交换”可以利用参与主体的逐利动机,通过满足其利益诉求,换取其积极合作。杭州市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机制。例如,女装丝绸行业整体发展所隐含的经济利益,将行业企业和协会聚集在一起;业务活动经费、免费的办公场地、政府的背书成为社会组织进驻凯益荟的动力;提升名望、结交精英、获取课题经费促使专家学者成为社会复合主体中的常客。
除了互惠互利之外,价值认同也是使彼此独立的主体进行有效协作的重要机制。“利益交换”并不能完全解释女装丝绸行业发展中多元主体的踊跃参与现象,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重振核心产业的信念也许更加重要。
(四)参与主体角色
我们用“发起者”、“策划者”、“决策者”、“执行者”来界定参与者的角色。
在整合中,政府的角色与非政府主体的角色有着显著的差别,政府不仅是无所不在的参与者,还是无所不在的主导者,而其他主体只是作为政府的整合对象而存在。政府承担了所有的角色,从发起者、策划者、决策者到执行者无一遗漏。但是,既然是多元整合,就不是政府包揽一切,更何况整合的初衷就是政府要利用其他主体、资源、机制实现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的目标,所以政府也真诚地希望其他主体积极参与。然而,其前提是非政府主体能够在政府搭建的统一框架下活动。
在上述所有案例中,杭州市政府都是唯一的发起者。非政府主体也许会有想法、主张,甚至会向政府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但这些并不能成就一个项目。一切想法、主张、建议、要求,只有成为政府的意志之后,才有可能转变为项目。
与“发起”不同,在项目的策划、执行环节,政府会邀请非政府组织加入,甚至会允许它们参与决策,发挥自身优势。例如,运河综合保护中所有的建设工程都是政府外包项目,由中标的建设公司承担;通过整合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行业专家的力量,杭州市政府解决了如何促进丝绸女装行业发展的专业问题;为减少工程实施中的冲突和矛盾,在庭院改善工程中,政府将项目中的部分决策权下放给了民间庭改办;政府也会邀请民间社会组织代替社区提供基层公共服务……但上述一切的背后,是政府的统一规划和许可。尽管民间庭改办为公众提供了直接参与决策的渠道,但决定是否进行庭院改善、在何处进行庭院改善等重大核心问题的是政府,甚至民间庭改办的出现也是政府培育的结果。而凯旋街道民间社会组织的活跃也在政府的统一掌控之中。政府对在哪些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社会组织以及引入哪一家社会组织有统一的规划。因此,社会组织准入权、活动权都由政府一手把控。“我们的圆桌会”也同样体现了政府对非政府主体优势的利用和政府的主导。鉴于媒体具有专业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政府赋予杭州电视台技术层面的决策权和策划权,但对节目的话题选择、嘉宾确定等,政府都毫不含糊地把控着决策权。
(五)小结:权威式整合
归纳总结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在杭州市的实践中,多元主体、多元机制、多元资源并存,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发挥作用。第二,不同主体和机制之间的整合广泛存在,且类型丰富,既有不同主体之间的整合,也有不同机制之间的整合。这些整合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实现了不同主体、机制的优势互补,完成了单一主体或机制无法独自完成的任务。第三,政府运用多元的组织结构和整合机制为多元主体、多元机制整合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第四,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它是唯一的发起者和重要的决策者,也是频繁出现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市场和社会只有在符合政府统一规划的前提下,才被允许按照各自的机制发挥作用,否则,就要按照政府的意志做出调整。第五,杭州实践中的整合出现在众多领域,几乎涉及政府的全部职能,而且自产生以来不断拓展、不断深化。可以说,此种整合是杭州市政府带有全局性的、稳定的行为模式,我们将其称为“权威式整合”。在这一概念中,“整合”是指多元主体、机制、资源之间的整合,而“权威式”则揭示了整合的核心特质,即政府的主导作用。“权威式整合”是以政府为中心,通过多元的组织形式,利用行政命令、利益交换和价值认同等多元整合机制,动员各类主体(各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发(各类主体掌控的)各类资源,运用各种机制(政府机制、市场机制、非营利机制),高效率地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公共治理机制。
三、解释:权威式整合的生成逻辑
为什么在此时此刻的杭州会出现这样一种公共治理机制呢?
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一元化体制,政府掌控一切的局面不复存在了。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之一是社会中最重要的部分——经济活动——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脱离了政府的直接控制,社会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权。市场化的深入使财富或资源“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蛋糕”中不属于政府的那部分也越来越大,结果是政府之外的资源越来越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民间力量也日益强大。无论是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还是文化领域,独立于政府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多元化的机制、多元化的主体、多元化的资源出现了。相应地,政府的能力由“整一”变成了“有限”,而且越来越“有限”了。
尽管政府的能力相对下降,但是政府的抱负却依旧,表现为无所不包的责任和无比强烈的责任感。这是因为,首先,垄断了政治权力也就意味着背负起了无限的政治责任,意味着政府要负责解决一切问题;其次,政府必须依靠“有效性”来维持自身的权威和稳定,于是发展成为硬道理,发展业绩成为衡量各级政府工作的硬指标;第三,政府和社会共享的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为政府设定了宏大目标;第四,中国传统的“父爱主义”的政治文化也支持全能型的“大政府”。这一切决定了,尽管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但中国政府仍保留着浓厚的“无限政府”色彩。
如此,就形成了两个相互冲突的东西——“有限的能力”和“无限的责任”。虽然政府的客观能力从整一变为有限,但它始终想追求无限的目标、承担无限的责任,也就是说,政府自愿或不自愿地要完成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完成的任务。既然政府仅靠自己的资源实现不了自己的目标,那么它就需要把政府之外的资源也调动起来,为我所用,以实现超越自身实力的目标。因此,在多元化的时代,动员多元化的主体,整合多元化的资源,运用多元化的机制去实现超越自身能力的目标,就显得十分必要。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对多元主体、资源和机制的整合呢?
传统的官僚体制在用行政命令整合资源方面是高效的。然而,如今政府要整合的资源不限于自身内部,行政命令行不通了,合作、协作是必由之路。共同的利益和相同的目标有助于合作的达成,因此合作的实现或通过利益交换,或通过价值认同。当然,在合作的达成中,政府的绝对权威仍然在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重大作用。
然而,仅仅拥有整合的机制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形式恰当的组织结构。依赖行政命令,层级节制的官僚制组织只能完成对政府内部主体的整合,无法有效地整合外部主体,也无法充分利用利益交换和价值认同的作用。而网络恰恰适用于水平的协作或合作,即适用于整合彼此平等的主体。网络中的参与者是彼此平等的,把它们凝聚起来的是共同的价值观或利益上的互惠。
怎样才能把传统的垂直管理体系与新型的水平合作模式有效地整合起来?怎样才能通过它们实现多元整合?杭州市政府创造性地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这就是“权威式整合”。权威式整合具有把(政府擅长的)垂直管理与(网络式组织擅长的)水平协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功能,并借此有效地实现“跨界”整合,这种“跨界”表现为同级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不同政策领域之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
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主义以及政府主导型改革使得政府能够始终保持主导地位;权威主义政体使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能够自主地确立和追求自己的目标,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国家现有体制赋予政府调控经济的强大能力,加之市场还不成熟,使国家干预更加具有合理性,甚至成为必需;社会力量相对薄弱,既不能承担应有的职责,又不能抵御来自政府的过度干预。也就是说,权威主义政体、未完善的市场机制、行政吸纳社会[5]使得政府有能力支配企业和社会组织。这一切构成了权威式整合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支持其有效运行的“基础设施”。
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变是改革开放造就的“大趋势”,如何应对“多元化”的挑战是中国政府在重塑公共管理模式时必须回答的问题,而权威式整合就是杭州市政府提出的一种切实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政府发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多元化进程,但是它又要控制这种多元化,以防其削弱自己的权威。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一元化惯性与多元化趋势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推动和利用多元化的同时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总的来看,通过创建权威式整合,在公共管理领域,杭州市政府较为成功地回应了多元化的挑战,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权威。
四、讨论:权威式整合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权威式整合是对杭州市政府创新性实践的理论总结。无论是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还是相较于目前的西方国家,权威式整合都展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公共管理模式,权威式整合既有变革,又有继承。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掌控一切,一元化体制决定了不存在政府之外的主体、机制和资源,多元整合自然无从谈起,因此“多元整合”是改革带来的新生事物。但是,改革是“有限的”,今日的中国政府仍然有别于西方政府,在多元主体中政府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一元化体制的特有气质。由此可见,以“政府主导的多元整合”为基本特征的权威式整合是一种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公共管理新模式。
治理、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参与式民主等理论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当代西方主流公共治理模式。与权威式整合相似,当代西方公共治理模式也拥有多元的整合维度、整合框架和整合机制。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志愿失灵[6]的存在,决定了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因此西方政府期望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达成全面整合的境界。[7](P212-214)这种整合发生在三个维度,即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水平整合、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垂直整合以及政府与营利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的整合。[8](P29)在上述整合的实现中,垂直型组织和网络型组织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9];同时,行政命令、利益交换、价值认同[10]等整合机制同样发挥着作用。可见西方模式与权威式整合在整合维度、整合框架和整合机制方面有着极强的相似性。
然而,与这些相似并存的还有两者之间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更为根本或重要。在权威式整合中,各类主体是不平等的,发挥的作用也不同,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其他主体属于“配角”。尽管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拥有法律上的独立性,但是行政机制的优势地位决定了政府能够对他们施加有力的影响。正是由于拥有绝对权威,杭州市政府才能顺畅地进入市场或社会领域,才能完全自主地决定整合对象、规划整合形式,才能轻松高效地实现各类整合。作为公共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西方政府也处于“整合”的中心,承担着“掌舵”的角色。然而“掌舵”不同于“主导”,“掌舵”仅仅来源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法定分工不同,并不意味着政府或者政府机制可以凌驾于其他主体和机制之上。在西方公共治理模式中,多元整合建立在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或规则之上,而不是围绕着政府的权威和意志。在中国,法律并不完善,而且政府主导了立法过程,同时在执法过程中政府还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这一点是权威式整合区别于西方主流治理模式的关键之一。
由此可见,权威式整合与西方主流的公共治理模式,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之处。可以说,权威式整合是杭州市政府独创的、不同于西方主流公共治理模式的公共治理模式。
虽然权威式整合来自杭州市政府的实践,但是它适用于整个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局部”与“整体”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同构关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单一制国家,各级政府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以及基础性政策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因此可以通过考察“局部”来认识“整体”,或者说,可以通过对某个地区经验的研究来认识中国的经验。现实中,无论是中央政府制定的纲领性政策,还是各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权威式整合所指称的现象及其逻辑随处可见。有鉴于此,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断——权威式整合也是适用于整个中国的公共治理模式。
[1] 王国平:《培育社会复合主体 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载《培育社会复合主体研究与实践》,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
[2][3] 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载《管理世界》,2010(2)。
[4]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理论》(第二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 康晓光等:《行政吸纳社会》,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八方文化创作室,2010。
[6] 莱斯特·M·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8] Perri 6,Diana Leat,Kimberly Seltzer and Gerry Stoker.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Limited,2002.
[9]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 竺乾威:《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10)。
(责任编辑 武京闽)
Authoritarian Integration——A Case Study of Innov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actice of Hangzhou Government
KANG Xiao-guang1,XV Wen-wen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2.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Technology,Beijing 100083)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caused by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Hangzhou government has made a series of innovative practice.This paper summarizes it as“Authoritarian Integration”——relying on the dominant position,the government integrates the multi subjects,mechanisms and resources in the government,market and society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the nation.“Authoritarian Integration”is different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mode of China in planned economy period and the mainstream modes of western countries,and is therefore a new administration mode applicable to the whole China.
administration mode;integration of multi-element;authoritarian integration
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许文文:北京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讲师(北京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