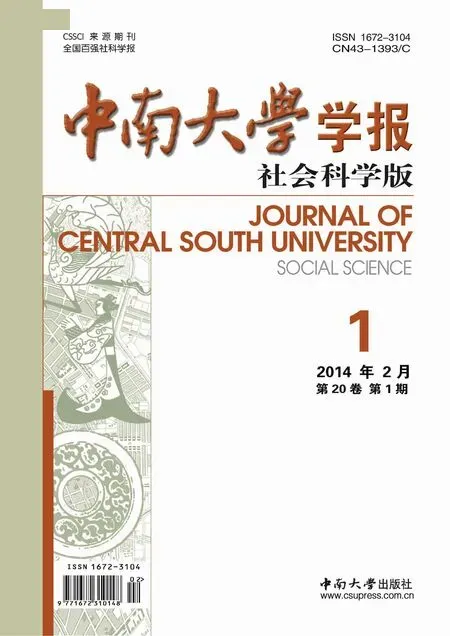马克思对“统一的法律”概念的因革及当代价值
张红艳,谭培文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桂林,541004;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衡阳,421001)
马克思对“统一的法律”概念的因革及当代价值
张红艳,谭培文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桂林,541004;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湖南衡阳,421001)
“统一的法律”是蕴含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命题。马克思从探究社会分层、劳动异化之扬弃和倡导平民文化实践哲学的具体的语境中将“统一的法律”作为批评的靶子,从批判中超越与创新“统一的法律”,建立形式和内容一致的、自由联合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统一体。马克思这一法律思想对指导我们正确理解不同层面主体对构建“统一的法律”的责任;立足现实建立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统一体”;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丰富法律统一体内涵,实现在普遍人权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保障个人人权的有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统一的法律;人权;法律意蕴
一、 马克思对“统一的法律”概念的因革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36)
“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政府”,从形式看,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是树立一个批评资产阶级靶子,但是实质上也是对资产阶级历史进步作用的肯定。在写作《宣言》的具体语境中,“统一的法律”固然有其具体所指,它是十九世纪初以来,席卷欧洲的民族国家统一的政治运动发展的真实写照[2](289-292),也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发达、生产资料的逐步集中以及经济和科学技术巨大变革的真实描述。但“统一的法律”本身不是一个偶用的或临时性的概念。放到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追求国家的统一和政治共同体的建立一直是一个核心的命题,统一的法律和政府也一直是一个红线式的概念。马克思本人不能不对这个有传统底蕴的话语和叙事方式有所继承和发扬。而在马克思的整个国家、政治和法律理论体系中,无论是相对主义的具体制度设计,还是绝对主义的价值理想追求,也都是在既反对“统一”又建构“统一”。
但是,马克思反对此“统一的法律”,并不只是要建立一个“阶级性质不同”的彼“统一的法律”,他有更高、更具实质意义的追求。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的国家思想时就提出了一个国家与市民社会相融合的、与“社会化的人的本质”相适应的“真正的民主”制度设想。①《宣言》中能表达马克思真正远景追求的也是“资本社会化”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更象是借以说事的工具性概念。显然,马克思要建立的“统一体”有着更深层次的意蕴。
马克思之所以要谈“统一的政府和法律”问题,首先当然在于他要面对时代赋予的现代性国家权力集中问题。因为资产阶级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要对一个分散的、组织薄弱的和封建的传统体制进行改制,这种集中必要的权力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历史的必然。但同时,出身于西方的马克思不可不受西方政治哲学特有的“政府-人民”“国家-社会”“法律-道德”等思维模式影响,也不会不受它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影响,所以马克思的学说中也有国家起源说、建立社会共和国说、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说和人类类生活说等。也正是有马克思思想的洗礼和影响,韦伯的政治共同体才会立足于经济与社会的实证范畴,才会添加现实意义“阶级利益”元素。[3](566)而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共同体才会注意清理卢梭、康德等人的共同体内的非实证性道德性因素和话语,并开始注重社会科学的方法[4](185)。
二、马克思因革“统一的法律”概念中的研究范式创新
19世纪4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马克思正是在这种社会分裂的语境中,继承了传统的有关统一的理论话题,指出了统一之下利益分化的实质,并由此预测出了政治和法律统一体崩溃和人性丧失的可能。为了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统一的法律”的解构为什么会而且能够达致他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以及他的“自由人联合体”又是怎样的另一个“统一体”,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研究和分析统一问题的理论新范式。以往我们只知道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了黑格尔们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以及用所谓“无产阶级立场”代替了“资产阶级立场”,这种仅停留在哲学基本原理方面和政治立场上的理解往往很宏大和宏观,没有对马克思的方法论进行精细的分析,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是政治口号式的和基本原理式的,缺乏实体內容。只有对马克思研究政治法律问题的方法有微观意义上的了解,也才能在学术和技术层面上了解马克思对“统一的法律”问题阐述和对未来社会理想追求的理论性实体内容。从马克思对“统一的法律”的解构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研究范式的三大创新。
(一) 探究社会分层理论,建立形式和内容一致的“统一体”
《宣言》的前部分有一句定调意义的话:“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1](31)这表明,马克思不象以往政治法律思想家那样从“国家-公民”和“政府-人民”这样的关系范畴内探讨政治共同体问题,而是从社会不同群体在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即一种社会分层的视角来研究“统一”问题。
思想史上,柏拉图也首先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在知识、智慧和德性上的差异,但他通过“各尽其能、各司其职”的办法化差异为一致,从而得到了一个理想共同体。亚里斯多德以现实和经验的眼光,看出了政体内和统治集团与服从集团、少数人与多数人、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社会阶层利益对立,由此,他明白了城邦不可能是柏拉图的一致性的统一,也认识到了阶层间力量对比决定政策体型,亚里斯多德的统一城邦也就是一种在城邦目的指导下的调合矛盾、平衡差异的“合两体而为中性”的混合式的共和政体。[5](204)
十九世纪初期的政治思想家葛德文可以说是第一个比较系统运用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析政体问题的思想家。在他的代表作《政治正义论》中开篇就是“从人的社会地位来研究他们的能力”。他说道:“首先我们应看到在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里,财产的不均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大量的居民被剥夺了足以保证小康或者安定生活的几乎一切便利条件。”正是这种不利于大多数底层人的社会结构状态,导致“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立法大致都是有利于富人而不是有利于穷人的”。[6](13)由于认识到社会分层结构背后的掠夺、欺骗和专横等,葛德文也解构了“统一的政府”,但他走向的是无政府主义。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更是清楚地表述到:“每个独立的国家分成许多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每个阶层和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每个人同自己的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然比他同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更为密切。”[7](298)亚当·密斯设想通过同情、原谅和宽恕等方式以及共同享用国家带来的稳定、安全等办法来粘合不同阶层从而维护一体的国家,即“各个社会阶层或等级都从属于国家,只是凭借国家的繁荣和生存,它们才有立足之地”[7](299)。
放在西方思想史的历史发展链条上,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无疑是一个环节,这就是在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等所追求的政治共同体或整体国家在形式上通过“统一”的法律和政府变成现实后,马克思又在社会阶级矛盾基础上有新的探索,这又影响了后来的韦伯、哈贝马斯甚至福柯。为了分析方便,马克思把他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层次简单化了②,即“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32)。这样就清楚说明了统一体内是阶级矛盾的统一,它孕育着社会革命,阶级间的利益斗争能让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变为现实。“统一的法律”内实质所要的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同一也是虚幻存在的。有意义的是,正是有了这两大矛盾对点面,社会才不会窒息发展的活力,这种活力能带来新的统一。马克思就既不会象葛德文那样走向无政府主义,也不会象亚当·密斯那样单纯地依靠人们的道德情操并无历史条件地寻求国家的庇护,马克思找到了新的整体存在的前提、形式和发展方向上。因为,“贫富之间的这一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8](43)。马克思正是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內,把黑格尔的辩证运动由理念版变成现实版,又吸收西方思想体系中的人文內涵来建立他新的统一体。
(二) 劳动异化之扬弃,建立自由联合的新的“统一体”
《宣言》文本内明显有这样一个理论逻辑:“统一的法律”之所以要被批判,在现象上最基本的原因和人性上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劳动的异化,“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1](38)。《宣言》延续了马克思在他的重要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详细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马克思在该著作中分析到由于劳动者对劳动产品对象占有的丧失,劳动不是劳动者的目的而是被迫的手段和工具,人则由此使个人生活和人生活也异化,失去了人的类意识,最后也颠覆了自己的本质目的。劳动异化直接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直接的作用使得社会共同性局限在一个资本支配的狭小范围:“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关系的两方面是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9](80)可见在这个统一的共同体内,普遍性是“想像”的;资本高于劳动使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地位和力量是极端不对称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立又使人类没有“类生活”,也就不会有其社会的“类存在”,这是对“统一”的最高层次批判。
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又延续了《宣言》的有关劳动范畴的思路。在这里,马克思详细闸述了具体生产劳动过程中财富分配的剥削性,用具体数据解说了“劳动越是不能给人以乐趣,越是令人生厌,竞争也就越激烈,工资也就越减少”[10](739)。工人和资本家在对立和斗争过程中“统一”于一个生产关系中,这是终将导致统一体的破裂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既新的统一体。
所以,通过对劳动的分析,马克思把政治法律问题立足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基本而真实的场域,也使得他对政治法律问题解说有经济支撑力和现实解说力,这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大突破,受到了后世一些学者的赞赏③。劳动概念的引入还告诉我们,政治和法律统一不光是国家生活公共领域的事,也是人的生活中私人领域的事,从而使得权力产生于权利的理念有了历史、现实感意义的依据和生活气息。同时,这也指明了真正“统一体”的实质,劳动异化破坏了一个“统一体”,劳动异化克服又将带来一个内在目的层次更高的“统一体”,即人的“类生活”,换句话说是“一种自觉的联合,或者说,实现历史之本质的,只能是作为那将物质生活过程置于其共同控制之下的,摆脱了资本拜物教的生产者的未来联合”[11](58)。
(三) 倡导平民文化实践哲学,建立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统一体”
如同柏拉图把“理想国”交于哲学王一样,《宣言》中把未来社会制度的创建寄希望于一个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资本的占多数人口的无产者。因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10](38)。“理想国”奉行真理、知识和善是美的,所以哲学王被推到前台。而《宣言》中之所以推举无产者作为一个历史主体,则在于它在现实运动和斗争中能带来一个不同的“统一体”,因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42)。
马克思把来自现实运动、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冠之有“历史主动性”。撇开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阶级立场”,这反映了马克思的“平民化”哲学转向。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家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社会上大多数人不具有美德、善、理性、智慧、知识等,所以不论如何他们在政治上都倡导一种统治术,柏拉图在构建国家法律制度时,也是由少数人居上作为立法者,国家管理员或向议事会成员来统治平民百姓,如柏拉图所说:“不言而喻,国家本身相当于共同体,因天赋和敏锐的思想直观而被选中的年轻保护者们则居于头脑的顶部而俯视着整个国家。”[12](422)尔后,亚里斯多德的“执政者”乃至奥斯汀的“政治优势者”都是高于大多数平民、“居于头脑顶部的而俯视着整个国家”精英。这当然不是什么“剥削阶级立场”的表白,而是基于稳定、安全的统一体建构的学理思量。洛克和卢梭等开始提到“大多数人同意和决定”“国家全体成员的公意”等并指出:“当人们刚刚联合而成社会时,大多数人具有自然而然的存在于他们的共同体中的整个权力”。[13](63)把统一体内的权力分配给大多数人享有,这是对精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克服。但缺乏现实和历史的根基,因此,只有解释的功能,并被质疑为一种民粹主义。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8](104)这已呈现出平民化哲学的影子。而《宣言》抓住一个从事具体劳动和历史运动的无产阶级,给予其历史创造者地位,这不但继承了自然法学中的民主和人本主义精神要素,又克服了斯宾诺莎的普遍大众不懂哲学的纯学理內判断,从而开创了“实践哲学”意义上的一个平民化哲学新境界。对此,阿伦特说到:“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本来谁都是认为哲学‘不是这个现实世界的’。马克思对传统的挑战,不只是一种暗示,而且他的命题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一点,然而,这是我们在他预言中看到的,即……一直是‘仅仅是为了少数人’的哲学,什么时候变成千万万大众共同根据常识感觉到的现实。”[14](4)
三、马克思“统一的法律”概念的当代价值
(一) 正确理解不同层面主体对构建“统一的法律”的责任
这里理解的统一一是国内法的统一;二是国际的“统一”秩序,其利益包括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就国内来讲,包括几个层面,一是国家政府层面的领导人,要建立真正的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共同体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那种虚幻的共同体,要制定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法律法规,赋予不同阶层、不同主体的统一的权利和自由,让他们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和获得社会财富,而其自身要依法办事,信息公开,统一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二是个人层面,作为独立于社会主体的人,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只有统一,才有社会和个人的安宁,因此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遵守社会共同的规则,遵守国家统一的法律,团结一致地反对藏独、台独以及国外对我国周边领土和海域的侵犯。就国际来讲,人类已进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时代,但人类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危险,少数列强干预别国国政,导致近几年战事频繁,领土纷争一触即发等等。因此,当今国际社会并没有真正摆脱德国思想家康德所描述的那种依靠战争解决争端的自然状态。作为爱好和平的中国人,要努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敦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的法治化,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既法律要重新考虑某些与人类利益相冲突的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正当性、合理性。
(二) 立足现实建立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统一体”
当今时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这项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众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马克思谈到:“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4](511)“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15](300)唯此,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际,执政党人要克服浮躁和懒惰,要从沉迷于世俗的迷信世界中解脱出来,深入实际和实践,调查研究,立足于本土国情、社情、民情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体系,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研究,如加强对妇女权益、儿童权益和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同时,更加关注个人人权的发展问题,尊重人、理解人、发展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三)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丰富法律统一体内涵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法治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尤其要加强对法律的信仰。今天,信条约定、信仰法律已成为法治国家应有的文化精神,有了对法律的信仰,才能成就法律的辉煌[16]。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谈到:“法治立法包含两层含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7](652)尽管这段话没有阐释何为普遍的服从,何谓良法,但已告诉了我们法治的形式要件,其内容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和发展。法治文化体现的法的精神、法的理念跟文化是一体的,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体现公平、正义的依法而治,即法律理念在人们内心的升华,从而对法律的认同和遵守,其内涵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精神层,包括法制的思想内涵、发展历程、价值取向和对法治的认知程度等;二是制度层,包括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和规章;三是物质层,法治教育场所、法治文化遗产等。“法治事业需要整个社会生活主体对法治的信仰和精神支持,而只有在社会普遍民众的普遍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真正基础与根源。”[18]由此可知,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自由、平等、正义,实现法的价值,保障人民权益。
注释:
① 英国学者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时指出:“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在逻辑上是先于、在伦理上是优越于它的两个构成因素:家庭和市民社会。马克思着手表明,设想国家能够具有一种使市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变得和谐并在更高水平上统一它们的普遍特征,这只是一种幻想。……所有这些制度——君主制、代议制议院、官僚制度——实际上在市民社会中都是特殊利益的掩护者:国家只不过是创造隶属于共同体之幻想的空洞的理想领域,……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举荐的政府形式是这样一种形式,在那里不存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它直接与‘社会化的人的本质’是相适应的”。详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205页.
②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划分也是一种理论模式的设定,而不是现实的描述,这也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因为阶级“这个词更像人性的一种要素,而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详见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出版,第304页.
③ 对此,阿伦特评价到:“马克思的从理论到活动,从精神跃到劳动,是在黑格尔把形而上学改变成历史哲学,把哲学家改变成历史学家以后进行的。”详见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00页;哈贝马斯则评价到:“马克思所娴熟的那种严格地客观化视角,成功地打进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传统。”详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第58页.
③ 对此,阿伦特评价到:“马克思的从理论到活动,从精神跃到劳动,是在黑格尔把形而上学改变成历史哲学,把哲学家改变成历史学家以后进行的。”详见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00页;哈贝马斯则评价到:“马克思所娴熟的那种严格地客观化视角,成功地打进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传统。”详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第58页.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 J·M·觊利. 西方法律思想简史[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5] 亚里斯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6] 威兼·葛德文. 政治正义论·第一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7]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9]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12] 柏拉图. 法律篇[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3] 洛克. 政治论·下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14] 汉娜·阿伦特.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16] 田成有. 坚守对法律的信仰[N]. 法制日报, 2011-09-14(9).
[17] 法学字典[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8.
[18] 袁学熙. 国家走向社会的司法权[N]. 法制日报2011-11-02, (10).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of Karl Marx’s unification of law
ZHANG Hongyan, TAN Peiw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The uniform of law has been a very important law topic contained in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rom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research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sublation of alienation of labor and advocating the civilian culture practical philosophy, Karl Marx took the “uniform law” as the target of criticism, and he surmounted and innovated the “uniform law” from the criticism, then established the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ty which is coincident with the form and content,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most people. This legal thought of Karl Marx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u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subject to construct the “uniform law”, based on the reality to establish “legal entity”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culture, rich the connotation of legal entity so as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safeguarding individual human rights on the basis of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Marx;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nification of law; human right; law connotation
A811
A
1672-3104(2014)01-0136-05
[编辑: 颜关明]
2013-03-24;
2013-12-17
张红艳(1968-),女,湖南祁东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南华大学法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谭培文(1948-),男,湖南衡山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