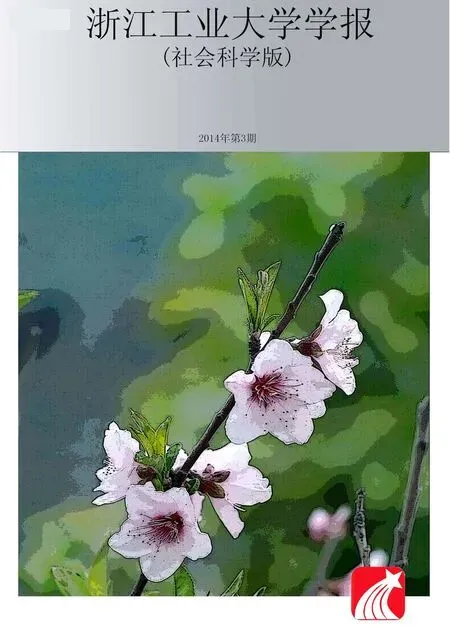《失乐园》创作与圣经叙事探析
(浙江工业大学 之江学院,浙江 杭州310024)
《失乐园》创作与圣经叙事探析
罗诗旻
(浙江工业大学 之江学院,浙江 杭州310024)
《失乐园》以《创世纪》中人类堕落故事为核心情节,它和《圣经》的关联不言自明,同时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本文从弥尔顿的神学思想、《失乐园》对《圣经》的神义论解读以及《失乐园》与《圣经》的叙事结构三个方面,对《失乐园》创作与《圣经》相关文本的关系作初步的探索,并得出结论:作为《圣经》叙事的复叙事,《失乐园》不是对后者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传统外壳之下的变革甚至颠覆,体现了时代和观念的巨大转变。
《失乐园》;《圣经》;神义论;叙事
《圣经》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碰撞融会的结晶,它不仅是宗教圣典,也是深受基督教浸淫的诗人们文学想象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圣经题材、圣经教义、圣经意象、圣经修辞乃至圣经文体和风格都是文学创作绕不开的基本背景,诗人们通过作品向圣经致敬、与圣经对话,甚至与圣经商榷和争辩,以此表达宗教信仰,探寻通向灵魂救赎和永恒福祉的道路。可以说,几乎所有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文学作品都是《圣经》的互文文本。作为英国文学史上继乔叟的诗歌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之后又一丰碑式的巅峰之作,弥尔顿的《失乐园》选取《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类堕落故事作为其核心叙事,无疑与《圣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考察它的创作与《圣经》叙事的关系对我们理解这部经典史诗至关重要。
一、弥尔顿的神学思想与《失乐园》创作
发端于十六世纪英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在十七世纪清教主义的推动下继续深入发展,与之伴随的宗教分裂与观念变革也触目惊心。英国国教与罗马天主教的斗争转变为国教与不信奉国教的各教派的斗争。根据英国宗教研究者柴惠庭的观点,这些不信奉国教者被称为“清教徒”,他们“是16、17世纪英国要求对安立甘国教做进一步改革的新教徒”,包括浸洗礼宗、公理会、长老会派、贵格教派等等[1]。形形色色的各个教派都拥有自己的教义主张、宗教仪式和教会组织方式,宗教思想呈现出色彩斑斓富有层次的局面。这一过程充满了激烈的宗教论争、政治争斗和社会变革,并在清教徒革命中达到了顶点。出身于清教徒家庭的弥尔顿拥有坚定的清教信仰,但他并非一个固定地归属于某个教派的信徒,而是通过研读经典哲学家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通过与底层激进文化的互动,通过与异端神学传统的对话形成了自己的信仰体系。他的神学思想对《失乐园》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失乐园》也成为他表达和探讨内心信仰的重要途径。
激进文化与异端传统对弥尔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是反三位一体说,它强调基督与上帝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坚持上帝为唯一真神,这是对一神论律法的重申。这个唯一真神在十八世纪成为自然神论中的最高存在,反三位一体说也成为现代科学兴起的源头之一[2]。与此同时,它淡化耶稣作为牺牲者安抚者的中间角色,转而着力于对他完美人性的塑造,强调他臻于至善的内心成长和内在修为,这也就摈弃了人与上帝之间存在的神性媒介, 高扬了人性在神恩扶持下自我完善的潜能。《失乐园》中圣父与圣子的对话或可称为辩论。圣子试图为人类请求恩慈与赦免,扮演了人类辩护人的角色,圣父反而由审判者而陷入了自我辩护的被动地位。“是他们自个儿决定的叛乱,不是我:若是说我预知,预知也左右不了他们的错误”①本文所引《失乐园》均依据金发燊先生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后文不再注明。(《失乐园》卷三,116—118行)。圣子不是上帝的另一个身位,而是需要自我证明其合法继承人身份的人性典范。其二是一元论,它主张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那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不存在本质区别。《失乐园》中天使拉裴尔对亚当夏娃解释自己与他们的差别时说:万物“原创造得尽善尽美,一概是原始质,仅赋予质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天使与人“只在程度上有不同,性质全一样”,“你的身躯终将化一切为精神,/随着时间而增益,插翅而腾空,/同我们一样”(《失乐园》卷五,472—499行)。天使与人乃至万物都是上帝的造物,都出自上帝,一概是由尽善尽美的“原始质”构成,差别仅在“质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这就突破了人与神之间原本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人的成长完善开启了无限的上升空间,并传达出众生平等的重要政治意味。其三是对上帝无中生有的创世观的反对。传统神学认为,上帝创世乃是意志创世,没有凭借或利用任何已有的材料和质素,但在《失乐园》对上帝创世的描绘中,创世之前已有“广阔无垠难估量的深渊,/海洋般狂暴、漆黑、荒凉、紊乱”,神子给这深渊、混沌划定了界限,形成了天空和地球,它们最初是“不定形的物质和虚空”,是上帝的灵气在其中“注入生命的能力、生命的暖流”(《失乐园》卷七,211—236行)。可见上帝创世是借用了已有的材料——深渊、黑暗、混沌、虚空都是它的名称,上帝与它之间亦敌亦友的复杂关系成为让《失乐园》研究者争论困惑的难题。从有些文字看它是听命于上帝的仆从,另一些地方又暗示它独立于上帝,是处于上帝管辖范围之外的古老存在。其四是对固定僵化的祈祷模式的反对。当时国王作为英国国教的领袖颁布了《祈祷书》,规定了民众必须按照《祈祷书》进行祈祷,这遭到注重个体与上帝直接沟通的清教徒的强烈抵制。弥尔顿也对此深恶痛绝,他将这种由权力强制的祈祷形式斥为邪恶的迷信,在《失乐园》中,亚当与夏娃堕落前对上帝的赞美感恩都是真挚自发的情感抒发,堪称宗教性的田园诗,堕落后两人的忏悔也真诚自然,毫无矫饰。其五是有死说,它或认为人死后灵魂陷入沉睡直至基督重临才复活,或认为人死后灵魂随肉体一同归于寂灭。《失乐园》中亚当夏娃堕落后展现的人类未来场景中,人堕入生老病死的自然循环,“青春、精力、华年”将变成“衰败、虚弱、苍老”,“一种冷漠抑郁的/沮丧之气将主宰你的血液,/使你精神颓丧,并最后耗尽/生命的香脂”(《失乐园》卷十一,539—546行)。有死说必然导致某种唯物主义,并进而引出对现世生命的看重,对禁欲主义的反对。反禁欲主义也是弥尔顿持有的激进观点之一,在《失乐园》中他大胆描写了堕落前亚当夏娃之间的性爱,称之为“夫妻恩爱神秘的礼仪”,上帝宣称“它是纯洁的”,是人类其他“忠实、合理、纯洁而亲密的关系”的基础,是父子、兄弟等人类伦常的原型(《失乐园》卷四,743—757行)。
反三位一体说、唯信仰论、有死说、唯物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弥尔顿的立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游移于清教主义与激进异端文化之间。在复辟的幻灭中弥尔顿开始相信,人性必须与神性结合才能建立一个新天地、新社会。他是一个伟大的折衷主义者,从激进教义中汲取了大量观念,但他从未将自己归属于任何派别、任何教会,而只是以开放兼容的心态接触各种思潮,并以自身的博学与睿智,最重要的是以内心的良知与信念对《圣经》做出自己的解读,从而形成独特的信仰体系。弥尔顿同样不认为自己的理解便是最终的真理,他所希望的是以他捍卫自身信仰之路的苦乐辛甜帮助他人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在此过程中,他不断回归到早期新教神学传统,求助于原初的路德宗教义,倚重信徒内心的神性光辉以对抗学术化的经院哲学的迂腐束缚。而这也为《失乐园》赋予了一种不同于世俗文学的神圣的宗教使命感,成为《失乐园》崇高风格的深层根源。
二、《失乐园》对《圣经》的神义论解读
功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1858—1917)分析了社会与宗教的关系, 他将宗教视作一种以社会组织为起点和终点的循环链。宗教的重要社会作用表现在人们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反复强化社会各阶层的群体意识,对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塑造作用。具体到个人,这种影响渗透于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成为个人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3]。宗教对社会整体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强化一种统一价值观形成团结某阶层某群体的凝聚力,还表现在将否定这一信仰及相应仪式的群体排斥在外,甚至对其进行驱逐乃至迫害。从该理论视角审视《失乐园》对《圣经》的神义论解读,可以发现弥尔顿通过《失乐园》传达出了重大的时代转折讯息。
(一)自由理性与上帝意志的冲突
如何在上帝的正义与慈悲、法理与仁爱之间达致协调,这是一个古老的难题。这个难题同样困扰着17世纪的英国人。“基督教原罪论与拯救观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尝试”[2]。作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的探讨与求索,《失乐园》选择《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类堕落故事作为史诗题材自然不难理解,他试图回到人与上帝关系断裂的那个原初性的关键瞬间,重临那个初始场景,以“向人类确证条条天道的正确性”(《失乐园》卷一,26行)。
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处于高歌猛进的革命洪流中的弥尔顿坚信,他为之效力的上帝格外钟爱英格兰民族,他拣选了这个民族为他完成伟大的拯救功业。这个上帝是一个理性存在,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与之交流。然而这一理想的破灭将诗人推入了深深的信仰危机。“如果说大空位时期是清教主义分裂的时期,那么,复辟时代则是清教主义理想彻底破灭的时期”[2]。这一理想的破灭意味着这个上帝变得陌生而狰狞,他的意志变得不可捉摸不可理解,诗人的服从随之丧失了依据。“上帝之道”让他无法接受,不仅对于人类始祖的遭遇无法接受,更对发生在1640—1650年代英格兰的一切无法接受。这种困惑通过亚当之口表述无疑:“你的正义似匪夷所思”。然而上帝的全能让他深知必须接受,因为“他的意志即为命运”。他无法将上帝认作邪恶,否则他的人生将如非利士人的庙宇一般坍塌为废墟。上帝即律法、即真理、即历史的真实,正如君主复辟之真实一般,虽然悖理违情却是必须接受的真实存在。此时他迫切地需要另一个上帝,以逃离这个不可知的“暴君”。他需要一个中介,通过这一中介,他可以达到与上帝的和解,因此就有了《失乐园》中的圣子,他代表了上帝的人性层面,在上帝与人类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并且,要将人类救拔于理想破灭后的虚无、喧嚣与混乱,要重建公平秩序与正义。他唯有仰赖《圣经》,唯有严谨执守《圣经》经文。然而问题在于:《圣经》庞杂浩瀚,其中不乏相悖相忤之言,给《圣经》的阐释带来了很大的模糊空间,于是“上帝之言”就成了各说各话的众家之言。一个解决之道是依靠信徒内心之光的引导解读经文,相较于经文辞句更看重其神髓[1]。对这一解决方案,弥尔顿的态度是谨慎而有限制的赞同,将人内心的理性之光作为解释《圣经》的依据引出一个问题:听凭每个人内心的引导,必会将上帝之言导向相对主义的歧路。
(二)自由理性与上帝意志的和谐
怎样寻找一个客观的标准?在弥尔顿看来,这一客观的标准就是个体的合于理性、合于正义的自由发展和利益诉求。这一诉求与上帝的意志契合一致,是上帝造物的目的所在,其理性的客观标准就镌刻于受教育阶层的内心天性之上。弥尔顿所从属所敬重的知识精英的良知正是检验《圣经》解读之真理性的客观标准,也是限制个人全凭一己意愿解释《圣经》所造成的任意性和主观性的准绳。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维护圣经的权威就是维护私有财产和阶级社会。弥尔顿的激进是以不危及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之下,他的思想可谓极端的激进主义。对于深受人文主义传统浸染的弥尔顿而言,个体的自由发展拥有最大的合理性。但这自由不是大众所能拥有的,它只限于精英阶层[4]。在《失乐园》结尾,米迦勒向亚当预示了人类未来,并预言说:“深重的迫害将落到所有百折不挠地崇拜神灵和真理的/这些人头上;其余,多得多的人/将认为宗教在金玉其外的礼仪/和形式中得到满足”(《失乐园》卷十二,531-535行)。这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可得拯救,只有少数受拣选的精英才有能力选择善,他们已内化了上帝的律令,只有拥有了个体的自由才能保证他们的自我实现。在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无条件的民主同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一样,都会导致不可拯救者将恶强加给可获拯救者。这种自由与律令、个人与社会、先定命运与自由意志的张力在《失乐园》中不仅表现为上帝与撒旦的关系,也表现为上帝与耶稣及亚当的关系。
《失乐园》于开篇即宣称:“向人类确证条条天道的正确性”是诗人的创作题旨(《失乐园》卷一,26行)。在这一过程中上帝第一次被公开推上被告席,被要求为其“天道”辩护。全知全能的上帝需要辩护?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从此之后对上帝的信仰、对地狱的恐惧、对永恒审判的敬畏就开始了一个衰退的过程,赏功罚过的世俗道德取而代之。结合十七世纪英国社会背景观照《失乐园》创作,似可得出以下结论:弥尔顿通过《失乐园》向我们展示,对神圣上帝的信仰也需要通过理性的质疑与检审来获得,这是对个人自由的极大张扬,宗教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世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先驱,它们共同开启了走向近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成为“一切近代思想的真正起点”[5]。
三、《失乐园》与《圣经》叙事结构的异同
从现世历史政治的横向层面,《失乐园》的创作与十七世纪英格兰清教革命密不可分。约阿希姆认为,继圣父犹太时期和圣子基督传教时期之后,存在圣灵第三历史时期。这是圣父圣子隐退、圣灵分裂内化为个体信仰的时期,是善与恶、苦与乐、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混杂不可分的时期[6]。在弥尔顿看来,复辟后的英格兰就处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直到基督重临的那一刻。《失乐园》中发生在天国、地狱、伊甸园三个时空场景中的事件都暗示了政治关系的思考与论辩。而从基督教宗教发展的纵向层面看,自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确立《圣经》作为人们信仰和行为的准则,《圣经》就在基督教世界成为至高无上的教义典范。《失乐园》扮演了与《圣经》对话的角色,作为一名诗人,弥尔顿明白,叙事结构和文本隐喻的变化比教义的变化重要得多,它们会在想象力和情感层面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信仰与观念[7]。
(一)同中有异的U形叙事结构
从叙事结构看,《失乐园》与《圣经》呈现出既相似又不同的面貌。弗莱在他研究《圣经》的经典著作《伟大的代码》中指出,《圣经》叙事是上帝的子民反复背叛与回归的叙事。它呈现出一个U型结构,背叛之后落入灾难和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的高度。在文学作品中,这是标准的喜剧形式,在喜剧中,一系列的误解与不幸使剧情跌到令人惊吓的最低点,然后来了某个幸运的转折,把全剧的结尾推向快乐的结局。因此,《圣经》可以被视作一部“神圣喜剧”,其中包含数个重复出现的U形结构叙事:《创世纪》之初,人类失去了生命之树和生命之水,到《启示录》结尾重新获得了它们。以色列一次次在异教王国的权力面前没落,每一次的没落之后都有一次短暂的复兴,重获相对的独立。较小的还有《约伯记》中约伯的灾祸与繁荣,耶稣讲道中浪子回头的故事[7]。对于异教王国和反基督,这个叙事则是一个倒置的U形,在文学中相应地属于悲剧的形式。《圣经》对待异教王国和反基督悲剧的态度是反讽,即只强调最终的突然失败,而淡化或无视在失败之前的成就功业中的英雄因素。《失乐园》叙事相较之下更为复杂。总的来看,它包含的是两个叙事,一个是撒旦堕落复仇的叙事,另一个是亚当夏娃创生堕落遭受驱逐的叙事。在前一个叙事中,撒旦经历了由天国坠入地狱又上升至伊甸园的过程,这一上升过程在他复仇阴谋得逞时达到顶点,但这个上升的行动是一个“伪事件”,这里的上升即更深的沉沦,到达的顶点也是坠落的低点——在他凯旋而归时他和部属都被变为了蛇形。在后一个叙事中,亚当夏娃由伊甸园中为上帝钟爱的纯洁的造物堕落为背叛者和罪人,被逐出完美的伊甸园,这是一个倒置的U形,但两人的忏悔祷告和救赎希望又预示着重新爬升的可能。
(二)各有侧重的叙事策略
《失乐园》叙事与《圣经》叙事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给U形曲线上升和下降过程分配的侧重点不同。《圣经·创世纪》中对人类始祖堕落的叙述只有394个字,其后的叙述都可视为漫长的爬升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包含数个再次堕落反复,以及每次堕落后又忏悔救赎的亚叙事。这一爬升过程至《启示录》的基督解救达到顶点。而《失乐园》将《圣经·创世纪》中短短394字扩充为长达九卷的史诗,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堕落的诱因(撒旦的诱骗)、堕落的过程、堕落的惨痛(堕落前的纯真幸福)以及堕落的后果(逐出伊甸园)。相比之下堕落后的忏悔救赎只占三卷篇幅,仅仅在米迦勒向亚当预示人类未来的篇章中模糊地暗示了救赎的可能性。对于撒旦的叙事,《失乐园》与《圣经》的差异更大。《圣经》中并没有直接的关于撒旦的文字,只有关于明亮之星卢西弗的少量叙述,后来又将卢西弗与埃及法老尼禄等同起来,更不见关于撒旦反叛被赶下地狱的描述,当然也就不存在撒旦来到伊甸园诱惑亚当夏娃的叙述。相比之下,《失乐园》对撒旦叙事倾注了大量笔墨。读者看到更多的是撒旦叙事的U形曲线的上升部分,在撒旦身上有古典英雄的形象,他结合了阿喀琉斯的勇猛与奥底修斯的谋略,他不屈不馁的精神、身先士卒的勇气、冲锋陷阵的英武、机敏狡黠的智慧使读者很难不产生钦佩乃至赞赏的认同感,也给《失乐园》增添了复杂含混的解读空间,相形之下,对他最后失败的反讽不免给人以底气不足之感。
《失乐园》与《圣经》叙事结构的差异深刻地影响着两个文本呈现的面貌以及它们各自传达的内在涵义。两者的差异体现的是产生两个文本的时代的差异,更体现了宗教与诗歌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弗莱所说,在宗教的“如此”和诗歌的“假定如此”之间,永远会存在某种张力[8]。
在弥尔顿看来,世间恶之存在的根源在于人之堕落,被逐出伊甸园那个原初的关键性瞬间使人的本然生命与上帝赋予他的神圣生命之间的关联断裂了,人陷入罪的沦落,其存在变得破碎不堪。历史现实的残酷血腥,政治领域的变幻反复,革命与复辟中的血雨腥风,突现出人的生存的悲
苦与荒唐。要抑制人世与人自身之恶,祈求生命的重生,恢复与上帝的原初关系,唯有回到那个堕落的初始瞬间,通过回忆人在上帝怀抱的故土中的存在,才能使沦入罪恶中的人重新回到神性源头。因此,弥尔顿返回到作为上帝之言的《圣经》,以此探索人之存在的本来面目和本真意义,以期将人类救拔于理想破灭后的虚无、喧嚣与混乱,重建公平、秩序与正义。但是,这一返回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传统基督教外壳之下的变革甚至颠覆,它体现了时代和观念的巨大转变。将两个文本并置,结合宗教维度探索《失乐园》的诗歌世界,必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也将使我们对这部史诗拥有更深的理解。
[1] 柴惠庭.英国清教[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10,188-189.
[2] 许洁明.17世纪的英国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83,186,197.
[3] 迪尔凯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23.
[4] Christopher Hill. Milto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M]. New York:Penguin Books,1979.346.
[5] 蔡琪.英国宗教改革[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74.
[6] 丁光训,等.基督教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50.
[7] 诺斯罗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2,220.
[8] 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82.
(责任编辑:金一超)
Milton’sParadiseLostandtheBilbleNarrative
LUO Shi-min
(Zhijiang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4, China)
With the fall of man in Genesis as its core plot, Paradise Lost’s connection with theBibleis obvious, meanwhile,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m is no less so. Through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 and disparity between the two texts from theological and narrative angles, this article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thatParadiseLostis not a repetition but a transformation or even a subversion of the Bible, reflecting a huge change in the society and era at large.
ParadiseLost;Bible; theodicy; narrative
2014-04-09
罗诗旻(1980-),女,湖北大冶人,讲师,硕士,从事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I106.2
A
1006-4303(2014)09-03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