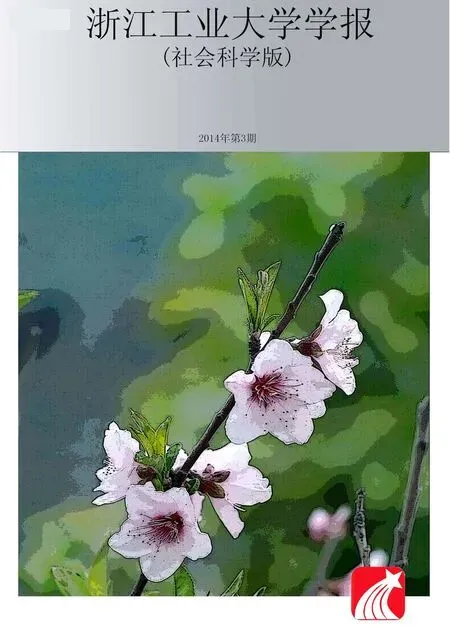元小说与元电影的叙事研究
——以《苏菲的世界》、《开罗的紫玫瑰》为例
,
(1.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2.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元小说与元电影的叙事研究
——以《苏菲的世界》、《开罗的紫玫瑰》为例
周洁1,付方琴2
(1.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2.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元小说、元电影是“元叙述”寄生的不同体裁,在叙事方面有类似于“大盒套小盒”的故事架构。“戏仿”、“拼贴”、“时空转换”等叙事技巧,复调的叙事架构,在自我指涉的过程中颠覆了艺术的形式,消解了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本文从叙事学角度出发,以元小说《苏菲的世界》和元电影《开罗的紫玫瑰》为例,比较元小说与元电影的叙事策略。
元小说;元电影;叙事;
“元小说”(meta-fiction)最先由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威廉·加斯在《小说与生活的人物》一书中提出,之后多位学者对其进行阐释。元小说主要特征表现为自动呈现小说创作的机制,揭示小说的虚构特质,并有意识地将读者的质疑点集中在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上,具有反讽效果以及后现代小说的自反意识。18世纪英国作家斯特恩的《项狄传》是“元小说”的鼻祖,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将“元小说”推向新的高度。“元电影”(meta-cinema)是关于电影的电影,包括所有以电影为内容、在电影中指涉电影的电影,在文本中直接借鉴、引用、指涉另外的电影文本或者反映电影本身的电影[1]。元电影并不能单一被看作电影类型或电影流派,它更像一种电影思维。元小说改编的电影并不一定是元电影,元电影必须要包含电影自身的东西。
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的小说《苏菲的世界》中有三个叙述者——哲学家艾伯特、苏菲和席德。前半部分主要描写苏菲的生活和哲学家艾伯特的哲学课程,下半部分直接跳转到现实中的主人公席德阅读父亲为他提前准备的生日礼物——一部名叫《苏菲的世界》的小说手稿。苏菲、苏菲的亲友和哲学家艾伯特的世界相互参照、穿插,构成一本典型的“元小说”。而美国影片《开罗的紫玫瑰》则是一部“元电影”。影片讲述女餐馆服务生塞西莉亚生活的全部乐趣,就在于独自去电影院观看《开罗的紫玫瑰》,看了一遍又一遍后,银幕上的男主角汤姆突然走下荧幕,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这类引用、指涉另一部电影,出现主人公抽离出现场进行自议,或是通过电影来反思艺术与现实生活、虚构与真实的关系,是“元电影”的典型特征。
元小说、元电影虽然在叙事方面具有“元特征”,但终因小说和电影分属不同媒介而显差异。电影叙事主要以影像符号为前提,而小说则以文字符号为基础;电影逻辑严谨,小说结构松散。这表明即使运用同一叙事技巧,其使用方式和呈现效果也各有不同。
一、随意自由的时空转换
小说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场所。小说发现人们的可能,电影展现“存在的图”。这里的“存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时间和空间。
“随意自由的时空转换”是元小说与元电影的一大显性特征。在叙述次序上,元小说注重时间转换,元电影侧重空间转换。
叙述(话语)与故事的时间关系在《苏菲的世界》中呈现为“回顾叙述”(retrospective narration)和“嵌入叙述”(embedded narration)的结合。“回顾叙述”指故事中的事件在发生之后被讲述。这里主要指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关于苏菲的生活和她的哲学史课程的叙述部分。下半部分直接转为“嵌入叙述”,叙述行为随着被谈及的行动而变化。这种方式常在书信体、日记体小说中出现[2]。元小说《苏菲的世界》包含三个层次——次故事层里哲学家艾伯特通过书信、录影带、面授等方式教授哲学史课程的时间维度;故事层中主人公席德阅读父亲为他提前准备的生日礼物——一部名叫《苏菲的世界》的小说手稿的时间维度;话语外层中作者叙述的时间维度。其中“中世纪”一章节里,哲学家艾伯特说了这么一段话:“上帝的时间和人类的时间不同;我们的‘现在’不一定是天主的‘现在’,人间的几个星期并不等于天上的几个星期”[3]。于是苏菲想到席德的父亲寄的明信片内容“对于苏菲来说是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对我们而言不见得这么长”[3]。这番描述打破了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一元论,也揭示了苏菲、艾伯特的被虚构世界与席德、艾勃特的虚构世界以及读者的真实世界在“时间性”方面的割裂与差别。
元小说和元电影在叙事空间方面通过故事空间(包括事件、人物以及在话语展现和发展的情节所发生的地点)和话语空间(叙述者的空间)两个方面呈现。在传统小说和电影中,后者完全不必指出,而元小说、元电影中话语空间和故事空间相互分离,将媒介的虚构性真实化地表现出来。
除此之外,小说塑造的空间较为间接,需要读者想象重新编码。小说中间部分,苏菲变成了席德阅读的《苏菲的世界》中的虚拟人物,苏菲和艾伯特活在席德父亲笔下的虚拟世界,任由他操控和摆布。最终苏菲和艾伯特、席德父亲和席德出现在花园里,他们分属不同的空间——隐性空间和实体空间。苏菲用扳钳敲席德的额头,席德感觉很痛,却看不见苏菲的样子。这是需要读者自行想象的二元空间,小说需要读者“意会”文字符号,将它们从头脑中转化为生动的空间形象,从而实现抽象空间的具象化。
相比小说,从电影的一些场景可发现,电影叙述时间相当于故事时间,电影的叙事空间以“场景”为具像,在电影中空间和时间扮演同样的角色。一方面,电影以空间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电影把时间的矢量加于图像的空间维度上。徐葆耕在《电影讲稿》里将电影空间分成三重建构——物性空间、心理空间、超人(神性)空间。物性空间指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心理空间侧重于人物心理的刻画描摹,而超人空间指向超越经验的空间,不受现实物质的界限,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和魔幻化特征[4]。显然,《开罗的紫玫瑰》中银幕上的男主角汤姆突然走下荧幕,现实中的塞西莉亚走进银幕的世界体验生活都属于超人空间。这随意自由地进出银幕空间体现出了电影具有更为直观清晰的空间感,将“打破媒介的边界”、“循环往复的媒介解构与建构”的元特质完全表露在观众的视线中。《开罗的紫玫瑰》体现了元电影的自反性。电影作为人们生活的精神出口,提供了虚假满足欲求的方式,逃避现实的观影过程,具有制度化的蒙蔽与欺骗,这些都是元电影《开罗的紫玫瑰》所批判和嘲讽的地方。
二、戏仿和拼贴
戏仿,指在作品中对其他作品进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戏谑、游戏目的的模仿转换而成为新的作品。《苏菲的世界》中“浪漫主义”这一章节中哲学家艾伯特借用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缩写的戏剧《皮尔金》的台词:“没有人会在第五幕演到一半的时候死掉”[3]。随后他讲到诺瓦里思的未婚妻也叫苏菲,她在十五岁的时候去世了。故事中的苏菲脸色凝重,哲学家以戏仿《皮尔金》的台词对苏菲说:“可是你不用担心你的命运像诺瓦里思的未婚妻一样”、“我是说任何一个读到苏菲和艾伯特的故事的人都可以凭直觉知道后面还有很多页,因为我们才谈到浪漫主义而已”[3]。这属于对源文本片段内容的戏仿,其典型的运作机制就是在当前文化语境下对源文本叙述话语进行改变方向或语气的转述。转述的目的在于置换语境或夸大某些文类的特征,使其从原本的框架中凸显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
元电影《开罗的紫玫瑰》里塞西莉亚和从银幕里走下来的考古学者汤姆进行了美妙的约会。他们去餐馆吃饭,付账时汤姆拿出拍摄电影《开罗的紫玫瑰》的假美元道具。他们去废弃的公园谈情说爱,戏仿罗曼蒂克的电影,汤姆突然好奇:“画面淡出在哪里?”“通常深情一吻之后,画面就会淡出”。这些戏仿情节将电影的虚构性滑稽戏谑地表现出来,产生喜剧效果。
拼贴是文本(广义)的创作阶段所使用的一种技巧,这种技巧的特征在于从整体上审视是新的,但组成它的每个部分却是原有的。拼贴技巧最早出现在乔伊斯《尤利西斯》和帕索斯《北纬四十二度》中,之后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广泛使用。巴塞尔姆认为“拼贴原则为20世纪所有传播媒介中的所有艺术的中心原则”[5]。《苏菲的世界》里使用众多拼贴技巧——书信、明信片等叙事形式,还将“小红帽”、“爱丽丝”等童话人物拼贴进故事中来。在“马克思”这一章节中,引入安徒生童话里的人物卖火柴的小姑娘和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中吝啬的资本主义者史吉吉,重构经典故事。盯着账本的史吉吉面对卖火柴的小姑娘不愿施舍一分钱,他说“我是靠努力工作才出人头地的。只要工作,就不怕没饭吃,这就叫做进步”[3]。戏仿的情节主要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冷漠无情的社会现状,为接下来谈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抛砖引玉。
电影中的拼贴主要有影片风格的拼贴、角色的拼贴、影片场景的拼贴以及影片人物形象的拼贴。《开罗的紫玫瑰》中通过对历史意象的拼贴,塑造出超真实的空间。电影故事背景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影片中女主角塞西莉亚的丈夫找不到工作就在路边丢钢板赌钱,无所事事的人们、冷冷清清的街道、废弃的游乐场等风格化的时代意象拼凑形成了关于经济萧条时期的整体意象,还原那代人的集体记忆。而当塞西莉亚走进电影中的生活,出没于各种鸡尾酒会、俱乐部等场所,熟悉的场面再现了好莱坞纸醉金迷的生活,历史的意义被表面化为影像符号群,真实的历史不可阻挡地陷落了。
三、自我指涉和复调结构
元小说的另一大特征便是极具自我表现意识的叙述人随意地评论叙述(小说虚构)的过程。叙述人挣脱叙述文本对他的束缚,打断叙述流,在编故事的时候随意评论正在发生的事情,以期语言的操作手段和现实表现性的剥离与隔阂。
自我指涉呈现出元小说和元电影的复调叙事结构。复调结构的小说摒弃了“全知全能的独白小说”,小说中不同人物发声,谈论自己的观点,而作者自己的声音几乎淹没在复调中。巴赫金曾强调复调小说的复调特征即语言被用来瓦解权威和解放权威的声音,这一特征和“元特征”不谋而合。因此在叙事人称多元化的元小说中,复调结构被充分使用。《苏菲的世界》里苏菲秘密地接受哲学启蒙训练,但当她收到席德的父亲寄来让她转交给席德的生日卡片后,她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哲学家艾伯特也会口误叫她席德,苏菲感到十分不解,艾伯特一语戳穿真实“你可以注意到席德的父亲已经开始透过我们的嘴巴讲话了”[3]。认识到自己的虚构身份后,他们开始反抗作家的意志。在《苏菲的世界》中常会有刻意打断情节开始自我评论的指涉性话语,小说中的人物告诉你叙述者正在编造他的故事,并邀请你加入到破坏叙事的行动策划,模糊小说叙述的本质。
复调结构也为电影叙事提供蓝本和启迪。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说:“视觉的能指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并发”[6]。爱森斯坦所说“蒙太奇,其中每一个镜头跟下一个镜头的联系,不仅通过简单的标志——一个运动、一个调式的区别、一个主题的展示或一类似之物,而是通过一系列多线条同时性展开,每一线条既保存其独立的结构秩序,又与整个段落组成的总体秩序不可分离”[7]。这在元电影《开罗的紫玫瑰》中也有明显的运用。在考古学者汤姆离开银幕后,银幕前的演员们对着摄像机开始对话、言语、评论,由于整个故事已经乱套,所有既定的人物情节台词难以重新演绎,慌乱中的演员们想到了神父,可神父一到发现这是第二场,他的戏份要到下一场才出现,便从画面镜头中离开。于是演员们开始辩论关于故事的定位——“关于一个追求自我实现的男人的故事”、“它是一个复杂心灵受伤的故事”、“是金钱对真爱产生影响的故事”。银幕中的演员原本是故事里讲述台词演绎行为的机器,而当原先的故事无法再进行下去的时候,他们恢复自我意识,重新审视反思电影、故事的虚构性和幻灭感。
复调结构在元电影中普遍运用,因为电影将画面、音响、对话、文字和音乐分置成不同的声部进行演绎和呈现。它们既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又形成交流性,声音、文字、画面多重叙事有机结合[8]。而在元小说里,复调结构以多元叙事的姿态出现,作者—创作者,被读者—读者,被评论者—评论者,多重叙事角色已不再是作者意识的“传声筒”,他们开始释放自我意识,为争取自我独立、自由而发声。
元小说《苏菲的世界》的时空自由转换随着作者的不断反思而变动。元电影《开罗的紫玫瑰》通过超人空间将想象付诸于现实能力,打破时空的真实性和逻辑性。元小说以源文本为戏仿素材,进行话语的变调;以书信、明信片、广告等媒介形式或从经典故事中截取进行拼贴,呈现出戏谑的美感;元电影则以情节、人物为戏仿对象,将影片的道具、场景、服饰等符号拼贴成时代的环境,呈现出历史的超现实感。在复调结构方面,叙事人称多元化为元小说的特征,叙述者打破他人的言论,虚构故事却又消解其虚构的意义,模糊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元电影中的复调在于画面、音响、对话、字幕和音乐分置成不同的声部排列组合,蒙太奇技巧把电影变成像复调小说一样。小说和电影两种媒介在叙事功能上有着不同的侧重。小说文本在话语层面自由多变,而这些是注重画面的电影无法任意而为之的部分。后现代文类元小说注重解构“文本创作的机制”,将叙述者的自反意识展露无遗,可电影往往需要整合叙述情节,展示人物行为和人物意识的同一性。元电影中的“创作机制的虚构性”,不再是元小说文本中“自反意识”所要揭示的附加品,“虚构”已然成为元电影的奇妙情节。超现实的情节、黑色幽默的台词将读者置于亦真亦幻的世界,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容易让观众抓住导演意识的画外音,在电影文本间实现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这也正是后现代语境中“元意识”的植入美学。
[1] 杨抒.电影中的电影:元电影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1.
[2] 雅克布·卢特.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6.
[3] 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
[4] 徐葆耕.电影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0.
[5] 杰罗姆·克林科维兹.巴塞尔姆访问记[J].世界文学,1999,(1):331.
[6]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0.234.
[7] 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6.
[8] 曾超.元小说中的复调[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8):46-49.
(责任编辑:金一超)
ANarrativeStudyofMeta-fictionsandMeta-cinemas——A Case Study of “Sophie’sWorld” and “ThePurpleRoseofCairo”
ZHOU Jie1, FU Fang-qin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Meta-fictions and meta-cinemas are different genres of parasitic “meta narrative”, and have similar features to the story of “big box set in a small box” in narrative. Narrative skills such as “parody”, “colla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polyphonic narrative structure subvert the form of art, and disp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reality in the process of self-reference. This paper, from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with a case study of the meta-fiction “Sophie’sworld” and the meta-cinema “ThePurpleRoseofCairo”, compared narrative strategies between meta-fictions and meta-cinemas and explored the “meta” aesthetics behind novels and movies.
meta-fictions; meta-cinemas; narrative
2014-03-24
周 洁(1989-),女,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付方琴(1990-),女,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
I0-03
A
1006-4303(2014)09-029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