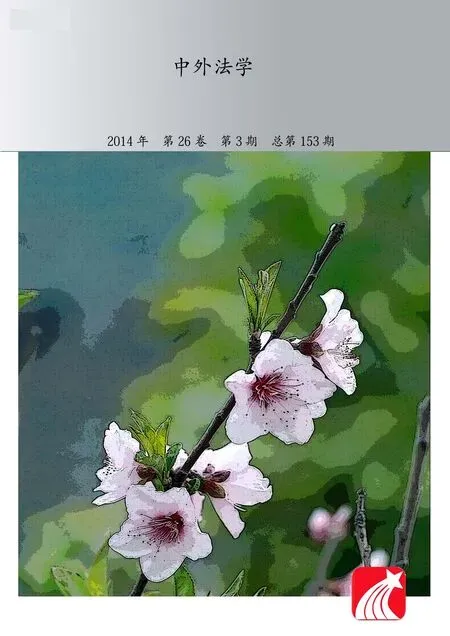现代政治代表的历史类型与体系结构
刘 刚
引 论
在中国宪法文本中,代表一词在以下五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第一,“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7段。第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同上注,序言第10段。第三,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见前注〔1〕,第一章总纲;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驻外全权代表;*见前注〔1〕,第67条第13项。第五,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见前注〔1〕,第16条第2款。
从修辞角度观察,上述涉及代表的条款体现出这样的表述格式:第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先进的文化,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统一战线下的各种力量;第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第四,驻外全权代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职工代表大会代表职工。上列各种表述最终可以抽象简化为这样的格式:A 代表 B。在此结构中,A是代表者,B是被代表者。通过代表这种机制,当人们看到A时,在某种意义上想到的是B。
从语义学来考察,代表一词亦展示出同样的结构。(动词意义上的)代表是指,“使并未真正在场的某物再次登场”;*Gerhard Leibholz, Das Wesen der Repräsentation und der Gestaltwandel der Demokratie im 20. Jahrhundert, 2. Aufl., 1960, S. 26.从代表一词的词源来考察,“代表(representation)就是使某物再次(re)出场(presentation)”。*Hanna F. 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8.
当进一步考察“A 代表 B”这个基本结构时,人们至少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第一,谁是代表者,谁是被代表者?第二,被代表的究竟是什么?第三,通过什么方式实现代表?第四,代表者与被代表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参见Johannes Pollak, Repräsentation ohne Demokratie, 2007 , p.1.; Dieter Grimm, Repräsentation, in: Görres-Gesellschaft, Staatslexikon (1988), Bd. 4, S. 878.
当人们抛开代表机制所处的具体语境,抽象地从语义或修辞角度考察代表时,所得到的只能是上文所示的一种内容空洞的结构。虽然这个结构给我们提示了考察代表时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但是,若离开具体语境,这些问题根本无法得到回答。因此,仅从抽象的代表结构入手,上文所列的宪法文本中的代表场景只能得到初步的阐释。据此,我们只能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代表”语境中是代表者,政治协商会议在统一战线语境中是代表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层面是代表者。在三种语境下,被代表者某种意义上都和人民有关。可是三个代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人民在哪些不同的意义上被作为被代表者看待?三个代表者与人民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些对于揭示中国宪法的代表结构至为关键的问题,靠一个脱离具体语境的抽象代表结构是无法回答的。
因此,代表结构必须被置于特定的语境中。*“代表”一词至少在认识论、法学、政治学、哲学、神学的语境下被使用。本文所讨论的代表,限定在法学和政治学的语境当中。系统地在不同语境中讨论代表概念的文献,英文和中文文献尚不多见,德语可参见, Hasso Hofmann, Repräsentation, 4. Aufl., 2003.就本文目的而言,代表结构要放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中考察。因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见前注〔1〕,第2条。就此而言,中国宪法的代表结构乃是人民主权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本文除导论和结论之外,主体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笔者将从历史的角度,以绝对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为三个理想类型,考察代表结构的各个维度在这三种不同政体形式中的安置模式,从而为解释人民主权语境下的代表结构提供类比参照。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笔者将从系统的角度,揭示民主共和制语境下解决代表问题的各种方案,并努力把这些方案整合进一个体系结构当中。在最后的结论部分,笔者将以前文的历史和系统考察为基础,提出思考中国宪法代表结构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一、 代表制的历史类型
当人们直观地感受政治现象时,它通常表现为一种命令——服从的支配关系。*纯粹的直接民主除外。就此而言,作为一种经验事实,不同历史时空下的政治尚未显出差别。但是,围绕此种事实性的命令——服从关系,人类智慧又制造出许多不同的说法。这些不同的说法就变成命令——服从关系的不同类型。由此,命令——服从的支配关系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经验事实,而经由人的解释转变为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现象。因此,“支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自足的,而总是需要被正当化,借助于正当化论证,这种社会现象获得了新的本质。……在支配现象的背后,总存在着其他价值和秩序”。*Rudolf Smend,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 und andere Aufsätze, 1955, S.150.这些其他的价值和秩序,就构成不同的代表类型。当命令——服从的支配关系获得规范意义后,命令者在发号施令时,就不会使用“你必须服从,因为我比你强大”这样的逻辑,而是要诉诸于“你应该服从,因为我的命令代表了某种更高的价值”的修辞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纯粹的直接民主之外,任何一种统治关系背后总存在某种特定的代表结构。*在直接民主的情况下,政治背后的形式原则就不再是代表,而是同一性。关于代表和同一性作为政治形式的两个原则,参见(德)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页218以下。
在下文描述不同的代表结构时,所预设的前提是:不同类型的代表结构都在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政治统一体如何形成?这个共同的问题构成不同代表类型之间进行对比参照的基础。政治统一体并非一个含义明确的概念,但是,它被使用的频率却相当高。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无需去梳理它的各种含义。*概念性的探讨主要可参见Ulrich Scheuner, Das Wesen des Staates und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in der neueren Staatslehre, in: Ulrich Scheuner, Staatstheorie und Staatsrecht, 1978;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als Schlüssel zum Staatsrechtlichen Werk Carl Schmitts, in: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Recht, Staat, Freiheit, 2006.真正重要的是阐明政治统一体这个概念所涉及的问题逻辑。“在人类生活的现实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方式”,*Konrad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 Aufl., 1995, S.5.在此情况下,国家的任务就在于把它们“约束在统一的行为和效力之下,营造出政治统一体”。*同上注,S.5。概言之,政治统一问题的根本逻辑或曰任务也就在于“从多到一”。*Konrad Hesse,见前注〔15〕,S.5。关于“从多到一”的论述,另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的各篇论述。
任何一种特定的代表结构实际也就是在处理“多”与“一”的关系。“多”与“一”各有存在的独立性,二者没有被同一化,否则便是直接民主,而不再是代表制。“多”所指的乃是具有各种利益和偏好的经验世界当中的人,“一”乃是把这些杂乱的人群凝合为一个整体的纽带。至于这个纽带到底是什么,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回答。“多”与“一”并存的这种情势,暗示了任何一种代表制都包含一种二元化,也就是说,“多”与“一”之间存在内在区别。这种区别或者是外在的,如下文要讨论的绝对君主制;或者是内在的,如下文要讨论的民主共和制。而不同代表结构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处理“多”与“一”之间的联系时的不同方式。
下文将选取绝对君主制、立宪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三种政体类型作为考察对象,阐述代表机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在这些不同政体类型中分别以怎样的方式得到回答。此处选取的这三种政体并未在逻辑上周延地涵括历史上所有的类型,而是限定在主权概念兴起、现代国家出现之后的西方语境下的政体类型。依照这种时空限定,主权国家在西方兴起之后,完成了从绝对君主向民主共和的转变,君主立宪是此过程中的过渡阶段。在代表问题的语境下,这里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包括:第一,被代表的是什么,或曰“一”是什么?第二,代表“一”的代表者与经验层面的人群之间的联系机制是什么,或曰“一”与“多”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第三,代表者的产生方式是什么?
(一)绝对君主制
就其法律特征而言,绝对君主制可以定义为:君主的意志在法律上享有最高效力,不受任何其他意志限制,君主独享最高的统治权。*参见Georg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3. Aufl. , 1922, S. 669.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其他意志,是指经验意义上的人群的意志,也就是其臣民的意志。所以,君主意志不受限制,是指不受其臣民意志的限制。然而,君主意志这种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威亦有其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被代表物,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一”。以此为基准,绝对君主制又可以分作两种类型:
1.诉诸超越权威的君主制
在这种模式下,君主被视为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同上注,S.670。君主出自上帝,是上帝的肖像。*参见施米特,见前注〔13〕,页304。这是中世纪的普遍观念。根据这种观念,整个宇宙是一套统一的秩序,“是一个完整的王国,上帝是这个王国的君主”。*Otto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 Cambridge, 1922, p.30.尘世的教会和国家都只是这个统一秩序的一部分。作为其组成部分,尘世的国家必须模仿整体秩序。通过这种模仿,上帝的秩序在尘世的有限范围内亦得以再现(代表),“而完成此目的的最佳途径是,把尘世的统治权赋予单一的一个人。”*同上注,S.32。从类比上帝作为统一秩序之君主的意义上说,这个单一的个人自然就是尘世国家的君主。
在这种模式下,被代表物或曰政治统一体的“一”是上帝的统一秩序。这就意味者,作为代表者的君主的权威并非来自于其臣民,也就是说,并非来自于“多”。如果臣民全体在并不精确的意义上被看作国家的话,那么,君主是高于和外在于国家的。君主和臣民之间存在一种外在意义上的二元性。君主是把一套外在于臣民共同体的秩序安置在臣民共同体当中。臣民对于君主行使其代表职能来说,并无法律上的价值。
从其产生方式来看,绝对君主制下的君主多以世袭的方式产生,并经过某种仪式获得神圣性。这导致君主和臣民,或曰“一”和“多”之间的外在二元性在形式上得到强化。
不过,从绝对君主制逻辑的内部来看,其中实际蕴含着非绝对化的因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君主以一个肉身同时承载两种角色:他一方面是拥有七情六欲的凡人,另一方面又是始终代表上帝意志的神圣权威。这两种角色存在混淆的可能。一旦君主凭其神圣权威满足一己私欲,其代表地位就将遭受质疑。限制君主的学说正是抓住这个关键点。它们指出,“君主一职是神圣的,正因此,它是一项…使命;君主是一个公共职位,是为整个共同体提供服务的公职”。*Otto Gierke,见前注〔21〕,S.34。这个学说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在共同体——也就是作为经验层面的臣民群体的“多”——的利益与上帝的意志之间建立了关联。这样一来,服务于共同体利益也就是在践行上帝的意志。君主若做出偏离共同体利益的行为,就等于违背了上帝意志,因此也就丧失了代表资格,这个行为也就变成君主以普通私人身份做出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如果仍要求臣民服从的话,君主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主,而是暴君。这样一来,绝对君主制背后的上帝——君主这个封闭的框架中,被加进一个要素,变成上帝——君主——臣民的格局。而且,臣民的利益与上帝的意志具有内在关联,甚至可以说,在尘世范围内,符合臣民利益的,才是符合上帝意志的。
造物主上帝,对其创造物拥有完全的权威,因此,除非上帝允许,否则没有哪个创造物拥有凌驾于其他创造物的权威。但是,上帝通常并不以可见的方式直接把权威授予某人。他只是把理性赐给人类,人类因此拥有了为自己设定行为规范的能力。在尘世间,人需要被统治,但是,上帝并不亲自统治,也不亲自指定统治者,他允许人类自己指定。由此,人类群体从上帝那里得到权威,来指定自己的政府,这样一来,在尘世范围内的人对于人的权威,就其起源来说,就既是神圣的,也是世俗的;它必须来自于上帝,但它也可以同时来自于人民。*John Plamenatz, Man and Society, volume one, second edition, Longman, 1992, pp.235-236.
由此可以看出,从绝对君主制到人民主权,在观念上实际只有一步之遥。而绝对君主制的另一种类型,即诉诸内在权威的绝对君主制,可以看作此历史进程的过渡环节。
2.诉诸内在权威的君主制
在诉诸超越权威的绝对君主制中,代表者的正当性根据来自一个外在于经验性人群的源泉。由此,代表者所代表的“一”与经验性人群所构成的“多”处于一种外在的二元化对立当中。虽然在中世纪封建等级社会中,已经有诉诸于经验性人群来限制君主的理论与实践,但是,在根本原则上,超越权威作为代表的基础这一点并未受到根本质疑。如上文所言,即使各个等级谋求对君主进行限制,他们仍要努力与超越权威建立某种关联,而并非从自身的内在特质提出限制君主的要求。
针对西欧历史上16-17世纪存在的那些绝对君主制,已经有人从理论上提出了另一种论证。这种论证割断了与上帝代表的超越权威之间的关联,而是完全从具有理性的个人出发,建构出政治统一体。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推托马斯·霍布斯。当政治统一体完全立基于具有理性的个人时,其正当性基础已经转变为内在权威。与诉诸超越权威的代表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一”与“多”的关系当中,“多”这个要素开始发挥关键作用。
当霍布斯打算完全从具有理性的个人建构政治统一体时,他就必须首先把个人完全打回到在政治上没有意义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在政治统一体被构建出来之前,个人完全是自然状态下孤立的个人。然后,他需要再从自然人这个原点构建出政治统一体。具有理性的自然人依据自然法的原则签订契约。通过契约,自然人塑造出一个新的公共人格,也就是政治上的统一体。只有依凭这个公共人格,个人才脱离自然状态,获得政治上的意义。可是,这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完成了公共人格的塑造,这个人格在现实中仍然是不可见的。作为拥有公共人格的政治统一体,若想在现实中获得行动能力,就必须拥有统一的理性和意志。理性和意志若想在现实中得到统一的表达,又需要有一个现实中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代表者。“一群人经本群中每一个人个别地同意,由一个人代表时,就成了单一人格,因为这一人格之所以成为单一,是由于代表者的统一性而不是被代表者的统一性。承当这一人格而且是唯一人格的是代表者,在一群人中,统一性没法作其它理解。”*(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125。
在霍布斯版本的绝对君主制中,代表者代表的是具有理性的个人组成的政治统一体。这个思想成为所有现代政治代表理论的原点。它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指出了若没有代表者,政治统一体只能停留在抽象层面。而政治统一体一旦想要在现实中呈现,就必须由代表者来承载。就此而言,代表者就是主权者,它对于政治统一体具有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只有在主权者的行为中,个人才能获得政治意义;脱离了代表,政治统一体的现实性就将失去支撑,所剩下的只是散乱的个人意志。”*Giuseppe Duso, Der Begriff der Repräsentation bei Hegel und das moderne Problem der politischen Einheit, 1990, S.11.在观念层面,我们当然可以提出质疑,说代表者有可能偏离政治统一体的真正意志,或曰代表者可能违背塑造共同体的社会契约。但是,又能怎样呢?如果打算继续依靠内在权威来建构政治统一体,那么,代表者的绝对性在实践中就是无法避免的。
从上文提及的“一”与“多”的关系来看,虽然霍布斯版本的“一”建立在“多”这个基础之上,但是,几乎在同时,“一”就完全吸纳了“多”,以至于在现实层面,“多”对于“一”并不能构成实际的牵制。“一”与“多”之间虽然存在内在二元化的紧张关系,但是,这种紧张仅停留在观念的可能性层面。从现实层面来看,代表者的意志就是主权者的意志,代表者与主权者同一。直到立宪君主制的类型当中,这种紧张才外化为制度层面的现实性。
(二)立宪君主制
顾名思义,立宪君主制既包含了君主因素,也包含了共和因素。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混合体制中,谁是代表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立宪君主制所仰赖的最终原则,以及君主因素和共和因素的力量对比。*关于立宪君主制的进一步类型划分,参见Georg Jellinek, 见前注〔18〕,S.705ff。根据立宪君主制所依赖的最终原则,它又可被分作两种类型。
1.同时诉诸超越权威与内在权威的立宪君主制
在这种类型中,君主诉诸于超越权威,其背后的依据仍可推及某种神圣的权利,而共和因素(通常是议会)诉诸于内在权威,其背后的依据是人民主权原则。在二者的力量对比中,如果君主占优,那么,政治统一体的代表者便是君主。此时被代表的东西仍是某种超越的意志或秩序。*例如,作为典型的立宪君主制宪法,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序言的表述是:“我们威廉一族,蒙上帝垂恩,在帝国参议会和帝国议会协同之下,发布……宪法。”但是,在立宪君主制中,议会也会主张自己的代表地位,这种地位尤其表现为议会对于立宪和立法职能的参与。*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第23条:“帝国议会有权……提出法律草案。”在这个语境下,代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并不是指代表政治统一体的人格,因为这个人格的代表者是君主,而是指在君主这个代表者面前,把经验意义上的人民的利益表达和声张出来。
如果君主和议会的力量对比呈现另一种态势,也就是如果议会占优,那么,政治统一体的代表者实质上便是议会。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实际上只有象征意义上的代表地位,在政治生活中并不发挥实质作用。今日的英国当属这种情形。
2.诉诸内在权威的立宪君主制
立宪君主制的两个核心组成机关,即君主和议会,也可以同时诉诸人民主权原则。特别是,君主的权力亦可以奠定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上。*例如,1831年《比利时宪法》第80条:“国王即位前,应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作如下庄严宣誓:‘我宣誓遵守比利时人民的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人民主权原则在实践上要求统一的意志表达。当两个主体同时声称有资格成为此统一意志的代表者时,这只能意味着,政治体或者处于不稳定状态,或者只能有一方胜出,从而成为唯一的代表者。因此,诉诸内在权威的立宪君主制中的两个主体必然存在互相竞争的内在趋势。由于代表意味着成为政治统一体意志的唯一承担者,所以,在两个主体互相竞争时,各自都努力否定对方的代表性质。在19世纪的欧洲,“君主复辟时期的政治家认识到这个概念的政治意义,试图用各等级的利益代理来取代‘人民代表’。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民阶层的要求原本是会失去政治价值的”。*施米特,见前注〔13〕,页225。而自由市民阶层正是以人民主权原则为依托,主张自己的代表地位,不愿仅成为各等级利益的代理。在竞争过程中,一旦这个阶层“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而与国王相对立,君主制原则就会遭到动摇,因为这项原则的基础是,国王唯一地、完全地代表人民的政治统一体”。*施米特,见前注〔13〕,页226。当二者的力量暂时处于势均力敌之势时,便会形成一种过渡形态,也就是并列地设立两个代表,这就是立宪君主制在代表问题上的“二元制”。*施米特,见前注〔13〕,页226。
二元制只是一种过渡形态。历史发展的最终事实是,议会在力量角逐中最后胜出,成为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统一体的代表者。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即使形式上仍然被保留,在实践中也只具有象征意义。
总之,立宪君主制是从绝对君主制走向民主共和制的过渡形态。在此过渡过程中,政治统一体的根基从一个超越权威转变为内在权威。也就是说,政治统一体的“一”不再诉诸于与经验人群构成的“多”毫无关联的一个源泉,而是逐步转到从“多”生出“一”的逻辑。在绝对君主制下,谁是代表者这个问题,并未成为争议的焦点,所争议的只是代表者是否真正完成了代表功能。而在立宪君主制下,争议的焦点问题则变为:谁是代表者?二元代表制并未真正回答这个问题。直到最终过渡到民主共和制,谁是代表者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代表的另一个维度的问题就会马上浮出水面,即代表者是否真正完成了代表功能?
(三)民主共和制
如前文所述,代表的基本结构是A 代表B。在A与B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也就是说,二者并不是同一的,而是二元化的两个主体。在诉诸于超越权威的绝对君主制中,这种二元化体现为两个主体的外在紧张。君主虽然在尘世代表上帝,但是,上帝的存在本身并不依赖于君主。然而,一旦被代表物转变为内在权威,具体来说,转变为人民主权原则中的人民,代表结构所含的那种紧张关系就转变为一种内在紧张,或曰内在二元化。
在人民主权原则下设想代表制的可能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民要在自身当中分出两个主体:一个是有资格成为被代表物的公意,另一个是没有资格成为被代表物的众意。而更关键的问题是,一方面要在公意和代表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分离,不至于使二者完全同一;另一方面又要为解决公意和众意的关系寻求一条恰当的出路,以免使公意在经验世界完全没有着落。
霍布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并非从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而是针锋相对地从人天生是自然动物出发,导出政治体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必须建构而成的结论。由此,他奠定了所有现代代表问题的原点。在霍布斯之后,人民不再被认为是先天就存在的政治统一体,而是被建构出来的统一体。作为被建构的统一体,只有通过代表才能获得存在形式。因此,在霍布斯那里,代表者与主权者必然同一,代表者就是主权者。主权者与代表者之间本应存在的分离无法获得现实的可能性。在这里只能存在绝对的代表。
卢梭争锋相对地指出,主权者是人民。
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120。
卢梭打破了霍布斯的绝对代表,否认霍布斯的代表者就是主权者的命题。霍布斯的代表者在卢梭的体系中只是权力的行使者。由此,卢梭的主权者最终必须自己亲自出场。
民主代表制必须在霍布斯和卢梭之间找到中间道路。一方面,主权者必须通过代表者来获得现实表达;另一方面,主权者与代表者之间又必须保持必要距离,能够对代表者形成必要牵制。这一切的关键点在于人民的两种身份(主权者和臣民)以及两种意志(公意和众意)之间能够形成某种沟通。*参见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Demokratie und Repräsentation, 1983, S.26.康德正是要寻找这样一条中间道路。他分三个步骤完成这项工作。首先,康德赞同霍布斯,认为只有代表者才能承载共同体的统一人格,从而带来和平秩序。因此,臣民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也就是说,臣民没有反抗权。
其理由就在于: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公民体制之下,人民就不再有权利来经常判断那种体制应该怎样进行治理。因为即使我们假设他们有这样一种权利,而且那的确还是反对现今国家领袖的判断,那么又由谁来决定哪一方才是正义的呢?双方无论哪一方都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审判官那样来行事。因此在最高领袖之上就必须再有另一位最高领袖,以便在前者与人民之间做出判决,而这是自相矛盾的。*(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193。
其次,康德赞同卢梭的公意理论,认为公意应该成为代表者行动的内在指南。代表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代表者,就在于其按照公意行事。不过,康德理解的公意并不是“一项事实”,*同上注,页190。而是“纯理性的一项纯观念”。*康德,见前注〔36〕,页190。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公意对于代表者没有约束力,相反,“它却有着无容置疑的(实践的)实在性,亦即,它能够束缚每一个立法者,以致他的立法就正有如是从全体人民的联合意志里面产生出来的,并把每一个愿意成为公民的臣民都看作就仿佛他已然同意了这样一种意志那样。因为这是每一种公开法律之合权利性的试金石”。*康德,见前注〔36〕,页190。公意对于代表者的约束力体现为一种思想实验。代表者每次作决策前,都要在自己的思想中设想对全体人民发问:你们会同意我的做法吗?他必须保证自己的决策在思想实验中能否经受公意的考验。当然,人们可以质疑说,这种仅停留在观念层面的公意仍是虚无缥缈的。
康德在第三个步骤中,在公意和众意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或者说建立了一种机制,使经验层面的具体个人有可能对公意的形成做出实际的贡献,从而对代表者构成事实上的牵制。这种机制就是言论自由。*参见Giuseppe Duso, 见前注〔26〕,页13。虽然公民没有反抗权,但这并不是因为代表者完全不可能对其做出不义之举,而是因为反抗权的逻辑将导致政治体的解体。“因为要是假定领袖绝不会犯错误或者是能够无事不知,那就把他说成是特蒙上天的启示而超出人类之上了。因此,言论自由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守护神,但须保持在尊敬与热爱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体制这一限度之内。”*康德,见前注〔36〕,页198。当臣民行使言论自由、批判代表者的言行时,他实际上不是以私人的“小我”在说话,而是作为公民在发言。通过言论自由的行使,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构成接近公意的一条路径。以此方式,康德在上文所说的“多”与“一”之间,或者用今天的话语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沟通机制。*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页121。民主发展到今天,这种机制越来越完善,如选举、基本权利诉讼等。
在民主共和制当中,被代表的是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人民。在契约论传统中,人民是通过契约建构出来的统一体。因此,代表的首要功能是通过具体的人赋予这个统一体一种存在形式。在另一个层面,代表理念始终要求代表者真正体现被代表者的意志。民主共和制的特色在于,在经验层面的人和承载主权的公意之间建立沟通机制。
(四)小结
在绝对君主制中,命令——服从的经验现象可转化为这样一种代表结构:上帝——代表者——臣民。而在民主共和制中,命令——服从的经验现象可以被解释为:人民——代表者——个人。被代表者从一个超越的权威转变为一个内在的权威。但是,绝对君主制与民主共和制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在于:代表者不能仅凭强力发号施令,而是必须诉诸某种更高的权威。这种更高的权威到底是什么?如何处理代表者与这种更高权威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代表者与经验领域的人群之间的关系?这是任何类型的代表结构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提出代表的系统框架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上文的描述是以欧洲大陆的历史素材为参照的。欧陆的代表观念一定程度上受其哲学气质的影响。当和英美世界围绕代表问题的讨论相比较时,会发现两个传统对于代表问题的核心关注并不一样。以美国学者皮特金讨论代表问题的经典著作为例,作者很少提及欧洲传统下的公意概念。“人民”一词,在英美传统下,也大多是在经验意义上理解。由此,英美传统对于代表问题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代表者对于选民的回应性(Responsive, Responsiveness)。*参见Hanna F. Pitkin,见前注〔7〕,页213、224、232、233。而下文的系统框架将会展示出,欧陆传统下对于代表问题的关注点集中于对公意的认定。两个传统的差别恰好为我们理解代表问题提供了更加完整的参照。
下文将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把代表所涉及的各个维度的问题放在一个体系结构当中。并归纳这些问题的主要答案,以期为理解中国宪法的代表结构提供一个参考框架。
二、 代表制的体系结构
在实践上,民主在古希腊的表现形式是直接民主;在理论上,人民主权理论的鼻祖是卢梭。如上文所述,卢梭明确反对公意可以被代表。然而,在当今世界通行的民主模式中,代议制民主却是主流。因此,欲证明代议制民主的正当性,就必须首先证明直接民主不可行。这正是美国采取代议制政府的论证思路。
一种纯粹的民主政体——这里我指的是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共和政体,我是指采用代议制的政体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它能保证我们正在寻求的矫正工作。……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两大区别是,第一,后者的政府委托给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第二,后者所能管辖的公民人数较多,国土范围也较大。*(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页48-49。
当由于操作层面的技术原因(直接民主无法避免党争,无法适应领土广阔的国家)而必须采用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时,就产生了民主语境下的代表制结构的第一个维度的问题,这就是授权问题。
(一)形式代表
在授权维度上的代表,可以称之为形式代表。通过形式代表的各种机制,人民不再亲自治理国家,而是选定自己的代表者。从代表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并非以自己的名义治理国家,而是代表人民。从形式代表的机制来看,至少可以分出以下两种选定代表的方式:
第一,程序性选定机制。当今世界上,通行的程序性选定机制是选举。为保证选举的真正落实,通常要通过宪法确立配套性的保障机制。这至少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选举平等、政党竞争等。但是,在形式代表层面上,关键的问题是议员的地位,或曰议员与选民的关系。从理念上说,议员是人民的代表,而在现实操作中,议员始终是由特定选区内的一部分选民选出的。于是,我们可以在各国宪法中看到这样一些似乎矛盾的条款:“德国联邦议会的议员……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不受委托和指令的约束,只基于其良心任职”;*《联邦德国基本法》第38条。“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46条。议员究竟是否要听从其选区的选民的指令,抑或只根据其良心做符合全体人民的决策,这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新问题。*在封建等级代表制中,代表者要受其选举委托人的约束。而根据法国大革命开启的现代代表观念,代表者只受其良心约束,代表全体人民。在苏维埃代表理念下,代表又受到原选举单位的约束。关于这个问题,参见Christoph Müller, Das Imperative und Freie Mandat, 1966.
第二,历史选定机制。在这种模式下,代表者代表地位的取得,是通过某些历史事件奠定的。而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代表者地位的确立,被认为是人民意愿的反映。无论采取哪种选定机制,都尚未触及代表问题的更深层面。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这个更深层面的问题可以表述为,代表者是否真正代表了人民?对于这个层面问题的回答,可以称之为实质代表。*关于形式代表与实质代表的区分,参见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见前注〔35〕,页18-19。 但是,本文在每种类型下所讨论的内容,与Böckenförde的框架并不一致。
(二)实质代表
代表者是否真正代表了人民?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人民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从逻辑结构本身来看,至少可以在两个层次上理解人民:第一,人民是人群形成的政治统一体;第二,人民是公意的主体。
当在政治统一体的层面上理解人民时,代表者代表人民就意味着,代表者要以可见的形式保证政治统一体被感知。这个层次上的代表可称为静态代表。当在公意的层面上理解人民时,代表者代表人民就意味着,代表者要确保公意能够在现实中落实。这个层次上的代表可称为动态代表。
1.静态代表
人民已经形成政治统一体,而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是静态代表得以成立的前提。通过代表,人民这个政治统一体获得存在形式,而不是因此才存在。即使在霍布斯的意义上,代表者也是赋予缔约以后的人民以存在形式。当然,人们也可以说,若无形式,存在本身毫无意义。
既然静态代表要以政治统一体的存在为前提,那么,它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使这个政治统一体不断再现,从而防止其解体。在施米特的概念中,政治的标准就是划分敌友。*参见施米特,见前注〔13〕,页138。当把“政治”和“统一体”结合为一个词时,这就意味着,尤其在一国内部的语境下,代表者要尽力缓和矛盾,防止其上升到敌友区分的程度,从而保证人们虽有异见,但仍可在最低限度内结成统一体。*对施米特思想的此种自由主义解读,参见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见前注〔14〕,页345-349。所以,如何在任何领域的矛盾都有上升到敌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的前提下,确保统一体这个底线不被触及,这才是关键问题。政治统一体的状态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面临两方面的危险:一是外来的危险,二是内在的危险。二者都有可能把已经达成的统一体撕裂,从而使敌我冲突在国内层面再次变为现实。静态代表的功能就在于提示人们注意一条底线,这就是首先要确保政治统一体成为可能。
2.动态代表
动态代表就是要在积极的意义上回答,政治统一体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回答如下:当代表者始终保证公意能够实现时,政治统一体便始终可能。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公意是什么?对此,历史上存在的论说更是不胜枚举。*最新的研究及其相关文献,参见张龑:“没有社会的社会契约”,《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笔者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首先归纳人们所界定的公意的类型,然后阐述接近不同类型公意的方式。
不管对公意的内涵如何界定,它总是指某种应该追求的、正确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此而言,当指出代表者应该代表公意时,实际是强调政治行为不能仅仅是强力,而应追求某种更高的目的。因此,公意是代表者行为的指南,是政治领域的真理。人们可以在两种方式上理解公意:一种是把公意理解为已经存在;另一种是把公意理解为有待建构。*此种划分,参见Herbert Krüger, Allgemeine Staatslehre, 2.Aufl., 1966, S.236.
①决断代表。当把公意理解为已经存在时,那么,代表者的任务就在于去发现、揭示它。在绝对君主制中,虽然不使用公意概念,而使用上帝意志,但是,上帝意志同样是指某种已经存在的绝对正确的东西。由于君主蒙上帝的恩赐,具有发现和感知上帝意志的特权。而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基本的假定是人人都具有理性。这就预示着,人人都具有发现公意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中,公意的指向只能是唯一的。如果承认人人都能发现公意,而人人发现出的公意却又互不一致,这将导致政治的瘫痪。因此,在人民主权语境下,如果假定公意是已经存在的,就必须同时假定,人群中的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优秀,更能够正确地发现公意。代表者就是这样一些更加优秀的人。因此,如果这样理解公意,那么,发现公意的方式最终只能是代表者的决断。
至于是否应该这样理解公意,本文不做评判。但是应该指出,这种思维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学思维的类比。它假定现实政治背后仍有一套更高的本体秩序。政治秩序应该努力去接近这套本体秩序。在接近这套秩序的过程中,会有各种竞争性的邪恶利益施加干扰。代表者不能对各种主张等同视之,而必须果断地识别并压制那些邪恶的利益,声张公意。
以魏玛时期的德国为例,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主张可归入这种代表类型。此种主张对应的制度设想便是总统充当代表者。这种制度所要应对的危机就是议会对于各种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等同视之,无法区分善恶对错。由此可能导致那些意欲颠覆现存秩序、以党派私利冒充公意的极端力量也合法地登堂入室。在这种危机状态下,总统就应该代替议会进行善恶识别,做出对错决断。通过这种临时性的专政手段重建秩序,然后再还权于议会,由议会主导正常状态下的常规政治运转。
②竞争代表。当不把公意看作已经存在而是有待建构,那么,在人人都有理性的前提下,建构公意的一种方式就可以是竞争。这种思维背后的假定是:虽然人人皆从其对于公意的主观认识出发,但是,经过竞争机制的加工,在黑格尔所言的“理性的狡计”的作用下,最终会自动产生出符合公意的结果。
这实际是把市场的逻辑完全套用到政治领域。竞争机制并未要求参与竞争的人必须秉持一颗公心。它相信即使人出于谋利和贪婪这些自然欲望,仍可以最终产生出公意这种政治上高尚的东西。
仍以魏玛时期的德国为例,公法学家汉斯·凯尔森的主张可归入这种类型。这种主张把建构公意的重任全寄托在议会身上,成败得失都交给议会程序。议会程序对各种竞争性的意识形态和利益主张一视同仁地全部开放,只凭借多数决原则产生最终的结果。虽然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各种主张有善恶对错之分,但是从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出发,无人能够超然地识别和确认。因此,政治过程就是利益之争,各种利益并无善恶高下之别。通过竞争机制赢得多数赞同的利益,就应该被认为是最接近于公意的结果。
③商谈代表。商谈代表同样假定公意是有待建构的,但是,并未把建构公意的事业完全交给竞争机制,而是要诉诸商谈。*本文无意重述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商谈理论的内容。详细可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尤其是第三、四两章。在商谈理论看来,竞争模式下的人们常会采取策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表面上会达成合意,但是,这种合意并不是对于解决方案的真正认同,而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妥协。相反,根据商谈理论,应该为人们创设一种理想的商谈情境,其中,不同的意见可以真诚和彻底地相互交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商谈是对竞争的完善,突出政治机制区别于市场机制的特殊之处。
以二战之后的联邦德国为例,哈贝马斯倡导的商谈理论属于这种类型。商谈代表在制度实践上与竞争代表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重视议会在建构公意过程中的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商谈代表模式扩大了建构公意的空间和领域。由此,联邦宪法法院和公共空间的讨论都发挥着建构公意的作用。
决断代表、竞争代表和商谈代表是接近公意的三种方式。表面看来,决断方式与竞争方式互相对立,但若细心观察,二者实际上共享同样的前提预设。决断代表预设了一种已然存在的绝对正确的公意,代表者之任务在于通过决断使公意得以显现。竞争代表看似否认这种公意的存在,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其实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否认绝对正确公意的可认知性。因此,两种代表模式都从绝对正确的公意这一共同的前提预设出发,只是基于不同的认知立场,最终表现出判然有别的行为态度。决断代表要在不同立场间一争对错,竞争代表则对于不同立场一视同仁。商谈代表在认识论层面区别于前两种模式的地方在于,它所理解的公意根本不是绝对真理意义上的一种实体。在商谈代表模式看来,只存在关于公意的各种主观主张。这些主张要获得认可,必须在主体间的交流过程中提出充分的论证。而且,这个交流过程也不能仅仅是各种力量和利益的角逐,而要符合基本的正义标准。
三、 结 论
从原则层面来讲,代表理论要求思考政治秩序时至少要关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一国人民首先要在政治上保持成为统一体的状态。否则,任何关于代表模式的讨论都将失去前提。因此,代表者的任务在于持续地关注政治整合,*关于整合思想以及各种整合模式,德国魏玛时期著名公法学家斯蒙德曾首倡并系统论述。参见Rudolf Smend, 见前注〔12〕。应对国际压力,缓和国内矛盾。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一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再能够识别和界定自我,那么,政治统一体实际就已经消融在国际秩序当中。在国内语境下,不管哪个领域引发的矛盾,如果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那就触及到了政治统一体的底线。代表者的任务在于事前采取理性的政策,防止矛盾激化到这样的程度。
意识到维系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之后,随之产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维系这个统一体,或者怎样实现政治整合?在启蒙运动打破神学思维和神权秩序,树立个人自主和人的理性之后,本体论和目的论思维在政治领域很难再唤起昔日的感召力。由此,人类在思考政治秩序时,很难再诉诸于一个既存的超越模板,而必须从经验世界的个体出发。但是,政治统一体的维系始终又需要某种超越个体的因素,而不能仅仅是个体意志的叠加或妥协。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这个难题就转化为:公意既要以众意为基础,又要超越众意。公意的建构若完全无视与众意的联系,就只能寄托于政治家的道德修养,而这种基础是脆弱的。同样,公意若不能超越众意,则政治就会沦为个人私欲的驰骋场地。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代表的结构展示为:人民(公意)——代表者——个体(众意)。代表者必须顾及公意与众意两个维度,唯有如此,才能在多元化的现实面前,既为个人自由容留出必要的空间,又为政治统一体不断注入生命的活力。
人民主权原则在中国宪法中展现出一种特定的实现模式。在理论上理清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宪法代表结构的关键。中国宪法的代表观念一方面体现出对于历史规律或者说历史发展方向的肯定,因此,代表者并非仅仅为经验领域的人群之喜好诉求提供竞争或商谈的平台,而是主动去认知和实现这一历史规律;另一方面,面对利益多元化的现实,中国宪法又包含对此多元利益诉求进行回应的因素。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不只是理论的任务,更是实践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