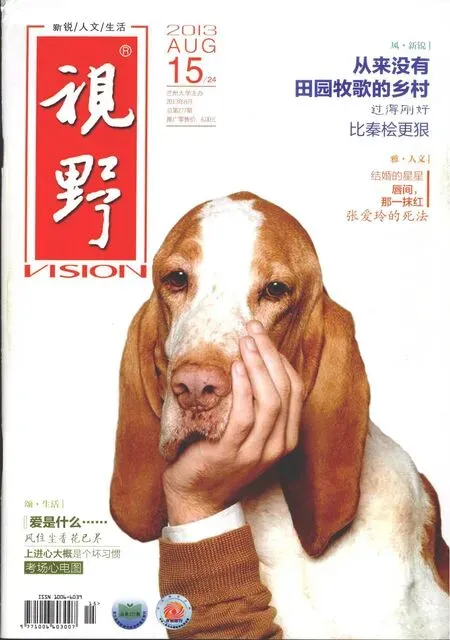从来没有田园牧歌的乡村
早上五六点,74岁的梁光正就起床了,整整齐齐穿好衣服,催促想睡懒觉的女儿梁鸿快点起床。梁鸿为了写关于梁庄人的书,要去采访老乡,梁光正比女儿还积极,见面的时间地点全帮着联系好了。
梁光正每年都会从河南来北京女儿家住一两次,最多待十来天就回去了。因为北京很无聊,除了天天看电视,没其他可做的事。但这一次,梁光正住了一个多月。
就像2008年,梁鸿为写《中国在梁庄》回到故乡。离开梁庄20年,即使每次过年和暑假都回去,梁鸿和梁庄也早已经互相生疏。还好父亲在。梁光正带着女儿,天天在村里走家串户。这位经历过大饥荒及后来许多政治运动的老人,本身就是一部村庄史。他帮着梁鸿破解了梁庄的密码。
三年后,梁鸿用一年多的时间做了梁庄系列的下半部分《出梁庄记》。她顶着频繁过敏有时肿得像橡皮一样的脸,走访了十多个省市的三百多人,记录梁庄人外出打工的生活。
两本书让梁鸿频频获奖,也让那个普通的村庄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著名样本。但梁庄的一切仍未变化。梁鸿也不知道,那个持续凋敝的村庄,以及散落在四方的梁庄子弟,是否还有可能重新开始。
梁庄的距离
梁鸿离梁庄的距离是17个小时的火车再加一个多小时的汽车。
少女时代的梁鸿渴望离开梁庄。“但这种渴望不是特别清晰的,不是天天哭着喊着要走,它就在那,是每一个农村少年的自然想法,特别必然。”离开村庄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生活,才能达到闪闪发光的三个字——“商品粮”。只有考上学才能通往这条路,而出去打工在村里人的观念里不算离开村庄,因为你还要再回来。那时候甚至没有“打工”这个词,只叫“出去干活”。
大姐考上南阳医专离开村庄,她写信给梁鸿,一行字下带有着重号:“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
后来,梁鸿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乡镇小学。工作三年后,考上南阳教育学院读大专,之后通过了本科自考,再考上郑州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接着读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博士。2003年,她成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留在北京。
她记得最初想要看世界的冲动。十八九岁,刚刚在小学教书一年多,攒了一点钱,梦想是看大海。她写信给福建海边当兵的同学,坐上火车跑去找他,却遇上他拉练去了。梁鸿和一起去的同学茫然无措,第二天往回走,海也没有看到,回去的路费还不够了。
现在的梁庄少年依然抱着相似的梦想走出家乡,但不管是进入工厂还是跟着父辈去偏僻的地方学手工艺,忙碌且无上升希望的生活,会很快碾碎梦想。
乡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爱它?
2011 年,梁鸿又一次重回梁庄。初看到她,村里人仍是一脸怔忡,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她打招呼。对于村子来说,她仍是陌生的存在,即使她在此地出生、成长,两三年前还回来遍访乡邻,写出那本《中国在梁庄》。“就像你投了个石子下去,石子很快不见了,涟漪泛起后也很快没有了。我觉得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他们自身没能力打破的,我们其实也没有能力打破。”
梁鸿记忆中的梁庄,是紫红的桑葚结满一树;是麦场上的电影;是坑塘里种满了莲藕,小伙伴手拉手蹚进水里摘最近的莲蓬;是男人女人们挤在大树下的大平台上,传着闲言碎语,拿着盆子大的海碗吃面条……现在,曾经的大平台旁边是连绵的废墟,荒草和灌木覆盖一切。麦场、坑塘、莲藕、桑树都不见了,只剩下淌着黑色淤流的污水坑。河道里因长年挖沙暗流涌动,上百亩耕地因长年烧砖泥土尽失。
那个记忆中的梁庄,有美化的部分吗?梁鸿摇摇头:“那些都是真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梁庄。”她还写了饿死的爷爷,被批斗时打得浑身是血的父亲,还有贫穷的童年。“从来没有一个田园牧歌的乡村。我们从历史上看,只有帝王将相,农民从来没有在历史或文学史里出现过。直到元明清小说,才有市民,才有个体。所谓的田园,都是一种想象的生活。到了1950年代,农民被告知不能离开土地,因为要建构城乡二元的户籍。80年代,农民被告知要离开家里打工,因为城市需要建设者。现在被告知,上楼吧,要占地了。如果农民想留就留下,在家里面还可以生活得不错,想走就走了,这是自由的,是双向的。但显然今天农民必须得走,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在抛弃他的生存环境,他不得不走。这不是一种自由,这是伪自由。”
日渐凋敝的梁庄也有崭新的部分,那是沿新公路修盖的一排排新房屋,高门楼,卷闸门,气派得很。它们的主人绝大多数在城市打工。他们省吃俭用盖下豪宅,一年却只能回来住一两次。
“你可能觉得农民怎么这么愚昧,还不如投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爱梁庄,是因为他们只有回去一条路。在我们今天这样整个社会都在普遍抛弃乡村的状态下,我觉得没有农民真的爱乡村。乡村什么都没有,他为什么要爱它呢?”梁鸿说,“你要知道一个人是需要找到家的感觉的,他在城里是一个漂泊的身份。在梁庄盖房子,是他的身份、他的安定、他的尊严。”
你会回到梁庄吗?
梁磊的老婆去年从深圳回到梁庄生孩子。梁磊的妈妈从打工的西安回家,和儿媳妇一起照顾孩子。这让梁鸿特别意外。
30岁的梁磊是重点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生,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完全城市化的年轻人,梁鸿以为他能跳出梁庄人父母和孩子总是分离的命运,但他失败了。
上学不再那么能带来向上流动的空间了,想着都害怕:“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看起来大家都纷纷融入了城市,但早上五六点,74岁的梁光正就起床了,整整齐齐穿好衣服,催促想睡懒觉的女儿梁鸿快点起床。梁鸿为了写关于梁庄人的书,要去采访老乡,梁光正比女儿还积极,见面的时间地点全帮着联系好了。
梁光正每年都会从河南来北京女儿家住一两次,最多待十来天就回去了。因为北京很无聊,除了天天看电视,没其他可做的事。但这一次,梁光正住了一个多月。
就像2008年,梁鸿为写《中国在梁庄》回到故乡。离开梁庄20年,即使每次过年和暑假都回去,梁鸿和梁庄也早已经互相生疏。还好父亲在。梁光正带着女儿,天天在村里走家串户。这位经历过大饥荒及后来许多政治运动的老人,本身就是一部村庄史。他帮着梁鸿破解了梁庄的密码。
三年后,梁鸿用一年多的时间做了梁庄系列的下半部分《出梁庄记》。她顶着频繁过敏有时肿得像橡皮一样的脸,走访了十多个省市的三百多人,记录梁庄人外出打工的生活。
两本书让梁鸿频频获奖,也让那个普通的村庄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著名样本。但梁庄的一切仍未变化。梁鸿也不知道,那个持续凋敝的村庄,以及散落在四方的梁庄子弟,是否还有可能重新开始。
梁庄的距离
梁鸿离梁庄的距离是17个小时的火车再加一个多小时的汽车。
少女时代的梁鸿渴望离开梁庄。“但这种渴望不是特别清晰的,不是天天哭着喊着要走,它就在那,是每一个农村少年的自然想法,特别必然。”离开村庄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生活,才能达到闪闪发光的三个字——“商品粮”。只有考上学才能通往这条路,而出去打工在村里人的观念里不算离开村庄,因为你还要再回来。那时候甚至没有“打工”这个词,只叫“出去干活”。
大姐考上南阳医专离开村庄,她写信给梁鸿,一行字下带有着重号:“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
后来,梁鸿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乡镇小学。工作三年后,考上南阳教育学院读大专,之后通过了本科自考,再考上郑州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接着读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博士。2003年,她成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留在北京。
她记得最初想要看世界的冲动。十八九岁,刚刚在小学教书一年多,攒了一点钱,梦想是看大海。她写信给福建海边当兵的同学,坐上火车跑去找他,却遇上他拉练去了。梁鸿和一起去的同学茫然无措,第二天往回走,海也没有看到,回去的路费还不够了。
现在的梁庄少年依然抱着相似的梦想走出家乡,但不管是进入工厂还是跟着父辈去偏僻的地方学手工艺,忙碌且无上升希望的生活,会很快碾碎梦想。
乡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爱它?
2011 年,梁鸿又一次重回梁庄。初看到她,村里人仍是一脸怔忡,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她打招呼。对于村子来说,她仍是陌生的存在,即使她在此地出生、成长,两三年前还回来遍访乡邻,写出那本《中国在梁庄》。“就像你投了个石子下去,石子很快不见了,涟漪泛起后也很快没有了。我觉得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他们自身没能力打破的,我们其实也没有能力打破。”
梁鸿记忆中的梁庄,是紫红的桑葚结满一树;是麦场上的电影;是坑塘里种满了莲藕,小伙伴手拉手蹚进水里摘最近的莲蓬;是男人女人们挤在大树下的大平台上,传着闲言碎语,拿着盆子大的海碗吃面条……现在,曾经的大平台旁边是连绵的废墟,荒草和灌木覆盖一切。麦场、坑塘、莲藕、桑树都不见了,只剩下淌着黑色淤流的污水坑。河道里因长年挖沙暗流涌动,上百亩耕地因长年烧砖泥土尽失。
那个记忆中的梁庄,有美化的部分吗?梁鸿摇摇头:“那些都是真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梁庄。”她还写了饿死的爷爷,被批斗时打得浑身是血的父亲,还有贫穷的童年。“从来没有一个田园牧歌的乡村。我们从历史上看,只有帝王将相,农民从来没有在历史或文学史里出现过。直到元明清小说,才有市民,才有个体。所谓的田园,都是一种想象的生活。到了1950年代,农民被告知不能离开土地,因为要建构城乡二元的户籍。80年代,农民被告知要离开家里打工,因为城市需要建设者。现在被告知,上楼吧,要占地了。如果农民想留就留下,在家里面还可以生活得不错,想走就走了,这是自由的,是双向的。但显然今天农民必须得走,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在抛弃他的生存环境,他不得不走。这不是一种自由,这是伪自由。”
日渐凋敝的梁庄也有崭新的部分,那是沿新公路修盖的一排排新房屋,高门楼,卷闸门,气派得很。它们的主人绝大多数在城市打工。他们省吃俭用盖下豪宅,一年却只能回来住一两次。
“你可能觉得农民怎么这么愚昧,还不如投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爱梁庄,是因为他们只有回去一条路。在我们今天这样整个社会都在普遍抛弃乡村的状态下,我觉得没有农民真的爱乡村。乡村什么都没有,他为什么要爱它呢?”梁鸿说,“你要知道一个人是需要找到家的感觉的,他在城里是一个漂泊的身份。在梁庄盖房子,是他的身份、他的安定、他的尊严。”
你会回到梁庄吗?
梁磊的老婆去年从深圳回到梁庄生孩子。梁磊的妈妈从打工的西安回家,和儿媳妇一起照顾孩子。这让梁鸿特别意外。
30岁的梁磊是重点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生,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完全城市化的年轻人,梁鸿以为他能跳出梁庄人父母和孩子总是分离的命运,但他失败了。
上学不再那么能带来向上流动的空间了,想着都害怕:“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看起来大家都纷纷融入了城市,但早上五六点,74岁的梁光正就起床了,整整齐齐穿好衣服,催促想睡懒觉的女儿梁鸿快点起床。梁鸿为了写关于梁庄人的书,要去采访老乡,梁光正比女儿还积极,见面的时间地点全帮着联系好了。
梁光正每年都会从河南来北京女儿家住一两次,最多待十来天就回去了。因为北京很无聊,除了天天看电视,没其他可做的事。但这一次,梁光正住了一个多月。
就像2008年,梁鸿为写《中国在梁庄》回到故乡。离开梁庄20年,即使每次过年和暑假都回去,梁鸿和梁庄也早已经互相生疏。还好父亲在。梁光正带着女儿,天天在村里走家串户。这位经历过大饥荒及后来许多政治运动的老人,本身就是一部村庄史。他帮着梁鸿破解了梁庄的密码。
三年后,梁鸿用一年多的时间做了梁庄系列的下半部分《出梁庄记》。她顶着频繁过敏有时肿得像橡皮一样的脸,走访了十多个省市的三百多人,记录梁庄人外出打工的生活。
两本书让梁鸿频频获奖,也让那个普通的村庄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著名样本。但梁庄的一切仍未变化。梁鸿也不知道,那个持续凋敝的村庄,以及散落在四方的梁庄子弟,是否还有可能重新开始。
梁庄的距离
梁鸿离梁庄的距离是17个小时的火车再加一个多小时的汽车。
少女时代的梁鸿渴望离开梁庄。“但这种渴望不是特别清晰的,不是天天哭着喊着要走,它就在那,是每一个农村少年的自然想法,特别必然。”离开村庄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生活,才能达到闪闪发光的三个字——“商品粮”。只有考上学才能通往这条路,而出去打工在村里人的观念里不算离开村庄,因为你还要再回来。那时候甚至没有“打工”这个词,只叫“出去干活”。
大姐考上南阳医专离开村庄,她写信给梁鸿,一行字下带有着重号:“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
后来,梁鸿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乡镇小学。工作三年后,考上南阳教育学院读大专,之后通过了本科自考,再考上郑州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接着读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博士。2003年,她成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留在北京。
她记得最初想要看世界的冲动。十八九岁,刚刚在小学教书一年多,攒了一点钱,梦想是看大海。她写信给福建海边当兵的同学,坐上火车跑去找他,却遇上他拉练去了。梁鸿和一起去的同学茫然无措,第二天往回走,海也没有看到,回去的路费还不够了。
现在的梁庄少年依然抱着相似的梦想走出家乡,但不管是进入工厂还是跟着父辈去偏僻的地方学手工艺,忙碌且无上升希望的生活,会很快碾碎梦想。
乡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爱它?
2011 年,梁鸿又一次重回梁庄。初看到她,村里人仍是一脸怔忡,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她打招呼。对于村子来说,她仍是陌生的存在,即使她在此地出生、成长,两三年前还回来遍访乡邻,写出那本《中国在梁庄》。“就像你投了个石子下去,石子很快不见了,涟漪泛起后也很快没有了。我觉得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他们自身没能力打破的,我们其实也没有能力打破。”
梁鸿记忆中的梁庄,是紫红的桑葚结满一树;是麦场上的电影;是坑塘里种满了莲藕,小伙伴手拉手蹚进水里摘最近的莲蓬;是男人女人们挤在大树下的大平台上,传着闲言碎语,拿着盆子大的海碗吃面条……现在,曾经的大平台旁边是连绵的废墟,荒草和灌木覆盖一切。麦场、坑塘、莲藕、桑树都不见了,只剩下淌着黑色淤流的污水坑。河道里因长年挖沙暗流涌动,上百亩耕地因长年烧砖泥土尽失。
那个记忆中的梁庄,有美化的部分吗?梁鸿摇摇头:“那些都是真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梁庄。”她还写了饿死的爷爷,被批斗时打得浑身是血的父亲,还有贫穷的童年。“从来没有一个田园牧歌的乡村。我们从历史上看,只有帝王将相,农民从来没有在历史或文学史里出现过。直到元明清小说,才有市民,才有个体。所谓的田园,都是一种想象的生活。到了1950年代,农民被告知不能离开土地,因为要建构城乡二元的户籍。80年代,农民被告知要离开家里打工,因为城市需要建设者。现在被告知,上楼吧,要占地了。如果农民想留就留下,在家里面还可以生活得不错,想走就走了,这是自由的,是双向的。但显然今天农民必须得走,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在抛弃他的生存环境,他不得不走。这不是一种自由,这是伪自由。”
日渐凋敝的梁庄也有崭新的部分,那是沿新公路修盖的一排排新房屋,高门楼,卷闸门,气派得很。它们的主人绝大多数在城市打工。他们省吃俭用盖下豪宅,一年却只能回来住一两次。
“你可能觉得农民怎么这么愚昧,还不如投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爱梁庄,是因为他们只有回去一条路。在我们今天这样整个社会都在普遍抛弃乡村的状态下,我觉得没有农民真的爱乡村。乡村什么都没有,他为什么要爱它呢?”梁鸿说,“你要知道一个人是需要找到家的感觉的,他在城里是一个漂泊的身份。在梁庄盖房子,是他的身份、他的安定、他的尊严。”
你会回到梁庄吗?
梁磊的老婆去年从深圳回到梁庄生孩子。梁磊的妈妈从打工的西安回家,和儿媳妇一起照顾孩子。这让梁鸿特别意外。
30岁的梁磊是重点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生,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完全城市化的年轻人,梁鸿以为他能跳出梁庄人父母和孩子总是分离的命运,但他失败了。
上学不再那么能带来向上流动的空间了,想着都害怕:“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看起来大家都纷纷融入了城市,但很少能有人进入城市的上层或者中层。”
梁磊在深圳每月挣五六千元,与一对带孩子的夫妻合租两室一厅。妹妹去找他时,只能住在客厅里。
孩子大一点后,梁磊的老婆会再出来工作,孩子留在梁庄给老人带。带到几岁呢?没人想好这个问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青岛的电镀厂,是梁鸿最想去又迟疑怕去的地方。她童年最好的伙伴、堂弟小柱28岁那年喷血死亡,被怀疑是在电镀厂打工中毒。
只踏进电镀车间一小会儿,梁鸿就像鼻腔、口腔里被塞满各种湿金属,堵到几乎窒息。小柱去世后,堂叔梁光亮依然在这里打工。他知道接触那种叫“氰化物”的东西就是慢性自杀,可依然在这儿干了十多年,工资不过涨到每月两千多块。因为资历深,老板给了他一项特权,可以带着儿子打工。偌大的厂区里只有他能带着孩子。
许多人问:“为什么他还敢留下?”梁鸿说:“这么问其实都是外部视角,对农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外出打工,来到一个地方就这样生活了。一开始去西安蹬三轮车就蹬下去了,去内蒙古校油泵也就干下去了。他们很少有其他的选择机会。”
今年,梁光亮还是离开了电镀厂,因为他们的儿子长大该上学了。
梁鸿几乎询问了每一个被访问的老乡:你会回到梁庄吗?答案各种各样。梁鸿自己的答案写在了书的最后一句:我终将离梁庄而去。
面对媒体,梁鸿的父亲会自动切换到可能是电视上潜移默化的接受采访状态,冒出些宏大句子:“这事对国家有益。”“让城市了解乡村。”梁鸿在边上哈哈大笑:“咦!老头可有觉悟了。”
五年前,梁鸿带八岁的儿子回到梁庄,要下火车时,他指着地面说“脏”,哭着不愿意下车。等到离开时,他已经习惯在房前屋后和小伙伴们挖泥、捉蚂蚁,满脸通红跑来向妈妈要水喝,健康茁壮的样子。
现在问他:“你喜欢梁庄吗?”他说:“有点旧了,原来我没去过的时候应该很好看。”
再问:“你会想回梁庄玩吗?”他想一想,咧嘴一乐:“想穿越时空回去玩,穿回妈妈找到爸爸的时候。”这个梁庄的下一代,已经远离梁庄。
凌玉洁摘自《南方人物周刊》,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