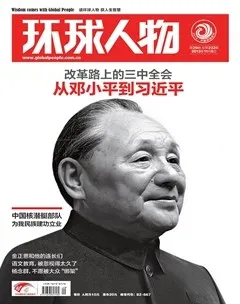德不孤,必有后
不像今人,古人多有自己长长的影子,或迫切希望寻觅和找到自己长长的影子。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会尽可能地追溯重要人物的家族历史,尤其是在“本纪”和“世家”中。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一种“崇敬祖先”的信仰传统,一般人也都想知道一个人物的来历。而且那时距世袭社会尚不远,巨人巨室不那么容易横空出世,甚至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后起,后来从边陲夺得天下的秦国,也有自己祖先的长长一段历史。
当然,这种追远有时会伸入渺茫难知的传说,甚至掺入神话的因素,这有时是因为古代记录和传播手段受到限制,有时也是出于后人神化祖先的愿望。故而我们对有些人物的准确生活年代不可太当真,但有些基本的线索和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试来看周文王姬昌之前的周人一族的历史。据说周人的始祖曾被遗弃。世界文明史中多有从弃婴开始的领袖,例如《圣经》中的摩西,甚至今天的乔布斯。如此不幸的命运却往往能够激励有些人的大志,当然,要成功还要得到良好的教育以及运气。周人的始祖就因为父母“初欲弃之,因名曰弃”,但他有“巨人之志”,热衷于那时社会文明的根基和进步的标志——农业,在这方面多有造诣,后来被“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所以,他又名为“后稷”。
这一对农耕的成就甚至可说是周这一部族的传家之宝和兴旺之基。周人活动范围在西陲,常处戎狄之间而受到其压力,但还是屡次努力回到文化中心,回到定居文化和农耕文化。另外,其兴旺也和中央政治有密切关系,往往得官则兴,失官则衰。周人的历史也有起伏,有时会向原始的部族社会回落,只是后来又因强化内部制度和外部联系而复兴。
周族的几个重要复兴领袖公刘、古公等,除了重视农业,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德行,且通过德行而“得人”。如公刘继承后稷的事业,“务耕种,行地宜”,百姓都来投奔,“周道之兴自此始。”到了古公期间,“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当戎狄欲来攻打时,古公说,如果百姓因为我在战场上父丧子亡,我怎么忍心当他们的君王!于是离开自己居住的豳(音同“斌”)地,来到岐下,老百姓扶老携幼,也跟他到了岐下。
暴起往往容易暴落。暴得的大名往往是虚名,暴得的大利也往往靠不住或者有污点。过渡时代或有通过不当的“原始积累”的手段挖到“第一桶金”的侥幸,正常社会则应当是通过法治,来保障所有人都只能用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另外,我们或也不必太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甚至不必太计较当世之输赢。一个人、一个家族要多去想和做比较长久的事情,一个国家也要多去想和做比较长久的事情,而长久的事情莫不和德有关联。古人说“德不孤,必有邻”,我们或还可说:“德不孤,必有后!”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我们或还可说:“积德之国,必有后福!”而这“后福”也包括持续发展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