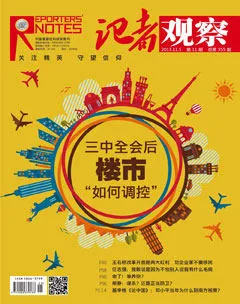中国地名的“崇洋化标签”
是的,这里是中国,好多洋地名儿的中国。
近几年,河南各地不断出现“洋地名”让人眼花缭乱,如郑州的“曼哈顿”“威尼斯”,洛阳的“加州1885”等。近日,河南省政府发布第156号政府令,宣布《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经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其中规定。禁止使用外国人名和地名做地名。其中包括宾馆、商场、写字楼等大型建筑物及居民住宅。
禁令一出,一片哗然。有人叫好,称阜应该治治这土不土洋不洋的怪现象了;有人质疑,问难道狗剩儿子就不能取名叫大327这洋地名儿,到底取得取不得?有没有人或机构在管取地名这个事?
事实上,取地名这个事,还真有政府部门一直在管理。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地名委员会”。早在1986年国务院出台的《地名管理条例》中就有规定:县级以上民政管理部门(或地名委员会)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名工作。这个条例中还明确规定:不以外国人名、地名命名我国地名。
这就奇了怪了,有机构管理,有明文规定,可为何中华大地还是照样“洋地名”频出呢?
根本原因在于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有效的违法、违规的惩戒、监管措施,只是软绵绵地规定着:“各级地名管理部门对擅自命名、更名或使用不规范地名的单位和个人,应发送违章使用地名通知书,限期纠正;对逾期不改或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后果者,地名管理部门应根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可地名的确定单位一般为本地政府,各级地名管理部门又怎敢对本级政府的行政行为“指手划脚”呢?你又何尝听说过某街道、某商场、某住宅因命名不合规,而收到限期纠正通知书呢?法律得不到执行,失去了监管,也就失去了生命,形同虚设。
不过,话说回来,这洋地名是不是只有中国特有呢?
倒也不是。韩国的洋地名儿也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新建小区的名字,那是一个比一个洋气,比如说乐天建设公司的“乐天Castle Morning”小区,现代建设公司的“现代Prime”小区,大宇建设公司的“PRUGIO”小区等。因此韩国网络上曾有过这个一样段子——问:“最近的小区名字为什么又长又复杂?”答:“为了让婆婆找不到回来的地方。”(韩国的儿媳和婆婆经常不和,而上了年纪的婆婆外出回来时,由于小区的名字又长且又是英语,她们根本记不住,所以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为了鼓励使用韩文,恢复民族的主体性和自信心,韩国政府从2012年起。将一年一度的“韩文日”升格为了国庆日。
而日本洋地名更多,楼盘的名字多由外来语和汉字构成,比如“戈兰西二子玉川”“东向岛戴亚蒙多公寓”“莱恩斯板桥冰川町”“西提豪斯中野新桥”“西提豪斯樱新町”等等。这些外来语在日本并不普遍,很多普通的日本人都听不懂。而且看起来也不如汉字那么好辨认。日本前首相小泉曾亲自提倡多用原有日语,少用外来语,但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
那是不是只有咱们东亚人热衷取洋地名?就像咱们愿意给自己取英文名一样?
也不是,以澳大利亚为例,在悉尼的街头,你能看到不少英国、美国的地名和人名,用一些GPS导航软件时如果不注明查找的是澳大利亚的地名,一不小心就被引导到千里之外了。悉尼南部有一个城市叫卧龙港,而这个卧龙港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一个中国的寺庙叫做南天寺。
要说世界上影响最大、使用最多、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洋地名。恐怕非唐人街莫属了吧?
考察世界各国的洋地名儿可以发现,洋地名儿出现的最关键原因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主动学习,“洋”不“洋”其实不重要,关键是“强”不“强”。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韩国把叫了800年的汉城改名叫首尔。
曾有研究社会文化的专家曾做出如此分析:洋地名儿现象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出现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化中占据强势地位。这更加深了亚洲一些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不自信,洋地名儿泛滥是这种不自信的体现。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禁得住外国地名,但挡不住文化不自信和媚外情结。
对于“洋地名”而言。无论是频出还是禁止。都彰显了文化的不自信——洋地名频出是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所以才崇洋媚外;禁止洋地名则是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所以才对外来文化异常排斥。
在一个文化不自信的氛围里,即便禁止了“洋地名”,其积极价值亦不是很大。媚外情结不在这一个舞台上绚丽。就会在另一个舞台上璀璨。
因此,在“洋地名”一事上,核心的问题不在于禁止。有时候越是禁止越会让人心生好奇,关键在于树立文化自觉。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是这样解释文化自觉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
仅仅叫停“洋地名”,就能唤起我们的文化自觉了么?
或者换个角度思考。不取洋地名儿,我们现在又剩下多少好听的富有中国味道的新地名儿呢?是遍布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人民广场,还是很多城市里都有的建国路、解放路、北京路?当我们准备给自己的城市取个新地名时,才赫然发现,取一个新的、有中国味道的地名儿居然这么难!
2005年。韩国将“江陵端午祭”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息一出,中国人认为“韩国盗取中国的传统端午节”,指责韩国为“文化盗贼”。随后。中国政府于2006年5月正式将“端午节”列入国家文化遗产名录。并于2008年正式将其定为法定假日。但时至今日,国人的端午节又是怎么过的?除了逛街旅游吃饭。你还知道端午节的哪些风俗?端午节节味一年淡似一年,以致有媒体发出“端午节不能只剩吃”的感慨。
瞿秋白曾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而鲁迅则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中国社科院教授、作协书记白庚胜回忆:“小时候流行‘破四旧’,我哥哥是红卫兵。他每天都拿把刀子刮家里柱子上的花纹,把那些充满美感的文化产品搞成没有美术、没有音乐的状态。”
2004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禁说中文,尽管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学者参加,但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甚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中英文双语要求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
大概再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么心狠,也再没有—个民族像我们一样这么不热爱自己的母语。
在美国布朗大学教育系副教授李瑾看来,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无知,始于鸦片战争时期丧失文化信心,自此走上了消极的否定之路。之后100多年来,其代表儒家文化被反复拉出来批斗,传统文化的地位始终没有摆正。
我们无法用一篇小小的文章来说明为何中华传统文化会衰落,但必需正视的是,城市承载的是一个国家深厚的居住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在城市地名这个专属名片上,拥有其特有的文化属性。洋地名儿泛滥的根子,出在传统文化的式微上。而文化的败象,想用简单几纸政令挽回,着实是有心无力。
台湾诗人余光中当年曾说: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现在情形却可能已经改变:当女友改名叫小蛮,你又能否写出一首《虞美人》送她呢?
禁了好莱坞大片。也救不了国产电影;取消了“曼哈顿”“纽约”,也不能让河南重现东京梦华。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有句名言:凡我在处,就是德国。与其纠结洋地名儿乱象。不如安安静静到全国的曼哈顿广场读几页诗经,沉下心来感受下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只因:你我所在之处,便是中国。
摘自新浪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