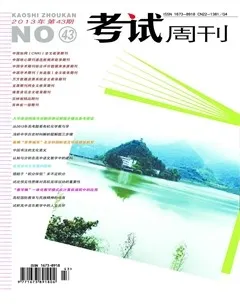论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归化和异化这两组翻译中术语的定义和起源,同时也阐明了另一组翻译术语直译和意译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对归化和异化的发展前景作了分析。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直译 意译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实践积累的日益增加,翻译已不再被看做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更多地涉及包含在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文化信息的传递手段方面,翻译界引入了归化和异化的概念。
1.归化与异化的来源及其内涵
因为翻译涉及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两种不同文化的转换,就很自然地产生了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内部产生了分歧。一般来说,可分成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1.1异化的代表人物韦努蒂
Venuti可以说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其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在翻译中表达这种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这也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认为文化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和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异化就是承认并容忍差异,并且在目的语中表现该文化差异。
1.2归化的代表人物奈达
Nida可以说是归化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重视读者反应是为了让译语文本读者大致和原语读者一样去理解和欣赏一个文本。奈达的这一功能对等理论的目的就是,译文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完全自然的,通过归化的翻译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因此,通顺可以看做是归化翻译理想的策略。
1.3 Assimilation & Alienation和 Foreignization & Domestication的关系
Assimilation & Alienation是较早提出的一组定义,assimilation的实质是说两个性质不同的事物因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一方向另一方靠近以至逐步融合的过程。用在翻译中,具体的指经过翻译,原文与译文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原文的语言及文化特色相当一部分消失,而译文跟目的语的语言与文化非常接近,甚至跟目的语作家的作品无法区别。而alienation则相反,在翻译过程中,它力图保持原文的特点,与译入语及其文化保持距离,使译入语读者在阅读时感到“陌生”,意识到在读一部译作。
Foreignization & domestication这对术语由美国著名翻译家韦努蒂(L.Venuti)于1995年在其著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译者的隐身)中提出,它们是用以表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strategy)的。Foreignization的作用是在翻译中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的特色,让译文语言的读者感受到异域风情,感受到其他文化的存在与独特魅力。
Domestication的含义用到翻译策略上,则是强势文化为达到对弱势文化殖民统治的目的与需要,重组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点,使之符合强势语言与文化的规范,而这层意思assimilation没有。Foreignization & Domestication和Assimilation与Alienation相比较,这对术语不仅反映了语言与文化方面含义的不同,还由此看到了这种不同背景后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文化不平等关系。
2.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到归化与异化
直译和意译(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之争在翻译领域由来已久。从古到今,无论是东西方关于这两个翻译策略的争执都涌现了不少代表人物。在古代、现代和当代中国,归化与异化作为翻译的两种策略,前后有三次大规模的论战。
古代,归化异化之争的雏形是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梁启超指出:“……直译意译两派,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陈福康,2000:8)他所说的“直译”和“意译”就是佛经翻译中所谓的“质”译与“文”译。
到了近现代,“质”译和“文”译为“直译”和“意译”所取代,其第二次交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一批左翼学者主张直译,而以梁实秋为首的一批右翼学者则主张意译。
当代中国译坛归化异化之争可视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直译意译之争的延伸。率先对在当代中国译坛归化翻译主流提出挑战的当数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路”(1987)一文。十年之后,由许钧在《文汇读书报》上发起的对《红与黑》译本的读者调查和讨论直接引发了归化派和异化派的交锋,当代中国译坛归化与异化的对话从此进入高潮阶段。
在当代国际翻译论坛,引起归化和异化之争的人应该是Nida,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描述这对翻译策略的是以色列学者Even-Zohar,而将这一对概念引入你死我活的角斗场的则是美籍意大利裔学者Venuti。
3.归化与异化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究竟翻译手究竟哪一种更有利于促进跨文化交流,沟通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理解呢?先看下面几个文学翻译的例子。
(1)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红楼梦》,156)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 Xianyi: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2)至于才子佳人等书,……(《红楼梦》:5)
As for books of the beauty-and-talented type...(Yang:4)
And the“boudoir romance”...(Hawkes:SO)
(3)更有一种风月笔墨,……(《红楼梦》:5)
Even worse are those 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Yang:4)
Still worse is the“erotic novel"……(Hawkes:49)
杨用异化手段翻译“才子佳人”(the beauty-and-talented)、“风月笔墨”(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这些在中国读者看来心领神会的译文,英美读者未必就能轻易理解、接受。而霍克斯的boudoir romance,erotic novel之类地道的英语表达法,在外国读者看来却很可能是传神之笔,妙不可言。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的手段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而霍克斯则舍弃了源语谚语的形象,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虽译文更为自然,却使译语读者失去了一个了解源语文化、欣赏其趣味的机会。
下面我们再看看在其他翻译作品中“异化”与“归化”的不同作用。
(4)All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大路通罗马。
(5)The monk may run away,but the temple can't run with him.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6)Easy come.Easy go.
来得容易,去得快。
通过上面的几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应用。可以看出前面四组习语的翻译都用了异化的手法,而后面的两个句子则用了归化的翻译手法。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译者在将外语译成本族语时,几乎都会对译文作归一化处理,而将本族语译成外语时,情况恰恰相反——异化的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4.结语
在文化交流中,翻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如果一味采用异化译法,就会增强读者对译文的陌生感,增加读者接受的难度,阻碍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如果过于强调归化译法,则是以牺牲了大量附载信息为代价的。异化与归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采用异化或归化的原则,也可以两者相结合应用,在不同情况下做具体灵活的处理。
参考文献:
[1]白瑶.英汉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前沿,2002(12).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陈丽莉.翻译的异化和归化[J].中国科技翻译,1999(2):43-45.
[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5]裘姬新.论习语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语言与翻译,2002(2).
[6]秦洪武.翻译中的句法异化与归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5).
[7]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1).
[8]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中国翻译,2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