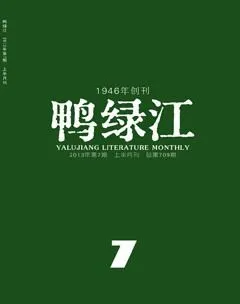泥土之上(组诗·创作谈)
冯金彦,1962年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歌集《敲门声》《水殇》《泥土之上》,散文集《一只鸟的颤栗》,理论集《背向城市》。作品获《人民日报》诗歌征文奖、《人民文学》散文征文奖、《诗刊》诗歌征文奖等三十多次奖励。先后在《人民日报》《诗刊》《人民文学》等发表作品,作品被《诗选刊》选载,被收入三十多本文集。
午后的阳光
蝉的声音 一丝一丝
它讲的是什么
你不需要去翻译
淡淡的花香过不过来
都是风的事情
它自己的事情
生命并不是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个午后 放下所有的欲望
只晒晒太阳
此刻 你也和虫一样和花一样
是一个小小的生命
此刻 你不需要关心这个世界
甚至不需要关心自己
一棵小草的哲学
命运 像一棵小草一样
不知道 哪场风就会把它折断
一棵断草 对土地没有什么意义
阳光只玩了一会儿 就丢掉了
命运还和小草一样的是
无论秋风的刀子如何锋利 一场好雨
小草会依旧在春天走出来
小草是这样
人生也是这样
许多次 以为是命运把我们摔倒了
其实是生活在教我们
学会怎么站起来
春天 一个玉米的故事
一定让一粒玉米的种子去地里站一会儿
这里是不是玉米的家不重要
关键是 春天点名时
无论叫到了谁
都让玉米先答应一声
在异乡的街头
即便我和蛐蛐一起
躲进最绿的叶子后面
一声乡音
也还是把我捉出来
秋天的太阳
随便在大街上把我炒了几下
就炒出了一股故乡的味道
春之初
最后的雪花注定是一个密码
一下子把春天打开
春风大了之后
我就不能在文字里流浪了
随便找一首唐诗住一些日子
或者借一首宋词换一些面包
总之是春天精神之后
我不敢再病了
印象
告别是告诉一声才离开
可太阳什么也不说 天就黑了
寂寞的铁轨是生锈的弦
火车一次次只弹出了一声声再见
那些喝空的瓶子
是留下的记号
我和一只落在窗台上的麻雀商议
谁先离去
车前草
车轮就这样轻易地
把一个生命撕成两段
撕就撕吧
既然最后总是要死去
又何必去计较
怎么样的结局
死在秋风里和死在车轮下
没有什么两样
道理
有一些道理
就像家里的院子
你扫不扫
只有自己知道
正像有些人高尚了
依旧还是人
有些人卑鄙了
依旧还是人
人的进化是用万年计算的
一个人的丑与恶
都因为小于四
而被世界忽略
恶是掉了一地的毛
证明我们曾经是野兽
而善是我们
留给所有动物的路标
告诉它们
从这里可以走上一条
做人的道路
美
羊大了叫美
羊大还是羊 吃草
吃一些晒干的日子
人之初性本善
人大了只有性了
就把善丢掉了
于是许多真诚的话都是孩子说的
于是许多罪恶的事都是大人做的
孩子的目光里
只有星星
大人的目光里
只有欲望
羊把草当作粮食经常吃
人把草当作野菜偶尔吃
吃不吃草
并不是人和动物的区别
和羊打交道几十年了
至今 我们也从不称呼对方兄弟
锄草
这些庄稼
也是从草中走出来的
可今天
仅仅为了庄稼活着
仅仅为了让
这些庄稼活着
我们就要让所有的草死去
没有粮食
人活不下去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把草消灭
可那些草也是有生命的
也是牛和羊
是天上飞鸟的粮食
没有它们
牛和羊也活不下去
鸟也活不下去
泥土之上
泥土上面的叫花
泥土下面的叫根
泥土之上
东奔西走的叫后代
泥土之下
沉默不语的叫祖先
生生死死
是门里门外的事
一层泥土的厚度
就把相逢变成天涯
泥土之上的叫风景
泥土之下的才叫家
公正
公正
不是把阳光扫在一起
晚上
一人拎一袋回去
给蜜蜂花朵
给鸟儿天空
一只鹰和一匹奔跑的骏马
需要的并不是相同的食物
许多时候 公正
就是把一个生命真正需要的东西
放在他们手里
关于野菜
在春天 我从大地上
剪下来这一块布料回去
是为了
给我灵魂上的裂缝
打上一个补丁
衣服旧了换一件就可以了
可灵魂只有这一个
破了也得穿一辈子
诗歌悟语
1
诗歌创作是一种创作,小说、散文创作也是一种创作,但为什么写小说、散文的人叫作家,写诗的人叫作诗人?这就是说诗比其他文学形式更需要人格的光芒。
诗人、诗人,有厚重的人,才有厚重的诗。
2
诗人的人格力量,并不是在某一个句子上跳一下,是充盈于整个作品或者整个创作的。
从字句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人格的体温,从诗行里我们可以摸到诗人的心跳。诗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被某一个句子绊倒了,不是这个句子的成功,而是一首诗的失败。
3
一首诗不是某一个句子的独唱,而是所有句子的合唱。鹤立鸡群,不是鸡小而是鹤走错了地方。
我们常常说诗眼,是说一首诗总要有一两句精采的句子,有一两句打动人的句子。可诗如人,仅仅有一个精彩的眼睛怎么行呢?还要有健康的鼻子、嘴、有力的四肢,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诗亦是。
一个人的脸上,没有鼻子,没有嘴,整个脸就一个大眼睛,那不是人,是一个怪物。
长在合适的地方,还要合适的大小,对人是这样,对诗也是这样。
4
看一个诗人不是看他的笔,而是看他的心。煤堆积在地层深处,我们开不开采煤都在。诗也一样,诗堆积在诗人的心中,写不写,诗都在。写了,就是把诗从我们的心中运到地面上,就是诗人。
诗人也是一个力工,只不过用文字作工具搬运思想和情感。
5
我们说一个诗人,不是从他发表作品开始,而是从他在自己的心灵里堆积思想和情感开始的。文字上的写作,只是他的一个搬运的过程,是一个诗的表达过程。表达的重要是把内心真实地给这个世界看,给读者看。太注重文字上的推敲,而不注重内心的修炼,就是“字”上谈兵,诗就没有力度。
6
悟使作品厚重,悟使作品独特。独特是诗人的个性,也是诗人生命力的保证。我们说百花齐放,是说有一百种花在绽放,而不是说一种花的一百朵在绽放。
独特,你就有自己的名字,就不是在别人的枝头,就是一种花,就不是一朵花。你想在枝头闹春意,你就可以闹。
7
写作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一定的数量是质量的保证”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只有保证了一定数量的写作,才能提高水平,这是写作初期的事,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二是只有保证了一定数量的写作,才能保证作品的高水平,这是一个限制的意思,是深度的写作。太多数量的作品,难免分散我们有限的才气、思想和激情。
量小非君子,是指人的胸怀,而不是作品的数量。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获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可他一生的作品并不多,据说至今也才发表一百六十首左右。
伊索寓言有一个故事。
狐狸取笑母狮无能,说她每胎仅能生一子。母狮回答说:“可我生下的毕竟是一头狮子。”
贵重的价值在于质,而不在量。
无论是寓言还是诗人的实践都说明了一个相同的道理。
8
任何一种作品的创作,其实和耕地;没有什么区别,都需要弯下身去,都需要洒下汗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后,才有一地稻谷的飘香。
9
诗和散文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形式,在于分不分行;而在于其内在的诗性的光芒,思想的力量。
正如,一只羊穿上衣服还是羊。
一个人穿上貂皮,还是人。
10
其实,一个作者文字的无力,是生活的苍白和灵魂的浅薄。一个人,一生只在月光里洗澡,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遗憾。
11
写作只是一种职业,我们用作品擦亮的是我们的灵魂而不是我们的名字。写作者与街头掌鞋的老人、工地上砌墙的民工一样,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不能冷静地审视自己,而把会摆弄一点文字作为不可一世的资本,就会使自己迷失在成功之外,使自己成为人生和生活水面上的浮萍。这是诗歌的悲哀,更是诗歌作者的悲哀。
12
无论怎么说,诗歌也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正像天空只是鸟儿和云朵的一样。
因此,如果我们想用自己的作品去感动整个世界是不可能的,诗歌只打动应该打动的人就可以了。